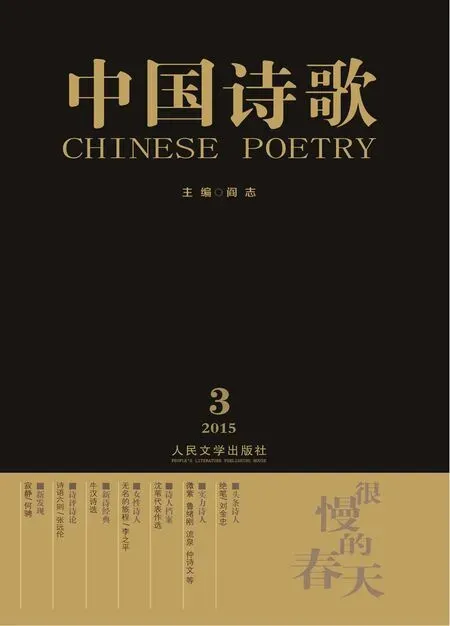一团拒绝修饰的活火
——牛汉诗歌导读
□郝俊
一团拒绝修饰的活火——牛汉诗歌导读
□郝俊
牛汉的诗,在触碰的那一刻,就使人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灼热,质朴淳厚的文字就是生命的热血和生活的原质,越是深得其味,越是分不清这究竟是鲜活的历史,还是烫手的诗歌?是沉痛苦难选择了命运多舛的诗人,还是坦诚炽烈的个性决定了燃烧至尽的书写?诗人自己说过:“我深深地感到,只有那极珍贵的充分燃烧的短暂时间里,才能生成真正的诗,才能从燃烧的烈火中飞出那只美丽而永生的凤凰。”(牛汉《让每首诗都燃烧尽自己》)
诗人牛汉生于1923年,原名史成汉(早年名为史承汉),山西定襄人,是“七月派”诗人重要的一员,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位铁骨硬汉。诗人七十多年的诗歌创作,成果斐然,其大量的诗歌作品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极为厚重的一笔财富。
1
“诗如其人”的形容,对于牛汉来说,仍觉轻浅,他的诗与自身的关系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像”,而是“诗”与“人”的同构并在。诗是牛汉紧握的那根刺手的命运之“藤”,是用点燃生命的代价为人生立的“传”。“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写诗已然是诗人的真实存在,或者说写诗成了诗人受难灵魂的惟一救赎。
为了比较清晰地呈现诗人的创作历程,本文试以创作时间为序,分三个时段予以梳理:第一,从1939年开始诗歌创作到胡风案件发生前。第二,自1955年5月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牵连被捕至1980年该案得以平反。第三,1980年以后。
牛汉是一位典型的早慧诗人,中学时代开始诗歌创作。据史佳、李晋西整理的诗人年谱记录,牛汉于1939年7月7日开始第一首诗歌的创作,主题是讴歌抗日战争,刊于学校墙报,并首次署笔名“谷风”。1940年冬,在兰州《现代评坛》上发表诗歌《北中国歌》,随后诗歌《沙漠散歌》、散文诗《沙漠》在谢冰莹主编的《黄河》上发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艺术才华已初见端倪。诗人早期诗歌语言干净明快,有一种大漠风沙般的苍劲与壮美,有些诗句至今读来都令人震撼:“春天,/驼队涉着冰河,/踏一条黑蟒般泥泞的路,/铃铛像嘶春般的黑猫长啸。/夏天,/红云映着黄沙,/沙窝像古罗马斗牛场中的/野兽的红眼,/呕吐着灼热的火舌。”另外,诗中有些妙喻寓意深远,如“长的驼队,/是沙海的浮桥”等。《走向山野》、《山城和鹰》、《我必须到山野去》这类诗笔触相对温和,大多是渴盼怀揣的自由在恬静的山水中得以实现。
1942年刊发于《诗创造》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风格清新开阔,草原不仅是诗人赞颂的绿色家园,碧波绿海之中还深藏着诗人向理想进发的豪情。诗人曾说:“《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就是我们准备投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地写陕北,我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就神往。历史和现实的情感在我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着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作为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此诗风格洗练,情绪激昂,诗人相信疾劲的草原风扬起的一定是生机和希望。诗人始终听从民族命运的召唤,很多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在抗战时期,诗人说过:“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皖南事变”之后,诗人用“野花”和“弦琴”两个意象,表达了当时复杂的内心感受(《野花和弦琴》)。在诗剧《智慧的悲哀》中,诗人用象征的手法传达出梦想受阻后的激愤,“歌声悠悠地飘响着,渐渐地低沉了,静默了……这时大风暴狂野地吹卷起来,天野更黑。林丛中的火堆,像一片飘摇不定的红叶。”历经极度失望,胸怀信念的诗人仍旧用心中不灭的火种等候天边的曙光,“过了很久,大风暴渐沉静,沉重的夜雾隐退进深谷与林丛去,黑色的云也碎裂了,繁星连串地沉落……天色转成微白。”当然,更多时候,诗人还是喜欢直接抒怀,表达“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脉相连,如诗人在《九月的歌弦》里写道:“在北方/我的心/人民的心/扭成了一束/九月的歌弦。”
《在牢狱》、《希望》、《捕这只鼠》、《控诉上帝》等诗,与此前的创作相比,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些诗写于1946年的汉中第二监狱,诗人因1946年4月领导学生运动被捕。狱中的诗篇就不单是内心对自由的呼唤,而且还是遭受囚禁后的哀伤和鸣冤。《在牢狱》这首诗语言平淡,像是轻描淡写的叙说,读来却令人隐隐作痛:“春天/菜花正飘香/我被关进牢狱。//母亲/穿一身黑布衣裳,/从老远的西北高原,/带着收尸的棺材钱,/独自赶来看我:/听说/你死了,/脑壳被砸烂……//我并没有死。//母亲/到牢狱看我,/我和母亲中间/站着一个狱卒,/隔着两道密密的铁栅栏,/母亲向我伸出/颤颤的手,/我握不到,握不到……//但母亲和我/都没有哭泣。//母亲问我:/狱里/受罪了吧!/我无言……//母亲懂得我的心,/狱里,狱外/同样是狂暴的迫害,/同样有一个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或许是因为被捕时遭遇毒打和随后经受的牢狱之灾,催生了诗人思想上的憬悟,在黑暗时期,监狱外面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诗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狱里,狱外/同样是狂暴的迫害”,只有具备“敢于犯罪的意志”,才拥有奋起抗争的强大力量。同年5月,经组织营救,诗人以“因病保释”的名义得以释放。出狱后的诗人投身“地下”工作,并与妻子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出生入死的年月,写诗一直被诗人视为另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1947年牛汉完成了《春天》、《悼念鲁迅先生》、《我的家》等诗作,写这些诗时,诗人已是一位在火中淬炼过的革命者,对战争形势的认识有了一种辩证的视角,即最终的胜利往往诞生于艰难险阻的战火之中,“不是没有春天,/春天在冬天里,/冬天,还没有溃退。”(《春天》)1948年诗人创作的长诗《彩色的生活》,以气势磅礴的行文,表现了战争的艰巨和浴血奋战的壮烈,抒发了誓死卫国的壮志豪情,“祖国啊!一个人有一个灵魂,/一个人活着,就要呼喊着你,和你一同呼吸,一同/受难,一同战斗,/祖国啊!祖国啊!/我在惨烈的肉搏里,/护卫你,即使是匍匐地前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这首诗时,诗人第一次用“牛汉”的笔名。诗人在自述中对这一笔名有过说明:“因为‘谷风’(曾用笔名)有重名,改用‘牛汉’。牛是妈妈的姓,再从史成汉中取一个字,也是大汉,牛一样的汉子的意思”。应该说“牛汉”二字十分恰当地概括了诗人做人作诗的特征——牛一样的憨厚忠实,牛一样的蛮勇倔强。
新中国成立前夕,牛汉主动申请到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他参加抗美援朝,被分到志愿军司令部,编辑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文化部的《空军卫士报》文艺副刊。1951年到1954年,先后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的面前》、《爱与歌》,这些作品在题材上较为集中,以歌颂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为主,风格大多酣畅质朴,心中的情绪,像炽热的篝火一样尽情欢腾。
2
往往命运多蹇者,对历史的一时荒诞带来的厄运,有着切肤之痛的体会和终身不忘的记忆。1955年5月14日,对牛汉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次转折点,这一天,他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第一个被拘捕,1957年5月才被释放回家。不料,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1969年,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4年底结束干校生活。在近二十年噩梦般的生活中,诗人饱受摧残,与诗人相依相伴,共受磨难的就是诗人视为生命的那些诗,这些诗像“伤疤”一样见证了历史,也像“伤疤”一样警示后世。这些诗,并不是为了一味地记录和表现个人的疼痛,而是突破“小我”,理性地审视历史,希望以自己的血泪史为个案,使人们从中读出历史的痛苦,企盼悲剧不再重演。诗人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汗与血几乎跟我不可分离,浑身上下处处是伤疤,色泽有黑的,有灰的,还有鲜红的。每个伤疤都连着一个长长的、深深的记忆。……我晓得汗血的疼痛是无法轻化的、淡化的,我深知汗血的神圣和不可亵渎,汗血是一个诗的也是人的庄严的精神素质。唉,我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让后人真正活得快活些吧!”(牛汉《谈谈我的汗血气》)的确,让人感佩的不仅是诗人与诗相依为命的自我激励,更有一种在“伤疤”中解读历史的深邃,把“苦难”熬成诗行的艺术使命。在写于1970年的《鹰的诞生》中,诗人以“鹰”来象征坚强的人生一定诞生在狂飙骤雨之中,“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有时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不仅考验意志,更让人洞悉受难的人生,“雷声使人清醒,/闪电照清面前的道路。”(《夜路上》)
灾难的洗劫让失去自由的诗人一无所有,但也正是因为受难,诗人的诗一次次如获重生,“每一首诗都灌注着我全部的生命力。咸宁让我受难,但1972年、1973年以后,我解脱了,有再生的感觉。……早年写的诗很单纯,咸宁写的诗每一首都有再生的感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从诗艺的角度看,《半棵树》和《华南虎》最为突出。《半棵树》写于1972年,诗人通过一棵遭到雷击受创的树表现了自身的生命境遇:“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刷刷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作为意象的“树”跟以往诗中的“鹰”已迥然不同,“树”只能被种植或移植于某处,实指被动的、受禁锢的生命,但凡生命在受到迫害时,都会表现出一种抗争的力量,哪怕只是一棵树,也要“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然而,以诗人的切身体会,个体生命的对抗,在命运面前,很多时候只是徒劳,甚或因为抗争遭致更大的打击,“从树尖到树根/齐刷刷劈掉了半边”就是完整的生命受重创致残的悲惨结果,“半棵树”就是诗人仅存的“半条命”,因为强悍倔强的性格,即使是“半棵树”也要站成“一棵树”的姿态,“那样高”、“那样伟岸”是指矗立挺拔的人格。诗的最后一节,读来让人心生怜悯又引发深思,看似浅白的书写,其实寓意深刻,“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简短几句道出了在“特殊”时期,诗人乃至某个群体的命运走向悲剧的必然性。
牛汉的许多诗,一般在诗的第二节,要表达的情绪就逐渐深入心坎,并形成强烈的起伏,一时忘了语言是如何地进行,这与诗人不喜修饰,习惯直接有力的表达有关。创作于1973年的《华南虎》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震颤灵魂的诗。此诗起笔就言有所指,但以往被很多论者忽略,视为简单的过渡,实则不然,“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意在点明“老虎”所处的大环境是“小小的动物园”,即充满伟力的强者,也无法避免遭遇囚困,甚至被当众羞辱的命运,“动物园”和“铁笼”构成双重禁锢。很显然,因为长时期在监禁中受到迫害,精神的内质已损耗殆尽,丧失了成其为自身的特质,“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这首诗比一般的咏物诗的结构要复杂,不是简单的物我对应,除了“不在场”的施暴者(施暴者的存在是通过老虎被困和老虎所受的伤害来体现),还有“观众”的介入,“笼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块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喝/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击那些可怜而又可笑的观众?”诗人觉得自己也是“观众”之一,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诗人本属于另一类“受难者”,对此情形,有着更为深切的同情,对于“老虎”被困又无能为力,虽然不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观众(用石块砸、厉声呵喝、苦苦劝诱等),却也只能袖手旁观,于是强烈的愧疚感油然而生,“多么令人感佩的一匹不甘寂闷的困兽,一个在命运面前顽抗到底的生灵,它一直背着我们,用钢鞭似的尾巴一挥一扫地要撵我们走开。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牛汉《桂林的大蟒和老虎》)老虎对所有“观众”的态度都是“一概不理”,如此淡定从容,一是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对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们和事不关己的看客早已习以为常,二是因为内心积郁的悲愤和彻底的绝望,除了在墙壁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其他一切想法和举动都是枉然。当然,艺术创作并非一定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停滞不前,诗的最后一节让愤慨难抑的情绪得到了有力的释放,“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这一幕让所有人,包括“观众”,目睹华南虎失而复得的雄风和伟力,诗人坚信被困者一定有破笼而出的那一刻,哪怕带着惊心的伤痛。
诗人非常看重《半棵树》、《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等作品,这些诗,触目惊心,深邃有力,标志着牛汉在人生和诗艺上日趋成熟。诗人在谈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时,与以往创作有一个比较,“我一生有两段时间的诗写得最为狂奋,一段是在四十年代初的万寿庵,一段是在干校后期。……作为诗,我更看重后一段的诗。……这种让灵魂敞亮,从生命深处升起的光芒,完全不同于早年的梦幻色彩,而在艺术的创造上也相应地成熟了许多。此时,每创作一首诗都是一次心灵和人生的艰难的发现,人和诗真正地成为息息相关的生命。”(牛汉《把被删去的人生追补回来》)不难发现,牛汉的真挚感人,是把生命当作惟一的燃料,燃起艺术之火,一种毫不保留的燃烧,炼出了藏在诗歌中耀眼的真金。
3
1980年胡风案件平反后,诗人重回诗坛,写于干校时期的诗作陆续发表。作为“复出”诗人,牛汉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创作力著称,八十年代及其后出版的主要诗集有《海上蝴蝶》、《蚯蚓和羽毛》、《沉默的悬崖》、《牛汉诗选》、《牛汉短诗选》等。牛汉既作为高产的创作者,同时又以创刊人、编者等身份介入文学活动,是一位对新时期文学事业有着卓著贡献的歌者。八十年代及其后的诗歌创作,诗人在表现手法上更加丰富灵活,思想上更趋深刻,注重对灵魂的开掘和人生的追问,开始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精神认知和哲学体悟。
反刍过往历经的苦难是诗人选择思考的方式之一。在新时代对“苦难”命题的思考不同于以往对“苦难”的直接呈现,以前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一种“现场感”,强调个体感性经验造成的内在冲击,现在有一种经过沉潜后的表达。写于1982年的《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就是一首形象生动又意深耐嚼的纯熟之作,“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只有我一颗通红/红得刺眼/红得伤心”,因为早熟,失去了应有的青春和成长,“红得刺眼”是客观效果,扎堆同龄人中太惹眼,“红得伤心”是主观感受,自己才能感知的滴血的伤痛。早熟的原因是内心过早地遭遇侵蚀和伤害,“一条小虫/钻进我的胸腔/一口一口/噬咬着我的心灵”,早熟的特征是心灵世界有一种未老先衰的迹象或表征,没有青年时期应有的青涩鲜嫩和绿意盎然。面对自己已有的病态的成熟,诗人只能是暗自伤怀,并希望所有人都能洞悉“成熟”实际上是灾难催熟所致,“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很红很红/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把早熟的枣子比作一滴受伤的血,确是高妙的手法,动态地呈现了红枣泛红的缘故——内心遭到噬咬,流血外渗,浸染而红。没有人在这样的诗句面前不为所动,时常听到“青春易逝”的喟叹,而诗人似乎连青春都不曾拥有过,没有常态的“青春”供诗人追忆和凭吊,只能在想象中羡慕属于青春的绿意。诗人不仅寻找表达对苦难的感知和反思,也赞美了战胜灾难的不屈意志,如《硬茧颂》、《雷州半岛》、《小溪》、《第一朵花》等都是寓意生命的高贵,表现对灾难的逆反和征服。有些诗在构思上非常别致,有如寓言一般,表达独特的生命存在是因为致命的伤害所赐,如《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黄河与鲤鱼》等诗作想象奇特,肯定了顽强的生命势必有能力将苦难转化为财富,以此成就自己坚强而奇伟的人生。诗人自己也说过:“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牛汉《回顾与思考》)
苦难促成了诗人的生命书写,奉献则表达了诗人的使命担当。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若依此言,牛汉毫无疑问“配得上”所受的苦难。诗人在新时代咀嚼苦难,是希望世上的苦难可以彻底地消弭,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宏愿,那么,毫不保留地奉献和竭尽全力地创造就是诗人从不间断的行进。诗人坚信个体生命如果真有价值,一定是在奉献中表现,“哦,铁的山脉,/我听到了你的回声,/听到了从你心胸深处爆发出来的回声:/开采我吧!/炸碎我吧!/熔化我吧!”(《铁的山脉》)再看诗人用心良苦经营的《一盆小石榴》,即使身有伤痛,也要加以掩饰,在奉献自己的时候也要展示其美丽的姿容,“小石榴把自己笑裂了。”《血的歌声》更以喷薄而出的豪情表达对祖国的深爱,“我的一生/将带着浑身的血/唱血的歌/把血和歌/献给生我养我的祖国。”《长跑》、《汗血马》等诗作实际上都是诗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动人写照。此外,《梦游》第一稿和《梦游》第三稿通过半虚半实的手法回溯个人历程,探寻生命本质,是极具现代意识的成功之作。“我的体魄顽健/头脑也算清楚/但常常在深更半夜/从床头猛地蹦起/心脏是起爆的火药”(《梦游》第一稿第一节)。诗人因为早年头部受伤,的确有梦游症状,但这样的叙说,很明显并非完全是对病症的描述,即不是失控的异常之举,之所以“猛地蹦起”,还是因为内心有太多震荡的记忆,即使在最容易让人宁神静心的深夜也会猛然涌现。末节“那一束雪白的亮光”是诗人在希望中寻到的指引,“我有一个/神奇的夜”,暗示自己有一半的人生是不同寻常的。《梦游》第三稿更为深刻,一语双关之处频频出现,“梦游的人不走看得见的路/我不信任路/陷阱都埋在路上”,“可我从来没有走到过尽头”。这种不断开拓,努力超拔的念头已深藏于心,无论是在混沌的梦境还是现实的人生。这样的惊人之作,可能要归功于诗人燃情不止的生活态度和在艺术上敢于突破的胆识和才华。
诗人还有一类诗,形而上意味相对浓郁,致力于表达命运、生死等重大命题。《圆弧》中的弧线不仅是视线所及的边界,也是个体生存的界线,人似乎生活在既依赖于此又渴望逾越它的悖论之中。《并非虚幻的风景》采用虚实相叠的手法,表现对立事物的相反相成,以及易混难辨的神秘和诡谲。《血和泪》意指戕害肉身的暴力无法剥夺高贵的灵魂,“刽子手们猎取到的只是血和尸骨/坚贞的泪他们休想捕猎到一滴”。牛汉后期的创作有时特别注重灵性的舒张,通过深刻独到的体察,赋予司空见惯的事物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是的,火焰可以泼灭/但仍然捕捉不住火焰/看到的只是焦黑的/被火焰烧过的痕迹”(《火焰》),这样的诗除了见出生命的热度,还有一种骨子里的倔强。再看《青春——读蒙克的画》,“只等那一星火苗扑来/突然之间向她点燃//她升华成一个人形的太阳/愈燃愈烈,愈升愈高大”,诗人认为倘若生命中真有如火的热情,肆意地燃烧就是生存的惟一使命。
“火”是牛汉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词汇,是光焰不熄的诗歌灵魂,这与其说是出于诗人的苦心经营,不如说是火热生命的本心契合。抓住了“火”,就找到了牛汉诗歌创作的肯綮所在。有很多论者用“雄鹰”、“汗血马”抑或“华南虎”等意象概括牛汉的诗歌精神,这固然有些道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似乎没有进入内核,如果深读作品,就可以发现“汗血马”其实就是一团飞奔的火,展翅的“雄鹰”就是凤凰涅的诗意表达,笼中囚禁的“华南虎”就是郁积已久的那一把心火。“火”是自由的狂热,不躲藏,不伪饰,同时又有随心赋形的特征,似乎什么都可以“是”,而归根结底,是诗人的那颗火热的赤子之心。诗人崇尚彻底“燃烧”,对自身而言,不是嗜热的耗损,对他者来说,不是暴烈的焚毁,而是一种最为真切的生命表达和“把火焰塑形为诗”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