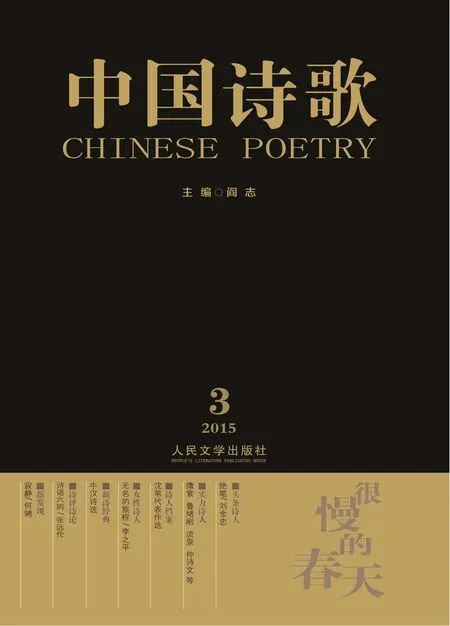雪和雪的互证与改写:沈苇诗歌札记
□于贵锋
雪和雪的互证与改写:沈苇诗歌札记
□于贵锋
这是以札记形式记录的关于沈苇诗歌的点滴。蓝本是长江文艺社出版的《沈苇诗选》,以及在网上搜索到的沈苇的诗。行文之中,如同沈苇对自己的诗歌、现实对诗人的改写一样,我似乎也在不停地改写着我的阅读记录。
上篇:到达混血的城
“中亚”这个词
《一个地区》写于1990年,是《沈苇诗选》的开篇。诗中的“中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地理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还是诗学意义上的?“深不可测”,吸引和拒斥两相存在。干木般的质地,火与冰的温度,玫瑰与白与蓝的色彩,构成其诗歌的初步景象。这近乎谜一样的诗,孤零零地,很突兀,就像初次读到沈苇一样。这直觉的词,需要多少时光来照亮?
新疆的入口
显然,我指的是滋泥泉子。沈苇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年?关于诗歌,关于生活,这个地方对沈苇的影响有多大?他获得了怎样的,观察周围的人,观察自己的角度?他有没有获得更宽阔的、更深刻的视野?
可以肯定的是,沈苇在《滋泥泉子》一诗中,已然意识到了来自地域的、民族的、生活的差异。他融合的努力,他对生存状况的认知。葵花和白杨,这两种植物,似分别有指。莫合烟,对于那个时代的烟民,有一种亲切的异域的温暖:那正是贫困中的美好记忆,那是痛并快乐着的日子。
在其《植物传奇》,他透露出,白杨树,是他切入另一个现实世界和内心的裂缝,从那儿,他走了进去。或者说,光从那儿射出来,照亮了他的意识,南方与西域差异性、底层观照眼光、隐忍态度、自然视角等初露端倪。
“在滋泥泉子,即使阳光再严密些/也缝不好土墙上那么多的裂口”,这样灵动而生活化的句子,几乎为他的那种强烈的在场和情感评判感埋下了伏笔。
一切都是那么稀松平常,那么安静,但发生的正在发生,生长的正在路上。
蛇的教诲
第一遍和第二遍读到的内容竟然不一样!我又读了几遍。嗯,《自白》,这是我喜欢的那种有后味的好诗。不愿做空心人,想拥有孩子般的纯真,也想有鸟的飞。是原因还是转折,诗人接着用几个“看不见”说明对自身之外或者说也是自己的日常之疼的漠视。但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耻辱和羞愧在那儿。同样,蛇教会了如何处理这种疼痛、耻辱和羞愧,——皮肤一般蜕去。以这种方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一词,具有了多重性:大自然,生命的自然性,很正常的日常行为,貌似超然的理由。最后四句,将不同的诗意融合到了一起,得之于诗人对前面几种不同状态的同质把握,水到渠成,有线性中的复线。
接续中的节制和遮蔽
1993年到1994年(《哀歌》除外),沈苇是抒情的。和许多抒情诗一样,看似很接近内心,但实际是被外在事物吸引,激动、忧伤、自恋等。有所不同的是,沈苇这一阶段的抒情诗,有一种难得的节制,和西域风景带来的青铜质地和干裂、热情,有不同于软绵绵的内在和外在的硬度,具有健康的语言肤色。
但同样,这些诗中,有一种对古老的诗歌传统的回归,这回归不仅体现在熟悉的物象,也体现在感知的方式上。题材对诗歌的影响,在沈苇的这些诗中,是存在的。特别是,沈苇在寻找自己诗歌之路的过程中,同样也被“西部”的宏阔吸引,也就是在无意有意中,加入了“西部诗”的合唱。景物是新疆的风景,中亚的风景,热爱是更为炽烈的热爱,但这些,在一种背景中成为他愿或不愿的标签。更为重要的,就是这种接续获得的认同,或许让沈苇从情感上陷得更深。好在,有一天,他会认识到这种接续中的遮蔽,并在更深的层面上从自己的内心和写作上开始剔除。这是后话,但也是我对沈苇刮目相看的理由之一。
菜地的音高
《菜地》一诗,日常生活和自然泥土,通过一件小事联系在了一起。是清新的、温暖的。同时可以看出,这种连接有点小心翼翼,还尚未触及更深层的东西。而他在1995年写的其他几首诗(《庄稼村》、《川上》、《春天》、《夜曲》、《面向秋天》)不仅感知方式回到了传统的“季候性”感知方式,而且声音有所降低。
对,就是这种迥异于“西部诗”的低音,才有可能将沈苇从众多的高音中加以辨认。诗人看到了“小事物”,认识到了这些事物的“现实性”。包括1995年诗人对故园的回望中,那些切近的事物,依然在内心存活的事物,都是一种小的现实。但也只是有可能,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很重要的开始。
诗人生来彷徨
但《楼兰》,让我对自己的判断怀疑,沈苇是否真的将过去纳入现实?他仿佛有两套或不止两套语码系统,他回到了1995年以前的表达路数?一种想象的、美丽的、高蹈的诗歌再次出现。想想,也不奇怪。
一方面,任何容易的改变,有多大的意义自不待言,反过来也说明,他接续的东西,对心理结构和言说方式的影响是很深的。另一方面,改变是开始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完成。
两种不同的事物和情感向度之间,需要一个契合点。热爱,成为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在面向故园的时候,是已然抽身而出的“观察”态度,这种视角,也开始对应于他在西域看到的景象。比如《沙漠的丰收》,就是基于整体认知上的一种尝试。而后,越来越具体,将视点集中于某件事、某个细节,《坠落》、《三个捡垃圾的女人》、《运往冬天》等的出现,可以从中看到诗人角度的变化和心的下沉。
伴随着观察出现的,就是沉思、思辨等,就是对存在的思考。《坠落》等诗,与其说是一种向低的写作,毋宁说是借助这种具体的现实事件,对生存、存在的一次思想探视。
《混血的城》:对生存现场的初次综合性审视
1998年,《混血的城》成为沈苇诗歌写作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这首诗中,出现了沈苇诗歌最为根本性的主题:差异的融合,包括了个人记忆与现实、异乡人与本地人、江南风景和异域风情、东方文明与异域文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等。
但无论怎样,就是在这首诗中,沈苇将它们融合在自己的热爱中。赞美的声音,淹没了差异性导致的痛苦。由于开始“扎下了根”,漂泊感,或异乡感在减弱。一种异常饱满的诗歌质感,和扑面而来的生活热情,在表明着诗人此时此刻的深切感受:他被这种看似复杂、激荡互冲但充满活力的生命景象所吸引。可以说,此时的沈苇,他的诗歌是盛大的,他的诗歌疆域是广阔的。
从这时候开始,无论是两类质素融合的诗歌,还是各有侧重的诗歌,都成为《混血的城》这首诗歌的主题的分支,成为从他扎下根的心上长出的面貌各异、味道各异的植物。而且,沈苇开始的对具体事件和细节的重视,使得他的诗歌血肉丰满,如同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诗歌生命,让读者在细碎的诗歌之外,读到了一种燃烧着火焰的诗歌,一种将人间烟火和艺术高蹈紧密结合起来的诗歌。甚至,就是在这种对“混血的现实”的满足中,诗人对于生死也似乎悟透了。生者和死者的和平静处,恰当地说明了一份宽阔的葱茏。《清明节》和《吐峪沟》,这两首关于生者和死者关系的诗,如同一个历经沧桑的人随意安歇下来,享受着生命之宁静大美。没有了怨恨,没有了伤痛,甚至没有了思念。只是安歇,只是过着惯常的生活。
吐峪沟
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
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
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
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
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
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
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
这首《吐峪沟》写于2003年。但我第一次接触到它,是它的声音。不,是诗人的声音。大约在2005年吧,在兰州农民巷我听沈苇背诵过。他的声音错落有致,如同生死的高低。我一下子就被那种生死之间的豁然祥和抓住了。一直以来,我把它看成是沈苇最好的诗。我认为这里面,是沧桑之后的一种愉悦的述说。且慢。在读《混血的城》时,当读到如下诗句,我突然感觉到诗人内心的不安实际上已经出现,缝隙已经裂开:
让我再来写一写那些通宵达旦的聚会
烈酒唤醒头脑里的精灵
也惊动骨子里的恶魔
一次,当天才的程娃放肆地亵渎圣灵
我在他身上浇下半瓶伊力特
以便盛开一朵液体火焰
圣灵岂能亵渎!瞧,虔诚的基督徒大可
如何克制着内心的愤怒
也就是当另一极出现的时候,诗人只是把它当成了聚会中的一次充满快意的玩笑。他要用这种方式,让混血的城这现实,看起来那么美好。但,诗人是敏锐的。
或许从这时开始,怀着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同等热爱,诗人尝试着去理解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他想调和、融合,但事物之间的裂缝依然存在。当诗人说鳄鱼“对血腥的嗜好”,“正如我们对人间有所留恋/徒劳地怀着朦胧的渴望”(《鳄鱼》),你会发现,即便站在存在的即合理的角度,诗人的辩驳都有点牵强和苍白,他无法说服内心的声音。所以紧接着,他会借助《一个老人的话》,说出他看到的景象的本质:
一切是那么短暂
短暂性的荆棘刺进万物的肉身
成为冰凉粗暴的法律
命运中的牛头马面露出了狰狞
睡梦中,我见过太多的魑魅魍魉
并再三提醒:
不要过分迷信大理石
即使黄金的崩溃也是瞬间的事
甚至他看到了“死后的大地、人群和现实”:
命运就像旷野上的风滚草
被风中不可知的暴力驱赶着
如同嫩芽努力咬破种子的皮壳
新命运的蹒跚总是紧跟着古老命运的踉跄
…………
短暂,易碎,被暴力驱赶,蹒跚和踉跄,没有什么是真正平静的、坚实的、安宁的。伴随着这种预言的出现,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迅速膨胀的欲望,是人们内心无限的孤寂。
然而她的孤寂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
沈苇在诗中,多次写到了“孤寂”。而让我暗暗心惊的,是《阳台上的女人》。作者反复在有意混淆着现实和幻觉,因此,这个也许只是作者作为路人瞥见的阳台上的女人,“被阳台虚构着”,被诗人不断地虚构着,而此刻,被读到她的我虚构着。她被虚构出来,她又虚构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这个女人是美的,优雅,性感,堕落,沉静,“然而她的孤寂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是的,诗人塑造了孤寂。不是女人,是孤寂本身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人能进入她的内心,没有人能看到她生活的背后都有什么。她孤悬在阳台上,孤寂也在阳台上,没有人能“触抚到她内心的一点疼痛”。
诗本身的意蕴内聚和延展,使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女人,呈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不仅仅因为她身在阳台,更因为她同时要朝着不同的方向,她可能随时会蒸发,随时会附着在几盆沙漠植物、吊兰、远方、地平线、日升日落、木梯、鸟雀、呼吸、心跳、翅膀上,会消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是的,这是一首极富穿透力的诗。它看起来不像沈苇一贯豪阔的诗风,但可以看得出来,沈苇对这个女人,就像一个雕塑家对自己的作品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他在把她生出来。他在一点一点地把她生出来,赋予她外形,赋予她动作,赋予她情感,赋予她想象。沈苇,生出了一个名叫“孤寂”的女人,生出了孤寂。
而《夜。孤寂》,就如同是对“孤寂”的注解:
走在深夜的街上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生命就是孤寂。
爱是孤寂,悲伤和愤怒也是孤寂……”
夜是孤寂──悄无声息的孤寂
这和人们对新疆这片充满热情、能歌善舞的土地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或许这反差,让诗人也心生疑惑?就诗歌本身来讲,我不相信诗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孤寂的力量,但我相信,诗人会给自己找借口:
夜只是呈现,放弃了徒劳的表达
用隐秘的嘴和星光的牙
囫囵吞下我
是的,他不是不想表达,而是认为表达是徒劳的,况且,有什么隐秘的东西妨碍了表达,“星光的牙”,也在把他撕咬。那么,星光的牙,是什么呢?从诗人的表述看出,那是更为辽阔的事物,那是虽然痛苦但诗人乐意被其撕咬的事物。诗人,也许觉得还有不同的一面,还有化解孤独的事物,比如理解,比如爱,──即便他说“爱是孤寂”。
和自己争论
或者说这一时期,沈苇内心的矛盾,大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像企图理解鳄鱼那样,他希望从自身开始,拆除一些内在的禁锢,让自己《苏醒》,“世界是我苏醒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为虚假经济对艺术的压制鸣不平,为“仅仅一个小时,他们就被不知不觉/取消了热情、幻想和性”(《文工团》)而叹息;他提醒自己要把目光向外,看得更远一点:“如果我只专注于个人的痛苦/那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眺望》);远方,有自己惦念的故乡,“流水中突然静止的摇篮”(《两个故乡》);身边,是女儿从学校《归来》后,那因同学的亲人去世而产生的些微的不安、忧郁和“严肃的思考”;“阿花啊……不要扔下了我!”“他泣不成声,抱着一点点冰凉下去的她/像抱着污泥中的一只月亮”,──他将听过的,在人民公社废弃猪圈里发生的,这最“悲痛、深情的颤音”,写成了《爱情赞美诗》;他关注《黑的雪》覆盖的环境,妓女的暮年(《冷库》),“孤零零的慈航”(《无名修女传》)。诗人将自己的心敞开,去感知,去理解,去爱。他在思考着,也在和自己争论着;他在爱着,也生出了爱的忧郁。他对自身的情感进行审视。他这时候的诗歌,我明显感觉到,要沉郁得多。这距离写下《混血的城》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中,一个诗人在生出新的质素。尤其在2003年,似乎诗人内心的冲突达到了沸点,逼迫他不停地倾诉,写下许多优秀的诗篇。除了上述作品,还有《占卜书》、《植物颂》、《石头上的塞种人》、《美人》、《月亮的孩子》等。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
沙漠,一个感悟
沙漠像海:一个升起的屋顶
塞人、蒙古人、突厥人、吐火罗人
曾站在那里,眺望天空
如今它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
在地底,枯骨与枯骨相互纠缠着
当他们需要亲吻时
必须吹去不存在的嘴唇上的沙子
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
但天空依然蓝得深不可测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
这首同样写于2003年的诗,看起来没有那么感性,几乎就是对思想的直接描述。但是,在沈苇众多作品中,这首诗绝对不容忽视。它概括了从1998年以来,直至2003年,在诗人内心一直徘徊着的一个疑问,以及在经过与自己和解的努力之后,依然无法释怀的一个声音:关于新疆,关于异域,也许多年来,在有意无意之中,借助“地域性”的掩护,在获得名声的蛊惑中,诗人成为了一种浅层“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或许,最直接的就是,诗人和大多数“外地人”一样,对新疆的理解,停留在优美的风景、歌舞、好客、可口的食物等印象中,而忽略了这片大地,乃至更广阔的“中亚”历史与现实中包容的巨大内涵。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颠覆性的。他可能在指向别人的同时,更多地指向了自身。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诗歌的发生以及基础、情感的质地,可能都将面临着严酷的审视。那些在沈苇诗歌中甚至是作为其写作重要特征的异域性、语言的热度、美丽家园等等,都将被自己怀疑,因为这里面,作者直接指向了写作道德。就像他认为快速写作、为个人的痛苦写作是可耻的一样,这一次,他是对自己的诗歌质素发出了质疑。而这质疑,在这首诗中,来自于他“突然”发现,沙漠,就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不同种族的、文明的“枯骨”,依然存在着阻隔,依然有死亡也抹不掉的“沙子”。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情况继续在发生,“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显然,城镇、村庄是文明的一部分,它们的生活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文明在消失着,文明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依然陶醉于风景,“天空依然蓝得深不可测”。由此,沈苇诗歌的又一个面彻底打开了。他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歌者,地域的歌者,也由此成为一个文明的歌者。他的视野,将深入现实和历史的旷野,捕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
这首诗,成为沈苇诗歌的一个思想分水岭。我认为以此为始,沈苇在走向《混血的城》的过程中,他诗歌中出现的孤寂、不安以及爱、幻象、废墟等等,都将暗化为他对自己诗歌疆域的一种新的关注,更强烈的、悲悯而痛苦的,然而也是更大的爱的关注。
下篇:从乌鲁木齐带来的安魂曲
挽歌一:娱美人
2003年到2007年,沈苇的诗歌焦点开始转向废墟、遗址、传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的人事、文献和歌谣以及一个个具体的地域等。或者说,诗人关注的对象看似没有多大变化,但其诗歌的质感和情感向度发生了变化。当然,作为一个内心充满爱、将这片土地视为又一个故乡的诗人,沈苇的方式还是一种努力探求的态势,他不是简单地呈现,而是试图揭示真相,并且力图通过自身的写作,复原、重现一些失去的美好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衰老、消退的一天,废墟、老人、一些植物、石头、文字、种族、美人、雪山和城市等,或许就是这种消失之前,时光常见的“承载物”,这时,他们一边回忆曾经的辉煌、青翠、年轻,让这份温暖在内心存留,一边他们也看到了未来的空无和苍茫。而只有诗人,具有穿透时空的能力,能够看到沙漠上的亡灵在呼号“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家园,在哪里”(《废墟》);能够听到“哀伤的老山羊”(《一个老人的挣扎》)那样的咳嗽,和体会到他衰弱躯体里一份热望;能够感受到“荒漠植物”的顽强(《植物颂》),“它们从死亡那边移植过来”,“享用着干旱和荒凉”等等。而诗人的这种能力,则必然来自他敞开的心,以及为了挽留做出的诗歌的、灵魂的种种努力。对突厥文、哈萨克歌谣的仿写(《占卜书》、《谎歌》),则是一种呼唤,像人模仿动物、植物发声,和它们交流,了解它们,唤醒原本在人的世界里沉睡的事物。他写下了他的“柔巴依”,一种诗歌的体式,如同歌谣、文字等,就是对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回望和激活的具体参与,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精神种植;石头残存着塞种人的记忆,也残存着他们的生活气息(《石头上的塞种人》),但“河流与草场早已成为石头的一部分/他们的羊群永远吃不到青草”,这无尽的哀伤,也是一种广阔的提醒。在喀什噶尔、叶尔羌、楼兰、罗布泊等地,在南疆和北疆,在中亚,他寻找、挽留那些失落的、消散的事物。从灵魂最隐蔽的层面来说,或许诗人,实际上在努力地挽留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虽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但理性认知和情感上的接受是两回事。这需要勇气。多年的行走、思考,诗人不得不接受面临这样一种状况:他诗歌中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或者说,他的诗歌中的现实,是真实现实的一部分,更多的现实,在风景的背后,在湮灭的历史和荒凉的沙漠中,在身边每一个人的孤寂、沉默中。
有两首诗,我个人认为,可以考量诗人情感的力度和美学的趋势。
个案一:《美人》(略)
这首诗起句“她配做一名时光的妃子”,很宽泛地定了调:她是被时光选中的;她属于时光;最严酷的时光也认为她“配做”;认为“配做”的还有除时光之外的所有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价值判断者。退一步,即使“时光”熄灭,她好像仍然属于宗教的新月,属于国王、乐师、小丑的崇拜对象,被宠爱,被歌声传颂,被领进口口相授的传说和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什么,只因为她美,她是“美人”。虽然她只是一株普通的、散发芳香的沙枣树在旷野中被尘土侵袭,也散发着羊奶和驼奶造成的膻腥,但是,为了让她与人们给她设定的角色相符,“要把她放在玫瑰花液里浸泡三次”。经过所有力量的共谋,“风暴的争夺”,她失去了“牧羊女,一个樵夫的女儿”这样的身份,成为一个美人,成为美的一个符号。
是的,“每个人用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将她塑造”,甚至包括时光,她被塑造出来,她是美人的代名词,是各种欲念的需求的总和,是被反复切削、打磨、雕琢而成的“时光的妃子”。“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隐秘,她乳房的疼痛”,“没有人能进入她日复一日的孤寂和忧伤”,她不能有自己,她没有了自己,她的美,让那些将她塑造出来的事物如同吸食了毒品,忘记了美之外的所有东西,沉溺于其中。美,成为他们的一种物品,隶属于他们,处于一种绝对的被支配地位。他们,就像“一束强光暴徒般进入她的身体,使她受孕”,使她沦为一种他们欲念的工具。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共谋犯,实际上是沉溺于自己的欲念,在他们自己的欲念之外,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而这,反过来,“美”如毒素,进入他们的血液,控制了他们的意识,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然而,它确实是诗人眼中的世界。事物与事物之间,在表面上是美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同“美人”,但实际上,事物各自是孤独的,存在着隔阂,存在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美是她的面具,她感到痛苦无望的是/她戴着它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美人自己“摘不下”美,制造这一切的事物,也摘不下来。美是美人的面具,也是制造这一切的事物的面具。
诗人这种强大的感受力,穿透了时空,指向了一些终极问题。但对应到现实,它又是具体的,是自己凝神的对象。不错,我认为,长久以来,人们对新疆、中亚等的认识局限于外在的美,并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之间极力维护这种美,而那些原本无辜的风景、风俗等,也被扯进来强化着这种美,这必然使各种事物在相互之间,都有了距离,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止于“美”。在这儿,美,是存在的,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但美,也是所有的事物共同打造出来的。如同那“美人”,她“配做时光的妃子”,她也用她自然的美、真诚的自我反抗着,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我们,享受着、欣赏着、娱乐着这永恒的“美”,这看起来光彩夺目的美的面具。而在更广大的“人间”,娱乐,正借美之名义扫落人心。
在这样的意义所指上,沈苇在一步步地完成着突破和救赎。
个案二:《一张名叫乌鲁木齐的床》(略)
从这首诗中,我读到了几组对应的事物:博格达峰→自然,保姆→历史,床→现实,天山→梦境,人→羊群,呢喃(醉歌、表情)→内心,睡去的→醒来的,乌鲁木齐→美丽牧场等。这些对应的事物之间,不仅形成一种互相阐释的关系,相互之间,在诗行的推进过程中也可以转换。但不管怎样,最终都被这样一种情景所限制:“那些不被认识的心灵/是另一些心灵的长夜”。也就是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对应的,或在寻找中的互换,都不是恰切的互相依存,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不被认识”的孤寂,并各自成为对方“心灵的长夜”。这样一种境况,对应于更大的现实结构,就是“雪山←乌鲁木齐(美丽牧场)→沙漠”的结构,那美丽牧场如同床一样,并不是安宁的,而是在不同向度的撕扯中,吱嘎作响。无论睡去还是醒来,乌鲁木齐这张床,这美丽牧场,都在漂泊着、动荡着。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它所代表的整个新疆、中亚,面临的来自文化等多方面构成的、复杂的困境,以及它的无归宿感和一种长久存在的、持续的内在伤痛。
如同《美人》一样,这也是一首大诗。
两个案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所处环境的不同侧面。如果说《美人》是在突出“美”的形成过程,强化那美的面具本质的话,《一张名叫乌鲁木齐的床》则不仅延续《美人》的意义,让我们感受到,床、美丽牧场,也都是表象和“面具”,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这面具背后的“吱嘎”声。《美人》不因描述个体而小,《一张名叫乌鲁木齐的床》不因描述整体而空,小和大共同成为一种现实的侧面、整体。作为两个单独的个案,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扩大着诗歌内涵的覆盖面,将沈苇诗歌提高到一个让人信服的高度:真诚。
我们再次发现,沈苇说他“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并不是一句空喊,而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了他的写作中。他的诗歌,和他的情感与思想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挽歌二:游魂记
从2003年到2007年,诗人如他一贯所做的那样,在关注“边疆”的同时,也关注着故园。
他写代表思念的《月亮》,但“一次又一次,月亮被支付给了死亡”,他只是储蓄下了“美、孤独和荒凉”,“没有一把扫帚去清扫天空的灰烬”;他写《星》,他想让它在陨落之前“保持最美的弧线和亮度”,但“它的飞翔”还是“迅速划破洁白的稿纸”;在《雨的回忆》中,是“雨和雨,这贫穷缔结的婚姻”,“几个遗骨坛子”;在《南浔》,在这曾经有过“蓊郁而孤独的恋情”的地方,“雨滴仍在屠夫们的案板上跳跃”;在《三个傻子》中,生命的灰暗和局促,是“一代代人,像一茬茬韭菜被割掉了”(《黄昏散步到一株香樟树下》)……
故园,他精神的另一极,对于他的内视的眼睛来说,如他所说,有着“外在、多变的显现”。依恋和内心的温情依然存在,但故园,已然荒芜,还在荒芜下去;“游荡的虚无”,掏空了桑园,掏空了泥土,掏空了人心,也种下虚无的青烟和荒草。
对故乡的回望,如果说是“还魂”,还希望“在淤泥卡住的梦里”,如睡莲那般重新升起、莅临一种轮回般的生长,那么,回望的结果,是发现到处是“游魂”,是在温润之中,一种腐烂气息的弥漫。
这时候,我想起沈苇早年的一首《回忆》,在那时,隐然出现的文化冲突、梦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的冲突,通过对故乡物事的回忆,对花蕊上蜜蜂的深情凝望,就可以借助“宽恕”解决了。然而,这种被注定命运的简单超脱,就是在现在,得到“纠正”。诗人,自己纠正了自己。诗人,被现实纠正。正如他在《月亮》中所写:
他发现,他是被失去的事物
被一只死去的月亮,创造着
诗人情感向度的转变和思想的裂变,由消失、悲伤来完成,这是又一曲挽歌。
就在这边疆和故乡的挽歌声中,诗人认识到,并领受了自己的“命运”。他被种植在了旷野中。他说,《墙是不存在的》:
现在,他心房的另一侧又长出了一颗心
仿佛为了成就一种对称,一个法则:
道德,对道德的嘲讽
自我,对自我的质疑
现实,对现实的背叛
“你左边的心只为一个人珍藏,
右边的心要献给更广大的世界……”
他依然在说,墙是不存在的!
《安魂曲》:严重的时刻
或许,在当下的境遇中,在与边疆有关的死亡事件频繁发生的这一年,人们会偶尔想起乌鲁木齐的那个夜晚,会说“某某事件”。显然,它早已作为一种记忆符号,进入了时光的仓库,或已经被时光粉碎。但沈苇的《安魂曲》,为我们记录了那个夜晚及它所带来的震惊、伤害和改变。
我最初读到的《安魂曲》中,选入《沈苇诗选》的有《郊外的烟囱》、《哀哉》等。《烟囱》是旧作,如耿占春所言,是预言;而《哀哉》,是一种借助宗教的人性哀叹。或许,这是大多数人心中所认为的一个诗人面对此类事件时,所能发出的最“恰切”、最为稳妥和无奈的声音。它们足够让人心生慌乱和痛彻心肺。但,它们显示出的力量,远远不能代表《安魂曲》。
完整的《安魂曲》,最初的20首组成《安魂曲》上;《安魂曲》下有17首,《安魂曲》外编有13首。50首诗,创作时间跨度达6年。
《安魂曲》上,写作于事件发生的当月,如诗人所说,更多像是对事件本身的即时反应,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写死亡的突然性、残酷性,以及死亡带来的“情感的无所适从”。我的理解,如前所说,即便诗人对死亡、消失等,不管具体、抽象,不管多浅表、深层,不管多迷茫、痛苦,毕竟早已目睹。但那个晚上,“死亡”将诗人彻底击翻在地,如同他内心深处对美的一点幻想,彻底被连根拔出,只剩下赤裸裸的现实和存在。或许与身临其境有关,或许与意料之外有关,无论如何猜想,也猜度不出诗人受震动的程度。哀伤、悲痛、无助、愤怒(但似乎无法确指),并更多地夹杂着惊恐的喘息。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确如题记所引里尔克的几句诗:“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死亡是无端地、无缘无故地出现的;死亡就在身边;死亡逼视着诗歌。于是,死亡进入了诗歌,被语言不厌其烦地、“残忍地”书写。
《安魂曲》下,写于事件一年之后的九月份。相对而言,诗人即便已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但疼痛却深深地刻在了心里。死亡和疼痛,逼迫诗人再次面对事件。是的,我认为这首先具有逼迫性。《安魂曲》表面上有诗人的所谓良知等,但从一个生命个体的角度看,这再次的面对带有逼迫性:因为创痛之深。哪怕是为了忘记,为了摆脱梦魇,为了从“死亡的眼神”里走出来,都得面对。只不过,作为诗人,他借助诗歌来面对。因此可以说,《安魂曲》下,首先是诗人对自己处于黑暗中的灵魂的拯救。他要找到无端死亡和自身惊恐的原因,就这一点来说,诗人的反应还是一个普通人遭受意外的最正常不过的反应。或许不同的是,事件的内在成因复杂得多,涉及历史、文化、现实、民族等等因素,任何的追问,对于诗人来讲,都只能是追问。这一点,或许是由诗人在社会中的身份所决定:诗人的身份之一,就是一个提问者;他提问,但不提供方案;他渴望解决问题,但只限表达美好的愿望,表示着诗人的一种情感向度。诗人所能触及的,也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一个能够对不同因素有所体现但根本上还是与人有关的领域:人性。我以为,从诗歌的角度来说,以具体事件作为背景,人性,或许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终极问题。无论如何,诗学也是人学,离不开自己、他人,离不开个体、群类。沈苇的思考,正是面对具体事件这个“遗址”,以人性为核心,从人的意识对精神的伤害出发,思辨人性中的善恶,思辨爱恨等情感的意义。在这儿,我宁愿相信,来自时间远距离观照的冷静,加上诗人对诗歌纯粹的敏感,都使诗人的追问,无论涉及到什么,都是在它们的本义上进行,都因为它们自身意义的延展,和其他意义互为生成,且都最终与人有关,与人性有关。《安魂曲》下的题记所引阿多尼斯的两行诗,清楚地表明了《安魂曲》两部分之间的关联,以及《安魂曲》下的整体立意:“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颅,/这团烟雾,是人类的一声叹息”。
《安魂曲》外编,写于2010年至2013年。我只是想说,诗人把它们放入《安魂曲》,是因为它们诞生于那个死亡之夜,它们来自于一张名叫乌鲁木齐的床。或者说,在诗人内心深处,那团死亡的烟雾并没有散去,依然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游荡,烟雾中依然有暗火在把心时不时灼伤。内心这种状况的持续,意味着他被种进了“无缘无故的死亡”。他的诗歌之花,也改变了颜色。现实,在纠正诗人的意识之后,在改写着诗人的内心。他被改写的心,开始“改写历史”。
站在死者一边
就诗人的写作来说,《安魂曲》是他不得不写的诗,是他不得不走的诗歌之路。在经历内心的波澜和死亡的击打之后,《安魂曲》不仅成为他诗歌的新的出发点,也成为他诗歌精神结构的重要部分。
他首先表明,他“站在死者一边”,“——你来自哪儿?”“——你有什么悲伤?”“——你想说点什么?”“——你站在哪一边?”四个问题,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也构成我们的生存境遇(《对话》)。起始一句,就把情景置于一个荒凉的、时空的旷野,生命在那儿似乎是醒目的、孤独的;接着提出一个看似没有来由但十分确定的问题,你是“悲伤”的,你的悲伤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像是一次采访,好像悲伤者可以表达点什么;第四个问题,提问者表明了他的立场,也要求悲伤者表明,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四个问题,就像一个个陷阱,将生命从虚无的开阔,逼到一个越来越逼仄的境遇:旷野,乌鲁木齐,遗弃之城,墙,一个立场。那四个似乎充满关爱的问题,看似轻描淡写却咄咄逼人,最后仅仅为了一个立场!而回答,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否定中进一步肯定。在“不是,也不是;没有,也没有;有形的,并不可怕;不站在,也不站在”之后,是“此时此刻,只有,无形,只站在”。悲伤者亦即回答者(受访者、幸存者、诗人)被压缩着且自我压缩着,但没有退却。对话的张力,来自于某种较量,艺术的张力来自于现实和语言。但此时此刻,如同提问者是想知道一个立场一样,回答者也立场明确:站在死者一边。这并不是一个收缩的、偏狭的立场,而是一个包容的立场。站在死者一边,就是站在人性一边,站在生命一边。
这个表白,也是一种诗歌“主题”的表白。在这儿,诗人从融合的努力和努力的自我安慰中走出来,在诗歌精神上,和“厌倦做地域性二道贩子”彻底打通。他不顾理论或谬论设立的诗歌不关注具体事件的禁区(或误区),选择直接面对事件本身,选择面对现实和现实的存在。他的这种选择,不仅表明了一种精神勇气,也表明了一种诗学勇气。不错,在这儿,诗歌成为诗人对具体事件的“回应”或“回答”。他试图将诗歌从个人情感的载体以及美学范畴中分离出来,试图以诗歌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甚至不惜让诗歌变得粗砺甚至粗暴。就诗人本身而言,他扩大了他的“现实、历史、文化、人性以及美”等概念的疆界,但依然反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是存在,是内心,而不是物象的现实、臆测的现实。《安魂曲》作为诗歌,由此承担了更多的东西。这种承担,也是对诗人内心的呼应。
他改写事物的属性。原本熟悉的、亲切的事物,原本被赋予美好情愫的一些事物,似乎在一夜之间,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改变了外貌,还改变了骨骼和血肉。那个夏日,颠覆了许多东西,如同白昼瞬间变黑(《夏日的颠覆》):
一声惨叫颠覆一首新疆民歌
一滴鲜血颠覆一片天山风景
一阵惊恐颠覆一场葡萄架下的婚礼
一截棍棒颠覆一棵无辜的白杨树
一块飞石颠覆一座昆仑玉矿
一股黑烟颠覆一朵首府的白云
一具残尸颠覆一角崩塌的人性
一个噩梦颠覆一个边疆的夏天
一个夏天颠覆一整部《新疆盛宴》
以这血腥的语言,诗人也在试图改写人们心中的记忆图景。
他改写文本。《安魂曲》中有两首改写的诗。一首是《改写版<混血的城>》,他说:
时隔十年,如此混血了:
是死者之血
与死者之血
的混血
他说:“时隔十年/我的语言深受重创/我的诗歌目瞪口呆”。所以改写文本之前,他双重地改写了自己的诗歌语言。另一首是《乌鲁木齐:一张遗弃的床》,是对《一张名叫乌鲁木齐的床》的逐行改写,那些几乎相同的词,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遗弃。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改写,也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指向了过去那些已经完成的诗,它们也在被诗人改写。比如《吐峪沟》,现在看来,是诗人在不经意间,获得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安详,即便不能说是一个表象,但也可以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介于现实与幻觉之间。
《安魂曲》是沈苇诗歌精神,也是沈苇诗歌文本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在这之后,他的诗不仅在诗歌向度上出现了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或许原本在诗歌意识中存在的江南的细腻和边疆的粗犷间的美学平衡被打破。在《安魂曲》中,沈苇把对诗意更为直接、快速的到达,把诗歌的冲击力量,作为他对应于现实的美学重点。美学服从于现实,服从于内心,服从于生命,服从于生,更服从于死。从《安魂曲》开始,或许他更在意,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
美与真之间的倾斜
在读《沈苇诗选》之前,我读过他的《植物传奇》。那些自然的、美的、历史的植物,它们在沈苇的语言下复活。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会同样对应于植物的现实,会幻想、会辨认、会叹息和渴望。每一种植物,都有它们各自的命运。这是植物的颂歌。而沈苇,正如他自己所说,“已被大地的气息囚禁/被命运种植在旷野深处”(《月亮的孩子》),是一种名叫沈苇的植物。大地的气息、旷野、“移民经验和故乡记忆”的命运,以及“在异乡建设故乡”的梦想,都使痛苦和热爱的气息弥漫在他的诗歌的枝叶、躯干和根里。
在《安魂曲》之前,我读了他的《一行诗》,有77行的“一行诗”。那种独特的体式,那种一行就是一首诗的独立构造,每每让我心动。那是77首诗,77篇文章,充满热望与绝望、经验与超验、常识与悖论。那是“阳光翻阅的裙裾:一本无字的神秘之书”,是从祖父继承下来的仍在咆哮的斧子,是丈量蚯蚓身体和情欲的一把泥土的尺子,是“书斋与旷野之间的路”,是“吐出矿渣”“就能长出新芽的”内心,是从前额无声冲出的一匹白马,是“汹涌的树”。在《安魂曲》之前,或许诗人把自身的生命感受和更为宽阔的生命存在,提纯为坚硬的、封闭的一行诗,他要把内心所有的汹涌都囚禁在“一行诗”里,要保持在“美的自治区”就已经领悟到的青铜般的质地,以及它固有的明亮。
在《安魂曲》之后,我读他的《喀纳斯颂》和《驶向喀纳斯》。前者,我会理解为诗人的一种自我调适。也是随着阅读的逐步深入,我发现沈苇逐渐形成了一种借助自然之美、西域文化疗治现实之伤的手段。他在现实和自然、现实与异域文化之间不停穿梭,从而保持了一个诗人心智的平衡。理性之光,出现在幽暗和明亮的缝隙。而后者,让我知道,如“结冰的湖面上紧发条”,诗人走向的喀纳斯已不是原来的喀纳斯。几年过去,他还是回不到大自然纯净的怀抱,在大自然中,他的意识和情感,都给冰面上紧了发条。
美依然是美,但开始被质疑。就关注的对象而言,就像“塞菲里斯的海伦,从未到过特洛伊”(《论新疆》)一样,诗人可以说,人们想象里和眼中的新疆是一个幻觉。但无论是死亡、幻觉,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否则有违真诚:美依然是且应该是诗歌的“题中之义”。抛开与事件以及与事件本质相同的其他现象的关联,抛开与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民族等因素的意识关联,单就美的自然属性而言,美仍然需要也可以被赞颂,仍然是诗歌美学的自然性对应,也符合人的“爱美之心”的天性。只不过,当美与真之间出现互证和伤害,它们之间也必然出现倾斜。对美的质疑,恰就是这种倾斜的体现。沈苇有首诗,叫《读〈754年纪事〉》。安达卢西亚所写的754年,自然与乌鲁木齐没有关系,但读到这些文字,又觉得是写乌鲁木齐,是写诗人的心境:“这片土地……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之后/依然如此美丽,就像一颗八月的石榴。”痛苦和美丽,都是事实。但正如诗人说的,当“果实汹涌琼浆”,沉睡的一切就被日常行为所唤醒,就会产生“红的隐喻,血的关联”,石榴“这些因沉思而饱满的头颅/转瞬变成一颗颗胡乱堆放的/婴儿的小脑袋/像被时光之斧砍下……”石榴和婴儿头颅之间,行为和意识之间,真与真之间,美与真之间,就会出现倾斜,将我们的心压弯,并倾斜诗歌中的平衡。“——依然如此美丽?”这种对美的质疑,是一种心理现实,也成为诗人诗歌思辨质地的强化。
漫长的灵魂出窍
死亡夜之后,沈苇的每一首诗都是安魂曲。这是我的直觉判断。事件以及《安魂曲》之后的现实,包括《安魂曲》本身的际遇,都构成一个更大的、更深的隐喻和创伤。这创伤,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写什么,都会从心里投射到文字中,增加文字重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文字的暗影。他决绝地说《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与“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一起,将他生命中原本最珍视的两极,完成拆除,他在“合二为一”的同时,一种深切的悲凉进入他的诗歌。这是一次《漫长的灵魂出窍》:
一大早我就离开了自己
远方,并未向我发出召唤
像一个榫子,锲入陌生的土地
有人提醒我,可能会锲入一个墓地
在异族面影中,同时看见友善和疏离
有时则共同忆起昆仑山上的费尔黛维西
在城市与荒原、群山与流沙、岩石与鸟蛋
甜瓜与苦荞之间,如今我与后者站在了一起
诗的外形像极了被切开的金字塔墓地,它没有尖顶,没有“另一半”,这恰如沈苇诗歌的选择,他选择“后者”。就诗歌而言,沈苇似乎舍弃了原来美学的向度,而选择了“后者”,与他明确表明要写的“混血的诗”之间有出入。
但也未必。选择“后者”,意味着选择了低于土地的部分,是在黑暗的深处,将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观照。同样,选择了“另一半”,也就是选择了“那一半”。选择了“后者”,就是选择了“前者”。“前者”和“那一半”,作为意识深处的一种真实存在,成为潜在的参照。
《安魂曲》是现实,现实进入诗歌,便抓取了时间的一瞬,给历史作证。即使是一个《荒凉的证人》,但也“被颤栗团结在一起”:如果是“大风吹歪的房子”,就“挤在一起取暖”;如果是一个雪球,就“滚向流亡之路”,雪和雪互证。互证那些消失的、死亡的;互证过去的春天和现在的寒冬;互证美依然存在,宇宙依然豪迈,星空依然“只是一些美丽的雪球/旋转,翻滚,奇幻”;互证“雪花像一败涂地的异族/其实是流离失散的亲戚”,“众人的善也是我的真”。即便“忧心之后便是遗忘”(《雪》),雪来覆盖,“从白到白/从茫茫到茫茫……”雪和雪依然会互证;即便《清雪车》把积雪“倒进死者喉咙”,“给沉默塞进一个冰坨”,依然,《雪,写下诗篇》:“雪,安静了,不是因为冷漠/而是言辞终于贴近了/低处的心”。
是的,低处的心。严寒和残酷,让诗人听到并找到了或许是自己最重要的声音。就诗歌而言,即使在极端险峻的立意下,也会如诗人在《树与水果》中所言,当果子落进空盘之前,他都会用有限的重“保持一棵树的风景:一种多义的平衡”。在这种意义上,《安魂曲》这组诗,不仅从上篇的现实激情和一定的粗糙,回到下篇的冷静思辨和语言的控制,从事件反应,回到艺术创造,而且《安魂曲》也成为沈苇诗歌建筑中轴线的重要生成者及关键环节:至此,从《菜地》开始,到《混血的城》中的不安,到《阳台上的女人》中的孤寂,到“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的思想突变,一路自我争论和被“月亮创造”,被死亡夜裹挟,他“低处的心”,终于和他的诗歌彻底融合,也将沈苇与其他诗人做了进一步的区分。
是的,我的阅读仅是我理解的“一义”。我多么希望如同沈苇自己对诗歌的改写,我对我的阅读加以改写,剔除掉那些臆测的部分,剔除那些诗歌之外的深刻,我希望,我仅仅是在借此辨析沈苇诗歌的向度。
…………
你不是一个潮湿的人,但水是你的摇篮
你不是一个干旱的人,但沙漠是你的墓地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你早已患上快乐这一绝症
你不是一个痛苦的人,但你享用痛苦像享用一罐花蜜
…………
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你随便掐一掐自己也是疼的
你不是一个虚幻的人,但风把你随意吹送
你不是一个活着的人,但你耕耘、播种,拥有一群宇宙的私生子
你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但活着时你已死去多回
…………
这就是《人的肖像》。写诗就是写人;写诗就是自画像。阅读沈苇的诗歌,就是读他的自画像。他是自我的人质,也是“他者的人质”。他是现实的人质,也是诗歌的人质。他是雪。诗歌的雪。无论是喀纳斯的雪,乌鲁木齐的雪,江南的雪,都是雪。雪与雪互证,互证自我与他者,互证美与真,互证读者和作者,互证此刻的你我。在互证中,梦回多雨的故乡桑园,想起滋泥泉子,到达混血的城,在中亚的废墟,从一种植物移到另一种植物,在乌鲁木齐笑着、哭着、死着也生着。雪和雪的互证,就是心房中的两颗心互证,就是让我时时想起,沈苇那“做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诗人”的梦想和他现在的“诗人与诗歌状况”的互证。不错,雪与雪互证,在互证中改写,在改写中互证。他的诗当然是灵魂的摇篮,他的诗也“为垂死者带来安宁”,更“为亡灵弹奏”了《安魂曲》,甚至还试图用人性来感化“国王”。
就是在互证与改写中,沈苇的诗学方向与起始发生了偏移,“中亚”以及新疆这片土地上,文化、历史、现实与自然的美,依然是他内心中试图在诗歌中赞美的对象,给大自然及美,依然保留着一席之地,并成为其保持诗歌精神和心智平衡的重要砝码。但不可否认,现在的沈苇,正在唱着现实的、存在的、人性的、美的挽歌,热情支撑下的高蹈,变为内心的和诗歌的庄严。
但我依然不知道,站在诗歌的角度,沈苇是否“幸福”,因为即便在异国他乡(《加拉斯加之晨,或祖国之夜》),依然没有一张桌子“可以围坐在一起相互取暖”,依然没有一双筷子,能够“夹起寒冷、残酷的话题”;因为,在诗歌的美和现实的真之间,在生命的严酷和艺术的纯粹之间,做到平衡而不倾斜,做到融合而不排异,做到“喜悦”而不失重,对于所有的诗人,不,对于优秀而真诚的诗人,依然是一个“双重”的难题;因为,诗歌的孤寂、美的孤寂、真的孤寂和生命的孤寂,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