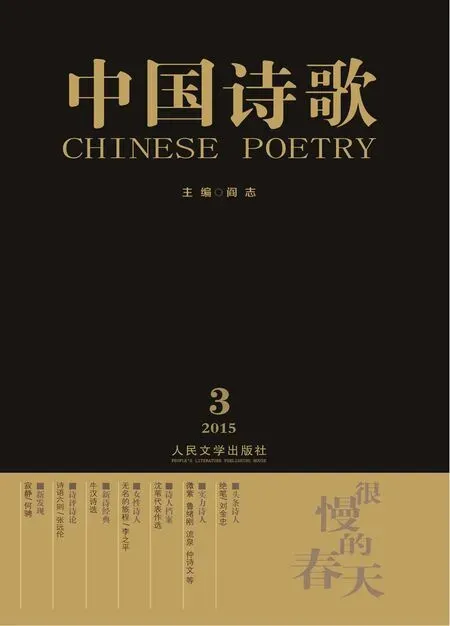诗学观点
2015-11-15 00:33:15韩玉
中国诗歌 2015年3期
□韩玉/辑
诗学观点
□韩玉/辑
●张德明
认为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地理而生发的诗意言说和艺术诠释,已然构成了中国新诗中极为重要的审美景观。地理是一种集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于一体的特定空间,地理诗意的彰显,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空间美学的建构。不管是对现实空间的描摹,还是对历史空间的述说,以及对想象空间的构筑,诗人都必须将诗意的呈现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用富于艺术性的笔法将这些空间精彩地打开,神奇地照亮。通过对这些地理的艺术阐发和诗性彰显,中国新诗的空间美学,才可能会被逐步构建起来。(《新诗空间美学的构建——读〈云朵打开远游的翅膀〉
》,《星星
》,2014年11月上旬刊)●杨亮
认为“交流诗学”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诗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叙事性诗学实践中的一种性别化特殊表达,它一方面指性别意识的转变,两性关系由对抗走向对话;一方面也标志着女性主义诗歌诗学观念走上了“叙事性”综合创造的演化阶段。“交流诗学”的形成,在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之余,也拓展了女性主义诗歌的艺术疆域,提升了其精神气度,使其从狭隘的二元对立性别立场中走出,具有普泛性色彩的人类经验重新回到女性主义诗人的文学思考范畴中,女性主义诗歌也由感性冲动回归至理性的诗体建构。“交流诗学”的形成标志着女性主义诗歌的成熟。(《性别视域下的“交流诗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性别化叙事诗学思维的形成
》,《文艺评论
》,2014年第11期)●解非
认为左岸先生的诗歌以人为本,以情为本,品读他的诗作总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也总是会从他流畅而舒缓的诗句中体会到诗歌的美学品格和诗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诗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赋予作品一种不平凡的使命,使诗歌具有精、气、神,这是非常不易的,也是神圣的。他的诗歌就像他的人一样,默默地书写着对人生、对亲人、对爱情、对朋友的诚挚善良的情怀,将情感的根深深地扎在北方广袤的大地深处,在风中恣意地展示着一个北方汉子的豁达与沧桑。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更是一个抚琴而歌的独行者。(《左岸诗歌以及评论
》,《诗选刊
》,2014年第11-12期)●赵四
认为诗怎么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对抗的产物,这是使诗维持住自己内部张力的最简单便捷也始终是最有效的方式。曾经是意识形态的压抑,使诗的主导声音是反意识形态的。如今是混乱的尘嚣噪音,各种各样的,商业的、低俗媚世的、隐蔽意识形态的、只为表现表演欲的……所以与之对抗的是拥抱梵音的理想。即便人类从来没有产生过完美的梵音,但也一直怀抱着对这声音的梦想。诗,当今的诗,尤当去建设这个声音,一种巨大的静音效果的声音。(《寻找一种个人声音诗学的可能性及其他
》,《作家
》,2014年第11期)●张远伦
认为乡村文明式微,曾一度让诗人哀叹,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前进,诗人们尝到了这种革命性元素的甜头。这种革命性,带来的是破坏力和建构力。在强大的破坏力里,诗人获得了不一样的诗歌写作资源。那些冥想与追忆、撕裂与疼痛、命运的提前和重置、生活的速度和重量,都让诗歌产生了越来越宽的可能。诗人面对钢铁的冰凉产生的抵制,恰好让诗歌具有强力摩擦的热度,而诗人用迷醉、颓伤、游戏、逸乐等词语对现实进行顺应的时候,恰好让诗歌复制了《诗经》般野性和放大的唯美。诗歌再一次拯救了和复苏了故乡,故乡是古老地存在着的,正因为古老,故乡才具备诗意的恒远。(《乡村文明的式微与古老的还乡
》,《红岩
》,2014年第6期)●毕光明
认为诗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保留着人类对世界的初始经验,结合了心灵与精气,以强旺的感受力与生动的想象力,创造出主客浑融的感性世界。在这一感性世界里,寄寓了人类的生存的根本诉求,因而作为思维方式的诗性对人来说具有本体意义。诗人用它具有原始性的思维创造了充满动感和交互性而又秩序化的意象世界,囚禁于肉身的躁动的灵魂,惟有在这个世界里才得以休憩。诗歌不仅自度还能度人,诗人俨然超拔俗世成为指点迷津的灵魂牧师,这也是所有现实中人需要诗歌和社会需要诗人的理由。(《留住诗性的根——评扬兹举诗集〈盛装的音符〉
》,《创作与评论
》,2014年11月下半月刊)●耿纪永、张洁
认为长期致力于英美现代派诗歌翻译和研究的袁可嘉,在对叶芝的译介中通过对译诗的选择、阐释以及具体的翻译策略对叶芝加以改造,体现出他所构建的“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学观念对叶芝翻译的操纵。在译诗选择方面他更青睐叶芝转型为现代派后所写的诗;在译诗阐释中批判叶芝的“贵族主义”,对其诗中的神秘主义采取回避的策略,并试图通过强调与突出等翻译策略来强化叶芝诗歌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袁可嘉的“中国式现代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定性,它就不可能发展为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而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学观念与翻译操纵:袁可嘉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与叶芝译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4年第3期)●谢海长
认为华兹华斯通常被认为具有“反科学”倾向,然而对华兹华斯作品做了整体细读后却发现,他对科技发展及运用现状的评价是辩证的:既颂扬蒸汽轮船和铁路等科技成就,又揭露科技滥用所引发的有害后果;既崇尚有助心灵提升的“大写科学”,又贬斥仅应用于物质性生活的“小写科学”。华兹华斯认为诗人既要像科学家一样奋发有为,又要贡献“神圣精神”去援助物质性或工具性科学,实现其“穿上血肉丰满的衣装”的“形变”,让诗与科学共生共荣、协同造福人类。(《论华兹华斯的诗与科学共生思想
》,《外国文学评论
》,2014年第4期)●张少扬
认为圣童在《形而上本体诗学》一书中所提出的“客观诗本体”的概念,从全新的角度将“诗学”重归纯粹哲学领域,打破了“诗学”只是一门涉及诗歌写作技艺理论的学科的一般性观念。在圣童的界定中,人的主体意识不再是“诗学”的研究对象,“诗学”所研究的当是隐于诗人诗歌作品背后的存在问题——而这一客观世界的存在具有彻底自在和完全自为的属性。“客观诗本体”指涉的是人的“灵魂”的“善”的“属性”,这直接关乎了人类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关乎人当如何看待世界,看待生存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人当怎样生活的问题。(《客观诗本体:一种新的诗学理论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李亚伟
认为诗歌的阅读和认可从来都有滞后的特性,人们只读前朝诗歌,只了解和认可定性了的前朝诗歌。不管你多聪明,你只要不是当朝诗歌中的作者,你就只是一个普通大众,你对诗歌的了解比普通大众的程度高不了哪儿去,你最多只能读懂部分当代诗歌。通常的情况下,最先进的文化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与生活磨合才能引领生活,最前卫的诗歌、艺术也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对社会审美挑衅才能被审美。(《诗歌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关于当代诗歌的评价及诗人的身份问题
》,《扬子江
》,2014年第6期)●辛笛
认为大陆要重新谈论现代派,重新学习现代派,其实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二者一方面不可割断,另一方面又不能重演。在时间、空间、条件都不一样的情况下,谈论现代派就是要把现代派的优点吸收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吸收西方的好的方法。同时,诗歌创作还应该做到兼收并蓄,各方面的诗的风格,都应该能够让它繁荣起来,只要我们写得好,就可以存在,作品多起来,好的作品就会来了,要“多”中求“好”。(《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1981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现代中文学刊
》,2014年第6期)●利兵
认为安妮·塞克斯顿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与她的心理疾病不可分割,诗与治疗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诗人需要这种私密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现实中失落的生活的希望,从诗歌中重新找回。诗歌和治疗一样给无意识提供了话语方式,给诗人封闭的自我提供了一条交流和倾诉的渠道。此外,写诗不仅是诗人内心治疗的需求,而且反映了社会环境对精神世界的扭曲,诗歌在反思个人的同时也在反思时代。诗人这一职业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它能启发读者,救赎心灵。(《安妮
·塞克斯顿与诗歌治疗
》,《外国文学动态
》,2014年第6期)●沈奇
认为一个时代之诗与思的归旨及功用,不在于其能量即“势”的大小,而在于其方向即“道”的通合。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百年中国之诗与思,是一次对汉语诗性本质一再偏离的运动过程。如何在急功近利的“西学东渐”百年偏离之后,重新认领汉字文化之诗意运思与诗性底蕴,并予以现代重构,是我们首先需要直面应对的大命题。当前,现代汉语之诗与思,在历经百年的“与时俱进”后,已然深陷中西“夹生形态”(张志扬语)之矛盾处境,其“矛”也“西”焉,其“盾”也“西”焉,短期内很难自外于“他者”而独树于世界。(《“味其道”与“理其道”——中西诗与思比较片谈
》,《文艺争鸣
》,2014年11月号)●白连春
认为文学和世界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如果有人把文学和世界对立起来,硬要理清文学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便是一个错的命题。实质上,文学与世界没有关系,因为所有文学都是世界,因为全部世界都是文学。文学就是反映世界的。文学即世界本身。世界是白的,文学就是白的;世界是黑的,文学就是黑的;世界是和平的,文学就是和平的;世界是幸福的,文学就是幸福的。不论别人的创作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白连春认为自己的文学就等于他的世界。(《尽可能地还原生活的真实——与白连春对话
》,《莽原
》,2014年第6期)●马永波
认为当代诗歌充斥着对个人化小情感的描述,这样的诗歌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从中只看到了诗人在温室中自叹身世的“私心”,诗歌缺乏了大的现实关怀和人类永恒的主题。诗人多习惯将以往的“逻各斯”分散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在碎片中透露出若干生存信息。这么做,固然有让诗歌卸下过重的意识形态负担的好处,能让诗人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生活中的经验与体验,但同时也带来了诗歌琐碎化和私己化的倾向。因此,倡导健康向上的精神高度与经验深度的整体性写作的难度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难度写作的再倡导
》,《诗林
》,2014年第6期)●李犁
认为经过百年的发展变化,中国新诗已经确立了自己独立且耀目的诗学传统。但是活跃和喜新厌旧的品性一直让新诗处在前沿和动荡之中,速变与速朽是新诗的特征,也是技术更新的动力。新诗在进化的同时,也在变异。过分的“诗言志”加上对世俗趣味的沉迷让诗歌中的志向及理想越来越淡化,审丑在流行,低迷低俗以及苟且犹如诗歌中的阴霾在弥漫。诗歌需要热爱和温暖,需要气度、高度和温度。忌功利和世俗,坚守寂静和狭义,是诗人原本就应有的品质。(《百年新诗需要坚守些什么
》,《诗刊
》,2014年11月上半月刊)●黄灿然
认为诗人应当接气和安气。接气就是指一个诗人先要奋发,无论是出于抱负、野心、虚荣,还是别的,总之要精进,包括技艺的精进,要使自己的母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不应是由别人判断,那会变成追名逐利,而应由自己来判断。这个气最初不是它来了你接,而是你努力让自己够得着它。这一步相当于建立自信。自信建立后便应是安气,不断接近自己心灵最内核的东西,这个时候要把接气过程中的杂质全部清除。也就是说,要扬弃。总之,气即是我们天性中的自然、清白、纯洁、天真甚至幼稚、愚笨。(《黄灿然访谈:枯燥使灵魂长智慧和善良
》,《诗歌月刊
》,2014年第11期)猜你喜欢
作文周刊·小学二年级版(2022年12期)2022-03-19 19:19:07
少儿美术(快乐历史地理)(2018年10期)2019-01-29 07:00:06
中华诗词(2018年6期)2018-11-12 05:28:18
读友·少年文学(清雅版)(2018年5期)2018-09-10 06:07:14
扬子江诗刊(2017年1期)2017-01-17 06:25:11
火花(2015年3期)2015-02-27 07:40:48
英语学习(2015年11期)2015-02-01 19:57:13
北方人(2014年10期)2015-01-09 21:16:05
意林原创版(2014年1期)2014-05-31 16:12:04
外语学刊(2012年6期)2012-01-19 13:4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