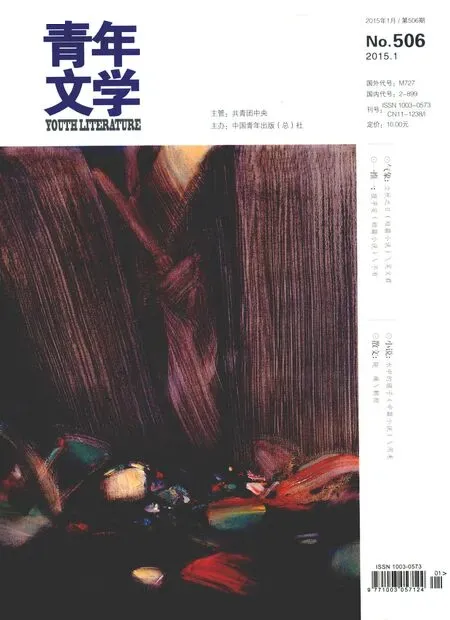牧斯的诗
⊙ 文/牧 斯
牧斯的诗
⊙ 文/牧 斯
牧斯:原名花海波,江西宜春人。一九七一年出生。写诗多年,著有诗集《泊可诗》《作品中的人》。
山岭学
上到光家山垇背,就是一片高地。
这儿的地形像龙趾。
左边是顾年冲,可看见烟火;
右边一个茶山窝,叫狗家塘。
往下走,王积垇,伍家塬反向而驰。
我喜欢在那里捡柴,干茶树,好斫。
再往下有个坡,几座老坟;同一块岩石上的水
却各奔东西,流入上易家冲,寄塬。
两边层林尽染,杉木和茶树苦撑着,
分别走向苦塘和上布。
就在我们称为对门的对面,是我的家,
它那样破落,低矮,仿佛要垮掉。
小叔不在了,德叔的家七零八落;会财走了。
只有我家,还在生火,是老双亲。
对门的那边是王狗寨,一处较远的密林,
再往下是下易家冲,以前有人,有庙,现在没了。
而右边是下东源,一线天水,冲天而鸣,
往下的左边是青苔上,右边是婆官山;山在这个地方
有一支分到别的地方了。但我继续
往我熟悉的方向。前面是歪嘴里,有我一个要好的同学;
右边不大清楚,一个大山垇,趔趄而下,
据说可以看见莲香女俚的墓。再往下,
就是拐点了,山势平缓,快要连着水了。
那是别人讲故事的地方。
娟女俚
或许,她还在那里做工,
在父母的日思夜想里。
已从花季少女变身成
辛酸肥胖的中年人。
嫁给一个懦弱的人,
不让给家乡写信,动辄施暴。
可怜的她,奔波在
纸厂和洗衣坊之间。
儿子也不听话。
她不识字,
也不记得家乡的名字,
再也没见过家乡的人。
但是,或许,她死了。
曾抛尸荒野,被挖出双眼和肝,
之后遗弃在垃圾桶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
就是这样;
人可以凭空消失,
火车上有人抢劫。
二十多年,她没有音讯。
我记得,她十四岁,
敦厚可爱。
父母十余次南下找寻,
托人打听;
就像生活中的无数可能
她挑中了最疼心但还不是
最绝望的一种。
因为,这至少还可以
让她父母寄予无限的思念。
上山认墓得句
找墓门上有蛛网的墓,
那便是管事的墓。
茂景的墓垮了,茂森的墓上没有字。
那武举人的墓蹿出一蓬烟,
由此打消迁它的念头。
更早的墓只简单地
围几块青石。甚至只有土堆。
连青石也碎裂了。
父亲说:“找墓门上有蛛网的墓,
那便是管事的墓。”
“蛛网上有露珠的,更好。
说明他最近还出来……”
山林中荆棘和杂树丛生,
我、父亲、德叔和崽一同上山。
其实找到了,也不能怎么样。
就回去。心里想着
他们管着怎样的大事。
为父亲十一月十日离家出走而作
父亲在苦撑,独守
在雨林或整夜灰色的寒噤中。
父亲像只无家可归的小狗儿,
在冰冷的柴草中绝望地望着晕眼的天光。
以前,还会自己给自己挖眼**注释:挖眼,即挖墓穴。
这一次他自己将自己放逐。
抛开放浪作恶的妻子,叮嘱儿子:
“永远不要回来。”这作恶的十甘庵山乡。
但是,我,作为儿子,也知道母亲的不易。
花季少女下嫁贫族花氏,里外张罗得靠人情,
有一回我甚至想似话剧演员那样下跪深情张望,
说:“这才是我们所说的人生。”
“正因为有不羁、不合,才会有风浪。”
才会有我们。父亲说他忍耐了一辈子。
不是为了这个家族早就一拍两散。
他说的是花氏,在十甘庵八百年仍是一根小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