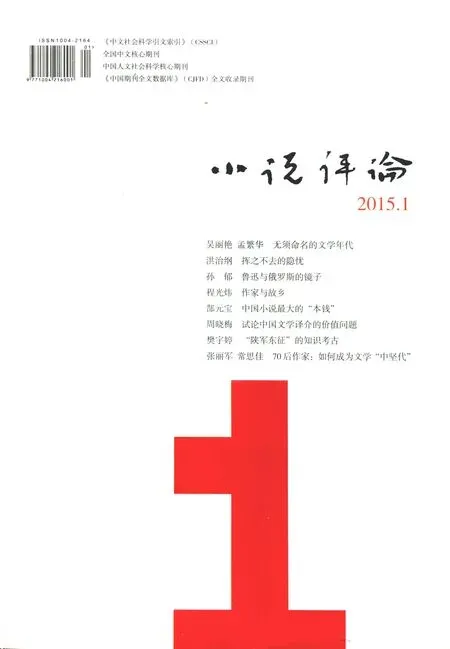现代主义与新时期以来的广西小说
杨 荣
现代主义与新时期以来的广西小说
杨 荣
纵观广西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它从边缘迈进中心的艰难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引领广西文学进入中国文学版图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我拟以新时期以来的广西小说创作为例,梳理和探讨现代主义小说是如何在广西本土萌芽、生长、成熟乃至走向全国的。
一
广西虽处边地,远离中心,但文学步伐还是和中国文学主潮基本一致的。1985年前后,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与裂变,文坛相继出现了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以及莫言、残雪等人创作的“新潮小说”。这些新观念和新作品的出现,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与创作方法形成了巨大冲击,而这个冲击波也同样扩散到了广西。1985年3月,《广西文学》发表了杨克与梅帅元合写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在文中,他们表示:“花山,一个千古之谜。原始,抽象,宏大,梦也似的神秘而空幻。它昭示了独特的审美氛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百越世界,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整体。”并认为理解这个奇异的“百越世界”,“对我们探索形成新的自成一种风格的文学现象有着重要意义。”杨、梅的宣言迅速引燃了广西青年作家的创作激情,在这一年的《广西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梅帅元的《黑水河》、李逊的《沼泽地的蛇》,张宗栻的《魔日》、张仁胜的《热带》等小说。“百越境界”小说的出现,也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并不约而同的将重点放置在了对其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阐述上。如蒋述卓的《“百越境界”与现代意识》,张兴劲的《“百越境界”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百越境界”小说的出现,可以看作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广西的最初萌芽与实践。
二
1990年代,对于广西文学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间段,东西、鬼子、李冯、陈爱萍、常弼宇等人的小说,相继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收获》、《花城》、《作家》等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特别是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与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分别获得1997年和2000年的鲁迅文学奖。这些都鲜明地标示着广西文学创作有了本质意义上的突破,真正地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梦想。鉴于“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的创作实绩及其在文坛的地位,本节我将以三人的作品为主,论述广西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东西、鬼子、李冯在此时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其中尤以东西用力最勤,主要作品有《迈出时间的门槛》、《原始坑洞》、《抒情时代》、《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反义词大楼》、《目光俞拉俞长》、《把嘴角挂在耳边》等。鬼子本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有《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谁开的门》等。李冯则主要创作了《孔子》、《多米诺女孩》、《碎爸爸》、《辛未庄》等小说。综合起来看,三位作家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地也相当不错,并大致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小说主旨充满了形而上的抽象意味,为了配合这一主旨的表达,作者熟练地运用了夸张、变形、荒诞、隐喻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没有语言的生活》呈现了一种极其夸张而荒诞的生存状态,聋子、瞎子、哑巴集中在一个苦难的家庭生活。虽然个体先天不足,但一家人竟能奇异的互相配合,瞎子(王老炳)发问,哑巴(蔡玉珍)点头或摇头,聋子(王家宽)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最后“三个人就这么交流和沟通了。”这样一个悲苦的三凑之家,却不仅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情,反而备受欺凌和侮辱。王家宽喜欢的朱灵被小学老师张复宝占有了;王老炳制作的腊肉被刘挺梁几个偷走了;老黑、狗子还帮王家宽剃了阴阳头;蔡玉珍则在黑夜遭人羞辱。为了躲避村人这种无尽的伤害和骚扰,王老炳无奈地选择了举家迁徙——掘开对岸的祖坟建了座破屋。按道理,远离村庄,应该远离了是非,可现实并非王家人想象的那样。王老炳的孙子王胜利第一天放学归来就吊着嗓子唱:“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小说结束了,可精神的戕害却仍在继续。东西用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文化环境中,独异“个体”被“集体”侵害的这种非正常状况隐晦、深刻地传达了出来。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性恶”,更是一种文化环境孕育出来的深厚的“集体无意识。”
李冯的《孔子》也充满了某种荒诞意味。表面上看来,小说不过是重述了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在这段历史的重述中,作者却注入了十分鲜明的当代意识与自己的审美评价。作品中的孔子师徒已然卸去了历史圣人的璀璨光环,沦为了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他们周游列国、救民于水火的宏伟理想,也不过开始于一个有些荒诞的臆想——试图让沉湎于女色的鲁国国王意识到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并委以重任。然而,这样的愿望却化为了泡影,孔子师徒不得不尴尬而又宿命般地行驶在未知的路上。在作者看来,孔子师徒能否最终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经艰险后,他们仍然“在路上”,仍然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信仰。正因为这样,“那样的一次旅行,是不可能消失和被抹杀的,即使在遥远的时间那端,它也依然会熠熠闪光。”
比较起来,鬼子的小说风格似乎与东西、李冯有着相当的差距,因为他的作品写实性更强。《被雨淋湿的河》写了一个充满血性的乡村少年的杀人与被杀;《瓦城上空的麦田》透视了城市、欲望对现代人人性、良知的吞噬;《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寒露则在母死父失踪的艰难困境中踏上了未知的旅途。鬼子用他充满同情的笔触描摹了一幅幅灰色、阴暗以至于令人压抑的现实生活图景,表达了对这个病态的世界的诅咒与鞭挞。但尽管这样,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叙述却充满了荒谬的现代主义色彩。李四(《瓦城上空的麦田》)因为三个孩子忘记了给他过60岁生日,所以赌气上城去唤醒他们的记忆。没想到由此开始,他遭遇了人生中最巨大也最离奇的变故。三个孩子的记忆未能唤醒,自己却莫名其妙的被死亡了(开的死亡证明书写了他的名字,他又故意将自己的身份证放到了骨灰上),而李四的死又引发了老婆的死,最终李四成了活着的死人。子女不仅一次次鄙视他、凌辱他,最终还彻底抛弃了他。与李四的悲惨遭遇相似,少女寒露(《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的厄运则是从一块脏兮兮的猪肉开始的。由于母亲偷肉的丑行败露,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更加雪上加霜,最终父亲选择了逃离这个家。没有了父亲之后,整个家庭陷入了一片困顿。于是,寻找父亲也就成为了母女的生命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寒露遭遇了迷奸且不幸怀孕、堕胎,母亲怒急自杀。最后,孤独无助的寒露踏上了“寻父”之旅。由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惨绝人寰的生命悲剧,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这却是发生在当下社会的活生生的现实。鬼子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揭示了生的艰辛与死的惨痛,读来令人为之扼腕。
当然,作家们对人性与社会弊端的犀利批判,并不止于上述有限的几篇作品。在《耳光响亮》、《反义词大楼》、《不要问我》、《谁开的门》、《唐朝》等一系列小说中,我们照样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生命意义、对存在的追问与思考。《耳光响亮》里庄严的“寻父”之路,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绝望旅程。因为当“我”千辛万苦找到父亲时,父亲已经失去了记忆,把“我”当成路人。《不要问我》中的副教授由于失去了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而沦为了“非人”,因为他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谁。当人的存在必须用一堆废纸来证明时,人的本质已然丧失殆尽。《唐朝》中的李敬自始则至终在深思“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办?”的个人存在问题。可以说,无论是对悖谬现实的辛辣嘲讽,还是借古人之口抒现代人心中之块垒,这些小说都触及到了关于人性、关于存在的最根柢的问题,因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深度与力度。
二、“广西三剑客”都表现出了对叙事艺术的高度热情,尤其在叙事语言和叙事结构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东西、鬼子、李冯的小说中,异彩纷呈、逸趣横生的语言是其一个显著共性。他们都喜欢采取以轻击重的方式,用戏谑、调侃的语言制造巨大的反讽力量。例如,鬼子把酒店门前的侍女比作为“肉栏杆”,将经商女人的笑区分为“专业的笑”和“通俗易懂的笑”。在生动形象的语言背后包含了作者对当今商业社会的讽刺。东西在《耳光响亮》中这样写牛红梅出嫁的场面:“三辆车子缓缓地驶出长青巷,我们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在那样一个假、大、空盛行的年代里,作者说“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这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意味深长的。可以说,“这些糅合了特定时代政治术语而又生活市井化了的文学语言,既形成了东西的语言个性,还很切合那个戏剧化的时代背景。”因此,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力。李冯的小说语言则表达出强烈的颠覆与解构经典的欲望。在《另一种声音》里,作者这样嘲讽伟大的“西天取经”事件——“完全不像后来艺人们吹嘘的那么牛×哄哄”,“一路上,最大的问题是小腿抽筋和肚子饿。另一个问题是人心不齐”。而对于经典人物形象,作者也最大限度地去神圣化,将其还原成普通人物。于是,武松成了醉鬼,宋江沦为小人(《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唐僧肥胖又健忘,孙悟空丧失了法力, 变成女人、娼妓和仆妇。(《另一种声音》)。在所有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语言背后,其实都深深地传达了作家们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和理解,也表达了他们最鲜明的爱与憎。
在关注语言的同时,“广西三剑客”也十分注重文本的叙事结构。东西的小说明显受到西方元小说的影响,他常常故意将小说设置成一种开放式结构,让作者、读者共同参与到小说之中去。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就设置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是蔡玉珍生下了个又聋又哑的小孩,但仍然没有摆脱村人的骚扰,远处的侮辱性歌谣飘过河岸声声入耳。二是蔡玉珍生下了个健全的小孩,可上学的第一天就将侮辱全家人的歌谣带了回来,在爷爷的训斥下,小孩变得和聋哑人一样沉默。小说一反传统的封闭式结构,给读者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思考向度,同时也让小说的意义变得多维与复杂。东西类似的作品还有《幻想村庄》、《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等等。鬼子小说的叙事结构也有某种趋同性,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苏通之死》等几个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李四、寒露还是苏通,他们最终的悲剧命运(死亡或未知)都源自于最初的某种缺失。李四不满子女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寒露想寻找失踪的父亲;苏通投稿被拒。由于这种缺失,他们想通过各种办法来进行弥补或改变。于是,李四用各种办法暗示子女;寒露日夜不停的守候与寻找父亲;苏通选择纵欲。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达成任何效果,所以这些人物最终都走向了死亡(或未知的旅程)。需要指出的是,鬼子的小说虽然具有相似的叙事结构,但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却采用了倒叙、预叙、插叙、空白等多种叙述方式,因而整个文本的结构仍然摇曳生姿,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先锋性”。李冯的小说主要体现为戏仿结构。他故意将经典文本拆解开来,然后重新拼贴与组合,形成一个崭新的表意文本。像《孔子》就是对《论语》及相关史料的戏仿,《十六世纪的卖油郎》是对《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戏仿。这些戏仿的文本虽然受前文本一定的制约,但显然已经注入了作者的现代观念与审美意识,因此具有强烈的颠覆意图和反讽意味。在文本内容推陈出新的同时,李冯还经常使用穿插、中断的叙事策略,使小说结构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像《另一种声音》里就插入了对吴承恩的考证,《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中突然中断了对武松打虎的叙述。这些戏仿与叙述中断,虽然不难看出西方元小说的面影,但也体现了李冯敢于实践与尝试的勇气,使封闭的文本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
客观地说,“广西三剑客”的小说比较明显受到了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等西方经典现代主义作家(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带有不可避免的“影响的焦虑”。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说又不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简单移植与复制,而是借鉴中的创新与发展——即现代派表现手法与中国本土现实的高度融合。正因为这样,广西现代主义小说在他们手上走向了成熟与辉煌,用无比精彩的文字和娴熟的叙事技巧创作了一篇篇令中国文坛刮目相看的佳作。
三
新世纪以来的广西文学继续保持强劲发展的势头。一方面是业已成名的作家东西、鬼子、黄佩华等人佳作频出,如东西的《后悔录》、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黄佩华的《生生长流》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另一方面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如朱山坡、光盘、李约热、杨映川等。鉴于前面已经论述过东西、鬼子等人的小说,所以本节将重点论述新崛起的青年作家。
在我看来,朱山坡是新世纪之后广西文坛成长最快的作家。2005年以前,朱山坡在写诗,2005年以后,朱山坡主攻小说。迄今,已相继发表了《多年前的一起谋杀》、《我的叔叔于力》、《山东马》、《中国银行》、《鸟失踪》等70多万字的小说,引发文坛的广泛关注。朱山坡的小说大多与乡土、苦难、底层有关,当然也与现代主义有关。用奇诡、荒诞的想象去撕开生存的创面以抵达生命的真相,这是朱山坡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山东马》是他较早的一个作品(2006年)。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人竟然被惨无人道的当成“畜生”——一匹马对待。阙三让他抓回来的“山东马”(一个精神病人)住在牛栏,吃隔夜饭,干牛马般犁田、拉车的活。稍不如意,就是鞭打、枪击(玩具枪),直至用木棒打得半死。阙三这种毫无人性的虐待,终于激起了“山东马”的仇恨与报复,他毫无征兆的死在了饭桌上,“头壳碎裂了半边,脑浆都一团一团地流出来了”。人沦为“非人”,这是现代主义小说中最常见的表达。当阙三将他的同类当成“非人”时,他的人性已经荡然无存。而在人性一片幽暗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必然是触目惊心的残忍和死亡。朱山坡以相当冷峻的笔触写出了底层的愚昧与苦难,同时也写出了令人绝望的人性之恶。事实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朱山坡小说中比较恒定的一个主题,他常常用一种寓言式的写作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鸟失踪》叙述了一个相当离奇而荒诞的故事:父亲因为对一只鸟的迷恋,放弃了正常的人类生活,离开家、离开妻子,遁入森林中与鸟为伴,最终不知所踪。父亲宁愿逐林而居,与鸟为伴,实际上不仅仅是出于对回归自然的一种渴望与向往,也是他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深沉的失望。在与人同在的世界中,父亲不过是一个酗酒、好赌、懒惰,偶尔还去嫖娼的堕落男人,但在与鸟相对的时候,父亲却“忘记了酒的存在,忘记了通往赌场的路,甚至忘记陈村有一个操着贵州口音的暗娼。”相对于人性的复杂、冷漠,甚至邪恶,我想,鸟的世界恐怕要纯净、澄明的多,而这才是父亲真正心向往之的地方。朱山坡曾经说过:“将正常的世界扭曲给人看, 实际上是一种荒诞。有些东西在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往往比正常状态下看的更清楚、透彻, 更逼迫真实, 也更有力量。”我同意他这种看法,也十分欣喜的看到,他在《喂饱两匹马》、《爸爸,我们去哪里?》、《灵魂课》……等一系列小说中,将这种变形的叙述表达的越来越有力量。
光盘也是2000年之后崛起的一个重要作家,迄今已发表《王痞子的欲望》、《我是凶手》、《柔软的刀子》、《美容秘方》等各类文学作品150余万字。光盘的小说触角大都延伸在一个叫“桂城”的地方,通过这个光怪陆离的繁华都市,作者表达了对现代人生存困境与心灵伤痛的深入思考。《错乱》中的孙国良是桂城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只因为一年前生了一次病(精神分裂症,但很快治好了),从此与精神错乱结下了不解之缘。周围的人为了从他身上捞取油水,把所有罪责都归到其头上——砸坏别人的房子、强奸妇女、暴打村民等等。在周围人众口一致的证词下,没病的孙国良最终确认自己的确犯了精神病,并希望通过杀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出乎意料的是,孙国良没有死,却亲手杀了前来杀他的人。当然,孙国良没有被枪毙,因为他是精神病!光盘用幽默而荒诞的叙述展现了一个病态错乱的社会,以及那些被欲望完全扭曲了的人心。小说中的孙国良显然是一个隐喻和象征性的符号,由于没病的他面对的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和一群错乱的人,所以他最终只能认为是自己不正常。光盘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细腻而深刻,他清楚地体察到了当代都市社会的人心病象,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真实地裸现了一幅幅人生百态图,展示了人类在荒诞现实中的生存之痛与心灵之伤。”
李约热的小说创作大致始于2004年,虽然整体数量不多,但大都出手不凡。《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涂满油漆的村庄》、《青牛》、《李壮回家》先后获得过国内一系列大奖。来自乡村的李约热,将叙述视点基本定位在底层社会。但是,他并不喜欢铺陈苦难与艰辛,而是擅长在幽默、诙谐甚至不无调侃的语言中,温婉地表达内心深处尖锐而绵长的疼痛。《巡逻记》叙写了一个因赌博而失血的村庄。在这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玩“三攻”的人们,老少不分,如痴如狂。“我”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竟然被所长授意为秘密的“看护”,当起了赌博的保护伞。作者以近乎荒诞的手法呈现了乡村社会中赌博泛滥的真实景象,展露了比贫困更可怕的精神堕落。《李壮回家》则书写了一个关于理想遭遇现实的悖谬故事。年经气盛的李壮怀着对理想、爱情的憧憬逃离家乡,远赴北京,可最终却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重返故乡。当他声嘶力竭地大喊自己先前所痛恨、所不屑的“那个有狐臭的杨美,那个一只腿长一只腿短的杨美,那个已经和十二个男人睡过觉的杨美”时,我们看到的是,理想在现实面前无奈屈服的盛怒与悲伤。在李约热的小说中,这种荒诞而真实的场景还有很多。一对恩爱夫妻因为一部外国电影而离婚(《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一个单位的同事夜晚集体出动跟踪领导(《这个夜晚野兽出没》);——李约热用一幕幕荒诞的人生场景,戏剧化的展示着这个社会的病态和畸形,在看似轻松的笔墨中寄寓着自己的沉痛与哀伤。
作为后起之秀,朱山坡、光盘、李约热等人凭借不俗的文学功底,游刃有余的将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穿行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文学的哈哈镜,折射出了生活背后的辛酸与苍凉。正因为有这样的才情,他们的佳作才频频发表于《当代》、《花城》、《作家》、《北京文学》等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昭示着广西文学的蓬勃生气。当然,他们的创作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譬如叙事的偏执、理性的缺失、情节的漏洞等等。希望他们能在今后创作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写出更为优秀的作品来。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这样一篇短小的文章里,纵论三十年来的广西现代主义小说,的确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我能做到的,只能是浮光掠影的梳理三十年来广西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大致历程及其取得的部分成就。另外,我也无意于评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优劣,只是如实地阐述了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引领广西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校人文社科课题,项目编号SK13LX327。
杨 荣 玉林师范学院
注释:
①杨克、梅帅元:《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广西文学》1985年3期。
②李建平:《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③橙子:《朱山坡:从不同视角观察新乡土》,《 南宁日报》2006年6月16日。
④杨荣:《荒诞背后的生存之痛》,《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