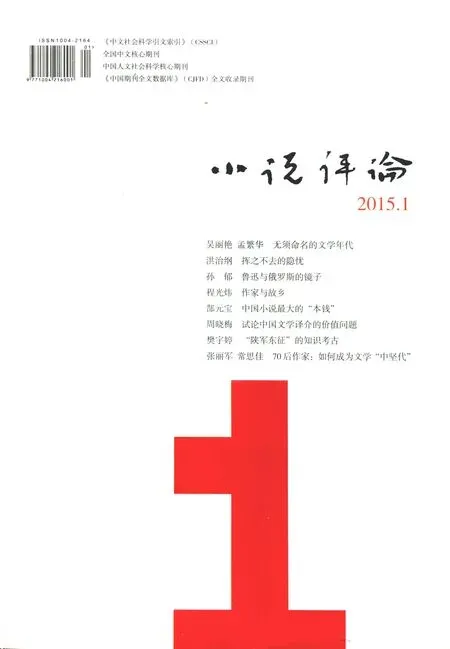沉默与呐喊
——自述
邵 丽
沉默与呐喊——自述
邵 丽
不管别人觉得当一个作家多么光鲜,很多深谙内情的人却知道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其实写作就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一个作家要把别人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情想到想透,还得用一种艺术或者文学的方式告诉人家,这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据说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一个职业——干上帝的活儿,帮人家拿捏命运,能落得个好吗?
在大多数时候,作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TA生活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缘地带,而且界限尚不是那么分明。但TA又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稍微觉得超出常识——物理、人情——TA就会放声呐喊。TA就是这副德性,因为TA是一个作家。
然而,很多读者问起我为什么写作时,我常常无言以对。这是一个轻易就能拿起来、却很难放得下的问题。事情就是那么发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从故事本身到我的写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谓灵感,也许就是上帝之选,在合适的时间,把某些东西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东西”,肯定有它坚实的内核和内在驱动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仅仅是把它呈现出来,所能改变的,无非是表现的方式,尽管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和方向。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宿命,甚或有人认为是傲慢。不过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话,我就只能这么说。
难道还有更合适的解释吗?我做不到,也不相信。很多人以为,小说家都是凭空编故事的人。这么说也许没错,但除非是用唯心主义或者先验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一切,否则是站不住脚的。故事从何而来?从形式上看,它可能是一场白日梦,可原故事不是这样的,它是生长出来的,它先于文字和作家存在。讲故事的人会死去,可是故事不会,它会永远活下去,直到人类的最后一个被毁灭——不过,这也是一个故事。
也许到这时候,可以初步回答读者的提问了:故事就在那里,我忍不住要写出来。但这样又容易诱发另外一个问题,莫非所有的写作都来自于生活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多玄幻和科幻小说,它们横空出世,却又非常轻巧地嫁接在现实生活上,甚至连茬口都不留,好像生活本身就具有千奇百怪的N度空间。但是,我不禁要问,那些点石成金、死生穿越的人,他们面对的不是现实问题、解脱的不是当下的苦恼吗?它介入我们的生活,不是否定或者改变了世界,而是改变了我们看世界或者处理与这个世界关系的能力,变换了新的角度。因而不管它有多么想当然,它是现实的,是活生生的,是接着地气的。
因为现实,我常常为笔下的人物忧伤万分,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也许就是这种绝望逼出了我的决绝,因而使我的作品有了态度。《刘万福案件》里的刘万福,每每想起他来,我总觉得非常惭愧。虽然我把他领到了读者面前,引起千万人的围观,可是那于解决他的问题,改变他的命运,并没有任何裨益。甚至往深处说,即使解决了他的问题,那孙万福,陈万福,张万福们的问题呢?
绝望——如果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整个社会都将被逼入绝望。
《第四十圈》里的齐光禄,是我笔下另一个杀人者。这部小说交出去很久,已经被《人民文学》刊发,以及多家刊物转载。但他那带着风声的刀光,还一直纠缠着我,有时候会在我独处的时候上下翻飞,嗖嗖作响。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齐光禄会成为一个好老板、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可是,就连这一点卑微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点一点地把它掐灭。说实话,当他怀揣着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场的时候,我的心情踌躇万端,写到这里,或者每每读到这里,我既血脉贲张又泪流满面,久久地回味着这个细节,五味杂陈。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也不忍心让他停下来。那是他这一辈子惟一的一次生命绽放,如飞蛾扑火般决绝和神圣。我更不忍心指责他,因为我没有资格那样做。
我的两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生存质量》,有人说是官场小说,有人说是自传体小说。都对,也都不对。我写的确实是官场,但已经远远地“去官场化”。如果官场是一条大河的话,这两部作品应该是站在河边的反思。这两部作品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对于官场,从进入到退出,是一个轮回,也是一种升华。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长。我们最后能够面对,既是坚毅,也是无奈,因此这就是生活。
从小秋、秋生到小舅舅,那是我看到的另一幕生活图景。与快意恩仇相伴,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世界的依偎、眷恋和忍耐。小舅舅这样的人,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把不平和不公化于无形,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为别人活着。这本无对错,它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并以此延续五千年的香火。而小秋则恰恰相反,她希望看到不变之中的改变,希望找到芸芸众生里的自己。她有目标,有性格也有态度。她给我们以希望和安慰。我的其他作品里的人物,我常常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用词语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让我牵挂,也让我踏实。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价值观多元且思想纷呈的时代,我们被信息所覆盖,也被它捆绑。我们写出来的,到底是被缚的感觉、解脱的愉快还是对绳索的“斯德哥尔摩”依恋,很难说清楚。这很有意思,也着实令人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