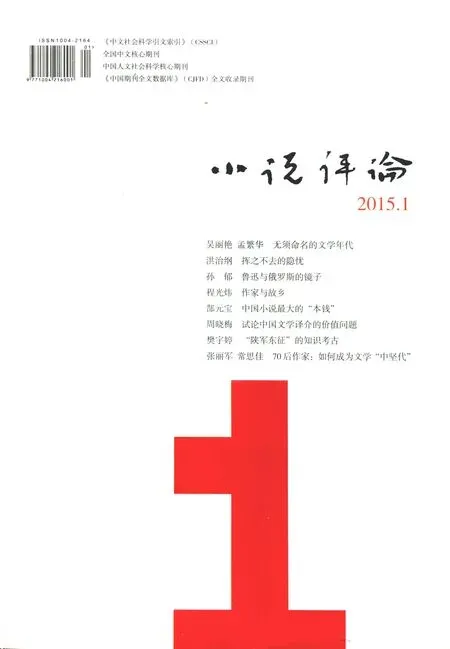文学与“中国梦”
——邵丽访谈录
2015-11-14 22:27:21张延文
小说评论 2015年1期
张延文 邵 丽
文学与“中国梦”——邵丽访谈录
张延文 邵 丽
一、现代性的困惑
张延文:
自近代以来,在几代人呕心沥血的追求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二十一世纪之交,在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城市化、技术化等混合动力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始了持续、高效、飞速的发展,在“中国奇迹”的背后,是各种副作用带来的“现代化的困惑”。这对于身处其中的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考验。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作家来进行民族精神进程的书写。您的创作恰恰是从新世纪以来开始的,面对剧变的社会生活,您创作的立足点或者说着眼点是什么?在创作时,有没有发生过相关的困惑?邵丽:
我想说的恰恰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边缘化,甚至是异化。我写的很多是边缘人,他们的生活处境,左面是一堵墙,右面也是,而只有一条逼仄的通道,还得偏着身子前进或者后退。多少发生一点变故,就会毁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焦虑,几乎成为他们的生活全部,无论是明惠还是马兰花、小秋,都是如此。但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您说到的民族精神,它到底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民族精神被谁拿走了?我们有相同的精神和身份认同吗?我们不信神,也没有理由相信其他,所以我们只相信眼前,相信利害。这个民族会不出问题吗?这是我的困惑,抑或是创作的动力所在。张延文:
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明惠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聪敏、美丽又要强的乡村女孩,却被同村进城从事“按摩”工作的昔日玩伴桃子轻易地击溃了自尊和自信,那么,她投奔城市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明惠最终也成为了“按摩”女郎,并被别人包养,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结尾明惠却在锦衣玉食的好日子时自杀了,这就出人意料。明惠的出走,是对乡村的背叛和逃离,古老的乡村在城市的面前丢盔弃甲,毫无抵抗能力。为什么明惠在离开乡村时,显得那么决绝和义无反顾,她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懒得再去理会?明惠的死亡,是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还是一种灵魂的救赎?邵丽:
那不过是她自以为的“尊严”。当明惠为了得到城里人身份的时候,她可以去做“鸡”。当她脱离“鸡窝”,被人包养而成为一个“贵妇人”时,即使是一句简单的玩笑话,她也承受不起。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一个人越有尊严,他(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就越脆弱。一个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可能经不起学生的一句嘲弄而沉湖自杀。一个老农被人指鼻子叫骂,只会一笑了之。这实际上说明我们所谓的“尊严”不过是面子而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严。现在,我们提城镇化,说关键是人的城镇化。人怎么城镇化?我们靠什么去“化”?如果还是就业、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区,这个“化”还是空的,没有精神填充。怎么让更多的农民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怎么打造一个让我们的后代从身体到智能可以正常发育的社会环境,才是最重要的。有一次在德国乡下,我看见一个老农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捧着一部长篇小说在读,心里满是感动和感慨。对于这样的现代化图景,我们确实要走很长的路。
张延文: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乡村社会正在趋于消亡,《城外的小秋》中的小秋,她的身世要比明惠幸运得多,她爹在城市开诊所,堂而皇之地通过经营实现了农村进入城市的理想,她还有一个宠爱她的奶奶在乡村,以及爱她的男人。小秋,作为“逆城市化进程”的代表,对于城市生活天然厌恶,甚至抵抗。她只有在乡村才能获得鲜活的生命力。同样的,还有《北去的河》里的雪雁,她从乡村到大城市,却找不到归属感,只有再回到乡村去。梁鸿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乡村的挣扎和呻吟,那么,表现类似的题材,您觉得作为小说叙事,它的优势和缺点在哪里?您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邵丽:
实际上,现代的乡愁已经变成一种比较功利的、只是为了得到安慰和解脱的一种精神图腾了。而真正倾心于乡村建设的人,又没有找到解救乡村危机的良策。在我的小说里,小秋和雪雁都回到了乡村,可是她们真的能回去吗?或者换句话说,小秋和雪雁回去之后怎么办?作为小说叙事,可以给读者留下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让我们暂时得到精神抚慰,可在现实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反城市化”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没人会真心愿意待在农村;即使回到农村,也得自设一个微观的城市:交通、通讯、朋友圈、微博和脱脂奶。我得承认,在这些问题上,我一样的有无力感,有矛盾和纠结,有憧憬和批判,也有自我麻醉。
张延文:
2008年,您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包括后来发生的社会影响力,都不亚于获奖的四部作品。您是怎么看待文学评奖的?在您的心目当中,理想的文学评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邵丽:
像鲁迅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这么大的文学奖项,在中国的评奖公正性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评出来的作品都是比较好的。如果现在再让看我的这部作品,我觉得它还是有不足,它的时代感太强,有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我站位太低,看得不够清楚,想得也不太透。所以它没获奖是我的幸事,否则我的后半生就要活在不安之中。张延文:
《我的生活质量》当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入木三分,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文本——把官员还原成了人。其中王祈隆自乡村进入城市,经过个人奋斗,再加上机缘巧合,终于成为了城市的管理者,但仍然无法摆脱作为“乡下人”的自卑感,乡村的宿命成为了一种铭心刻骨的“原罪”意识,自始至终伴随着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路遥的《人生》当中的高加林,从乡村进入城市并铩羽而归的人生轨迹,曾经引起过广泛的热议。在城市化的初期,高加林是可以幸福地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王祈隆作为中国乡土社会里“耕读传家”的“耕读文化”的受辱者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鲜明的挽歌意味,其时代象征的意义是深远而持久的。您在创作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作品会对时代文化发生什么样的影响?邵丽:
正如您所言,当时我就是想把官员还原成人,他不是类型化的人,也不是某类人。官场和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场一样,是现实文化的一部分。过去我们的官场小说,要么官员就是两袖清风六亲不认,要么就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而没有正常人。王祈隆从进到退,是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是新时代官场文化的一种变种。就他本人来说,他的经历、社会资源和文化储备,只能让他走那么远,就像一辆车一样,燃油基本快耗尽了,他走不了多远。因此您用挽歌这个词,我觉得非常恰当。张延文: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程度的深入,在文学创作当中,都市题材的作品已有超越之势。您的作品当中也有不少对于城市女性的描写,比如《迷离》中的安小卉,《寂寞的汤丹》中的汤丹,《亲爱的,好大的雪》当中的杨妮,她们作为城市女性的代表,内心动荡不安。在变动不居的城市,人是很难像在乡村一样可以将脚踏在沉实的土地上。《马兰花的等待》当中的从乡村到城市打工的中年妇女马兰花,对于城市的繁华和时尚她并不排斥,她每天都会从微薄的收入当中拿出一些来,在茶馆里安然笃定地享受两个小时的温馨时光。马兰花将勤劳朴实、善良忍耐的乡村传统美德带入城市,对于正在形成当中的中国都市文明来说,是抵制欲望化的都市的一剂良药。《明惠的圣诞》里的下岗女工,朴素、勤劳,笃定而令人肃然起敬。作为底层劳动者,她们恰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者,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真正的依托。城乡之间,不仅有冲突,还有融合,而其血脉相连之处,正是我们的民族魂。您的这种关注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生活体验好像和您个人的生活经验是比较远的吧?您是怎么去感知她们的内心世界的?邵丽:
小时候,因为父母受到政治迫害,我在乡镇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后来虽然进城了,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农业城市,而且亲戚很多还在农村,加之又下派挂职锻炼接触农民较多,所以对农村,对基层还是有相当的了解。说起来城乡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很多都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比如我原来生活的那个小城,开始的时候,上班路上还能看到玉米田,后来即使跑很远也见不到了,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可是那些社区的人,还是农村的生活习惯,把楼下的花拔掉种上菜,在阳台上养鸡,把消防栓打开冲澡。有时候想想很有意思,在这些琐碎里寻找小说资源就是接地气。张延文:
您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失落的何止是文明》当中,谈及印度文明时指出:“如果人类不能自我救赎,神能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在这个有着几十万个神祇,但却没有统一的民族意志和核心价值观的国度,失落是必然的,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这部小说虽然与全球化有关,与后殖民时代有关,与印度的民族纠纷有关,但与之更有关的是,全人类一致的人性和相似的境遇。难道我们每个人不是正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失落吗?它其实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您的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基于人类普遍命运的人性和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落在实处的。比如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就是以三代人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为经,通过家庭伦理的新变化来透视中国社会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并为我们提供鉴别和衡量的伦理尺度。您是如何在纷纭的世相里准确把握时代的脉络的?和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级的关于人类社会人性变迁的作品比较起来,您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吗?邵丽:
与印度的作家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作家缺乏真正的政治解构能力和社会担当,比如阶级意识的批判,民主意识的培植,我们往往采取大而化之的办法:要么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嘲讽,要么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关怀。我们不能“进入现场”,因为对这些问题我们既缺乏经验,也缺乏观照。其实在《我的生存质量》里,尽管对政治和社会生态多有涉及,但是也是先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多,鞭辟入里的东西少。不是不敢深入,是不能,我不具备那种能力,也没见到有几个作家具备那样的能力,所以这是中国作家共同的悲哀。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希冀通过三代人精神的成长来反映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变迁,从而达到某种和解——与社会、与父母、与孩子的真正和解。但与《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相比,不是需要改善什么地方,而是我们就没有那种“地方”——那种弥赛亚式的、具有宽博仁厚的基督情怀的和解,我们无法望其项背。我们缺乏宗教净土,而这是解决我们灵魂最终归宿的惟一办法。
二、“挂职”小说
张延文:
近期您原发于《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第四十圈》被多家刊物头条转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这会不会有点出乎您的意料?这是您的第几篇关于“挂职经历”的小说?邵丽:
这是第几篇也没统计过,我下派挂职之后,整个写作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第四十圈》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看看我们周遭的现实,可能就不会那么讶异了。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也好,安阳公交车砍杀案也好,包括最近比较密集的暴力案件,说明这个社会的暴戾之气处在一个爆发期。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纾解机制,没有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法律政策环境,那么,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齐光禄”们的刀锋,就是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张延文:1
996年12月,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并由此引发了作家挂职锻炼的热潮。但这次热潮过后,却没有出现与预期相符的关于挂职生活题材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能不能谈谈您的挂职生活以及您的挂职题材的创作?邵丽:
挂职的关键是职而不是挂,想挂在那里看个究竟,是很难写出真正的东西的,必须要沉底,与基层打成一片。即使现在,我与挂职所在的那个县的干部群众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好的故事,他们总是会兴冲冲地来找我。所以我每部作品出来,常常会看到那个县的网民的留言,说某某某就是某某某,哪个哪个事情他经历过,现在他怎么怎么样。我很开心,感同身受这种东西,既要设身处地,更要置身其中,去看,去想,去体会。张延文:
是的,这得益于您能够深入社会基层,并对当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连续而持久的反思。您的挂职题材小说,包括《刘万福案件》、《挂职三书》等,在当代文学里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挂职体”小说系列,在文体上也有创新之处。这些作品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却也不乏思想和艺术上的闪光点,您是怎么把握这类作品的社会性的善和艺术审美的微妙平衡的?邵丽:
在我挂职系列作品的热闹之中,如果认真看,是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带有根本性。像《老革命周春江》中的那些疑问,《挂职笔记》里的那些小把戏,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文化的、普适的。比如有一次,一个退下来的老领导跟我说,一个县最苦最累的是县委书记,中国最苦最累的是总书记。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话没人相信,可是事实上正如他所言。但要把这些底层智慧变成作品,是很难的,要么干巴巴,要么太水,太作。所以既要还原它的原生态,还要抱持艺术趣味,物之理、人之情。张延文:
如果有机会,您还会不会再经历一次挂职生活?您觉得生活的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对于作家来说,哪个更重要?邵丽:
当然,作为个人来说,我肯定希望再次沉下去,不过就目前的工作需要而言,再下去挂职的可能性很小。对于作家来说,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客观真实艺术化,就是艺术真实,所谓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非要把这两者作一个比较的化,我觉得把客观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客观为体,艺术为用,不能为艺术而艺术。
猜你喜欢
少年博览·小学高年级(2016年12期)2017-01-16 12:48:35
特别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
文理导航·科普童话(2015年6期)2015-07-29 16:46:21
环球时报(2012-04-16)2012-04-16 08: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