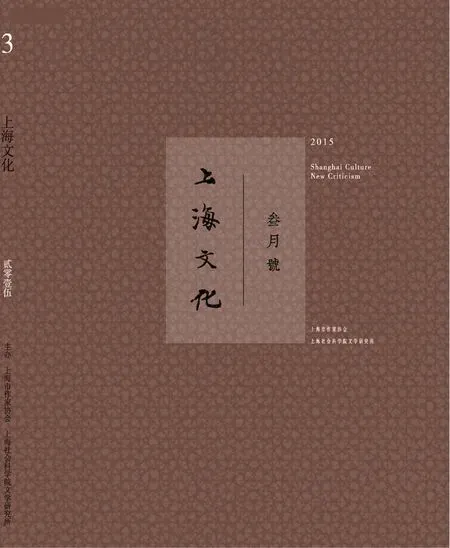嬉戏与战斗当代剧场一瞥
孙还
嬉戏与战斗当代剧场一瞥
孙还
城市即戏剧?
“戏”字从“戈”,最早是军事用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曰兵也。一说谓兵械之名也。引申之为戏,为戏谑。以兵杖可玩弄也。可相斗也。故相狎亦曰戏谑。大雅毛传曰。戏豫,逸豫也。”一说,“戏,角力也”。狩猎或打仗的操弄过程天然地与本能、力量相关联,是一种对抗。而“戏”字的逸游耍弄的意思,则是这种对抗的诙谐形式。究其根源,一是人类为了消耗过剩的生命力,二是因为我们惧怕孤独而渴望集会,于是就要制造一种更强烈的游戏、仪式或事件,哪怕这种集会是一场厮杀。
2005年前后,上海出现了许多民间剧社以及新的剧场符号运用,比如下河迷仓的创办以及组合嬲、草台班、聆舞剧团的建立等。而我本人的剧场实践和经验也恰恰始于这个时间节点。经过几年的观看、思考以及部分关于校园戏剧的实践,我依然会为它们激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犹疑和困惑。与上海话剧中心常年上演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剧或者《活性炭》这样的在春节、圣诞节、情人节搬演的应景之作相比,与可当代艺术中心《董小姐的树》、《那一年冬天很欧洲》此类不分时节针对白领制作并销售的时尚爱情剧、职场解压剧相比,与赖声川、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带着各自或原创或改编自经典的作品在各大城市巡演相比,我所说的那些新的剧场符号是边缘、另类的。它们是体制外的;它们来自民间,不是主流声音,与之相对的是专业的官办院团;它们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甚至完全拒绝盈利,反对雇佣式剧场的生产方式,站在商业路线的对岸,于是它们因此得以与收藏家、经销商、策展人所控制的微观经济体保持距离,更加与大众文化市场绝缘。它们更接近理查德·高夫所描述的“第三戏剧”:“第一戏剧是国家与地方的保留剧目,第二戏剧是已经成名的先锋派戏剧(罗伯特·威尔逊、皮娜·鲍什、铃木忠志、罗伯特·勒帕吉),而第三戏剧则关于被非法化的突发事件,关乎那些工作在边缘上的团体和个人——他们从事戏剧艺术并将之更多地视为一种生命意志,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职业;他们创造新的作品、开创新的潮流,尽管在若干年后这些作品和潮流在翻译、变异和背叛中可能都会被主流承纳和吸收。”非法的突发事件,这听上去也许略微刺激,在中国,这种具体现实其实就是演出团体没有取得文化部门的审批而直接进行表演。而眼下的文化审批通常会因为剧作中谈论了鬼魂或者意旨不够光明而取消你的演出资格,仅仅是高校学生邀请民间艺术团体进校做观众不满百人的小型演出也会遭遇禁演。
但这不是简单而粗暴地意味着,所谓的“第三戏剧”就是勇敢的或者了不起的,因为这种与体制、主流划清界限的姿态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卖点,即使他们坚持非盈利模式,这种不卖也恰恰可以成为一种卖。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尚处在咿呀学语的境地,其中不免夹杂着质地粗糙意思稚嫩却自我欣赏的存在,这些戏剧团体不是校园戏剧却带有明显的业余甚至玩票味道,不把白领当做目标客户却也只能把戏做出白领或小资的口感,聆舞剧团和测不准戏剧工作室就是佐证。
此刻,我们并不想要按照当代欧洲的剧场模版去找寻中国的当代剧场,然而事实上在去寻找和界定的时候,又无法抛弃欧洲给出的标准,比如近年来影响深远的德国学者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剧场”理论。并且,鉴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到一幅清晰的中国的当代剧场图路。在那幅我们期待的地图上占领最佳地标的往往是国立院团,在它们投下的巨大阴影下方才能看到那些最具当代精神的表演者、表演团体和空间:北京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纸老虎剧团、陶身体、上海的组合嬲、草台班、不乱扭、山东的凌云焰肢体游击队;北京的蓬蒿剧场、广州的水边吧、上海下河迷仓;吴文光、文慧、田戈兵、张献、小珂、赵川、李凝、江南藜果、臧宁贝、囡囡、Nunu、任明炀、蔡艺芸……有人用“独立戏剧”或者“边缘戏剧”指称这些人做的剧场事业,以凸显它们与主流的区别以及对抗资本、景观和消费主义的姿态,而笔者所谓的“当代剧场”在此基础上有意使其与前卫艺术发生关联,使人想到“当代艺术”,亦即强调它的临界性。这种临界或临场的诉求在于“模糊以往艺术分类中涉及现场表演的戏剧、舞蹈、行为艺术、身体艺术、偶发艺术、事件艺术、行动艺术、现场音乐、仪式表演等艺术界限,主要在于探索个人化现场表演方式之可能,是当代艺术与文化中的一种新思潮和方法”。当代剧场作品时常会推动观众发出质疑:这是戏剧?那些东西远远超出他们以往对戏剧的定义,于是也迫使他们进行自我质疑,正是这些作品慢慢变革、塑造着新观众。因此,我们早就不该继续只用“戏剧”范畴来谈论这些作品。姑且就用它们发生、上演的时间和空间来作称呼:当代剧场。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强调它们对于当下剧场艺术的革新意义。
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即戏剧。无论如何,2005年以来发生的这些新兴剧场实践都给上海剧场界注入了鲜活的能量,尽管它们品质参差不一,但依然可以作为这座城市性格的绝佳表征。它们的存在明显区别于话剧、先锋戏剧的概念,更接近雷曼的“后戏剧剧场”,即所谓脱胎于现代主义、又反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戏剧。这种戏剧形态在雷曼那里特指不再以文本和编剧为中心的戏剧,这种戏剧类型更加彻底地消除了与装置、舞蹈、媒体等其他艺术的界限。但为了避免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我们姑且还是用“当代剧场”来指称这些本土的新兴戏剧形态,以强调它们在当下上海乃至中国的前无古人。文艺复兴
时代的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画家、雕刻家)有段文字记录了16世纪早期的某个圣母升天日的游行场景,这段文字后来被芒福德用以阐释中世纪城镇的戏剧性:……我
看见盛大的游行行列从安特卫普的圣母教堂走出来。这时,全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每个人都穿上了适合自己等级的盛装,各阶层各行业都高举着自己行业的徽帜……他们当中有金匠、油工、教堂执事、刺绣工、雕刻工、细木工、粗木工、水手、游民、屠宰商、皮革商、织布工、面包商、裁缝、皮毛商,真是应有尽有。还有许多自外地来此地谋生的工匠、商人和他们的帮工,也走在行列之中……又走来了手持枪支、弓箭、弩机的猎手,以及骑兵和步兵。继而是执法官的卫队,以及披红挂金光彩夺目的精兵。而他们之前行走的是各色宗教教派和一些基金会的会员……还有一大
群寡妇也参加了游行……最后走来的是圣母教堂教士的队伍,包括全部牧师、教士、修士、司务、财务、司库等等……还有个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巨像,由二十个人抬着……游行仪
仗队里展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样样都装饰得十分华丽。一艘艘由马车改装而成的船只和其他造型,沿街巷驶过,上面还表演着化妆戏剧。随后是先知团的整齐队伍,还有《新约》中的一些场面……从头至尾,游行队伍足足从我家门前过了两个多小时。
中世纪的宗教节日非关戏剧,却使城市成为了彻底的剧场,这跟宗教仪式、节庆典礼的表演性有关。它们让各个等级、各种职业的男女聚集在城池的公共场所,当下那个唯一的欢庆主题使得平日里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等在此时此地的行为有了同一性,消除了不平等与差异,于是共同的时空中浓缩了巨大的行动力与可能性。这是日常生活无力做到的。
然而,中世纪城市的这种戏剧性,即广场节庆蕴含的特殊能量在当代上海乃至中国的戏剧圈已然变质,沦为了资本与政府力量的狂欢。对抗这两个庞然大物必须成为当下上海、中国的戏剧界之责任。1905年,陈独秀在《新小说》第2卷第2期发表了《论戏曲》,他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是普天下之大教师也。”这并不意味着剧场要以教化为首要目的,而是说它在客观上可以影响观者的所想。尤其在当下,填充静安戏剧谷这样庞大景观工程的戏码正如这工程本身一样,只是卖相诱人,但实际上每年的好戏加起来只要掰一只手的指头来算就足够。2010年上海推出首个商业戏剧奖项“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声称对飚美国托尼奖,姑且不谈其是否内定了得奖名单,就说该年度的十余部最佳戏剧的榜单上哪部戏是沪上制作?年度人物赖声川、年度最佳导演林奕华、年度大戏《恋爱的犀牛》,最佳编剧给了宁财神而不是黄维若。深刻、艺术让位于娱乐与商业,这样的获奖名单只能说明戏剧谷的评委们只会看票房数字而对戏剧毫无判断力。在主流院团被无脑人士把控的形势下,所谓的最佳名单不过是一纸儿戏。对此,当代剧场必须另有一套负隅顽抗的逻辑。它们革新观者的理念、观看积习和旧有期待,与强势的体制、资本针锋相对。尽管上海的当代剧场尝试才刚刚起步,新的剧场类型也少得可怜,但就在这样的剧场之中你已经闻得见火药味,剧场角落里散落着新旧剧场概念交战的残损弹片,很多时候这种战斗以游戏的形式出现,剧场工作者们则以嬉戏的姿态作战。
谁的节日
2012年赖声川一个电话,乌镇平地起了一座世界级的剧场,占地五万四千多平米,耗资四亿人民币。
戏剧节创始人的初衷听上去是再美好不过的——让青年戏剧人崭露头角,并邀国内外戏剧大师驻场,举办一场戏剧嘉年华——没错,十二部青年戏剧人的作品在乌镇进行了竞演,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一百二十多个艺术团体带来了五百余个街头演出。然而前去参加这场嘉年华的观众最好荷包充实,因为大师们的重头戏一律沉甸甸:尤金·芭芭的《鲸鱼骨骸内》票价分为人民币四百八十元与九百八十元两档(无学生票);罗伯特·布鲁斯汀《最后的遗嘱》票价四百八十元、五百八十元(无学生票);黄哲伦《铁轨之舞》为五百八十元与六百八十元(无学生票);赖声川《如梦之梦》分上下两场,每场从一百八十元到两千零十三元分九档(无学生票);田沁鑫《四世同堂》从二百八十元到八百八十元分四档(学生票五十元);孟京辉《空中花园杀人案》从一百八十元到四百八十元分四档(学生票五十元)。其中,仅中国大陆的两部作品考虑将尚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年轻人纳入观众群,其他四部的票价一律使人望而却步,其中赖声川的《如梦之梦》在已于大陆巡演捞金结束的情况下,在乌镇戏剧节依然丝毫没有降低票价的意思,而是设置了最高两千零十三元每场(整部戏分上下两场)的售票规格,使人只觉不堪。讽刺的是,有报道称乌镇的态度是“坚持民间、非营利的方式”,这种界定使人哭笑不得。当然,观众可以知趣地去看街头展演。虽然这质量参差不齐的五百个街头表演是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的移植,但恰恰是它们为乌镇制造了狂欢节日的氛围。这些表演大多是共时进行,观众只能选择一二,其余则走马观花。较之高价位的国际邀请作品,它们才是真正向大众开放的,前者只是属于富人们的消遣。可是又有几个观众是为了观看一两场他们无法拿捏水准的街头表演而奔赴乌镇的呢。这实在只是一次民间戏剧圈内的自我娱乐,至于观众,如果想领略这场戏剧嘉年华的话,你必须有钱。因为这是一次戏剧界的奢侈品展演,这是一个伪节日,因为整个事件运行的是资本的逻辑,剧场艺术家、戏剧爱好者以及观众在其中沦为了道具和棋子,一律是市场的附庸——就连格洛托夫斯基的弟子尤金·芭芭也无法例外。
在中世纪,“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显然,乌镇戏剧节绝不是嘉年华,而是一个等级明显的空间区位。主流作品掌握霸权,它们用高价将大众隔离在大剧场之外。在这层消费和文化霸权的密实围栏之外,才允许其余人进行娱乐。国际邀请剧目展演正如王尔德笔下那个巨人的花园,美丽却封闭,笼罩着艺术和阶级特权的严肃、冰冷和死气沉沉。它拒绝与大众共享,它的存在使得乌镇戏剧节更接近官方节日,因为只有在官方节日中,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差别才会被突出地显示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狂欢的街头表演空间,也是要收费的,也就是乌镇西栅的景区门票钱。我们该为此向“乌镇模式”的建造者致谢,因为他们到底没有为了这些街头作品向旅行者、看戏人将门票也抬至天价。
关于节庆空间,小石新八和牧野良三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它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中,通过消耗和派遣日益积聚起来的物质财富和心理压力,将被压抑着的人的本能愿望予以舒解释放出来的……而人类最初的这一本能欲念则是由对生命、对自然界的一种畏惧心理所产生的。”节日空间中的仪式、游行原本就弥散着戏剧性,而戏剧节则是节日的节日,它是戏剧性自身的叠加与强化,彻底完成了由日常世界向非日常世界的空间转换。现代都市中消费主义横行,买卖是最日常不过的行为之一,戏剧节或其他节日当然可以、也不免借助商业运作,但倘若资本支配了节日,那么所有的节日都将一律是货币的狂欢,无法像中世纪的狂欢节那样帮助人们完成身份、空间的转换、跳脱和颠覆。现代人明明只剩下大把花钱的欲求,还有什么本能需要去释放——既然资本已经反身为它,那么消费也就取代节日成为城市人最惯常的娱乐方式,可以说,消费和拜物就是都市人类的共同宗教。既然节日内外都深陷在同样的消费主义话语之中,我们还需要一个以刺激消费、带动地方旅游产业为目的的乌镇戏剧节做什么?
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指出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尤其以诙谐类为主)在中世纪人们的生活里占据着巨大位置。愚人节、驴节、复活节游戏、教堂命名节以及各种农事节,人们在这些节日里讽拟严肃庆典、上演宗教神秘剧、设立集市并让巨人、侏儒、残疾人和“学会特别技能的”野兽参加表演,它们“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⑾。巴赫金的“第二个世界与第二种生活”其实就是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之前的中世纪异托邦,既在真实与想象之外,却又兼容二者的差异空间。巴赫金固然无法预期21世纪强势的消费主义能够无孔不入,它使得人们被催眠似的带着这些镀金的枷锁一面游行,一面沉浸在意淫自由的祝祷中。强势的资本和体制意识形态却依旧是现代人与中世纪人们同样需要对抗的,几个世纪过去了,节日仍然要带领人们去反抗这些庸常却强大的压迫。
同样是戏剧节,逡巡在主流与边缘之间的校园戏剧节是怎样的?它的主体是谁、作为一个项目它是如何运作的?受地域空间及人文氛围的影响,上海的校园戏剧是温和的。它与主流剧场互动较多,故而也夹在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抗拒之中,但即便是抗拒,也是发生在招安之下,被主流默许的。
2001年,北京有了第一届大学生戏剧节;2004年,上海的一群校园戏剧爱好者在上海话剧中心的协助与支持下也行动起来,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由此创办。两个戏剧节的参与对象都是非艺术类高校的戏剧社团,没有门槛限制,学生自己组建的剧社与校立艺术团具有同样的参赛资格。在极度匮乏戏剧教育的当下中国,这两桩事件对于爱好戏剧艺术的高校学生实为福音。在美国,“由小学和中学开始,每个学校都有剧场,没有学校不演戏。跟音乐、美术一样,剧场是美国教育的基础成分”。当然,谢克纳强调,戏剧在中小学只是业余的课外活动,几乎不会像高校那样开设主课、正课;而全美的一千五百余所高校,大部分都设有戏剧、舞蹈学系,在这一千五百个剧场中,有一百五十个宣称提供专业训练,其余只进行宽泛的戏剧人文教育。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北京只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影,上海只有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专业被上述艺术类高校所垄断并负责制造、输出专业人员或明星。除此以外鲜有综合型大学像南京大学那样开设系统的戏剧教育,一个普通的综合型大学中最多只有开设戏剧史或者戏剧作品赏析之类的通识课,甚至连剧场都没有。这是中国不重视美育的症候之一,它结出的恶果种种譬如上述艺校的高学费门槛以及潜规则、戏剧艺术流派的极度单一、戏剧人才的模板化、优秀戏剧作品的极度稀缺等等。在这样的境况下,难道你还要说欧美可以大张旗鼓地开办戏剧教育,但是中国不需要吗?
这里要提到新近办起来的“中国校园戏剧节”,这个“目前唯一由国家设立的校园戏剧最高奖”的参赛剧目需要由校方或各省市教育部选送,并不允许校园剧社直接自行报名参与。这种运作机制意味着轮番的文化审查,不可避免地产出大量的主旋律产品。再者,这也造成了各校方团委为了获得声誉而比拚财力的局面,大大损毁了校园戏剧的质朴精神和创造力,例如第三届赛事(2012年度),沪上两所知名高校在各自参赛的剧目上的保守投入分别是二十万和四十万,其中一所高校剧社的仓促制作体现为编导在没有创作想法的情况下,抽取了自己过去几部作品的片段拼接出新作,大量的精力财力铺在了租借专业灯光等舞美设备的事项上。相形之下,大戏节与大话节每部剧目只需几千到上万元的制作成本。这不是说校园戏剧不需要金钱支持,而是要警惕它被金钱、行政目的或其他势力架空。但就是在这种无限的折衷主义里,上海的校园戏剧似乎总是缺乏有力量的精彩之作。
在没有科班训练、成员至少四年一洗牌、制作成本低廉的情况下,校园戏剧在整体水准上绝无可能与“正规军”比肩。以我所在的剧社为例,该社如多数学生社团一样,每年面向全校招收新社员,新社员多为大一新生。针对新人,我们开设由老成员组织的基础表演训练,而这种工作坊的举办次数实则非常有限,只能起到一种广而告之和基础体验的效用。好在新成员进入剧社时正赶上年度大戏的上演,他们有机会直接参与进来,以亲身的演职实践接触剧场。我们的剧社设有短剧节、年度大戏、毕业大戏、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参赛剧目四个核心运作项目。大话节以外的三个演出季,我们用卖票所得以及招收会员所得的会费作支出,若不足以支出,则需剧组人员自行支付。校园戏剧获得资金的方式无非几种:招募会员收取费用、公演售票、校方支持、拉赞助、剧社人员自行拼凑。具体到笔者所在学校,校内剧场并不对学生社团免费,也就是需要剧社自行支付每次演出的场地租借费用。鉴于社团经费匮乏并且剧社的售票行为又被场地租借方因故禁止,我们只好进行私下售票以“补贴家用”。在高校里,学生社团拉赞助需要走的行政程序更是异常繁琐,故一般不作考虑。与其费尽周折筹钱,不如把精力用于写好剧本、在低成本的运作下尽量呈现出有想法的作品。毕竟,校园戏剧并不在于比拼大型制作,而在于展示青年人的大胆创新。所幸,我们剧社每年参与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的剧目费用是由学校团委报销的,近几年每部戏的报销经费平均在一万元左右。而团委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倘若没有成绩,就无钱可拿。因此,大话节拿了奖,剧社成员们在兴奋过后必须自我质疑:我们是在做戏剧还是仅仅止步于一种对它的意淫或玩票。我们所谓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还是不过在被团委招安后为其完成了一个行政任务?是的,即便是我们这样的非校立社团,仍然被牢牢规约着。这不只针对与团委的合作关系,也针对大话节赛事的组织团队: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联。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一场主流赛事。虽然我们的剧目不需要经过校方审查,赛事的评委会也并非直接由体制把控,而是由话剧中心的演员组成,但参赛剧目的题材和意涵的限制在所有制作人心中不言自明的。即反思之后,剧社骨干们能做出的改变仍是有限的。因为如果你想让团队参与最终环节,那么就必须接受这个高考作文式的现实:收敛一点,不要过火。否则不如直接跟主流剧场资源一刀两断。显然,大学生戏剧节绝非乌托邦,在“青春”和“理想”这种字眼的掩护后,校园戏剧实际上是对主流文化亦步亦趋的。
相较大话节而言,笔者所在剧社的另外三个演出季反倒更具备节日的精神内核。刨除了与主流院团靠拢的心态,作品题材、思想寄托以及排演的运作方式,更大程度上把控在学生自己手里。但即便如此,上海的校园戏剧至今仍局限于话剧的门类中,与正在崛起的当代剧场十分隔阂。多数剧社仍将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奉为表演圣经,而对最新的表演学知识和剧场概念少有借鉴。这甚至也是体制内戏剧院校的现状之一,表演系的学生一边巴望着自己是明日的荧幕明星一边忙着演电视剧,戏文系的忙着四处接活给文化公司写电视剧,导演系的忙着拍电影,连老师也不例外。舞台剧乏人问津,没有多少人想知道什么是当代剧场。
人的共在与相互对话是剧场与节日的共同内核,时间因此驻足。资本与体制力量联手占领了节日,剥夺了人的在场,销毁了剧场作为公共空间的诸多可能性。奥古斯都·波瓦说,戏剧是革命的预演。节日被侵略了,我们可以尝试更多样式的剧场实践以重新夺回我们自己的节日,或者干脆创造新的。民间可以对抗臃肿而死气沉沉的体制剧场,甚至可以松动资本盘亘于剧场中的畸形爪牙,将庞大景观的牢笼捅开哪怕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于是,节日的嬉戏也可以成为一种战斗。
人的共在与相互对话是剧场与节日的共同内核,时间因此驻足
❶《国语·晋语》有言:“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友,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韦昭注:“戏,角力也。”
❷下河迷仓,由民间文化人士王景国出资建立的独立剧场,位于上海龙漕路。常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团体的排练、演出,甚至住宿,免费提供场地。创办于2004年,停业于2013年冬。
❸组合嬲,2005年成立,是以舞者为主,联合当代艺术领域的视听艺术家、新媒体艺术家等其他实验艺术家共同组成的艺术团体。主要作品有《舌头对家园的记忆》(2005)、《十四号病房》(2006)、《左脸》(2007)、《几号病房》(2008)、《陪我过夜》(2009)、《红楼梦》(2010)、《病房·清明》、《集体舞》(2011)、《无声合唱》(2011)。此外,也涉及偶发实践与社会剧场实践。
❹草台班代表作品有《鲁迅2008》、《狂人日记》、《共和笔记》、《小社会》系列、《不安的石头》等。
❺聆舞,由上海青年戏剧人任明炀、蔡艺芸于2005年建立的话剧团体,作品具实验风格,作品有《暗房》、《昨夜的双拥路》等。
❻《去中心:观照当代世界戏剧潮流的一个视角与九个框架》,【英】理查德·高夫,《穿越前沿(外国戏剧卷)》,上海百家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43页。
❼《台湾行为艺术档案1978-2004》,姚瑞中,远流出版社,第252页。
❽《城市文化》,【美】刘易斯·芒福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71页。
❾《巴赫金全集》第六卷,【苏】巴赫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1页。
(10)引自《现代都市空间结构中的戏剧性要素》,【日】小石新八、牧野良三,《戏剧艺术》1995年第3期。
(11)《巴赫金全集》第六卷,【苏】巴赫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6页。
(12)已更名为“中国大学生戏剧节”,面向全国高校征集剧目。
(13)北京大学生戏剧节简称“大戏节”,面向全国非戏剧专业高校;上海大学生话剧节简称“大话节”,参赛对象仅限上海地区的非戏剧专业高校剧社。
(14)引自《当代美国剧场发展与表演研究》,【美】理查德·谢克纳,《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5)赛区设在上海,但面向全国征集剧目,有专业组与业余组。
(16)扬之水中文话剧社,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社团,由该校学生自发组建于1999年9月,以搬演自己的原创剧目为特色。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飞那儿剧社、同济大学的东篱剧社并称上海高校剧社的三驾马车。该剧社由于校区的分立,设有两个,配有各自的行政人员和参演人员。由于校区相隔甚远,两个剧社的交流仅限于演出季的演出交流。作者所在的剧社隶属于闵行校区,参与时间七年余,任演员、编导。
(17)每年冬天举行,届时会有八部左右的短剧联合演出(两个剧社分别在中北校区、闵行校区各演一晚),这些剧目或原创、或演绎改编经典以及最新发表的戏作,每部戏时长半小时左右。闵行校区剧社一般以此作为培养新人之用。
(18)年度大戏、毕业大戏都是排演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剧目,或原创或演绎经典;其中,毕业大戏的演职人员一般多为要在当年毕业的学生,这几乎是他们告别校园生活的仪式,尤以演后谈的氛围都较为激动。
(19)参赛剧本多为原创,从建组、排练、校内公演直到并在上海市话剧中心公演参赛,为期两月余。该赛事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共青团上海团市委联合主办。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