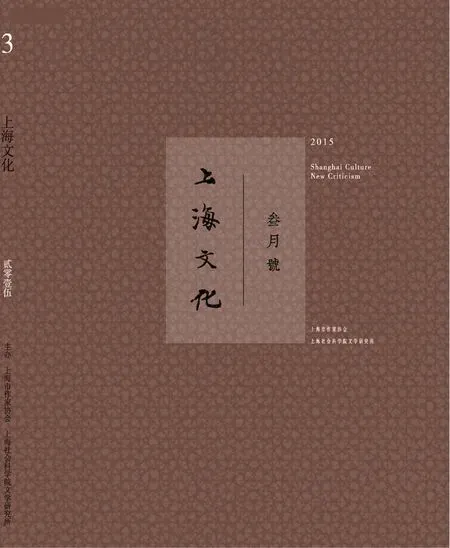观看生活世界的四种方式周嘉宁,阿丁,于一爽,徐则臣
张定浩
观看生活世界的四种方式周嘉宁,阿丁,于一爽,徐则臣
张定浩
周嘉宁
周嘉宁乐意呈现生活中令她困惑的一面。在对话和场景描写的简练隐忍上,她受益于海明威良多,同时,她也习惯于将场景安置在一个个相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的异质空间,如酒吧、度假地、路过的陌生城市、车上,等等。她有一篇小说叫做《荒岛》,虽然里面只是居家度日,却隐约也牵连到《丧钟为谁而鸣》的题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她笔下的人物,也每每处于某种危机(通常是感情危机)之中,需要借助一个异质空间或岛屿般的他人,在绝望的停滞中呈现这种危机,在呈现中暂时摆脱它们,“轻轻喘出一口气”。
周嘉宁常常会表达对于小说书写中男性力量的羡慕,但在同时代那么多男性小说家散发的自恋和自负的空气中,不断地自我怀疑又是她弥足珍贵的品质。她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小说,但其中大多数她都不愿意提及,在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以下简称《生活》)封面勒口的介绍文字中,已出版作品一栏是这样的:“长篇小说《荒芜城》等,短篇小说《杜撰记》等”,很多旧作就被这么“等”掉,这是周嘉宁的清醒和强悍。
《杜撰记》与《生活》,相隔十余年,却依旧可以看出隐秘的联系,甚至还有相同的人物。比如小五,这个在《杜撰记》中出现过的少年,也出现在《生活》的第一个短篇《爱情》里。此刻,他已是一个成年人,开车送她回故乡,像一个隐喻,那些青春记忆,那些“明明有过的永不消退的爱”,护送她踏入“生活伟大的乌云”,然后绝口不提。
更为重要的联系,是两部小说中相似的对于世界的观看方式。在这种观看方式中,世界就是某一个主要人物眼中的世界。小说不仅建立在这一个主要人物的视点之上,这个主要人物未必就可以武断地认定为作者本人,不能武断地认为作者就一直是在书写自己,但是,在其书写的时时刻刻,作者的确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移情为作品中的“这一个”人物的。也许在这一篇中这个人物叫做“菲菲”,在另一篇中叫做“她”,在更多的短篇中叫做“我”。不管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都不太有影响,重点在于作者和这个人物之间没有一个叙事者作为隔断,也就没有了一种保持间离和反思的空间。换句话说,因为作者的关系,这个人物,不可避免地高于并凌驾于其他人物之上。作为比较,我们可以在这种观看方式中看到日本私小说传统的千丝万缕的影响。
但是,别忘了写作《生活》时的周嘉宁,已经是一位沉醉和浸淫在海明威、耶茨、托宾、弗兰纳里·奥康纳等英语短篇大家气息中的成熟读者。和《杜撰记》相比,《生活》不再耽溺于一些个人的情绪,也不再迷恋于一些绵密华美的表达。诸如词语的简练,情绪的准确,场景描写的控制力,良好的节奏感,以及更为严苛冷静的自我审视,这些在《生活》中令人赞叹并足以将同时代大多数期刊写作者甩在身后的品质,可以说都受益于她近年来所热爱的英美短篇作家。
“我不知道别人的喜怒哀乐,其实我曾经为此异常难过。”这是《寂静岭》中的一句话。这部讲述几个女孩子之间同性情感的短篇,没有被收入《生活》之中,据说是因为作者不再喜欢。我猜测这种不喜欢主要是风格上的,相对于《生活》中的小说,《寂静岭》琐碎的温情大概是现在的周嘉宁所不能忍受的。但《寂静岭》中的这句话,依旧可以当成一个理解周嘉宁小说的窗口,理解她对于自我的专注和近乎冷酷的诚实,理解她对于自身局限的认知,和认知之后的努力,理解她在日式私小说和现代英美小说之间的逡巡,以及,理解她所喜欢的故事类型——
在这种观看方式中,世界就是某一个主要人物眼中的世界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在海明威的这部短篇中,源自个人的孤独体验和来自他人的日常言词相互打磨,并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在某个瞬间被来自高处的强光洞彻,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我相信,这也是周嘉宁在短篇小说中曾致力追求的美学。它必然是动人的。在为自己的短篇集撰写的序言中,海明威提到其中寥寥的几篇是为自己所深爱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是其中之一,但他还提到一篇《世上的光》,它在《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中紧随《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之后,讲述的不是某个典雅自重的孤独者,而是一群孩童、妓女和流民。于“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之外,还有在嘈杂纷乱中隐现的“世上的光”。从《生活》的最后一个短篇也是首次发表的《生日快乐》中,我竟然隐约也感受到一点周嘉宁在这个方向上的变化。
“但是生活最伟大。”周嘉宁大概会愿意把这句话作为《生活》的题词,因此能够毁掉的,不是生活,而仅仅是过去的自我对于生活的某些认识。倘若这样,不断地毁坏,也就是不断地新生。
阿丁
就像医生总是习惯于透过形形色色的人身去审视正在病变的器官,阿丁对人性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人的兴趣
我是在旅途中看完《胎心、异物及其他》的。合上书的时候,飞机正平稳行驶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气流层中,它的上方,湛蓝天宇被一缕缕卷积云拉住,金色的辉光映照其间,向下看,是浓稠翻滚漫无边际的雨云。我回想阅读几部阿丁小说的整体感受,就有点像在这样一个既暧昧又透明的夹缝中穿行。
早在《无尾狗》中,阿丁就展现了其统驭纷繁经验的叙事能量,以及感受和捕捉各种芜杂且易飘逝的人类声音的能力。但在随后出版的短篇集《寻欢者不知所终》里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迷恋于种种现代小说标签上印有的技巧实验,于是,一个热爱青年塞林格、对现实生活的粗糙和丰满具备相当感受力的饶舌者,企图摇身成为博尔赫斯式的投身于幻景的智者。
在一篇写作自述中,他讲道:“我喜欢把自己凭空捏造的人置于某种境地,然后任由他们行走、生活与争吵,甚至死亡……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而我像顽童注视蚂蚁那样端详他们,兴奋又忐忑地,等着发生些不可思议的事,那是任何一个职业撒谎者都无法预知的结局。这几乎构成了莫大的惊喜。但也有惊恐在内。写作者会因此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不可揣测的人性将在最初的设置之后如画卷般展开。这也是我写作之前绝不会打个什么提纲的原因。造物之手在创世的前夜,脑子里不会有万物具体的形象,才有这个世界的纷繁绚丽。写作也并不例外。”
对照其大多数小说,这段话可以视为诚实且重要的交代。阿丁虽然自比职业撒谎者,但在小说之外,他似乎一直以一副不屑撒谎的姿态示人。让人物自己行动,变化,这的确也是现代小说的基本伦理,毫无问题。但与此同时,这段自述也帮助我了解到,为什么在阅读阿丁小说过程中时常会泛起某种不快之感。
我有一种感觉,就像医生总是习惯于透过形形色色的人身去审视正在病变的器官,阿丁对人性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人的兴趣。为了让“不可揣测的人性如画卷般展开”,他每每把笔下的人物置于X射线之下,或是福尔马林溶液中,在这种试验室般的人造境地内,我们能看到一些被贴上各种“人性”标签的活物,却看不到活生生的人。这些活物的确也行走、生活与争吵,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作者“像顽童注视蚂蚁那样端详他们”。这句话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小说里的活物在我看来都如同虫豸一般面目模糊。在关于《胎心、异物及其他》的自述中,他谈及记忆之矿被挖空之后,“有胡思乱想和好奇心这两件利器,就不愁没的写”,但在他的全部小说中,大凡和记忆之矿无关,单凭想象力、好奇心而编造出的那些部分,基本上都是糟糕的。这种糟糕,倒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想象力和好奇心的问题,而是说,在阿丁这里,他仅仅满足于某种“顽童注视蚂蚁”式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对于他企图描写的那些人,他习惯于要享受一种俯视的姿态,为了速效地达到这个目的,他选择先将那些人勉强缩小为虫豸,而不是让自己缓缓长成为强有力的智者。
阿丁曾多次满怀感激地谈到舍伍德·安德森和理查德·耶茨,但在安德森和耶茨的每一部小说中,那些畸人和孤独者都裹挟着一个真实鲜活的世界而来,他们再怎么不堪潦倒,颓废凄狂,依旧是这个具体世界中的人,说着这个具体世界中的属人的语言,他们不是试验室中的活物,更非虫豸。而作为写作者的安德森和耶茨,也从来不曾凌驾于他们之上,而是就在他们中间。
在某个短篇中,阿丁借“我”之口,半真半假地讲述了某种有趣的文学观,“文学在我看来就是一群梦呓者在癫狂状态下的胡编乱造,至今还持此观点。我的导师与我观点一致,乔曾经对我说,随便拿点儿什么化学药物,调整下配伍和剂量,把这种药让第九大道的随便哪个不识字的乞丐服下,第二天给他一台打字机他就能写出一部《安娜·卡列尼娜》”。
或许,如今身为《果仁》主编的阿丁,也已然找到了这样的药方。但我更期待这药方偶然失效的时刻,比如在《胎心、异物及其他》里有一篇《魂斗罗》,讲两个少年的友情,和成人世界的对抗,以及懵懂的男女之情,在生猛中有一种清澈和明净,当然,它的动人依旧和所谓的“记忆之矿”有关。只不过,倘若我们不把记忆仅仅视作一座提供素材的矿产,而是将之与那位诞下缪斯的古老女神相联系,那么,她就是取之无尽的。
有些东西并非人性的弱点,而就是人性本身
于一爽
“我喜欢她小说里一种轻的东西。”在于一爽的小说里,那个名字总是叫做余虹的女主人公在欢爱之余偶尔也会谈论起文学。
“松弛。”那个名字总是叫做刘明的男主人公准确地回应道。
我相信每个认真的小说书写者对于小说这门技艺都各自有其深切的认识,他们之间最终不可调和的区别仅仅在于,写作是为了取悦他人抑或取悦自己,换言之,是依赖一些小聪明和花招,还是竭尽可能地忠实于自身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问题或许在于,小说家过分聪明而评论家过分不聪明。很多时候,那些聪明的小说家都太清楚评论家想要什么,虽然未必清楚自己最终想要什么。
于一爽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说一种松弛的语调和气息。当然有时候某种松弛也会成就另外一种造作,这种造作在年轻一代男性小说家的笔下屡见不鲜,他们习惯于把叙事者首先设置成一个男性废物,却是有可能被女人莫名其妙垂青的废物,从而以一种反智主义的姿态来轻松赢得自己的魅力。所幸于一爽与此相去甚远。她的小说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失败者的群像,但这种失败不是为了让叙事者获得某种类似无产者般的道德优势,相反,她是严肃的,对这些失败者痛彻心扉,但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他们。
在于一爽这里,松弛首先意味着一种情感上的不作伪。那种被性欲奴役之后作自责呕吐状的政治正确,不属于于一爽,因为她相信,在庸常男女之间自愿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珍视和怜悯的,在这一点上,女作家似乎要比男作家勇敢,而于一爽更是其中较为勇敢的一员。她明白有些东西并非人性的弱点,而就是人性本身。她时常会超越性别的视角去静静地审视这一切,或是从他人的视角返观自我,她乐意呈现某种真实,言谈的真实、人类关系的真实乃至性事的真实,在生活之流中呈现。这需要天赋和反复的练习打磨。最终,松弛将走向准确,就像卖油翁将油准确地沥入狭窄的钱孔,而准确才是每一门技艺基本的道德。
迄今为止,于一爽写的都是短篇小说,其中都是同一种人,同一种状态,虽然他们分身为男人和女人。有时我在想,也许她把这些短篇中的素材融合成一部长篇小说,效果会更好一些,至少,她不用让她的主人公们一再地以某一方草草死去收场,在长篇小说中,他们只需要死去一次。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倘若要满足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她就势必要去编织或想象更复杂多变的情节,而由此势必招致的某种虚假,或许又是她很不愿意看到的。有时候,阅读她的小说的感觉有点像观看旋转木马,那些成年的男女以一种不太得体的方式坐在旋转木马上,不停地绕着一个很小的圆圈飞驰,这场景起初是有些荒谬的,但又是令人感伤的,她不知道拿这些荒谬和感伤该怎么办,也许她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很容易放弃的人,但这种放弃里面有一种极度真实的东西在。爱,对他们而言,既不是某种意义的开端也不是结尾,就像那些木马无所谓起点终点。他们如《玩具》中的叙事者王羞所言,“无法控制事情发展的不完整”,但这种不完整中有一种极度真实的东西在。小说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忠诚于这种真实。
《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是于一爽另外一个短篇的名字。死亡发生在一切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可以视作一种小说家的洞见。有一个古老的猜测,革命后的第二天会怎么样?与之类似,于一爽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像在描写死亡后的第二天。那些衰弱和赤裸的魂灵还没有渡过卡戎掌管的冥河,还在河的这一边徘徊,他们不怀抱任何希望,却也没有剩下什么还值得绝望的。
接下来她要做的,或许就是要带他们渡过河流,给予他们新的烈火,以及新的生命。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假如她真的懂得“现代主义者永远不能与过去分手”(《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自序),那么她就应当试图去找回那些人的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她或许应当成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唯有如此,在河的对岸,地狱的某一层,那些人才会忽然自己开口,说话。
徐则臣
“无法控制事情发展的不完整”,但这种不完整中有一种极度真实的东西在。小说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忠诚于这种真实
徐则臣是一位非常成熟和有学养的小说家,在对于现代小说这门技艺的认识上,他完全不输于同时代大多数的批评家。他热爱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他为其小说《所有的名字》中译本所写的文章,可以让很多书评写作者乃至文学批评家汗颜。“我一直有种感觉,萨拉马戈的写作通常有个‘两步走’:第一步,大胆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假想;第二步,小心求证……这是萨拉马戈的写作方式,他列出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接着逐一解决。这个思维缜密的大脑,写小说如同做论文。”如所有好的文论一样,徐则臣在这里对于萨拉马戈小说技艺的谈论,最终也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谈论那个正在写小说的自己。
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如今已经在评论界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我相信大多数论者针对这本小说做出的判断和褒扬,其实都在小说家徐则臣的意料之内,就像一个写论文的严谨学者应该知道自己论文即将产生的影响。
因此,我想从另外一个似乎更为感性的维度,谈一谈自己从这部长篇中了解到的、徐则臣作为一个小说家观看世界的方式,它们可以被粗率地转化成三个比喻。
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他们在穿越一层层的泪水抵达洋葱中央之际,其实遭遇到的也不会再是虚无,而会是一个更好的自己
在《耶路撒冷》中,夹杂有一个由主人公初平阳写作的系列“专栏”,谈论70后一代人的各种问题。有论者认为,这个专栏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专栏形式,为小说带来的某种开放性和溢出感。我对这种粗暴的思维方式稍有怀疑。一个戴墨镜的人,未必一定是黑社会,也许只是眼睛怕光的普通人。而针对这个戴墨镜者的有价值谈论,是关于这幅墨镜和这个人的具体关系,而非单纯的人要不要戴墨镜的问题,更不是抽象的所谓墨镜哲学。在专栏和这部小说的具体关系中,我觉得,似乎和小说意旨贴得太急太紧,这明显是对读者的一种不信任,反倒挤压了小说原本可能具有的美学空间。举个最轻度的例子,在这些专栏中,有一篇《夜归》,写一家三口大雪天回故乡,本身是不错的短篇小说,但其中有一句对话,发生在父子之间,在车子在乡间小路上抛锚之后,父亲对儿子说:“出来,看看你爹生活过的大自然。”这一句日常谈话中有一个触目的概念语汇——“大自然”,暴露出作者对于表达意旨的急切,也让这个短篇从正缓缓达致的高度陡然滑落。
徐则臣很注重一部小说中的时代感,《耶路撒冷》在这方面也极为用力。读完全书,时代感也一定会是最为强烈的印象。但是,时代感和时代还不太一样,就像津津乐道的记忆不同于难以言说的回忆。如果说,可以把时代比作长河中的一段,那么时代感就如同用渔网打捞到的漂浮物和各种残骸。或许,小说家的使命,不是在岸边观看乃至展示各种用力网住的漂浮物与残骸,并以此作为时代的标记或时间的简史,而是有力量将那些过往行人召唤至长河之中,让那些无法网住的流水,再次穿过他们的身体。
“被一条叫做意义的狗追赶”,这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初平阳的焦虑,也是徐则臣在诸多访谈中表达的焦虑。生活何为?小说何为?对此的思考和探索当然是写作者最为重要的行为。然而,生活的意义乃至小说的意义,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在不同写作者那里又各有不同。我比较服膺罗兰·巴特曾使用过的一个类比,即洋葱与桃杏。有些人觉得生活应该是像桃杏那样的水果,在果肉内部一定有某种坚定存在且让人心安的核心,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找到这样的核心,甚至不惜代价建构一个这样的核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生活是如洋葱般一层层展开的生活,“没有心,没有核,没有秘密,没有约简的原理,有的只是本身外壳的无限性,包裹的无非它外表的统一性”。我是站在洋葱这边的人。在我想来,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他们在穿越一层层的泪水抵达洋葱中央之际,其实遭遇到的也不会再是虚无,而会是一个更好的自己。
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