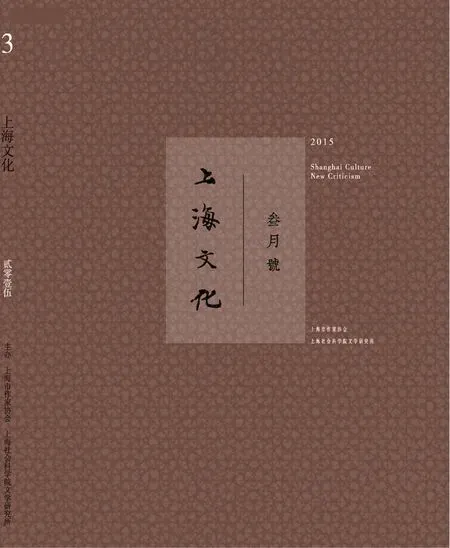海黑了又蓝蓝了又黑台湾女诗人陈育虹的诗
王家新
海黑了又蓝蓝了又黑台湾女诗人陈育虹的诗
王家新
诗歌是语言的希望
——荷尔德林
她留着台湾知识女性中常见的那种偏向一边的短发型,身着淡蓝色薄开领毛衣,披着一条轻柔的白色黑条纱巾——令人想起她常写到的“带着天堂香气”的栀子花。但是她很安静。无论是开会,还是在餐桌边,都带着一种天生的沉静。她的名字叫陈育虹。
我们相逢在花莲太平洋诗歌节上。她的朗诵专场我去晚了,去时她正在读她的最后一首诗《再见——给蓝猫》:“这棵山樱以后就是你的/春天为你开花结子……”她的眼圈开始泛红。我顿时想起我们家的那只白色小仓鼠,在它死后,十岁的儿子去花园里悲伤地埋葬它的情景……
她住在台北市郊的山坡上。那棵不断开花和凋谢的山樱。
一位优异的女诗人。祖籍广东,生于台湾高雄,文藻外语学院毕业,旅居温哥华十数年后又回到台北定居。在她的日记体作品《365°斜角》(尔雅丛书,2010)中,我读到她引证的作家塞林格的这句话:“我生于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
一个诗人应是一种独异的精神和语言的存在。她/他应该从众人中一眼就可以辨出。她/他的东西哪怕我们只看上一眼,也会感到某种特有的气息或力量。从台北坐大巴到机场的路上以及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埋头读着诗人送我的诗选集《之间》(洪范文学丛书,2011),整个被吸引住了:
我告诉过你我的额头我的发想你
因为云在天上相互梳理我的颈我的耳垂想你
因为悬桥巷草桥弄的闲愁因为巴赫无伴奏静静滑进外城河
诗歌的到来,总在一种无以名之的更新里
我的眼睛流浪的眼睛想你因为梧桐上的麻雀都飘落因为风的碎玻璃
因为日子与日子的墙我告诉你我渴睡的毛细孔想你
我的肋骨想你我月晕的双臂变成紫藤开满唐朝的花也在想你
我一定告诉过你我的唇因为一杯烫嘴的咖啡我的指尖因为走马灯的
夜的困惑因为铺着青羊绒的天空的舍不得
——《我告诉过你》
我还从没有读过这样的“情诗”。但它对我的意义却不在于其“缠绵”或“多情”,而在于对“情诗”本身的语言刷新。像“因为云在天上相互梳理我的颈我的耳垂想你”“因为日子与日子的墙我告诉你我渴睡的毛细孔想你”这类动人的诗句,我甚至不想说这是诗人在抒情。这是语言感官的醒来。而在走马灯似的意象和节奏运行中,最后那一声“铺着青羊绒的天空的舍不得”也很耐人体味,它像一声轻拨至空中的高音,不仅与前一节落下的“风的碎玻璃”形成抑扬对照,也恰好给人以某种“险韵诗成”之感。
这样的诗让我欣悦。这样的诗真有说不清的魅力。它不仅有一种人们所说的“灵魂的情色”,也让我听到了一种新的“诗的发声”。进一步说,它不仅和大陆的诗不大一样,和我读过的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也有明显的差异。我知道这些年来台湾诗坛弥漫着一种“后现代”风气,在育虹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类语言实验,但是她的探索并没有流于形式,而是带来了一种新感性,新声音。她以自己的语言方式重新定义了诗歌。
我想,这是育虹的诗歌最让我看重的地方。长久以来,我对所谓的“先锋派”或时尚写作总是持一种质疑的、有保留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诗歌的到来,总在一种无以名之的更新里”——这是多年前我曾写下的一句话,在今天我更是这样看了。的确,我们需要从语言内部重获一种自我更新的力量。我是愈来愈赞赏吉尔·德勒兹所说的这样的话了:“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
这样的描述,一语道出诗性语言的奥秘,也提示着像策兰、夏尔(甚至还有杜甫、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诗人们的卓绝劳作。在很大程度上,育虹也正是这样来“写诗”的。这是一位高度“自觉于语言”的诗人,纵览她二十年来的创作历程,可以说她愈来愈富有探索性,作品也显得愈来愈新颖、大胆。她的艺术蜕变和刷新,是词语(词汇、隐喻)上的,也是句法(对语法惯例的打破,跳跃、中断,等等)上的、发声(节奏、语气和音调)上的。以她2004年出版的《索隐》为标志,一个脱颖而出的诗人向人们走来。
首先从词语上看,她避开了一般女性诗歌常见的那一套修辞用语和调子。她引入了各类新的语言资源。除了植物学、鸟类学、海洋学的知识外(这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关),她还有意识运用了“星尘”、沙漠的“梵风”、“双子座流星雨”、“对流层”、“寒武纪的空窗”、“磁极”这类词语和意象。这不仅把她自己置于一个更开阔、陌异的修辞场域中,这种广博的知识,也使她形成了一种创造新鲜隐喻的能力,比如她这样写“想念”:“比一万六千行的荷马史诗长”(《想念》);这样写她的某种失落感:“因为太阳萎缩成白色侏儒/因为一平方尺内找不到一粒中子”(《之十五·隐》);这样写一个想象中的“异邦”:“窗是阿波罗的但床属于狄奧尼索斯”(《异邦》),等等。
她的诗就立足于这样的创造(因为因袭“是对创作本质的违逆”,《365°斜角》),即使从一些不起眼的语言细节,比如“白鹭鸶拍岸是风/羽量极”(《换季》)中的“羽量极”,我们也可见出诗人的匠心。甚至在她的散文中,也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尝试,比如她这样写文友相聚:“马汀尼可以更胡适些”;这样写鸟鸣:“一只不停发电报的鸟。嘟嘟。嘟。嘟嘟。……另一群则说这这这,这这这。”(《365°斜角》)。可以说,她这是在翻译一种语言了。的确,这是一位“作为译者的诗人”,从世界的动与静、光与影,也从鸟类、植物、天体物理、气候换季、外国语中,她在翻译一种未知语言——就像她自己在《异邦》一诗中所写的:“我们在门的张弛在床与异邦言语的/陌生中摸索”……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日常用语和一些常见的意象,但即使如此,她也能赋予其新的语言质地和意蕴:
不是背叛。是
两只风筝一路追逐愈离愈远
两只蚁交换了体味又错身而过
两片对生羽状叶在秋至分飞
两滴露珠相拥着却蒸发
——《之四十九·索》
……內战与地震与磨碎的咖啡豆
都过去了过期了所以
这是最好的姿勢
眼睛和闪电的眼睛小腹和火山的小腹
连夜的雨以及屋檐傾斜的
回答
——《异邦》
从世界的动与静、光与影,也从鸟类、植物、天体物理、气候换季、外国语中,她在翻译一种未知语言
且不说“火山的小腹”这类新奇而富有暗示力的隐喻,像“连夜的雨以及屋檐傾斜的/回答”这样一个结尾,也令人叫绝,可以说,那种李清照式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在这里已化为一种新的语言张力和姿态。
而这一切,也正和她练习一种“新的发声”相伴随(“有一种夜的连祷文/属于我们”,《换季》)。她在日记中曾引用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话“我们在字典的混乱中寻找音乐”,她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海黑了又蓝蓝了又黑”(《背影》),一种诗的节奏和声音也在不断形成和更新。在台北的书店,陪我去的女诗人颜艾琳一定要我买育虹的《索隐》。在这部奇特的诗集中,诗人的诗与她翻译的古希腊的萨福互文。那里面她自己的诗,大都是片断式的(献给“我的史前”),语调也显得很私密。到了她的下一部诗集《魅》(2007),语言节奏更为绵密,也更自由了,其中多半的诗都是没有分行、没有断句和标点符号的“诗片断”。即使分行,也往往是那种一气呵成、没有断句的长句。诗人陈义芝称它们有着“潮浪般的韵律感”。的确,它们有这样的冲击力,并留下了它们富有磁性的余音。
育虹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写的,这也许和她的气质有关,也许是因为生命本身的悬而未决、周而复始。她在她的诗中不断“换气”(策兰),不断吐纳和更新她的生命,像前辈诗人杨牧称赞的那样“深刻复透明”。诗选集《之间》附有一张“交响·诗”CD,它由“中板、慢板、稍快板、快板、慢板”五个乐章构成,为诗人十八首诗的录音及配乐。但我想,即使仅仅阅读她的诗歌文本,我们也能感到它们与音乐的密切联系。如用音乐术语来说,育虹的诗之所以新颖动人,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抒情调性(Tonality)。
如此看来,育虹有着她的“C大调”,也有着她的“a小调”,还有着她的复调和“无调性”。如果说她早期的诗往往倾向于喃喃自语,后来的一些诗尤其是长诗则愈来愈繁复,饱满,有力。她的《方向》一诗尤其让人动容,它由“没有方向”、“往蓝色的方向”、“那么教堂是不是方向”、“无憾的方向”四节组成,诗人在寻找,在分辨,在肯定,在质疑,诗情饱满,气韵连贯而又显得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的拍击力——“重要的是,那是波浪”,正如她引用的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所说。
不过,在更深的层面上,育虹的诗之所以让我认同,还在于这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抒情歌手,还是一个立足于对自身存在探索和追问的写作者。她的写作,绝不限于生活中的那么一点抒情,而是进入存在更本质的领域。
我们可以感到,她不仅面对个人的孤独,还一直在面对存在的虚空:“日子空/手空/眼前无人/屋子原是空……”(《中断》)正是这种虚空,这种生活的贫乏,这种“灰烬的静”,如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表述,使她听从了“在”的吩咐。
在诗选集《之间》的引言中,诗人这样描述了她的位置:光影之间、虚实之间、时空之间、聚散沉浮冷热动静轻重去留之间、死生之间、你我之间……她慨叹:“这介系,这容纳我们的方寸”。
“这容纳我们的方寸”,也就是哲人们所说的“在的地形学”。它具体而又抽象,有形而又无形,因不确定而显出多种“生发”的可能。它迫使一个诗人投入其中,像策兰所说的那样“命名,确认,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并且“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保罗·策兰:《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问卷的回答》)。
育虹所要把握的“之间”,正是生命与诗的“发生与到来”。
而她有意识运用沙漠的“梵风”、“双子座流星雨”、“对流层”这类宇宙性意象,不仅是为了革新语言,也是为了完成对存在的敞开。她的语境,她的诗之思,都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女性诗歌和都市诗歌的范畴。
她不仅是沉静的,内省的,也是富有“存在的勇气”的。她打破表象和时间之流,着意书写它的“中断”(“括号,附加语,插曲,间歇,中断”)。她知道“有一种夜/属于低飞的鹰/属于七里香/谨慎的听诊器也听不出的/心跳”(《换季》)。她在日记中还引用过Ann Carson的话以激励自己:“仅仅安全地站在窗口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往下跳,从已知跳到一个一无所知的空间,看看自己会在哪落脚,才可能学到东西。”请看下面一节诗:
有时你左脑滑落
水底
右脑却挣脱水面,俯瞰
月
留下的象形文字……
——《河流进你深层静脉》
这真是令人惊异。这样一幅生命写照,极尽存在的悖缪,它恰好印证了诗人在引用Ann Carson时所说的“冒险之必要”。
但育虹的作品依然是十分感人的。她赞赏里尔克所说的“心灵作品”(“视觉作品已经完成/现在轮到心灵作品”)。她自己的诗具有知性的、后现代的锋芒,但它们同样是对心灵世界的深入。在她那里我们会读到生命的无助与脆弱,迷茫与困惑,但她并没有简单地皈依某种信仰(纵然在她那里偶尔也会出现“佛”、“一柱香”这类意象)。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她不求虚幻的解脱,却有着她自己的超越方式和意志力量。她在日记中这样告白:“而《索隐》索寻的或许不仅是爱也是同样难以捉摸的缪斯。”
的确,这是一位听到更高、也更神秘的呼唤的诗人。她的诗往往即是对这呼唤的响应,“我有缘再次穿越三十七点二万平方公里的大流沙吗?如果再去你会同行吗?”(《365°斜角》)——
和你一起,在沙漠——
和你一起焦渴——
和你一起在罗望子密林——
豹子得以呼吸——终于!
写出这首小诗的不是育虹,而是艾米莉·狄金森。但是狄金森意义上的“你”,里尔克意义上的“你”(“我是孤独的但我孤独的还不够/为了来到你的面前”),也都出现在了她一首又一首的诗中:“那晚,我多么想/探身你的维度”(《之七·索》)、“我该怎样告诉你我的位置/……怎么让你听到冷泉与融浆的声音”(《只为那桃花梨花的盛会》)。在日记中她甚至还这样说:“不管怎么写必定有一个也在也不在的你。必须。”
“你”的在场与缺席,就这样决定了诗人自身的存在。在《定义》这首诗中,无论是诗,还是身边的种种事物,“没有你/也就(几乎)抓不住了”——这就是诗人最后所下的“定义”。
正因为如此,育虹的全部写作都在构建着一种如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这是从她自身存在中打开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也许正因为这个维度的打开,她写下了《那些法老们》等动人诗篇;正因为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我与你”,情爱诗被提升到存在本体论的层面:“那些流言都错了/你不是我的恋人,你是/更亲密的/——你是我”(《之五·索》)。
“生命被赋予必须完成”——我想这大概也正是育虹所听到的“最高律令”吧。她正是以这种不断书写的“我与你”,作为对自身孤独的克服,也以此“成全”着一个诗人的生命。
的确,正是这样一个“你”的存在,使诗人和生命、和语言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使她的抒情音调听起来也更为迫切动人了。
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她不求虚幻的解脱,却有着她自己的超越方式和意志力量
我就这样读着一位诗人。我想起她自己的一个定义“诗是某种活在陆地而想在天空飞翔的海洋动物的日记”(《365°斜角》)。她的全部写作都从不同角度指向了这一点。
也许我们都是这类悲哀动物。但她有着弗吉尼亚·沃尔芙这样的榜样:在现实的围困中,以写作“开启了死者的墓穴,开启了天空……”她也这样打开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语言空间……
甚至可以说她创造了自己的“气候”,而这自然与海有关。她一次次写到海:“关于海的狂草/不停写着又哗哗撕掉”(《关于二月十四的天气》)、“海黑了又蓝蓝了又黑”(《背影》)、“其实风是一切/时间是一切/光是一切/空间是一切,其实/(来了又去了/近了又远了/明了又暗了/聚了又散了……)”(《其实,海》)……
她的语言,吸收了北美雪的寒气和奇异光亮
她的海就这样为她呈现,或者说她自己就这样“从断讯的海岸來”。其实,空气也是一切,它构成了她的一切风景的秘密。我想,她也一定会认同曼德尔斯塔姆的这句话:“诗是盗窃来的空气。”
作为活在陆地上的海洋动物,她以语言的鳍呼吸。她也不得不以此来呼吸。
这也注定了这是一位献身于语言并属于语言的诗人。在日记中她写到:“可怜的王尔德说他花了一整个上午修改一首诗,拿掉一个逗点,下午想想又把那逗点放回去。”而她自己,可以想象,也不断地为那个“逗点”折磨着。
不管怎么说,她带来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诗歌语言。我不知道这种语言对亚热带的台湾读者来说是不是有着某种陌异性。别的语言特质不说,她的词语中有一种“几乎像北美初冬的干冷”,并透出“淡淡的蓝”。这当然和她在那里的多年生活经历有关。她的语言,吸收了北美雪的寒气和奇异光亮。
她以这种语言抒情,也以这种语言为存在写生:“我离去时/一只浅灰蓝螺贝/抬头看看我/没有说一句话”(《第三海湾》)。
当然,如我们已知道的:她也在翻译一种语言。实际上,她也是一位勤勉而优秀的译者。她本是学外语出身,翻译过萨福、里尔克、帕斯,等等,并出版过英国女诗人达菲、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译诗集。在双语的相互映照中,她一定瞥见了某种语言——就像茨维塔耶娃从“你与我”之间看到一个新的生命“侧面”。
维特根斯坦大概这样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即是想象一种生命。
她仍在继续着她的探索、想象和翻译。她要抵达的是“第三海湾”。她的诗要献给的,是“第十位缪斯”。
这也使我想起了兰波的诗歌宣言:“抵达陌生处”。而这个“陌生处”在何处?显然,它不可能是大地上任何一个地点。它指向了一个想象中的“异邦”,更确切地讲,它指向了一个“语言的异乡”。
我想,我们疲倦的肉体和不断被磨损的诗性,在那个“语言的异乡”才有可能真正醒来。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育虹会说“诗是给将来的”。不过,她紧接着又这样说“但爱/爱必须在现在”(《诗的联想》)。
这堪称为格言了。一个蘸着“夜汁”书写的现在,一个处在危岩上的现在。这是存在的迫切性,也是爱的迫切性。一种诗的未来也只能从这样一个“当下”诞生。
因此我必须向远方的诗人致以问候了——我甚至想起了茨维塔耶娃献给里尔克的伟大挽歌《新年问候》中这样的诗句:
向着那可以看到的最远的海岬——
新眼睛好,莱纳!耳朵好,莱纳!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