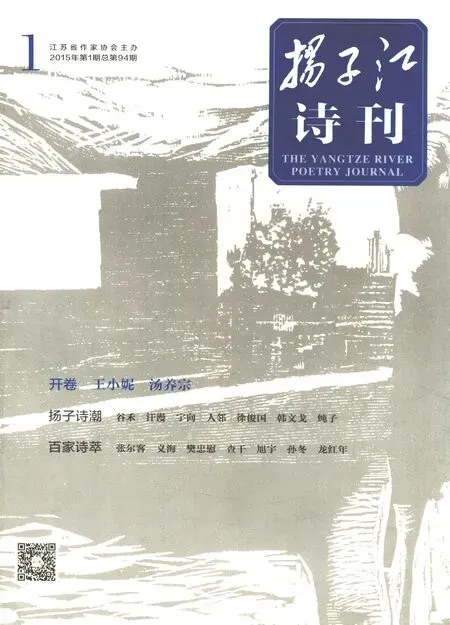诗人陈超
大 解
○ 视角 ○
诗人陈超
大 解
本期角度:作为诗人的陈超
“视角”为本刊新开栏目,意在使读者站在这个平台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一个诗人、诗歌现象或诗歌事件的多个棱面,对有关诗人的部分隐秘、本元或陌生的特质予以新的呈现,从而为诗歌及诗坛的构成提供更丰富的元素,并试图提炼出某种重要性。刚刚去世的陈超先生是成就卓著的诗歌理论家,这甚至掩盖了他的诗名。本期我们刊发他的部分诗作及大解、霍俊明先生的文章,意在彰显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一面。
作为一个诗人,陈超所走过的道路,伴随着朦胧诗以后直至今天的整个发展过程,并一直保持着先锋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当时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人物,陈超在关注新诗理论建设的同时,操刀上阵,开始了探索性诗歌写作。当时,人们在努力探寻脱开朦胧诗的路径,以便从历史意识和集体意识中走出,充分地展现自我,并建立个人的言说方式。可以说,从那时起,陈超就已经具有了敏锐的自觉性,写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作品。后来的一段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开始探索个人命运与整体世界的关系,甚至出现了表现小人物、小细节的作品(如:《弯腰赎罪》1986,《沉哀》1990等)。这些作品比当今的低于生活的叙事,早了至少二十年。
但是,向具体的生活靠拢,并不等于放弃审美的高傲,陈超的创作主调依然保持着激情和语言的活力。《博物馆或火焰》、《青铜墓地》等代表性篇章,依然表现出超越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思考;而《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等又将个人带回到具体的事物中,把纯美推到超然的境界。这个时期的作品,语言硬度较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把语言推上了悬崖,创作无疑成了精神历险。因此,在这种语境下,陈超的诗在深沉的思想力量之外,常常带有荡气回肠的感染力,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审美冲击。
陈超的探索并没有停留于此。在视角的转换上,他的自由度体现在个人的站位和精神需求之间,始终以“人”的立场在审视这个世界,并把自身命运置于运转的核心。这时,身体的出场就成了必然,亲历性和亲和性成了诗人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一旦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琐事就成了诗人通向精神远景的一条隐秘通道,远景和近景被随时挪移和置换,于是陌生化产生于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安静的上午》、《早餐》等一批素描式的生活片段就是这样。与他早期作品的挥霍才情明显不同,在这类作品中,他有着很强的截取生活以及叙事的能力,在取材上非常经济,叙述准确而生动,绝少有浪费的地方。从他的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身体的陈超和精神的陈超同时出现,游走于具体的开放的时空里。这时反而使人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幻觉,让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那些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却被人们忽略甚至遗忘的事物,正是诗意之所在。
可以说,在陈超的诗歌探索中,他的走向相对稳定,但胃口决不单一,他给自己预留了非常广阔的出入空间,以便在选题上有足够的自由。由于取舍的幅度较大,他的一些诗大开大合,放纵不羁,汪洋恣肆,而另外一些诗却走向了简约和澄明,读后有一种被阳光穿透的感觉。《无端泪涌》、《夜和花影》、《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等,无论怅然或温馨,都透人肺腑,给人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
与他的诗歌成就并驾齐驱,陈超的诗学理论建设是他的重要收获。在从业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探索诗鉴赏词典》、《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歌论》等著作的出版,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三十年的大致走向。
近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是快速的,流变的,其更新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期。流派的起落在短时间内完成,个人的沉浮也似乎带有戏剧性。在这种走马灯般的人流中抓住先锋者,并对其进行归纳、判断、跟进、助推,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贯穿几个不同时期的整体性诗学建设,是一项不小的工程。陈超的得力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一个诗歌写作者,他始终保持着写作的先锋性,这就使他具有纯粹理论家所很难具备的敏锐的感知力和亲历者的心路历程。他深知诗歌的底细,他走在诗人队伍中而不是站在外面说话,他所发出的声音是来自诗歌内部的声音。因此,他的诗学理论具有诗和论的双重特性,富有激情,同时又准确到位,总能切入诗歌要位,具有建设性和引导性。
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同时进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陈超是两面受益,互相滋长,成为他快速驱驰的两个轮子。我怀疑他有时是从自己的创作中寻找理论依据,有时也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论从事创作,从而成为互补和互否的完全式结构。因为他的诗与他的理论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他说到并做到了;换句话说,他做到之后,说出了普遍的道理。这就是陈超的方式。
作为诗人和诗歌理论家,陈超的作品是严肃而庄重的;而作为一个人,他的为人非常谦和厚道,并不像他的诗文那样高迈卓然,难以接近。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陈超的睿智和诙谐带有很强的亲和力,有陈超在的地方,人们总能爆发出笑声,因为他并不总是一本正经,或者说是很“没正经”。他出言即幽默。这与他的修养深厚,为人平和,健康乐观的性格直接相关。他长得高大威猛,虎背熊腰,像是一头雄狮,但内心却非常善良、正直,不曾伤害过任何人。在诗学讲坛上,他满腹经纶,风范儒雅,却语出惊人,滔滔不绝,带有极强的灵魂杀伤力。这样一个教授,一个大帅哥,走在大学校园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崇拜者眼神里流动的波涛,会把自己淹没。有一次我去河北师大西校区找他,见到一群女生走在校园里,我向她们打听文学院在哪座楼,她们问我找谁,我说找陈超教授。她们表现出惊异的表情,说你认识陈超教授?我说是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没想到这群女生一齐发出尖叫,眼里闪闪发光,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听说,学生们盼望听陈超课,几天之前就激动不已。他在校园里深受学生们爱戴,不仅是学生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可以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儒雅而又可爱的人,一个顽皮的人。记得在1990年代初,在一个旅游景区的文学采风活动中,晚上文友们在会议室自发组织了一场晚会,其中有一个作者要表演倒立唱歌,前提是必须倒立在人的后背上。在场的人们取笑说,你自己唱吧,没有谁当你的狗肉架子。这时只听陈超大喊一声,我来!只见陈超四肢触地,当起了他的肉架子,直到那个表演者倒立在他的后背上把歌唱完,之后人们爆笑不止。
我和陈超相识并成为挚友已经接近三十年了,日常交往很多,对他的为人,我心存敬仰;但谈论他的诗学,我还尚欠资格。因为他的诗和理论在前沿阵地,一直在往前走,不曾有所停顿。有时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我才发现,他在当年所做的探索,是多么超前,多么可贵。这一点,从他的诗集《热爱,是的》中可以看出。近年,我和陈超见面并不总是谈诗,但从他出版的新书中,我知道他的思考在不断深入,视野在不断拓宽。我感觉他一直在快速前行,就我的目力所及,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前面,而且总是在远方。
2014年10月31日凌晨,他突然停止行走,毅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从此,他以另外的方式活在我们之中,继续影响着当下和来者,影响着中国新诗和诗人。诗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中国文学史会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