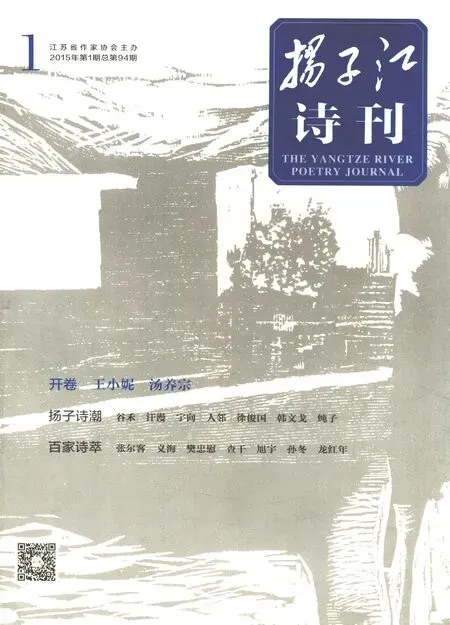一只虎的五种祛魅方式
——读周伦佑长诗《象形虎》
梁雪波
一只虎的五种祛魅方式——读周伦佑长诗《象形虎》
梁雪波
周伦佑是一位卓越的先锋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数的精英之一”(陈超)。他从文革中后期开始地下诗歌写作,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狂飙突进的诗歌运动中以“非非主义”创立者、代表诗人和阐释家的身份崛起,震动诗坛,他先后提出并系统阐述的“反价值”、“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变构诗学”等诗学理论,不但深刻切入当下现实,而且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已经超越了诗歌领域,而在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把诗人的类型分为气质型诗人和观念型诗人,周伦佑可能更多地属于后者。他的诗写依托强大的理论背景和近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是文本与理论的对创生成,他善于用理性之刃雕刻精神的火焰,赋予思想以水晶般的质地,这使他的很多诗作在智性与感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犹如站立在刀锋上的大鸟。
长诗《象形虎》写于2003年9月,全诗500多行,是一首能够经得住细读的现代诗典范之作。其典范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它以诗歌的形式对无所不在的权力文化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揭示和解构,尤其是对“象形虎”喻指的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第二,它以调动多种知识体系和修辞方式的变构写作,实施了一次对权力的剥皮术,全诗在结构中解构,在解构中结构,犀锐的思想与雄辩的言辞缠绕扭结,而又不失语境的澄明,显示出精湛的诗歌写作技艺。第三,它是一次对“不可言说之物”的介入式写作,彰显出“深入骨头与制度”的自由写作立场,捍卫了先锋诗歌应有的精神品质。
《象形虎》的出现并非偶然。纵观周伦佑持续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并非如一些评论家认为的“前后矛盾”、“反复无常”,而是有内在的延续性和递进性。在周伦佑的诗学话语体系中,与动物有关的作品为数不少,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意象群、隐喻群:猫头鹰、白狼、猫王、大鸟、死鱼、高蹈之鹤、矮种马、斑马、乌鸦……在这个由“动物诗学”组成的庞大家族中,隐喻是最鲜明的徽标,隐喻所具有的浓缩、密度、歧义,以及丰富的质感体现了诗语的生长活性,为思想与直觉的赋形提供了最佳的修辞方式。英国学者C·路易斯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更是认为:隐喻不仅提供信息,而且传达真理。在写作《象形虎》之前,“虎”的意象曾两度出现在周伦佑的诗中,在写于1987年的长诗《头像》中,它是博尔赫斯想象的幻美之虎,“在海边的礁石上晒它的虎皮/图案中央一团火焰慢腾腾升起……”而在写于1990年10月的短诗《石头构图的境况》中,那只超现实主义的老虎,却陡然变异为凶猛异常的食人兽,它与居高临下、随时可以让人粉身碎骨的“石头”形成共谋,喻指一种侵夺自由、吞噬生命的绝对暴力:
石头构图的境况如此这般
犹如一个人深入老虎历险
在虎口里拔牙,却突然牙痛
也许有一天你会得到一整张虎皮以此证明你的勇敢和富有
但现在是老虎在咬你,吃你
不可替代的处境使你遍体鳞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经历的时代与个人命运的转折,让诗人经常“痛醒在时间内部”,而两只“虎”的蜕变轨迹,正对应着周伦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化血为墨迹”的诗学转变:即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虎,一个徘徊在汉语中的幽灵,让诗人长期以来寝食难安。必须用一首强有力的诗去捕获它!打开一本关于老虎的书,即意味着开启一次深入到思想、精神、制度与修辞的冒险之旅,一场与虎谋皮的博弈惊心动魄。而翻书的手早已被虎牙所伤,像历史的烙印,五道齿痕暗示着五种阅读方式,五种解构虎魅的路径。
首先出场的是威风八面的“山兽之君”,一声吼啸震慑万物,但在“死亡的逆光里”,诗人“看不清虎的脸,只能看见它/黄铜的肩背被黑夜缠紧”。必须翻过这片国家地理的风景,退出猫科动物的词根,对虎进行一次文化考古,在钟鼎、建筑和部族图腾上,随处可见这不祥之物,它久久“盘桓于我们的梦魇与饮食”。可见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原型,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不是人骑在虎背上,是虎豢养/人的命运”。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无比智慧的动物,虎还深谙卦象之术,据说在捕食之前,它们常常画地作卦,卜算最佳的猎食方向。一只玄学之虎,登山临水,轻吟浅唱,取消了人世的痛苦,享受着灵魂与肉体分裂的自在逍遥,“总领八卦的奇数,占有天空的高敞/拥有金玉和美羊。”
单向的默读变成双向的对话,虎引诱着诗人的脚步,但虎的真身却始终隐而不显。在诗人不断的阅读、追索下,虎向语言遁去,在“一个恐惧的拟声词”中藏身,“它脱离自己的斑斓形体,从形象/演变为象形”。一只象形虎,“印刷体的生物”,由怒睁的大眼、张开的长有獠牙的大嘴构成,带着鲜明的“王道”标记,在语义学的深处暴露无遗。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它代表一切,统摄一切,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行近乎完美的垄断。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它征用各种思想、理论、学术来建立道统,例如中国自秦一统天下之后长达两千多年奉行的“外儒内法、政教合一”。它还苦心钻研语言炼金术,发明了一套精密系统的语法规则:“用近义词/团结同志,用反义词制造敌人/用形容词夸饰仪表,用动词愚弄公众”。一方面实行言论监控,大量制造文字狱,另一方面又为民众勾画“美丽的新世界”。
虎语——直译为谎言的有效性
在一种粗暴而不容置疑的语体中
虎被反复陈述。虎语的极端风格
延展为暴力的修辞
如果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词即是生命。那么“虎语”不仅是将语言变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实际上更是毁坏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摧毁了美和意义的乡土。在奥威尔的笔下,真理制造者通过发明“新词”来缩减和控制语言,从而达到缩减和控制人的精神能力,通过体制化的书写,将一切中心化、整体化、顺役化。当“虎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当中,就像散布在修辞、逻辑、语法中的“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被人们吞食,起初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时间一长这种毒性就会发作出来,中毒太深的人,甚至可能变成为虎效力的伥鬼。
阅读的过程伴随着“与虎谋皮”的凶险,因为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是弱与强、明与暗、寡与多、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残酷游戏,全能主义的虎能够“以匿名的方式/监视我们的谈吐和造句。它有时/就在我们头脑里办公,对我们进行/思想甄别,不放过任何一个隐喻/和异象”。这是虎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精密实用的统治术,将民众的驯化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它有老虎的头、皇帝的心脏、主义的花纹/体制的躯干、拖着一条人民的尾巴/牙齿是暴力的工具。”在这个异化的权力系统里,虎有遮蔽真相的功能,可以轻易启动“反阅读程序”,把人变成动物,变成犬儒者,变成精神病患者,而对难啃的异端,则变成消化系统里排出的残渣。这就是“我”面临的真实处境,布罗茨基说,诗人是一切极权专制的敌人。而实际上在专制文化中生存的人,几乎都被虎疫所感染,成了不自觉的暴力协同者。因此阅读、追踪的过程充满了焦灼与紧张,挣扎与反思,并伴随着克服内化的恐惧,从自身中剥离出“虎疾”的痛苦,“深入老虎而不被老虎吃掉”,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胆识、智慧,以及“日拱一卒”的坚韧意志。必须将虎关入牢笼!权力所在之处,就有反抗,而每一个微小的、局部的反抗都是对整体的消解。“王道的油彩开始脱落”,被剥除的虎皮也开始溃烂,再也保不住中心,这只貌似强悍的庞然大物终将解体,因为在它自相矛盾的内部有一个倒计时的引爆装置。
《象形虎》从对“虎”的五种阅读方式入手,分别以动物学、玄学、语义学、政治学和诗学等知识体系作为路径,对诡异之虎展开追踪,在不断的质疑、拷问、反思与搏斗中,揭开那些覆盖在虎体上的斑斓皮毛,消解它不可一世的威权,指出我们被权力之钉痛击的真实处境。
“一只披挂火焰的虎从我身上脱颖而出”,这一开放式的结尾,令人深思。这终结之虎,既可以喻指一只超越于种种符码之上的“原虎”,一只披挂着火焰的精神之虎,从人性的深处获得新生,也可以看作是阅读、追踪老虎的“我”最终被异化,变成一只食人猛兽。正如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它将带着全部的暴虐重返人间。
在周伦佑的长诗中,《象形虎》可谓最为精粹的一首。语言与思想反复交锋,深刻的历史反思与去伪存真的价值关注彼此激活,解构与结构交织缠绕,玄想与良知同步演进。在文本与现实的双重指涉中,展现出灵魂涉险的高难度。周伦佑认为,一首好诗不但应有诗学的意义,还应该有修辞学的意义。在《象形虎》中,动用了象征、隐喻、通感、悖谬、戏仿、暴力嵌合、反逻辑想象等现代诗歌修辞技巧,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呈现诗歌的丰富意蕴和内在张力。
长诗素来是考验一个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文体形式,一首长诗是否成功,除了叙述、结构、空间、时间等等需要考虑的因素之外,尤为重要的还有语气和语势的把握。中国古典文论中强调“文以气为主”,韩愈说“气盛言宜”,就诗歌来说,一首好的长诗应该是气韵贯通、一气呵成的,即在一首诗中,语象、语流与诗思应保持协同共振,语流的推进与涌动不能出现断裂。在某种程度上,艾略特的《荒原》因各个章节文气的断裂,像是由岩层堆叠而成的组诗,缺乏长诗应有的整体性。帕斯认为,长诗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整体中的变化,平直与奇异的结合。《象形虎》之气沉雄丰沛,迂曲绵密,像用一把夜色磨亮的钝刀,将切削之后的词语和词语嵌入咬合紧密的榫卯。而在语势上,作者也注意到了“整体中的变化”,例如:当虎现身时,语势是迫促、迅速、急转直下,而当虎隐身时,语势则迟缓、凝重、迂曲盘结。
面对口水诗、废话诗泛滥,诗歌品质下滑的当下,很多诗人和评论家感到焦虑失望,并吁求一种历史性与个人性并举,“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诗学”,无疑,周伦佑的《象形虎》正是这样的优秀文本,凭借深刻的思想力、坚卓的结构和语言变构术,在“正义之诗”和“美学之诗”之间实现了一次精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