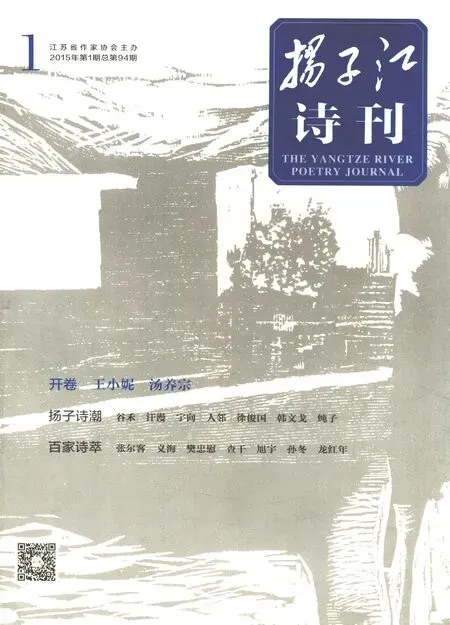诗之思
泉 子
○ 诗人笔记 ○
诗之思
泉 子
简洁不仅仅是语言的法则,它同样作为我们生命深处的圆满。
庄子的“得意忘言”道出的何曾不是尘世那共同的局限?
“忘”是对语言之局限性的克服手段,也是结果。或者说,“意”的圆满或“道”的凯旋,必须在“忘言”中才得以抵达与呈现。
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将简洁视为最高准则的更深处的秘密。就像《老子》、《论语》这些格言体经典,就像中国山水画,简洁不再仅仅指向语言、形式本身,它同样蕴含着对语言、形式甚至是这尘世局限性的深刻洞察。
用“以少胜多”来解释我们古人对简洁的理解依然是表面的。
从来没有胜利可言。这是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舍弃与放下,必须以无穷无尽地,接近于无的少,才能企及的这尘世的圆满。
诗作为一种自由的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全一次公平与正义,在语言的深处。
克服不是一种简单的摧毁或否定,而是对时代、对尘世、对你自身的局限性的深刻体认中的一次次地完善与超越。
诗是空无在时空中的位置,是道在尘世中状量自身的标尺。
或者说,诗并非语言。诗是道,是空无与我们在尘世中的相遇。
就像空说出的不是无,无说出的也不是无。
或者说,“空”是为容纳下这无穷无尽的有,为容纳下整个宇宙而必须被发明出的无边无际的辽阔,而“无”是为承载下无穷无尽的未来与往昔而甘愿永远不显现其自身的,一个被称之为“此刻”的原点。
那些担忧语言在因我们对道的抵达与揭示的一刻化为乌有的,是另一个杞人。
道永远无法抵达,在这尘世。
或者说,语言从来是这尘世局限性的见证,并终将因与道的切近而得以一次次重获这尘世的圆满。
每一个瞬间都深埋着一个通往真理的斜坡。
绝大多数人,因对这样的瞬间的忽视,而在无知中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生命是以消逝得以标识的存在,是你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是你选择与这些,而不是那些事物一同消逝时,那全部的艰难与喜悦。
一个人的神奇不在于他在二十岁时拥有一颗诗心,而是在于他在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当他历尽了人世的沧桑后依然成功保全了一颗赤子之心。
只有这极少者,只有这历尽沧桑,同时成功保全了一颗孩童般的赤诚与天真的人,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诗人。
他不再写下一个字,但他已尽得这人世的风流。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语言的限度时,我们才能真正领受到来自它的祝福。
诗歌并非分行的文字,而是你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凝固。
就像,书法不是汉字,而是你的悲与喜,你的赞美与祝福、你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这微小的点画结构中的呈现。
书法不会因我们在岩石上的勒刻而得以永恒。或者说,任何的媒质都是有限的,无论是宣纸、绢丝、竹简,还是在新近得以发明的电子储存媒介。它们都不过是一片新的沙地或一缕微风与另一缕微风之间的,那片辽阔,仿若静止的水域。
我愿意把春秋到晚清的两千年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这我们所自的一种如此伟大的传统与文明。魏晋至盛唐构筑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顶峰,而这之后的一千多年,勾勒出的恰恰是一种如此伟大的文明的衰败之路。就像在书法这一径上,王羲之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他完成了对“古质”的总结,同时开启了“今妍”之滥觞。或许,对“妍”,对形式的追求,恰恰是一种艺术,一种文明千年来衰败之症结。
这是一种文明自身在不同阶段的气数,也是一群人在各自时代中的幸与不幸。
而他们以各自的坚持,标识出一个又一个时代,并绵延成我们此刻回望中群山的奔腾。
一种伟大文明的复兴,或许,恰恰是在对“古质”的再一次发明中。
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五四”及辛亥革命的意义,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一个民族、一个如此古老文明的重新出发,那是对甲骨文、汉简、帛文以及北魏石刻的集中发现,那是在衰败到了极点之后,必须以大破才能抵达的大立。
现代艺术与诗歌,似乎更多地,或者说更擅长于表现一种分裂的情感与自我。这并非艺术家与诗人的一种新的创造,而他们作为尘世那最敏锐的部分,率先说出了一个时代深处共同的忧郁。
“现代性”是波德莱尔以来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命运。
如果说“现代性”是我们对真实的一次出发,那么,当“现代性”导致了诗人对语言与技术的极度迷恋,并对真实构筑出一道新的遮蔽的幕墙之后,我们又必须独自向真实再一次出发了。
顾客是上帝,说出的并非是对人的尊重,而是这个拜物的时代中,我们以他们的名义,说出的对物、对金钱、对商品价值的顶礼膜拜。
同样,那些以读者为上帝的人,并非一种自我的克制,而是在自我的放逐中,完成的对名与利的屈膝。
那些执意要在这个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构筑一个风花雪月的居所的人,不是因为瞎子般的盲目与愚人般的无知的话,那么,一定源自一个懦弱者的自欺。
一个自以为已然洞悉一切的人,一个自诩的“明白人”,恰恰是因为他丧失了抵达更远的不明之地的能力 。
无论是从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诗歌,还是以李、杜为代表的古典汉语诗歌传统,它们都一直经受着来自使诗歌仅仅作为一种技艺的那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的诱惑。但诗歌又必须在向时代,向政治、经济、风俗编织成的万物的敞开中,构筑出诗歌自身的救赎之路。
生活中的烦闷,是生老病死在尘世,在时空中无穷无尽地投射。
就像生老病死作为万物在尘世的标识,生活中的烦闷将永无止尽。
它们将共同标识出我们在宇宙,在时间的长河,在这尘世中不同的位置。
但依然有一条获得救赎的缝隙留给这尘世中的我们,当我们成功弃绝那将我们留在此时此地的无穷无尽的不同。
万物不分高、低,贵、贱,在神那里。
而我们,因各自的限度,而如此骄傲,而如此卑微,并赋予万物以如此的不同。
我们对事物的成见越多越深,就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局限性越大也越坚固,就意味着我们自身的束缚越多,也意味着我们最初的无边无际的丧失,并最终陷入了茧壳之内那逼仄的空间中。
你必须不断地放下你的成见,你必须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局限,你必须不断去挣脱这仿佛无尽的束缚,你必须彻底放下自我,以再一次与万物相遇,如那初见。
你必须积攒出所有的力量与勇气,以重新获得最初的无边无际,你必须成为那惟一,又是这广阔世界之全部,你必须成为那真理般悖论的再一次的见证者。
或许,我们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诗人所有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们还没能在这个如此喧嚣,充满幻相的时代中发明出一种抵达真实的语言,就像李白、杜甫,就像苏轼、陶渊明、屈原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中,通过各自如此艰难地开掘,并为我们呈现了那共同的真实。
你必须成为那是非分明,而又温和敦厚的人,或者说,你只有成为一个是非分明的人,才能成为这温和敦厚者。
它们共同地源于你永远无法企及的智慧,并因这智慧而是非分明,并因这智慧而谦卑,并因这谦卑而温和敦厚。
真正的精神是我们对千古不易之处的一次次发现与辨认。它从来并一直在这里,而我们每一次的发现,仿佛是又一次的发明,仿佛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惟有道或真理能高于生与死。
如果生与死之间的奇崛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通往真理的斜坡,那么,就从来没有过生,从来没有过死,就从来没有这生生灭灭堆砌出的,虚幻的人世。
知识是前人或他人为我们揭示的真实,智慧是你在前人或他人为我们揭示的真实中开掘出你一个人,同时是每一个人的真实。而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种群在面对知识那世世代代,历久弥新的诱惑、辨认与抗拒中,使一个人最终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种群成为了一个种群的秘密。
如果说薪火相传说出的是我们用知识的火炬,来开掘与发明出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世世代代的真实,而正是这相同的使命使得无数的人,使得那世世代代的我们成为了那同一个人,成为了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一棵小草、一片树叶那全部的秘密,即意味着我们已穷尽整个宇宙。
诗必须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来到我们中间。同时,我们又必须全神贯注地,我们必须用尽所有的力量,以辨认出那冥冥中的,那来自幽暗与寂静的至深处的召唤。
名实相符,或名至实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而这两者之间的偏斜,构筑出一个必然而如此坚固的尘世。
但诗人,你知道,相对于一个籍籍无名的优秀者所经受的来自孤独的考验,那些浪得虚名者,那些对名声孜孜以求的人,那些名满天下,那些得到的远远多过应得的人,他们因多余的名声而受到的伤害甚至远远超过那些不及者,那些终其一生寂寂无名的人,那些因坚守着可贵的寂静,而永远为世世代代的喧嚣所淹没的人。
我愿意与文学与诗歌毫无瓜葛,如果它们不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并帮助我涉过了人性中的沼泽,并因此而获得一个个神启的瞬间。就像我将《圣经》作为文学作品来温习,就像在我每天对《金刚经》的诵读中,首先将它作为一种呼与吸以及宁心静气的练习。
我曾经把《神曲》作为这个尘世的一种不可能之物,直到最近,我辨认出另一种可能,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它甚至比人类那共同的孕育与命运更长久,它在等待着一个更持久凝神后的瞬间,它在等待时间以更深之孤独完成的浇筑。
这尘世并非是栽给我们的,我们只是领受了这应得的祝福与惩罚。只有极少数者,被应允知悉我们因何获得这应得的祝福与惩罚,只有这极少数者,因他的知悉,因他对这尘世的通行证般的羞耻的辨认,并因这世世代代为羞耻激发的精进与克服的愿力,而终于免于再一次为忘川之水所隔绝。
阅读就是在体内挖坑,沉思与写作都是。你必须不断挖掘,你必须挖。铲的每一次挥动,都能搬走一块黑色的云。你必须挖,你必须从一种如此简单而重复的劳作,挖掘,并见证这尘世又一个盛大的节日,你必须穷尽人世的徒劳,以再一次见证这消融于万物之中的空无。
名声是我们心中的蛇,而并非传说中的恶棍。
如果不是我们心中的欲念之火,一次次将它从持续的酣睡中惊醒。
我们必须向农民学习与分享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与情感方式,
一种基于对土地的尊重与虔敬,
而越来越坚定的,对一种看似徒劳的重复劳作的坚持。
灵魂出窍,是一种真实而美好的生命体验,是如此庸常的尘世获得救赎的窗口在这一瞬间的开启。
诗必须是生长着的。诗必须在这密不透风的尘世的幕墙中如此坚韧地生长,并给我们以启示。否则,它们不过是一堆酸臭的文字。
如果必须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相信奇迹与神秘事物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科学不是许多现代人眼里的妖魔鬼怪。它同样是我们悟道求真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这样一种方式在今天需要我们做出更多反思的话,是在于今天的我们已把它作为惟一的方式与通道了,就像中世纪的世俗宗教带给人们的狂热与褊狭。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种孤立的、涣散或破碎的状态,而是孤独者在受到那“惟一”或“无”的越来越强烈的吸引,而从那种破碎、涣散与孤立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时,那全部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