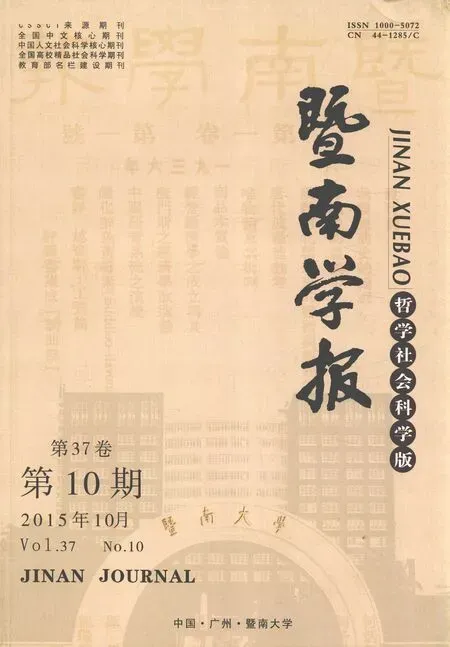咨文与龙牌:日本漂流民与清代中日关系
孟晓旭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北京 100091)
基于“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这样的华夷理念,明太祖在建国初即“诏谕”四邻各国、促令朝贡,致力于恢复并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明太祖的这一理念也被后来代替明朝统治中国的清朝所继承,尽管清朝知道自己出身于“蛮夷”。相对于朝鲜而言,日本对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政治热情并不高,甚至是抵触。1381年,日本甚至直白道:“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而17世纪中叶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统治者这一巨大变革,更使得奉行“华夷论”的日本拒绝和清朝进行大清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往来,甚至清初通过朝鲜遣送日本漂流民进而转达“宣谕”的行为一度引起日本的恐慌、不安和敌意。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稳定,在乾隆时期,中国和日本之间却同样通过救助与遣返漂流民事件使得双方之间有了官方的咨文往来和值得关注的龙牌下赐行为。尽管这种形式的官方往来缺乏持续实施的动力,注定了它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政治行为,但是它却成为清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清代中期日本漂流民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多以披露琐碎的史料为主。尤其是,既有的研究缺乏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对日本漂流民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也就难以界定出该问题在清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本文拟基于更多的史料,探讨建立在通过遣返日本漂流民而发生的咨文往来等中日互动以及清朝对日本漂流民的龙牌下赐等行为,进而由此为契机对当时中日关系进行深入的论述,以进一步丰富中日关系史的相关研究。
一、清初中日建立官方往来的坎坷
在入关之前,清朝曾试图借助朝鲜和日本建立起政治关系。1637年,清太宗在朝鲜南汉山城下迫使朝鲜仁祖与之缔结城下之盟,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开始变为“君臣关系”。在把朝鲜编入以清朝为中心的新秩序中的同时,清太宗还敕谕朝鲜仁祖:“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希望朝鲜能够把日本介绍到清朝的政治秩序圈之内。为尽快达到目的,清朝派去朝鲜的敕使也曾向朝鲜方面认真地提出与在朝鲜的日本使者见面的要求,试图进行清日的直接接触,“以开交邻之道”。但是由于朝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清朝的要求并没有给予积极的配合,导致清朝的政治意图流产。因此,入关前清朝企图通过“假道”朝鲜而“遣使”日本的期望最终没有实现。
1644年,满族入关、定鼎中原,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由于明朝既有的“华夷秩序”因为日本发起的壬辰战争和清朝的军事征服已经崩溃,于是清朝雄心勃勃地梦想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开创清朝之“洪业”。既然已经站在了中央之国的位置上,清朝认为它可以继承前代王朝明朝的历史遗产,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宗主国。无疑,日本也在清朝的经营范围之内。而正如很多学者所观察到的——“这种国际秩序(华夷秩序)的扩大与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事实上,刚刚入关、意气风发的清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是大力宣扬“德治”、以副“怀柔远人”,达到巩固和扩大以清朝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的目的。
1644年,日本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的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58人乘坐三艘商船在海上航行的途中遭到飓风、漂到中国满洲晖春附近。这给刚刚入关的清朝向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施加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幸存的日本漂流民在漂流到达的地方官吏的保护下被送到盛京,后随着满族的入关队伍前往北京。在北京,他们受到了清朝非常优厚的待遇:“对(日本漂流民)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办到”,提供的食物有大米、猪肉;喝的有茶、酒;穿的有丝绸、睡衣等,而且他们还受到了当时清朝实权人物多尔衮的接见。1645年底,清政府命令册封朝鲜世子的使臣祈充格把这些日本漂流民送往朝鲜,由朝鲜方面派人将之遣返回国,“启程时15人都骑着马,有100余名清军护送,打着大龙旗,拿着箭戟,一直送到朝鲜国境。”1646年,这些日本漂流民被送到朝鲜东莱府,移交给驻在釜山的对马藩士,再经由对马岛,于6月16日抵达大阪。
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帝在指示朝鲜遣使护送这些漂流民回日本的同时,还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大清的敕谕,敕谕的内容为:“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闵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很明显,刚刚定都北京、意气风发的顺治帝以“中华”皇帝自居,宣扬仁德,在“中外一统,四海为家”的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下向日本发出感召,希望日本在“慕夏主义”的支配下进入自己的“华夷秩序”之中。
但是,事与愿违,清朝此举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引起了日本的强烈敌意,恶化了清日关系。1646年10月,德川幕府在经过缜密的研究之后派使到朝鲜进行回谢,日本在谢书中不仅称清为“鞑靼”以示蔑视,甚至还筹划假道朝鲜,出兵中国。《朝鲜仁宗实录》记载道:“倭使橘成税、藤智绳到东莱府,盖为漂倭押还回谢也。智绳谓东莱府使闵应协曰:“江户执政等闻漂倭人来,惊曰:‘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而朝鲜受而送之,必须是与鞑为一也。’大纳言欲赴援南京。议者曰:‘彼兵不下百万,我虽发百万之众,平原广野,则必不能抵挡,不如假途朝鲜。’岛主言:‘顷年朝鲜酷被鞑兵之祸,人民死亡殆尽。且釜山至北京八千余里,绝不可轻举大众。’以此意,反复周旋。”
揣测到“鞑靼正欲夸大”,日本内心十分抗拒甚至要“赴援南京”。可以看出,日本对清的华夷秩序之主的地位并不给予认同,甚至想诉诸武力以表示日本之强大和“武威”。对于清朝救助并遣返越前日本漂流民一事,德川幕府派驻对马岛的轮番僧栢西堂则把之解读为“清国所闻日本政道之正,故使漂流民送来”,并不认为这是清朝对日本的“恩恤”行为。显然,由于明朝的灭亡使得正统的“华”在东亚失去了统治地位,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统治者这一事实导致了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华”已经不是汉人或中国的专有之物,日本也加强了“华”这样的自我意识。从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来看,清朝的主要着眼点还是在于把日本拉入以清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中的。1647年,顺治帝即又以“浙东、福建平定,颁诏天下”,曰:“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慕夏投诚”,就将之编入它的华夷体系之中。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对“蛮夷”出身的满族实现明清鼎革这一变革充满恐慌。在17世纪的日本,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郑成功广为所知,他被日本人称为“国姓爷”。同时代的日本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剧本《国姓爷合战》以和藤内(郑成功)与吴三桂一起胜利地复兴明朝为大结局,在日本引起前所未有的盛誉,并连续上演十七个月之久。这反映了中国大陆明清交替这一变化给日本带去了多么大的冲击,而剧中表现的明朝复兴更是日本的期望。甚至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藩山还曾预测:清朝既已取得中国,不久将要进攻日本,他甚至向幕府建议有必要囤积兵粮,拟订兵法,作好准备以积极应付清朝的入侵。1673年,当中国发生三藩之乱,日本官方人士“倾闻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之后,非常高兴,感叹道“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真切期望中国“华夷复位”。显然,清朝在试图让日本进入其新秩序道路上无疑十分坎坷。日本与清朝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尽管受到挫折,清朝并没有放弃它的“信念”,甚至还“幻想”日本会仰慕它的“德治”而来自请“通贡”。1682年,清政府派遣翰林院检讨汪楫为册封正使,内阁中书林麟焻为副使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王尚贞。在汪楫、林麟焻等离京之时,康熙在乾清门亲自召见,当时汪楫就如果遇到日本人应该如何对待的问题向康熙专门请旨:“闻海外日本诸国与琉球往来,今皆瞻仰德化。如有通贡之事,允行与否,非臣等所敢擅便,恭请皇上指授,以便凛遵圣谕,临时应对。”康熙明确指示:“若有通贡之事,尔等报部,听部议可也。”
意料之中,日本不可能进行清朝想象中的行动,甚至中国随后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贸易活动也被日本严厉地拒绝了。第一次是1685年。基于郑克塽提供的有关对日贸易有利的报告,康熙命福州总督、部院之官王国安,厦门之靖海侯施琅派人赴日本以台湾土产进行贸易。于是当年清朝官船十三艘,装载着台湾土产皮、砂糖等,在福州武官江君开和厦门文官梁尔寿的监督下开赴日本贸易,结果日本幕府命令江、梁二人率队返回,并让他们转告上级官员,不得擅自再派官船前往日本贸易;第二次是1703年春。浙江商人以“浙江守官”信使的名义,“持土产,将往江户,欲结邻好”,此举惊动了德川幕府。当时的日本将军是德川纲吉,他指示派去长崎的三个官员:“汉商愿交,出于尝试,汝等据理严斥,如有所更聒,一并屠戮,以杜日后之渐。”德川纲吉为了避免和清朝官方往来,甚至要“屠戮”来使。最后,日本的三个官员以江户和浙江之间“水路辽远,彼此疆界,本不关涉”为由拒绝了浙江商人的请求。
自1633年颁布锁国令为止至1703年,日本的“锁国”已经度过了70多年,锁国体制已经成熟。在“四口”维系的对外交往的实践中,日本认为它没有加入中国的华夷秩序圈之内的必要,而“华夷理念”更是日本与清朝疏远的思想基础。但是,是不是在1871年中日建交之前两国就一直处于这样的没有官方交往的状态之中呢?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在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中日官方之间是曾有过交往的,而且这种交往的媒介仍然是日本漂流民。
二、初次的咨文往来与龙牌下赐
正如1644年日本越前国商人漂到中国一样,有清一代有不少航行在海上的日本船只常常因遭遇飓风等原因而漂流。漂流船上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作“漂流民”,在中国的档案文献中,被称作“难番”或“难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漂流中丧失了生命,幸存者有的漂流到了外国,而因为地理位置的邻近和有海洋连接,日本人漂到中国的次数又最多。根据佐藤三郎的统计,在江户时代,有记录的日本人漂流事件至少有105件,而漂流到中国的就有45件之多。但笔者在日本所收集的资料显示表明与中国有关的漂流事件至少有100多件,其余的多为漂到朝鲜、菲律宾、南北美洲等处。到了中国的日本漂流民基本上都被遣返回日本。由于日本特殊的锁国体制,甚至那些漂到中国之外的诸如漂到东南亚的日本漂流民往往也是通过来往于长崎的中国贸易船只送回。
1751年3月,正是大清乾隆盛世之时,日本漂流民又五郎、伊七郎、利兵卫、利右卫门、长助、传六、文治、五兵卫等八人乘坐的“神力丸”因遭飓风漂到福建福鼎县之姆屿地方,接到当地民众的报告后,“役人立刻到船上进行调查,并派员日夜警护。”署理关税抚臣潘恩榘“免其输税,以恤难番”。4月30日福建烽火营参将蓝图庭奉命派拨哨船、差委弁兵将他们送交厦防厅。在厦门这些漂流民被安排住在城市之外的寺庙里面,并给予米薪菜钱等,受到非常好的照顾。(在厦门,日本漂流民传六不幸病死。)因“又五郎等呈恳回国”,厦防厅即派同安县商船户郑永顺把他们送到浙江鄞县。8月21日,日本漂流民到达宁波。当地官厅又立刻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以便“查觅日本便船附搭回国。”
在中国,很早就有救助与遣返外国难民的活动。1737年即乾隆二年,乾隆皇帝发布相关谕旨,标志中国对外国难民的救助与遣返活动走向体制化。谕旨曰:“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漂泊之人船,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可以说,直到清朝,中国对外国难民的救助才开始有定例可循。
按照以往救助日本漂流民的惯例,地方官厅把日本人漂到之事上报总督巡抚,然后总督巡抚上报皇帝,之后再把他们送到浙江的宁波或乍浦,交付给那些前往长崎贸易的商船主带往日本,最后再向皇帝上奏汇报销差,似乎就算大体完成了救助任务。但是,这次日本漂流民漂来中国的时机比较凑巧,“逢今岁圣驾南巡,当又五郎等遭风漂秦屿港之时,正皇上驾幸”。由于遇到乾隆南巡这一特殊事件,于是浙闽总督亲往杭州将这批日本陆奥国漂流民之事面奏皇帝,结果乾隆皇帝“昭赐日本难商各五爪龙牌一面,移浙江全省水陆提台,着令交付商船护送回国”。在特加保护遣返的同时,乾隆还赐给难民“皇赏”的银制龙牌,而此牌还附有其他功能,日本漂流民记到“将此银牌挂于颈上,要小心珍惜,即使遇到贵人,也可不用跪拜”。1752年2月4日,这些漂流民搭乘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郑青云的商船到达长崎。值得注意的是,在带回七枚龙牌的同时,他们还带回中国厦门海防厅官员许氏和宁波府鄞县官员黄氏咨文各一份。
厦门海防厅咨文为:
福建泉州府海防厅加三级纪录四次许为移知事。恭照本朝圣天子文教覃敷,四海禀一统之义,恩膏广被,万方无勿届之区,故凡属外藩倾心向化,恭顺输诚以及遭风漂泊者,无不加意抚恤,多方保护,俾得安全。兹有贵国又五郎等八人,于三月初六日船只遭风漂至秦屿港口。当经福鼎县查明,船内装有草包、咸鱼,约有二十余担。令其写字,写出日本南部金石浦人,饬给薪米,护送厦门馆驿安插。本厅随即讯供通详,奉各宪行令,按名每日给食米一升、盐菜钱十文。移行福鼎县查明船只不堪修整,准其自行变卖,同鱼货卖价钱给该又五郎等收领。内利气一名于五月十三日病故,俱一一抚恤口粮,并优免关税。复恐在厦守侯,又另给口粮,觅舟资送浙江宁波,便船附送回国,此诚天朝柔远深仁。至周至渥。所有贵国遭风抚恤缘由,理合咨明。为此备咨贵国王,请烦查照施行。须致咨者。右咨日本国王。大清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咨。
宁波府鄞县咨文为:
署浙江宁波府鄞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七次黄为咨明事。恭照本朝大覆载以无私,万国仰车书之盛,统胞与于在宥九天,沐日月之光,特沛恩纶,中外曾何异视,重邀宸券,颠连更荷深仁。今有贵国又五郎等船只被风漂至闽省,业经加意抚恤,因乏便舟,恐稽守候,当蒙护送至宁。本县随觅馆留置,给予薪水,病即拨医治痊,另给路费衣装,令商人信公兴、行商郑青云附送回国并将开棹日期通报各县外,拟合咨明为此合咨贵国王,请烦查照来咨,希将又五郎等七人回国日期,借乘交发该行商郑青云,饬令迅即回棹,以便转请题复,事关圣朝柔远至意,幸勿迟滞施行。须至咨者。右咨日本国王。大清乾隆朝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咨。
对于中国的这一行动,日方非常重视。1752年2月7日,护送这些漂流民回国的郑青云船上的童天荣和黄福两人曾被叫到长崎役所,被详细问询日本漂流民在中国停留期间的经历始末。问询中,长崎役所多次提到龙牌。而按照江户时代日本的规定,中国贸易商船的船民按照规定一般是不允许离开本国船只的。经过讨论之后,幕府指示长崎奉行管沼下野守“可以给厦门、宁波两处的官府回咨”。
长崎奉行给厦门海防厅的咨文为:
大日本西海道肥前州长崎镇府下野守源为覆书移知事。夫惟贵国仁網覆世,文教之化格于四表。恭照本邦德泽配天,恤生之意溢于九关,凡编户之民跨历海洋,运输货殖。所以黎庶治生,实系皇化广披而遭厄难者靡不沐其庇荫。……又五郎等人照数收讫。所携咨文并又五郎等口供书业经详悉。此诚贵国怀远之仁,洋洋盈盈,莫以尚焉。因此该商所载货物,即令贸易,格外越例,迅速回棹,以酬效劳。拟谢眷爱之盛。须致回咨者。右复。大清福建泉州府厦门海防厅许爷。大日本宝历贰年壬申贰月念八日。
长崎奉行给宁波府鄞县的咨文为:
大日本西海道肥前州长崎镇府下野守源为覆书移知事。夫惟坤舆肇基兆庶均谣击坏于欣,并我朝同运和气煦育,共承平之德化。……洵膺贵国雍熙之德靡所底止。该商郑青云诚实送到尤为可喜。业将所载各货概令变卖,格外越例,速回棹以酬致劳。此诚贵国柔远之泽光被所施均与本邦象天之仁。如今弁契为此伸谢于诚恳之霈然。须至回咨者。右覆。大清浙江宁波府鄞县正堂黄爷。大日本宝历贰年壬申贰月。
与之前救助和遣返日本漂流民案例大不一样,这次中国的地方官员却得以致咨日本国王。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的朝贡体系中,“咨”这种文书的格式背后具有重要的政治外交含义。何慈毅指出“咨”原来是中国朝廷对等官府机构(二品以上)之间来往文件的一种格式,自15世纪起接受中国皇帝(明朝及之后的清朝)册封的亚洲各国与中国朝廷官府机构(如礼部及各地方官府)之间的文书来往也常常用“咨”的形式。中国地方官员的致咨之举,显然是基于对大清是“华夷秩序”之主、日本是中国的藩属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从中国送去的咨文内容看,很显然是在彰显中国的“仁德”,而“仁德”在古代东亚外交中具有非常强的感召力量,可谓是古代国际关系中的“软权力”。中国地方官员咨文中的“恭顺输诚以及遭风漂泊者,无不加意抚恤”,对日本漂流民“曾何异视”等显然都是用来宣扬圣朝怀柔远人之意,号召日本“恭顺输诚”的。显然日本也非常熟谙东亚外交之道,其在回咨中除称赞清“仁網覆世,文教之化格于四表”之外,更是突出强调日本“德泽配天”,“坤舆肇基兆庶均谣击坏于欣,并我朝同运和气煦育”,突出展现日本的外交地位。刘序枫就观察到:“日方则避免使用日本国王名号,以长崎奉行名义回咨,即日本幕府与大清皇帝的地位相等,避免沦为清朝大中华朝贡圈内册封国的一员。”
三、咨文往来与龙牌下赐的持续与终止
1752年至1767年之前,被中国遣返回国的日本漂流民在得到中国地方官府发放的银制龙牌、或者是黄绫袋的同时,也都向日本带回了中国地方官给日本国王的咨文。日本也都以长崎奉行的名义给予了回咨。1767年之后,中日两国的这种交往再也没有出现过。
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咨文到底是乾隆皇帝的指示还是地方官的个人行为的史料,但是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该咨文及龙牌在随后的几次日本漂流民救助与遣返中仍然被发放,并且咨文发行和龙牌赐予这些政治行为的执行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两个官厅,而是包括厦防厅、宁波府鄞县、平湖县、苏州府等清朝各处地方官厅在内。可以推测,发放咨文的行为应该是乾隆皇帝所知晓甚至是亲自授意的,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与咨文相伴随的龙牌具有“不用跪拜”等皇权才能发挥出来的影响力。但乾隆皇帝的授意很可能不是正式授谕,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之后清朝方面咨文的发放和龙牌赐予因日方回咨行动的停止而立刻中止这一现象。
1753年4月27日在浙江省舟山漂着的日本陆奥国气仙沼村的“春日丸”漂流民回国时带回了宁波府的咨文与“黄绫袋十三个”(不是龙牌),“经过上裁,由长崎奉行给予回咨。”宁波方面的咨文为:
浙江宁波府鄞县为咨明事恭照。本朝德迈唐虞,率土仰车书之盛。恩隆覆载,普天沐休雨露之深,遐迩向化,中外输诚。兹有贵国殿培等十三人船只在洋遭飓风漂流定海县境,……贵国王烦请查咨。希将殿培等一十三人附送。回国日期备文交发该商信公兴。饬令迅即回棹,以便转请题覆。勿迟滞。须至咨者。日本国王。大清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咨。
1753年3月在吕宋岛漂流的日本“福聚丸”后来经浙江乍浦乘坐中国赴日贸易商船于1755年7月2日被送到长崎。他们带回浙江平湖县的咨文和银制龙牌。经过幕府老中协商之后,日本以长崎奉行菅沼定秀的名义进行了回咨。1759年漂流于台湾的“若市丸”带回浙江嘉兴府一个姓增的官吏给的咨文一份和银牌三枚。嘉兴府咨文为:
大清国浙江嘉兴府正堂加三级纪录十二咨曾为咨明事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遵内阁抄奉上谕,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呈贵国王,烦请看来咨,希将幸、平、德卫门等三名送到日期,祈即备文赐覆交给该行商夏时霖迅回棹,以凭转请咨呈题,须至咨呈者。右咨日本国王。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咨呈。日本方面则是长崎奉行藤原定英回复咨文一份,内容为:“大日本西海道肥前州长崎镇府、骏河守藤原定英为咨覆事兹因去年九月有本邦志摩州人民幸平次、庄兵卫、德次郎三名,原系贩粥鬲航海,不料在洋遭风,阅经多日,飘至贵国台湾地方,……为此除饬令夏时霖仍前准行贸易越例,迅速返棹外,拟合咨明,以副至意。至咨覆者。右覆浙江嘉兴府正堂。宝历九年八月十四日。咨覆。”
1762年5月21日在中国南通州水域漂流的日本“福吉丸”则带回了苏州府官李氏的咨文一份和银牌十五枚。在江户幕府的指示下,由长崎奉行石谷备后守给予回咨,大致内容为:
大日本国西海道肥前州长崎镇府备后守藤原为咨覆事。兹有本邦陆奥下总两国人民五右卫门等船只,在洋遭风,……着令该商格外贸易,越例越棹,备咨移覆贵府,并将该商功劳,须至咨覆者。右覆江南苏州府正堂。宝历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覆。
史料表明,中日基于救助与遣返漂流民基础上而产生的咨文往复仅仅持续了以上几次就告终了。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1767年在遣返漂到吕宋的日本筑前国难民的时候,中国船主汪绳武提交了伪造的嘉兴府知府咨文,为日方发觉。从此以后,日本即决定不再回复清朝的咨文。而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因日方没有回咨也随之将咨文转递行为中止。最终,中日双方通过遣返漂流民所建立的这种官方咨文与龙牌下赐关系不复存在。
有意思的是,在龙牌和具有“政治意味”的咨文之中,日本方面似乎对龙牌更感兴趣。在对1754年中国商船带回的漂流到广东惠州府的陆奥国相马漂流民的6人进行调查时,在该调查备忘录的结尾处,调查人员古渡七郎右卫门等人还专门汇报到“没有龙牌”,但没有提到“没有咨文”,这和清初日本对清朝政治举动的强烈敏感形成鲜明对比。甚至直到近代之后的1852年,日本在审讯由中国遣返回国的漂流民时,仍然会问讯他们是否有被赐予龙牌。日本还专门对龙牌作图描绘,并注明“长三分一寸,宽二寸,重一两四钱。”
日本的兴趣关注及其轻易断绝咨文的回复说明日本对与清朝的官方交往不热衷。那么日本为什么又回复中国地方官厅发来的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咨文呢?理由有二,一是对清朝的人道救助行为表示感谢;二是为了方便这些身负中国官府特殊政治任务并为送返漂流民做出贡献的中国船主完成任务及时返棹回航。在1752年第一封咨文到达日本的时候,宁波知府在发给郑青云的护照中写明严格要求郑青云“将又五郎等在途小心照看,加意供给,定限三个月回棹,取领日本王回照,以凭转请题复。事关圣朝柔远深仁,毋得在途逗留越贩,有误期限干咎”。而且,郑青云等在送还日本漂流民后向日本提交的恳请书中也说:“但云等有护照之事,办公紧急,将来回唐,各官府专侯贵国王上批给回文,以便驰京奏销完款。今因洋中风信不顺,稽迟月途,势必违误限期,云等寝食不安,荷蒙王上清心细问难商在唐始末情由,业经亲供据实陈明,今六人平安到崎,已蒙王上亲自查验收回,云等不胜踊跃,早期回唐。”
尽管清朝在咨文中流露出“事关圣朝柔远深仁”的政治抱负,但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立即中止咨文递送行为也说明清政府对这种方式下的对日交往也不那么重视。因为经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大清已经成为“帝国”,步入了它“乾隆盛世”的时代,此时的清朝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所处的中心地位已经牢固。此时期的中国认为它就是“华夷秩序”之主,是一个万国理应前来称臣纳贡的国家。甚至官方在乾隆十六年(1751)修的《皇清职贡考》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修的《大清一统志》上,都很自信地把从未向它朝贡过的日本列为“朝贡国”。显然,此时日本对自己的“地位”的承认对清朝来说似乎并不如清初时期那么重要。加上中国地方官转递日本国王的咨文却由长崎镇府回咨,这些“天朝”的官员显然是不愉快的。但在乾隆南巡的那次指示的惯性下,尽管行咨行动还在继续,但注定持续不久。在日方停止回咨后,清朝地方官厅也很快中止行咨。
四、结 论
乾隆皇帝的南巡是个“恩披天下”的行为,日本漂流民的恰巧到来使得他们也承担了向日本宣扬清朝皇帝仁德的使命,咨文和龙牌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日关系相对安稳的大环境中,日方经过讨论后,也以适当的方式给予中国回咨。清代中日两国在建交前有了颇为罕见的官方往来,在中日关系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但是,日本依然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自己在中国秩序圈之外的地位,在回咨中刻意突出日本的“德泽配天”,也没有按照清朝的期望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给清朝的地方官厅回咨。这和清初的日本对清朝的态度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也暗示当时渐行渐远的中日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和脆弱性。中国的发咨与下赐龙牌仅仅是乾隆南巡这个偶然政治活动引发的一种罕见的政治行为,缺乏实施的持续动力,一旦遭遇挫折就会脆弱崩溃。而清朝的“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更是这种交往没有持续下去的思想动力,“内政既修”的清朝坚信“华风既盛,夷心自然归仰”,希望日本在中国的“不治”之下能“慕夏”而自动归附。这种思想甚至发展到认为对日本更消极的“无为而治”对中国更有利。直到国家间交往密切已成大势的清末这种意见仍然存在,郭嵩焘就认为:“天下事求之过深,其失愈远……明成祖经营日本以召寇,终明世为边患。本朝以度外置之,而海疆肃清。其前之失,皆由求之过深。”清朝这种“不治主义”的外交思想和江户日本时刻对清朝保持的政治距离,加上日本锁国体制的制约,也导致了中日之间的这种咨文与龙牌形式上的往来注定是一种“只开花不结果”的政治行为。经过了短暂的咨文往来与龙牌下赐交往之后,中日再次陷入无官方政治往来的状态,直至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