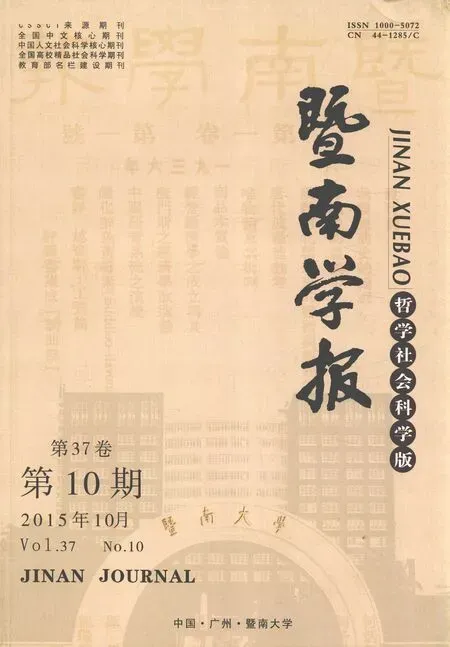1921—1922年厦门海后滩案与中英交涉研究
贺江枫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1921—1922年厦门绅商学等民众群体因反对英国领事强行将海后滩纳入租界,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请愿运动,进而造成中英两国旷日持久的外交交涉,此即谓海后滩案。若相较于清末民初诸多丧失利权的交涉案件而言,厦门海后滩案虽耗时数年,但终能迫使英方让步,民众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国家利权得以维护。学界对厦门海后滩案已有所研究,李禧利用厦门公民会遗留档案对事件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可谓目前最深入的论述,周子峰亦注意到厦门道尹陈培锟在厦门公民会抵制太古洋行活动中所持的包容态度,然而受资料及研究视野所限,该案的缘起、厦门公民会的作用、中央与地方政府态度的歧义及英方决策的变化过程等诸多问题仍有待深化。故而本文试图利用北洋政府外交部及英国外交部的双方档案,重建厦门海后滩案的相关史实,再现厦门民众团体、北洋外交部与英方彼此的主张及互动过程,以期对北洋外交的复杂性与局限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厦门海后滩案的缘起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在通商口岸内,开辟固定区域为英人居住经商之用,此即英租界的由来。租界初始选址于厦门水操台南校场,后因英领事以“距离码头过远,于商务上诸多未便”为由,1851年改为“自岛美路起,至新路止”,“除去筑前后公路四丈外,直长五十五丈,横宽十六丈,周围见方一丈,年纳租价库平一两”。因租界地处临海位置,租界前方海滩遭海水冲刷,不断淤积,“年年膨胀”,形成大面积的滩涂陆地。英人遂起觊觎之心,欲将海后滩地纳入租界。1877年英国和记商行试图填筑海滩,“当填筑之始,美人出而抗议,”厦门道尹司徒趁机“利用之,以拒绝英人,自行填筑,作为公路,不收英人地租”。1878年厦门道尹与英国驻厦领事就海后滩问题签订章程六条,试图以条约的形式确保中方的利益,结果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双方议定的章程中英文版本表述存在较大歧异,使得中英就海后滩归属权的认知争议时现。
海后滩章程六条的中文文本为:
一、该海滩填筑后,作为公地码头,不得别用。
二、查新填海滩是英国租后地出入门户,除后地租主之外,永远不租赁他人,如要租应先尽英国公平价值租赁。
三、新填海滩应照所批图式建作。
四、填筑完好,后面洋商原有利益仍须照旧保护,均不别建名目遮蔽后面利益。
五、凡要搭盖蓬寮等件,须会同英领事官商酌,不损坏后地各英商利益,方可搭盖。
六、填筑之后,该地接拢已经租地,由地方官托界各洋商代为经理。
英文章程同样为六条内容,但与中文文本的含义并不一致,尤其是英文本第六条之规定:“当填筑完工后,海后滩应被合并纳入已被当地官方托付租赁的部分,并由租界内英国商人妥为照料。”意即为已填筑之海后滩地将被并入英租界,与英租界视同一律。而中文本仅是该地接拢租界,由英商代为管理,并无并入租界之意。二者文意的天壤之别,造成此后中英双方就海后滩地的归属各执一词,争议时现。如1907年电话公司计划在海后滩地竖立电杆,英方坚决阻止,表示“立约纳租,方许设立”。待至1918年9月,因“闽粤交兵,厦地戒严”,英方更变本加厉,“藉词保护英商”,命令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海后滩地,“将左自太古栈起,右自义和行起,均至海止,连同海后后面之史巷路及番仔街尽处三处公路,一律筑墙设隘”,“大书大英租界地,闲杂人等不许乱进”,“又树杆升旗于官填海滩,一时交通杜绝。”
面对英方的单边行为,历任厦门道尹均试图据约力争,多次向英国驻厦领事抗议:“我国只认英国有租地之条件,并未订有租界之明文,且未将该海后滩地出租英国,英国亦始终未经议租,是该地为我国有完全地主之权”;英方则毫不相让,明确声明海后滩地与租界无异,“该英国租界系自七十余年前由中国政府交付英国政府,除经两国政府磋商允许外,本领事无权放弃,不能以现在状态变更”。厦门官民面对傲慢强势的英方,虽多有抗议,但亦是无果而终。为收回海后滩地,福建地方政府亦曾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希图由中央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直接交涉,挽回利权。1920年1月26日,外交部驻厦专员胡惟贤、福建督军李厚基先后致电外交部,详细阐述了海后滩案的来龙去脉,要求外交部“严重向英使交涉,以重主权,并希见覆”。然而外交部对于此事并未特别注意,迟至1920年12月,厦门地方官员仍旧“未奉指令”,新任外交部驻厦交涉员唐柯三无奈于12月13日再度致电外交部部长颜惠庆,强调“现在厦门地方安谧,秩序早经恢复”,海后滩“既非租界,则当由根本解决”,“应请钧部向驻京英使交涉,先将民国七年在岛美路头及新路头一带所设围墙铁门一并拆卸,并将厦门海后滩租界名义取消,以杜蒙混而符约章”。唐电去后,再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正因外交部对厦门海后滩案的视而不见、反应迟缓,使得中方收回海后滩地相关权利遥遥无期。待至1921年英商太古洋行在海后滩强行修筑栈桥码头,引发民众的反英风潮,此案才缓慢地进入外交部视野。
太古洋行修筑栈桥码头一事,最早是1900年6月由英方向厦门道台提出,表示太古洋行希望在海后滩地修筑栈桥码头,以便发展英租界的海运交通。清政府对此并无太大异议,随后太古洋行以向当地官府缴纳一万墨西哥银圆为代价,获得该项权利,并就栈桥码头的管理及归属问题,与厦门道台订有条款七条。然而1910年该栈桥因遭风暴损毁严重,当年7月20日英领事Tours特意致函厦门郭道台:“我从太古洋行处得悉很久之前他们建造的栈桥已经被风暴摧毁,现在栈桥处于一个极坏的、残破的状态。鉴于它目前所处的危险情况,太古洋行计划立即将其拆除,并在将来适当的时间重建,太古希望这件事能够有恰当的记录。为此,我恳请你相应地记录此事。”1910年7月27日,厦门郭道台回函英领事:“我已收到您的信函,知悉太古洋行的栈桥遭到损坏,即将拆除,并将在之后某个时间重建。我已通知海防厅相应记录此事”,实则默许了英方请求。然而问题是,太古洋行之后十年并未提及重修栈桥码头一事,却突然于1921年5月兴工修建,恰巧此时厦门各界民众因英国强行将海后滩地并入租界而愤怒不已,累及的矛盾与冲突便由此而发,“英人在厦门我国自筑之公路竖悬界碑,俨欲据为租界,太古洋行乘交涉未了,复在公路前面海滩强筑码头”,此举直是“侵我主权,蔑我国体”。一场轰动中外的闽人收回海后滩地的反英风潮迅即展开,“至此次太古洋行擅筑码头之导火线,厦人乃更为激昂,收回管理权之运动乃大炽烈”。
1921年6月厦门总商会、教育会及士绅代表开会讨论,认为“前清光绪四年兴泉永道与英领事议定填筑海滩章程六条,其第一条载明该海滩填后作为公路码头,不得别用,考英领所批议约亦声明现在中国国家自填,作为公路码头”,“本案具在明明,英人即强指为租界者,确系中国自填自管之公路,断难指鹿为马。夫公路租界之辨别昭然,若此岂能又在公路前面重占海滩,自由强筑码头,外人藐视吾国已极,言之令人发指”,决定动员厦门民众,收回海后滩地及拆除太古栈桥码头,“对此两层,不达到目的不已”。6月6日厦门总商会、教育会等联合致电北洋政府国务院、外交部,要求政府与英国驻京公使严重交涉,“饬驻厦英领将海后公路围墙旗杆等项,即日撤去,还我公路名义,一面先饬太古洋行将筑造码头一事即时停止工作,以保国权而平公愤”,并表示如果政府交涉无果,“人民另筹对付办法”。6月21日,旅京福建同乡会就厦门海后滩案致电外交部,要求外交部“迅向英公使严重交涉,否则内地随时均可认作租界侵犯主权,莫此为甚,除钞原函电呈阅外,合并函请迅速据约力争,以全国体”。
厦门民众的抗议举动,使得外交部不得不有所行动,遂令驻厦交涉员唐柯三与英国驻厦领事展开交涉,“太古洋行何得又在该地擅筑码头,请即谕令停工”,但英方“强词夺理”,以1900年致厦门道尹函件为依据,表示“当年柴桥拆卸时,曾经函知前兴泉永道声明,将来再行建筑,有案可稽。当时既无异词,此时何得失信”,且告诫唐“厦门各社会对于此案有提议抵制之说,请由官厅负责”。此时英方实则外强中干,6月13日福建旅沪同乡会致函太古洋行,明确指出太古此举可能引发的抵制风险,“贵行竟不顾国际惯例,已在该公路前面海滩内强筑码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商民异常愤激。查贵国人士来华最早,邦交素笃,若因兹事激动公愤,亦殊非贵行之利,万恳贵行照会厦门分行,于本案未结之前,停止码头建筑工程,以免发生意外事件”。6月21日厦门交涉员唐柯三又向英驻厦领事Tours表示无从压制民众抗议:“厦门总商会、厦门教育会完全有权利召开公众会议,即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国家主权。我无法阻止是次会议的召开,厦门商民与太古洋行有多年友好的商业往来,并且他们与太古洋行的纠纷并非煽动的结果。”厦门官方及民众的态度,使得英领事及太古洋行顾虑重重,试图采取让步措施。英驻厦领事先是向厦门道尹郭培锟商议,“承认该码头归与中国,唯海后滩应作另案,”未获郭同意之后,“面对这种即刻发生的抵制风潮及中国地方政府拒绝承担保护英国公司的行为”,1921年6月21日英国驻厦领事致函太古洋行经理,“同意将建筑工作暂停两周,以待北京公使的指示,”23日太古洋行暂停建筑码头。
二、厦门公民会与海后滩案
厦门民众的抗议风潮并未因太古让步而终止,1921年6月25日厦门绅商学各界组织成立厦门公民会,并推举洪鸿儒、卢心启为正副会长,主张将海后滩案彻底解决,“此案根本办法务将海后公路收回,取消租界名目,俾此后免生枝节”,并于次日电请外交部“据约力争,以平众愤而保国权”。为促使外交部明晰案件始末、早日将海后滩案彻底解决,7月24日厦门公民会致电外交部,“现已公举代表,不日晋京,带呈图卷面陈情节,藉明真相而便交涉。”
1921年9月13日厦门公民会决定推派代表厦门总商会会长黄廷元、教育会会长卢心启赴京请愿,初拟三项主张,不仅要求收回海后滩地,更对英国在厦租界权利提出质疑。第一,“辨明租界、租地之权限”,“海后滩后面接连市街,建设洋楼之部分,……此等地段果为租界与否,尚属疑问,如能划清权限,不与上海等处租界一例齐观,则前面之官填海滩无容英人干涉,自不待言。即以租界论,英人于条约上无完全之行政权,亦不能认为同等租界”。第二,收回海后滩地,“前面海滩既为官填,英人又未纳租,并无所谓租地,以光绪四年之草约、正约为根据,逐层议驳,则官址与租地区域自明”。第三,划明界限,“租地与官地区域载在地图,俱有丈数要求,英使派员会勘清丈立石为界,不至以蒙混之弊,再启纷争”。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921年10月厦门公民会代表黄廷元、卢心启北上赴京接洽海后滩案的处理。黄、卢到京后,计划首先向英国公使艾斯敦提交《厦门海后滩说略》、《厦门海后滩交涉说略》等文件,希望艾斯敦能够“照约公平解决,不惟厦民之幸,亦贵国商人之幸也”。
为避免交涉范围过于宽泛,黄、卢主动对9月份该会初拟的三条主张进行了变通,将首条辨明英租界、租地之权限删除,集中就收回海后滩地与划明界限展开交涉;并且不再回避1876年海后滩章程中英文本有关第六条的差异,为此特别声明:“该章程第六条所谓接拢已经租地者,系连接已租给英商之地,所以明其为中国自填官地也,不得以合并或归并之意误解”,并依据租地须有地租的常理反驳英方的归并说,“如当时愿合并租地,则中国何必争回自填,又租地有租地银,英商对于新填滩地未曾完纳此项租银,则其非租地可知”。此外,黄、卢为说服英方归还海后滩地,特意就保障英方在海后滩地的利益,做出部分妥协,声明海后滩地由中方收回后,“英商有促进商务利益地方之作为,均可商量允许”,并且“中国不有所更张,以妨碍英商面前之利益”。黄、卢的提案看似有理有据,现实却是一厢情愿,无从实现。
1921年10月26日,外交部部长颜惠庆、通商司司长周国辉就海后滩案,约见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参赞巴尔顿,英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提出“闻厦门人民派有代表来京,不知贵总长是否接见”,“不妨到本馆或在部一谈,或可以解释一切误会”。此时英驻华公使艾斯顿态度较驻厦英领事Tours要强硬得多,认为厦门公民会的抗议行动“系受他人蛊惑怂恿”,明确声明“我并没有准备就这一个长期存在的协议的合法性与中方展开谈判,尤其是在这些不负责任的煽动者面前”,指示Tours太古洋行修筑码头不必暂停,“应即复工”。1921年11月太古复工,一石激起千层浪,厦门民众面对英方的无理行径,先是于11月4日致电赴京代表,请其转告外交部“太古栈桥不听制止,已兴工,恐酿事变,迅与英使交涉”,在未获回复的情况下,11月7日厦门公民会召开市民大会,“到者万数”,决定收回海后滩地将“诉之自力,先实行抵制,大部若不迅速抗争,将有第二步对待”,10日又致电黄、卢代表,告知抵制风潮平息的最低限度:“非得栈桥停工及京派大员会勘海后滩消息,无从劝解。”厦门公民会的激烈抗议,进而刺激英方进一步的强硬措施,11月16日,驻厦英领调集兵舰七艘来厦,强行登陆,并在太古洋行大楼“架炮示威”,试图以炮舰政策迫使厦门民众妥协。
正当厦门民众与英方激烈对峙之时,1921年11月20日黄廷元、卢心启在外交部通商司周国辉司长陪同下,会晤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尔顿。巴尔顿告知向黄、卢二代表“厦人已发生抵制,海后滩无磋商之余地”,若代表电令厦门民众停止抵制风潮,则或有转圜余地,承诺海后滩地“旗牌墙均愿撤去,经理不善亦愿改良”。黄、卢当即回绝巴尔顿的要求,认为英方毫无和平解决的诚意,“口头官话,未有诚意,太古行又在代表到京时,背约兴工,代表对于厦人已深抱愧,尚有何词,以劝厦人”,提出发电最低限度条件是“唯有栈桥停工,不过一二星期,便可全局解决”,或者“栈桥纳租、旗牌墙同时撤去”。最终,“交涉无效”,双方不欢而散。同时,厦门紧张形势日甚一日,11月19日太古洋行造桥华工朱某被割伤耳朵,英领事强指泥匠林某为凶手,将林某私行殴禁,更怂恿造桥工人纠众持斧寻仇,召集军队登岸,致使厦民“群情愤骇,深恐发生重大事变”。面对抵制风潮随时可能失控的局面,公民会代表黄廷元、卢心启虽欲向外交部部长颜惠庆转达实情,即便有此前郭则沄引荐,亦是求之而不可得,“连日求见,竟未邀允准,莫测高深,殊怀危惧”,慨叹:“长此放任,万一演出惨剧,厦民固不足惜,其奈国权领土何哉!”11月23日再次致函颜惠庆,“钧长伟国肩钜,外交责无旁贷,坐视疮痍,亦于令名有损,代表别无要求,愿得钧长一言,以为进止,弱国后盾固不足言,然正当之抗议,谁得而禁之!”可惜函去仍旧毫无回音。至此,厦门公民会代表赴京交涉已告初步失败,但厦门民众抵制风潮并未因此终止,反呈不断扩大之势。
“厦门方面似已一致与该行脱离商业上之关系”,1921年12月1日厦门公民会决将抵制目标集中于太古洋行,“一、不乘太古之船;二、客货不装太古之轮;三、华人不代太古装卸货物”。太古码头工人一律罢工,“连日由上海装去之货,不但无人搬运,且办货商家已拒绝该行之运货提单,将装去之各货,一律退还。”与此同时,厦门公民会通过地域乡情的人际网络,将海后滩案的实情电告东南亚的福建华侨及京沪各地福建同乡会,以获取闽人广泛支持。12月13日厦门公民会致电旅沪福建同乡会:英使“恃强欺凌,厦人坚持抵制,望尊处迅予助力。”12月18日,旅沪福建同乡会迅即召开会议讨论海后滩案,“旅沪闽绅、商、学各界到者三百余人”,初步达成抵制方案。待至12月22日,旅沪福建同乡会再度召集沪市报界人士、福建广西两省重要同乡团体等百余人,共商海后滩案抵制方案,提出海后滩案解决三项原则:一、收回该地管理权,由我国警察保护;二、英国旗及围墙应即拆却;三、交涉未了前,太古洋行停止建筑码头。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要求“致电警告北京外交部,如交涉自损主权,国民决不承认”,并分电太古洋行上海总行及北京英公使,请其速电厦门英方退让,更通过三项抵制太古洋行的办法:(一)由该同乡会与泉漳会馆即调查该滩工人之工头,以便同上海工商友谊会设法劝告工人相助抵制,并为工人另筹生计。(二)推请代表赴招商局另派船往来厦沪汕间。(三)太古总行无退让意,定由全国各团体一致抵制太古洋行行业。
不容忽视的是,自五四运动之后,商人外交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领导组织之下,“从此前的萌发阶段进入基本成熟阶段,并在中国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2月23日,福建总商会以厦门海后滩案“亟应请求一致援助”为由,提请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召开临时大会,并获决议一致通过,“此案关系我国领土主权,亟应呈请外交部与英使严重交涉,务令将越界建筑及标识等即日拆除,万勿迁延,致生纠葛”。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当即致电外交部:“英商在海外滩地越界建筑一案,请向英使严重交涉,以保全领土主权”,使得外交部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另一方面,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开禁与通商口岸华工贸易的盛行,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华侨出入境的高潮,待至民国时期福建华侨总数已达数百万之众,华侨在近代闽南侨乡的地方政局及现代化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中,均呈现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厦门公民会亦将海后滩案交涉始末电致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菲律宾、爪哇、新加坡等地闽南华侨“咸深愤激”,纷纷致电外交部“恳与英使严重交涉,力争主权”,并在当地掀起抵制太古洋行的风潮,如爪哇港华侨自11月开始采取抵制措施,凡是运往厦门的货物拒绝由太古轮船装运。太古洋行从厦门开完汕头、新加坡的立南号轮船更是无货物可运,华侨亦拒绝搭乘该船出洋。同时太古自香港开往菲律宾的航线,因大部分船员为厦门人的缘故,业务因船员罢工遭受较大影响。在厦门公民会的运作与呼吁之下,厦门海后滩案由地方中英交涉事件,转变为海内外闽籍华人普遍关注的全国性外交悬案。抵制太古洋行风潮迅即在国内多地蔓延,如汕头民众自1921年12月21日起,在学生联合会的带动下,“遍发传单、抵制英货”,规定汕头出入口货不得装配太古船、来往汕头搭客不准搭太古船、内地各货不准入太古栈等,违者照货物价值十成取罚,或对接待太古乘客的客栈、旅馆,每名罚银五十元。
厦门公民会之所以能够掀起大规模的抵制太古风潮,福建及厦门地方当局的默许与支持,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亦是重要原因。厦门道尹陈培锟认为英方此举“是不特占已填筑之官路,并侵未填筑之领海,蔑视主权已极”,对厦门公民会赴京请愿极力支持,在公民会代表赴京前,还特意致函其姻亲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黄君廷元、卢君心启代表晋谒外交总次长,面陈情形,惟总次长政务殷繁,非有先容,难期接见”,请郭向外交部代为引荐,以便代表赴京请愿能够确有实效,“拟恳台端允予介绍,并随时指教”。随后经郭联络,外交部部长颜惠庆答允由通商司司长周国辉代为接洽。
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更是置英方抗议于不顾,对厦门公民会组织的抵制风潮多有维护。当12月20日厦门英领事会晤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请其取缔抵制风潮时,李厚基明确表示“他不能强迫人们去和任何特定商人做生意”“本案已在京交涉,如能早日归结,所有一切风潮,自能平息”,即便英领再三请求,李仍不愿直接表态,仅答允“致函厦门道尹,用善言劝谕商民,静候公平交涉,勿得轻举妄动”。而外交部部长颜惠庆、国务总理梁士诒在英方压力之下,均曾致电福建督军李厚基,令其消弭抵制风潮:“转饬地方军警严加防范,静候中央解决。”李厚基在回电中却反驳道:“该处商民尚知守法,不致发生逾轨举动。”北洋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威处于弱势地位,各省多有掌握实权的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事件的处理,往往是鞭长莫及。李厚基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外交部亦无可奈何。英方对福建地方官员无法消弭风潮极为不满,“该地方官等畏惧学生与商人,虽奉有中央训令,嘱其平息风潮,而实未展一筹,亦不照普通手续出示晓谕,对于中央则一味粉饰,致贵部无从得此案之真相,殊与此事之进行有碍,”“中国地方官玩视贵政府训令,致英商受损甚巨,此等官吏未能称职”,要求中国政府“另简能员”。外交部无奈只得令该部驻厦交涉员唐柯三去职,新派交涉员刘光谦赴厦周旋。
三、中英外交谈判的僵局
1921年6月太古洋行修筑栈桥引发海后滩案后,福建地方官员及厦门绅商各界均曾多次致电国务院、外交部,呼吁中央政府迅即组织交涉,收回权利。在各方压力之下,1921年10月5日,外交部部长颜惠庆正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现在厦门绅商各界深知土地主权不容抛弃,特派代表到京请求交涉,如不遵照条约,早予解决,万一激起风潮,于中英睦谊实为无益。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美意,速饬驻厦领事将海后滩所筑围墙及所标大英租界字样,迅行撤除,以符成案而息纷争。”10月26日,艾斯敦在与颜惠庆会晤时,表示海后滩地“无甚关要,多系误解,似无正式照会之必要,尽可从长讨论”,似乎艾斯敦对海后滩案并不过于关切,实则不然。即如艾斯敦所述,“显而易见的是,控制海后滩对于任何租界地而言,都有着必要的意义”。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亦赞同艾斯敦的看法,“我完全支持你的观点,并且授权你可以根据个人判断起草临时声明。”海后滩地相较于英国在华星罗棋布的众多租界,或许微不足道,但厦门民众力争收回海后滩地利权的行为,对于英国力图维持不平等条约体制而言,破坏力则不容小觑,故而艾斯敦初始态度极为坚决,几乎毫无让步余地。
1921年10月26日,艾斯敦告知颜惠庆:海后滩地“自填筑后,久为英国管理,为租界之一部分。前年因闽粤战事,华人多麇集租界,故本国领事因故缔防卫租界起见,建筑围墙,设置铁门,与他埠英国租界之建设相同,并非侵占行为,且门隘平时不关,绝无阻碍交通情事”,厦人反对围墙铁门之设,毫无道理。“此填地若非租界之一部分,何以英人管理数十年,全无异议。”颜惠庆提出此点系光绪四年章程英文翻译错误所导致之误解,英方翻译“一八七八年之约中,所云未免错误”,“委托经理并非并入租界,此事甚为明显”。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尔敦随后亦承认“海后滩地面问题,实因一八七八年约中英文之Incorporate与中文之接拢二语解释,不无出入”,但强调“兹事重大,须由两国政府互允修改,方合普通手续,不宜于此交涉未了之际,随意修改”。
外交部鉴于英方态度强硬,为使海后滩悬案早日完结,11月19日遂采取变通办法,向英方提交六款善后草案。该草案强调尽管海后滩地为中国官地,但管理权可由租界英商转为厦门海关税务司代理,海关仅负责海后滩地的卫生、道路维护及秩序安定等,在租界英商相关利益将获首先保障的前提下,任何人可以自由通行海后滩地。同时,英领须拆除围墙铁门,并将英国国旗移至租界之内,太古栈桥在向中国政府纳租之后准许建设。英方强调“倘不改英人经理之权,方可商议”,对海后滩地管理权改由海关税务司代理一款难以认同,12月10日又重拟善后草案四款,条件极为苛刻,不仅明确声明海后滩地属于英租界的一部分,且当英方认为必须戒严时“可封锁该公路码头之一部分或全部分,禁止人民或车马通行”,更要求中方押解人犯、集会游行等活动须经英领事同意后,方准通过海后滩地。如果中方同意上述条款,厦人抗议的围墙、铁门,英方认为“无保留之必要”,可以拆除。
中英双方各自所提草案,分歧极为明显,但外交部却较为乐观,甚或在给李厚基的电文中,夸口外部所拟善后办法六条,“虽英馆未能逐条均允,惟探其口吻,对于撤去墙围及大英租界国旗等,似尚可以就范”。外交部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英方承认海后滩地为中方官地的前提下,促使英方拆除海后滩地的围墙铁门,以便消弭厦门风潮,至于海后滩地是否由中方直接管理,尚在其次。若考虑到近代中国海关各税务司长期由英人掌控的现实,外务部所提由厦门海关税务司代理的主张,与由租界英商代理并无二致。即便如此,英方仍强调难以接受,为尽快达成协议,外交部再次做出让步,“如至不得已时,即虽可委托其继续经理,但亦须分清权限”。12月22日将“厦门海后滩善后办法兹行修正,改作五条,均与彼此会商意见相符”。新拟五条善后办法不再提由厦门海关税务司代理海后滩管理权,而是仍旧委托租界英商继续代为经理,并放弃太古修桥纳租的条款。
厦门公民会在得悉外交部新拟善后草案之后,强烈反对,1922年1月6日通电全国,“海滩案,外部提文,概不容纳民意,丧失反较光绪四年原约更大,计惟撤回代表,自谋对待。”10日厦门公民会更与旅沪福建同乡会、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旅京福建同乡会、旅京福建自治联合会联名致函外交部:“不能承认贵部所提之五条件,请即牒知英使,将从前提议条件根据公民民意取消,作为无效”。抵制太古洋行风潮因之更趋激烈。此时无论是厦门公民会,还是英国驻华使馆,均互不相让,“各走极端”。厦门公民会“仍很固执,”“非候飞桥停工,不肯取消抵制”,英方则坚持“非取消抵制,不肯续议海后滩善后办法。”外交部一方面因中央政府的弱势权威,无法电令福建地方官员切实消弭抵制风潮,另一方面又无能力促使英方就海后滩的主权问题让步,最终只能使得海后滩案交涉旷日持久、悬而未决。
艾斯敦认为海后滩案“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中国人继续愚弄我们的代表”,故而向英国政府强调“在目前中国这种状态下,学生煽动者视抵制风潮为有效武器,可以凭借任何借口,将之有倾向性的利用起来。除非我们反击,否则必定严重损害我们的利益”。1921年12月24日,艾斯敦在会晤颜惠庆时,告诫颜:“贵国政府若再一味延宕,无切实办法,本使将视为有伤两国友谊而报告本国政府,以为自由行动之准备。如元旦不便进公府觐见是也”。12月31日艾斯敦正式照会颜惠庆,不再参加元旦觐见总统仪式,颜表示“不能向总统报告,因社交活动必须与官方的分开”,艾斯敦并威胁道:“太古洋行所受损失甚巨,应由中国负赔偿之责”。颜惠庆被迫于1922年1月2日派私人秘书与艾斯敦会谈,艾斯敦“拒绝同中方就海后滩案讨价还价”,但在颜持续恳求之下,艾斯敦表示如果他能够看到颜明确致电福建督军,令其消弭风潮,或许他会重新考虑觐见之事。中英觐见风波遂即化解。
即便觐见风潮得以化解,但厦门抵制风潮的持续,仍旧令英方大为恼火,恰巧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在美英支持下,有望将日本在山东的各项权益收回。为压迫中方退让,1922年2月15日,艾斯敦向颜惠庆表示,“此次华盛顿会议,英国曾极力赞助贵国,不料贵国现仍有排英之举”,英国外相要求“除非贵国设法速将厦门各处之抵制英货风潮制止,本国则不得不改变对于贵国的友谊态度,至于贵国在国际上之志愿,敝国亦将不再过问”,若抵制风潮继续扩大,“敝国对于退还威海卫之允许,势必重行考量。”2月19日,驻英公使代办朱兆莘给外交部的报告,更加深了外部对英国拒绝交还威海卫的担心。英国外相明确告知朱:“英伦对华美意,可以近事为证。迄今态度如何,是诚憾事。损失一层甚巨,坚持前议,完全赔偿”,“风潮一日未息,威海卫一日不能开议”。3月2日驻英公使顾维钧再次致电外交部,请将海后滩案“设法早为了结”。外交部此时感到海后滩案事态危急,已至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
四、英方妥协与海后滩案终结
就在驻华英使艾斯敦向外交部强硬施压,以威海卫交换问题压迫中方退让之时,英方内部对海后滩案的善后亦存在分歧,1922年2月16日英使馆参议克某在与颜惠庆会谈期间,明确表示“本参议可以条陈艾公使,若厦门人民立予停止抵制太古,则本馆当预备种种之让步”,“万一铁门必须拆去,亦可商量。然不能以抵制英商、逼我就范。现在本国新任领事已有全权解决此案,只要先罢抵制英货举动,然后两方即可谈判让步,本国方面对于此案自有公道办法”。究其原因,则与太古洋行的态度转变有莫大关系。
海后滩案所引发的抵制风潮,对于太古洋行而言,可谓是灾难性的。太古轮船公司自厦门开往牛庄、烟台、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汕头至天津、上海、汉口、芜湖、厦门、香港、广州等地航线,因抵制风潮的缘故,无货可运,均被迫停航。太古轮船公司惊呼“如果问题这样持续下去,而没有得到友善的解决,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将有更多的太古轮船公司业务受到影响,并且那绝不是不可能的,它将迅速波及我们在中国的所有利益,甚至将影响到太古糖业公司的精糖销售业务”。早在1921年9月,太古洋行对于是否重启暂停的码头修筑计划,就颇有疑虑,“我们并不希望经历一场抵制风潮,因为之前的经验已经很清晰的告知我们,它将不可避免的向所有方面传播,并在任何情况下引发巨大的损失”,一度试图采取让步措施,“我们希望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付给他们空有其名的地租,以便获得修建码头栈桥的允许。”然而英国驻华使馆并不如此认为,指令太古继续建筑码头,结果即如太古所预料的那样,“目前抵制风潮对太古而言,已成为一种灾难。”1922年1月14日太古轮船公司经理John Swire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表示太古轮船公司正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正在香港至上海的航线上,同日本人的轮船公司进行激烈的竞争,并且在这个夏季时期我们与其他大的轮船公司也遇到了麻烦,他们正希望切断我们在中国沿海的贸易”,特别强调“太古轮船公司经营着目前英国在华沿海地区最大的贸易,如果我们遭遇损失,意味着整个英国的地位亦将遭受损害”;建议伦敦直接致电英驻华使馆,指示他们采取所有的措施,以使得太古摆脱抵制风潮的麻烦。2月6日,太古轮船公司经理John Swire再次致函英外交部,“我正在等待您的急件”,“我们必须向您重申目前太古所遭受的严重损失”。2月16日,Victor Welleglen回复John Swire,表示“我已经指示外相乔治·寇松,请其将您的信函转至中国的外交部,待其回复之后将与您联系”,“同时中国外交部已经答允采取各种措施,用他们的权力使得抵制风潮尽快结束”。
与此同时,上海工商各界纷纷致电太古洋行,对其形成不可忽视的压力。1921年12月25日上海广帮慎守堂致电太古洋行,劝其让步,“敝堂特为最诚恳的友谊劝告,务请贵行顾全我国舆论,笃念商帮情谊,速为让步,以免有伤感情,否则敝堂亦国民一分子,惟有与厦门帮各团体,取一同之态度”。1922年1月3日,上海杂粮油饼公会平时贩运杂粮油饼等货,大多由太古轮船转运,亦致电太古洋行“迅即让步”。太古洋行避免抵制风潮进一步扩散至上海,决定将建筑码头栈桥暂停,并于1月17日公开复函广帮慎守堂及杂粮油饼公会,表示让步,“关于厦门建筑飞桥一案,现经商妥,完全停工,兼已于今日电饬驻厦敝分行查照办理”,“事已就绪,不久即有相当解决之希望”。太古洋行暂停修筑码头栈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厦门抵制风潮,“民气缓和,不至别生枝节”。新任厦门交涉员刘光谦到任后,“见厦门各地方代表,即将钧部致李督军删电意旨,切实劝导”,2月18日厦门公民会决议暂停抵制两星期,“并商经陈道尹出示谕禁”。2月22日,外交部再次致电刘光谦,告知英方准备让步,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以抵制为要挟,“在我即应趁此转圜,万不可再走极端,致去解决之期渐远”。
太古洋行此时似乎显得更加急不可耐,希望抵制风潮尽快结束,“2月18日中国人提出暂停抵制风潮两周,以便英国政府能够与中国官方就海后滩争议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艾斯顿却通知中国人不能讨论海后滩问题,直到抵制风潮完全结束”,2月23日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表示严重不满,“拒绝谈判将严重损害中英友好的关系”,“艾斯敦采取的这种顽固态度,在我们看来至少是非常不幸的”,太古强烈要求英外交部改变指示,命令艾斯敦“允许两个政府就海后滩案立即展开商议,并且如果由于英国政府企图迅速达成协议致使中国政府递交的草案最终失败,风潮将无限期的持续下去”,建议英国政府立即采取让步措施,“中国政府提供的草案看上去对解决争议提供了一种可能,尽管他可能对双方的面子造成一点损失”。太古洋行建议英方应采纳中方的提案,却又是英政府暂时难以接受的,故而3月3日,Victor Welleglen明确告知John Swire,“我已经指示乔治·寇松,请其代为通知您,英国驻北京使馆仍将拒绝同中国讨论任何有关海后滩案的事宜,直至这个由地方军阀支持的抵制风潮彻底结束”,批评太古洋行的建议不合时宜,“非常遗憾的注意到贵公司目前所持的态度,看上去不能够给艾斯敦提供强力的支持,以便海后滩案获得满意的解决”。就在太古强烈建议英方采取让步措施的同时,新任英驻厦领事Eastes通过与厦门当地英商及中方官员的广泛接触,了解到“英商一致认为厦门民众之所以态度坚决,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被严重伤害的感觉,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解决的办法,无奈只得发动抵制风潮直到我们同意拆除铁门围墙”。同时,Eastes鉴于厦门英租界面积非常之小,仅仅长180码、宽70码,由十排作为办公的房子和仓库组成,没有外国人住在租界内部,“所有外国人都住在鼓浪屿岛上”,认为铁门围墙“可能在1918年福建南北战争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在现在不应该被考虑成是必要的措施”,强调将铁门围墙拆除并不意味着此举将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故而建议向中方主动让步,拆除围墙铁门、移走租界标示及英国国旗,以便抵制风潮早日解决。
当然最不容英国政府忽视的是,中国国内反英风潮的蔓延。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由于港英当局态度强硬,罢工工人遂即增至十余万人,约万余名海员陆续离港回广州。罢工使得香港海运、内河航运中断,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几乎完全停止,生活用品来源断绝,物价上涨,东方之珠瞬间成为“死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破坏性影响无疑加剧了艾斯敦对厦门抵制风潮的忧虑,2月22日艾斯敦就已致信英国外相乔治·寇松,表达他的这种担心,“由于香港的海员大罢工,目前已经持续长达五周时间,并使得整个南中国海沿岸的海洋贸易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厦门抵制风潮目前虽然没有造成如此灾难性的结果,但或许将来它会以其他方式出现”。艾斯敦向英外相建议是时候该采取必要的让步措施,“在我看来,非常有必要使得抵制风潮在海员大罢工结束之前解除”,他已令厦门海关税务司司长Macoun从中居间调停。中英围绕海后滩案的谈判再次展开。
1922年3月英方最终做出让步措施,“由英领撤除牌墙,为公民会取消抵制之换件”,厦门公民会欣然接受,通电全国取消抵制,排墙撤除“实行之日,关埠商民同声欢颂”。至于海后滩地的经理权等各项问题,则由外交部驻厦交涉员刘光谦与英驻厦领事Eastes继续商议解决,“光谦力与磋议,并晓以公民团等急切要求,众情莫遏。若再稽延不结,将来激烈风潮势必重起,双方谁任其责”,1922年8月19日,中英双方达成海滩善后办法三条。1922年10月12日,中英双方正式签订《海后滩案善后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一)英商太古行建筑飞桥应照从前位置,并遵守光绪二十六年所会订之八条章程,并于重修完竣后,因飞桥越中国领海之便利,每年由该行缴纳租费大洋二十元,交驻厦英领事转付中国地方官。
(二)中国地方官承认保护后面英商租界各洋商之贸易不受拦阻,唯人民不妨碍各洋商之贸易,而遵守中国法律之通行不得谓为拦阻。
(三)现时滩地内所树之旗杆及所升英国之旗,即行移在英商租界内,其各公路尚有未排除三个隘门,立即撤除,以便交通。
至此,英国人在厦门民众持续的抵制风潮中,终于低下高傲的头颅,厦门公民会所提撤除围墙、铁门,以及移除英国旗帜、租界标示,乃至太古栈桥纳租等项主张均完全实现,虽然海后滩地仍归英商管理,但英方对该地权属中国官地,再无异议,耗时数年的海后滩案终告结束。
五、结 论
厦门海后滩案无论是涉及人群抑或是影响范围,若相较于1921年同时期因华盛顿会议而兴起的国民外交运动,自然相形见咄。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海后滩案亦有其典型性与代表性,通过对该案前因后果的梳理,不仅可对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民间外交的实际影响有更客观的认知,亦可由此凸显北洋外交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首先,海后滩案的主要关注对象为海内外的福建人,厦门公民会作为抵制太古洋行风潮的主要运作者与推手,之所以能够将风潮持续扩大,并能给予太古洋行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主要就是利用地域乡情及闽籍华侨所具有的地方性与国际化特点,将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地域观念有效结合起来,抵制风潮迅速得以扩散至福建人所在的沿海各地区及东南亚,使海后滩案从局限于厦门一市的地方事件转而成为海内外闽籍华人关注的全国性事件。而厦门公民会作为厦门当地绅商学等精英群体主导的民众运动组织,既善于依据条约文本与英展开交涉,又能够控制抵制风潮的涉及范围,恰到好处,将抵制的目标集中于太古洋行,防止风潮无限扩大为全面的反英运动,进而可避免英人的干涉。当然,厦门公民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影响,福建及厦门地方当局的默许与支持,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其次,英方在海后滩案的处理过程中,其政策制定初始并未将英商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更多基于传统的条约体制思维,试图以炮舰政策逼迫中方让步,即如艾斯敦所言:“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不负责任的煽动者在条约口岸创造这样一个先例”,忽视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日趋兴起的民族主义所带来之影响。待至抵制风潮的不断扩散,太古洋行在南中国海地区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尤其是海员大罢工所呈现出的威慑力,迫使英方开始逐步调整交涉策略,不再强调维护条约体制的重要性,而是从现实的经济利益出发,以海后滩权益的让步,换取抵制风潮的终结。英国驻华使馆在事后反思该案得失时,坦称:“海后滩案的最终结果可能使我们在厦门当地损失了一些面子,但我们可以说英国的商业利益在这些租界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海后滩案的交涉,亦可清晰地窥知正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初期的漠视与不作为,使得海后滩案长期悬而不决,否则颜惠庆也不会有“此案久搁不办,致酿成重大交涉,殊属可惜”的慨叹。而北洋政府外交部在处理类似地方悬案的过程中,呈现一种完全弱势的态势,在挽回利权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一方面,因近代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国地位,与西方列强交涉的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尤其当英方态度坚决,意欲以压力逼迫中方让步时,外交部更多是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北洋时期的中国自袁世凯时代结束之后,各派系军阀之间互相争斗,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的权威呈现前所未有的弱化状态,当福建督军对外部消弭风潮的电令阳奉阴违之时,即便英方屡次照会抗议,外部只能是有心无力。厦门外交部交涉员刘光谦事后感慨此案“英领事之坚执既异寻常,公民团之对付亦达极点”,亦非虚言。因此,当今人试图对北洋时期外交有更多积极评价的同时,亦应充分认识到北洋外交所具有的局限性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