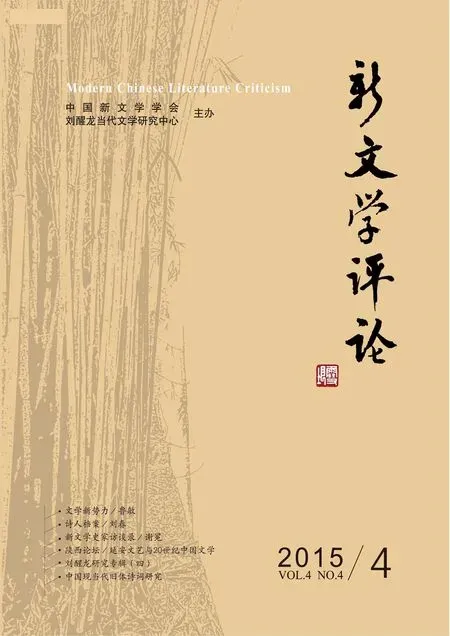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蟠虺》:诗骚和鸣唱楚风
◆ 吴平安
《蟠虺》:诗骚和鸣唱楚风
◆ 吴平安
湖北是《诗经》采集人尹吉甫的故乡,湖北也是诗人屈原的故乡。赓续两大文学血脉的湖北文学,理论上应当兼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呈现出别样的美学色彩来。遗憾的是,随着历史上南方楚文化被注重人伦日用、“子不曰怪力乱神”(《论语》)的中原文化同化,其“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刘勰语),终被纳入“儒家正统”而中庸守常,乃至于“小儒规规焉”(黄宗羲语)起来。延至今日,作为当代的文学大省、强省,虽然名家辈出,名作纷呈,总体的美学倾向,也是前者有余,后者不足。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把握刘醒龙长篇新作《蟠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探索方向,并试图衡估其价值实现程度的。
以大别山为文学故乡长于乡村叙事的刘醒龙,将笔锋转向了江城武汉,他要跨越的门坎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或“城市文学”,而是一个十分新鲜而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领域——楚学和文物考古,活跃其间的是以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为核心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各色人等。显而易见,作者若想涉足其间游刃有余,至少半个专家的学养储备是“准入”的先决条件,一个崭新书写空间的开拓是令人兴奋的,当然对作家也是极富挑战性的。
小说自楚学泰斗曾本之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收到一封死去20年的同事的一封甲骨文信开始,到能发出细微鼓乐之声和异样天香且“只与君子相伴”,若所伴非人则“自己会作出选择”的曾侯乙尊盘,“轰隆一声坠入江中”结束,其间悬念迭生,疑云密布,举凡“一语成谶”,龟甲卜卦,“花儿”传信,“人影”飘出,荒郊设厂,风水切口,下蛊解蛊,墓地联络,地摊售鼎,盗墓设局,追踪谋杀,快意恩仇,巧计掉包等等,诸多非常之事、灵异之事,贯穿首尾。如此这般,遂有论者或赞其“古典与现代、写实与浪漫,已经没有了边界,而推理、悬疑、奇幻,甚至盗墓等许多类型小说的因子都被整合进来”;或誉为“大胆借用侦探小说的结构来承载他要表达的严肃主题”,“充满了侦探小说特有的智力挑战”,是一种“文体试验”。在我看来,这一文本呈现方式与其说是对时下大众阅读趣味的俯就,毋宁说有更深一层的驱动力使然。因为单看这书名,若非是汉字大赛,估计念得下来的读者不会太多,敢于以此命名而不计发行量风险的作家也不会太多。作者既不是对市场折腰,更不是对网络文学效颦,其实在以往的小说与散文创作中,已可约略窥见作者“万物有灵论”的影子了。按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分析,楚国因为“浓厚地存在着氏族社会意识”,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楚地巫风弥漫,巫歌成习,乐舞兴旺,而这正是《离骚》得以“奇文郁起”(刘勰语)的土壤。《蟠虺》的用心,不过是集中书写了一种特定的内容,以及探索与之相顺应的表达形式,以此向遥远的楚人先贤致敬罢了。
作者挑选了一件曾侯乙尊盘,作为凝结整部长篇的核心道具。因为一则这是最能代表楚文化精华的青铜重器,二则“青铜重器里里外外全是刀光剑影”,“追究起来,哪一件背后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无疑给全书情节的铺展,寻找到了历史的凭附,或者说与“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的楚骚传统实现了对接,自然也同作者惯常的写实风格拉开了距离。
“古典青铜多为王侯将相之物,实在是太容易使人心生杂念了。”这“杂念”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学术的,甚至有恶作剧式的。
这些非常之事背后,当然活动的是非常之人。在围绕青铜重器搭建的舞台上,“惯于搞歪门邪道、偷天换日的贪贼”,与“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竞相粉墨登场,诸多人物,不管侧身殿堂、庙堂、江湖,无论分属红道、白道、黑道,都不乏神秘与怪异色彩。楚学院副院长郝嘉跳楼自尽,楚学才俊郝文章不惜以8年铁窗的苦肉计打探曾侯乙尊盘秘密,已非常人所为;“身有罪心不一定有罪”的青铜大盗老三口,华姐与之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为夫讨还命债的决绝,令人唏嘘;“当代的混世魔王,靠着装神弄鬼的邪术混迹在京城”的“熊大师”,与试图重温旧日气象的“云南王”后裔的较量,则透着一股阴气和邪气,就连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黄州漆局长,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开有私人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家沙海,也都非寻常之人。
“老省长”仅凭一句“楚庄王的转世灵通”的谀词,就拿准了郑雄并“放心大胆地委以重任”,不愧为久经官场历练的阅人老手,这“重任”,就是“将曾侯乙尊盘当作祥瑞之物,奉献给那些有着狼子野心的人”,因为虽然“所谓祥瑞之物只是一种文化暗示,但是,很多时候,暗示是可以变成某种神秘力量的”。 以此则可推断,那位隐于幕后自始至终不曾露面而又是主要操盘手的大人物,用华姐所言,就是“企图窃民窃国的大盗”了。静水深流,岂止是深流,滔天巨浪已隐含其中了。作为全书一个精彩的穿插,即便是那位独立身外的庄省长,也惑于让曾侯乙尊盘的紫气照亮大富大贵锦绣前程的诱惑,在最后一次楚学院的年检中,天衣无缝地安排了与曾侯乙尊盘的亲密接触,以至于“满脸祥瑞之气”。
正如屈原海风天雨般的浪漫诗风,彰显的是一个浸淫着儒家美政理想和爱国热忱的主人公那样,非常之事灵异之事的底色,也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批判锋芒,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小说“诗骚和鸣”的判断的。
这一理性精神与批判锋芒,凝结在篇首“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句话上,这是“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的曾本之“用尽全身力气”才写出的话,不妨视为作者对全书的一个隐喻。“识时务者为俊杰”是耳熟能详的箴言,古已有之,对它可以做或正或反或褒或贬的不同解读,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更多看到的,还是敌人在劝降革命者时的一句套话。
“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饣甫其糟而啜其醨?”神龙一现的江上渔父规劝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原始版本,与“劝降”而使其俯就“时务”并无二致。然而屈原不愿“与世推移”,“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而终于怀沙自沉,“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了,遂有千载以下国人对这位“不识时务者”的追思与祭奠,因为他已经不是“俊杰”而是“圣贤”了。
曾侯乙尊盘以它千年修得的庄重与威严,散发着一股无可阻挡的正气,“坚持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曾本之,“像青铜器那样中正肃静”,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属于同道的还有“神仙风格的马跃之”和郝嘉、郝文章父子。
这位“楚学界的无冕之王”,并非如人所言,是“食古不化,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子”,“老省长”拿捏郑雄极准,看待曾本之却走眼了。仅以“凤求凰”操盘水波纹镜买卖的老道,以蟠虺纹饰残片从容应对的机敏,只要是与不义之人较量,“也会搞阴谋诡计”,“原来是老奸巨猾”,如果“也来做倒卖青铜器物的事,只怕大部分文物市场都得关门”了。
曾本之并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一尘不染的化外之人,他也有私心“杂念”,这杂念不仅限制了他的学术视野,也干扰了女儿的婚姻大事。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个“吾日三省吾身”的儒者,“这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如何做才不会误入歧途,或者迷途知返”。这种反省精神使他得以逐步剔除杂念而实现了灵魂的自我净化。如果说将其毕生心血与名声所系的“失蜡法”自我否定,是作为科学工作者服膺真理的良知底线,并且是为身后名着想,仍然带有些许功利色彩的话,则毅然决然,回绝“老省长”“弄上一个”“比顶着厅长和部长的乌纱帽还管用”的院士头衔的利诱,从“每次听到院士二字,自己的心跳就会加速”,到视院士头衔为“鼻屎”,则无异于脱胎换骨,由小智而大智,升华到另一层境界,成就另一种人生,即便不是圣贤,至少是具备了“圣贤”品格了,这是曾本之穷其一生修炼达到的高度,是人之为人对自身的超越。
曾本之、马跃之以古董墨、老宣纸比斗书法一节,写得诗声琴韵,古意盎然,恍然使人想起大观园中题对额、行酒令、结诗社的日常生活场景,与二老的身份学养极为契合。其深层意蕴,则是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屈原《橘颂》)的人格理想的呈现。
作为曾本之的对立面,身兼高足和女婿双重身份的郑雄,是小说塑造的一个相当成功的人物。“就像对蟠虺的看法,有人说是龙,有人却要说成是蛇。龙蛇虽然同属同科,却非同类”。以“现实主义者”自诩的这位楚学才俊,天资聪慧,思维敏捷,长于口才,精于算计(即便是口吐一句谀词,也要选择对象以实现未来收益的最大化),“搞学术,当厅长,都做得比别人出色”。不过“研究青铜重器只是他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是一块敲门砖,是手段而非目的,实现其“用学术作跳板的春秋梦”,才是其终极追求。为了攀附曾本之这棵大树,不惜作“名义上的一家人”的隐忍克己,逐出家门时的平静泰然,其心理素质便非寻常之辈。捍卫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的“失蜡法”,不惜“拦截”反对者的声音,以至于“助手绑架导师”,“背着曾老搞学术专政”,以学术的名义开展种种非学术的活动,最终为“老省长”收入麾下,为实现“当国师”的春秋梦替某大人物奔走鞍前马后,走上了一条看似前途无量其实凶险莫测的人生之路。
毋庸讳言,当今学界,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亦即识时务的“俊杰”恐怕是多如过江之鲫的,整体上失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而不断犬儒化的读书人,或者向权力献媚,或者对金钱折腰,已成世间常态,则这一人物的概括力、覆盖面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在处理这一极具现实性典型性的人物时,分寸感的把握相当到位,对陷害郝文章内心的纠结挥之不去,为其提前出狱“竭尽全力”,关键时刻替曾本之遮掩免其下水,“还没有泯灭天良”,这便使人物获得了多侧面的立体感,而不至于流于某种概念化的符号。
其实,“以政治为职业梦想”并不错,“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读书人恒久不变的士大夫情结,也是几千年不变的主流价值观,只是其价值的实现,是以读书人的“操守”和“名节”为前提的,“修齐治平”,必得以“正心诚意”始,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是古人高标的风范。也正是当今“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弗利式的厚黑哲学大行其道,“不识时务”的圣贤品格已经渐行渐远,让我们时时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叹喟。倘若再作深究,一个缺少显赫背景的人如郑雄者流,纵然才高八斗,却恪守“操守”和“名节”的古训,现行体制能为他提供上位的公平环境和顺畅的渠道吗?这一反诘庶几能使读者感受到小说批判性更深一层的所指,也划清了复古倒退与改革开放的分野。正如作者借郝文章之口所言,“汉口出商人,武昌出才子……在监狱里呆了几年后再看外面,才发现武昌的才子变成了商人,汉口的商人变成了骗子”。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应当责备的是水土,应当改变的是环境。这也正是小说开篇如天书般的谜团,甲骨文书写的“拯之承启”(开始拯救)的谜底所在,“拯救”什么?自然是拯救日益沦丧的世道人心,拯救物质与精神的严重失衡,拯救如自然环境一样日趋恶化的人文环境;而“天问二五”,则无异于告诫郑雄者流:人在做,天在看。
当然,论及激浊扬清兴亡继绝匡正世风教化人心,文学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时人是不敢作过高估计的,但是作为诗骚传人,的确应该有一点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和舍我其谁的雄心。郑雄不是说“哪怕是根烂了五百年的朽木头,也还有一块树结是硬的”,并且开始“反省自己,还特地写了一个‘做老实人’的斗方挂在办公室里”吗?刘醒龙无疑是乐观的,这种乐观主义,来源于诗骚先贤的精神滋养,来源于一个作家对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的厚爱,以及心头那份不灭的家国情怀。
另外,还有聊可一提的是小说中的“武汉元素”,诸多非常之事、灵异之事发生的地点却是高度写实的,皆可按图索骥在武汉三镇找到对应位置。在我看来,这一技术性细节的意义在于:在方方、池莉多年来业已在读者中牢固建立了市民化的城市形象之后,刘醒龙展现给我们的是另一个武汉,或者说,是这座伟大城市的另一个侧面。
注释:
①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②贺绍俊:《刘醒龙小说〈蟠虺〉: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③李泽厚、刘纲纪:《屈原的美学思想》,《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页。
⑤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页。
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页。
单位:武汉文艺理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