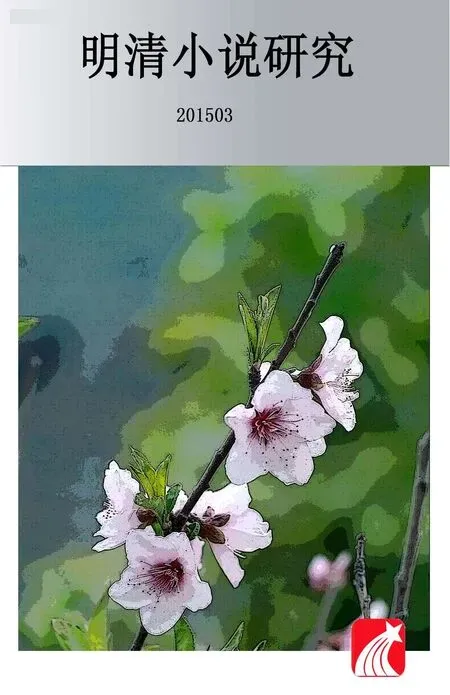南、北支水浒故事与《水浒传》成书
·胡以存·
传唱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事迹的水浒故事,因宋金对峙而在流传过程中分为南、北两支,各自传承,此点早经孙楷第先生揭出:“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实盛传于南北。南有宋之水浒故事,北有金之水浒故事。”吕乃岩先生更明确指出:“在《水浒》成书之前,水浒故事的流传,是在南北两地分别进行的,即山东的梁山泊一带,与淮南的淮阴、淮安一带,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流布于南北两地。”
地域差异深刻影响到水浒故事的流传及今本《水浒传》,因此,在依时间顺序“考镜源流”的同时,必须结合空间维度,才能更全面地勾勒出水浒故事流传的基本面貌。
一、地域因素对南支水浒故事的影响
南支水浒故事因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南宋广为流传,严敦易、胡士莹等先生在考辨说话四家之“说铁骑儿”时已有分说。但是,时代背景可以说明民众传播水浒故事所属的“说铁骑儿”的心理动因,却无法解释何以唯有“宋江三十六人”能够独树一帜、最终凝结成脍炙人口的文学巨著——《水浒传》。
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在两宋之交虽有一定影响,却绝非决定全局的大事件。且不说靖康之变、南宋肇建等军国大事,即以“盗寇”论,它也远不及江南方腊与洞庭湖杨幺。但是,这股活动于北方的武装集团,不仅没有被历史洪流淹没,反而衍生出绚烂多姿的民间传说,这说明,“宋江三十六人”更契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心理需求。
有人归功于招安,认为它有利于洗涮梁山好汉的“强盗”印记。招安确实是宋江与方腊的重要区别,但两宋之际被招安者不少,以致绍兴时盛传“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俗谚。李若水《捕盗偶成》便是针对宋江招安而作:“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足证当时有识之士对此甚为不满。况且,影响极大的洞庭湖杨幺手下众将也多有招安,但它最终却只能作为素材被吸纳进水浒故事。
真正促使“宋江三十六人”在众多事件中脱颖而出的,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域因素。
宋江事件不久便是靖康之变,这场奇耻大辱葬送了腐朽的北宋王朝,从而大大消褪了“宋江三十六人”身上所谓大逆不道的色彩。对朝廷的极度失望与痛恨,使民众将希望寄托在此前与官府对立的“盗匪”身上:“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当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时,广大中原地区转瞬之间成了遥远的故国。对南宋人民(尤其是逃难而来的中原人)来说,活动于中原的“宋江三十六人”,不再是阶级矛盾中的“盗匪”,而是民族矛盾中的“好汉”。“宋江三十六人”因地利之便,几乎成为当时北方抗金斗争故事的“外衣”,被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成为南支水浒故事极为重要的来源。
反观江南方腊,与宋江差不多同时,而规模更甚。方腊起事之地,正是南宋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尽管方腊已为北宋王朝镇压,但他与洞庭湖钟相杨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基业肇兴的南宋小朝廷。更何况,“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保留在江南人民记忆中的惨痛经历,使得他们在随后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以轻松的心态去面对这血腥的杀戮。
相较于“此地”的方腊,在“别处”的宋江更容易让南宋民众接受,梁山泊中英雄燕青便明确道出:“俺是那梁山泊黑宋江,不比洞庭湖方腊。”宋遗民龚圣与竭力赞扬梁山好汉,一则曰“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再则曰“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正着眼于此。
中源沦陷赋予宋江事件以新意义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尖锐的民族矛盾及南北对峙,可以使“盗”承载民众的家国之思,从而将“宋江三十六人”涂上厚厚的“忠义”色彩。脱离了这个前提,大一统时代的读者们就殊难理解了。因此,尽管《水浒传》中的宋江几乎成了愚忠的典型,但是,与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相比,先天不足的《水浒传》让民间更津津乐道他们的义气与“替天行道”,而文人赞颂水浒,主要感慨其英勇孔武: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
二、北支水浒故事的流传
与南支故事宋时便腾嚣众口不同,金国女真贵族治下民众对反抗大宋王朝的“宋江三十六人”缺乏讲唱的热忱。在沦陷于异族铁蹄之下的中原地区,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民众对北宋王朝的灭亡怀有无限的哀思,“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家国之外,夷夏之辨更是深入文人骨髓。如福建士人施宜生,弃宋仕金,曾“上书陈取宋之策”,但在金兵南侵的关键时刻,他却泄漏军机于宋,并因此被杀:
(正隆)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剌使还以闻,坐是烹死。缺乏民众共鸣的北支水浒故事只能作为民间传说局囿于事件波及的某些特定地域,并依然保持着强盗本色。它既没有全国性的影响,更缺乏中下层文人(及说话人)的整理。因此,北支水浒故事直至元代依旧简陋而零散,反映在水浒戏曲中,是人物面貌及故事情节的模糊。胡适先生基于水浒戏推断:“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写。”
这个“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是宋江“略史”:
幼年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致伤了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偻罗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如果说,地域因素使南支水浒故事在南宋凭“人和”取得长足的发展,那么,北支水浒故事则在元代占尽了“地利”,它因杂剧而获得了迅猛发展。历史上,“宋江三十六人”的活动范围颇为广泛,但《宋史》也确曾记载,侯蒙提出招安策后,朝廷即“命知东平府”,可证宋江与东平地区有特殊的关系。梁山泊(梁山泺)频频出现于早期水浒故事文献,再加上宋金时期东平梁山泊地区向为“盗薮”,至元时尚有水寇活动的记载,因此,人们将之视为水浒故事发生地,津津乐道于梁山好汉的遗闻佚事,是不争的事实。
东平又是前期元杂剧中心之一,作家辈出,身处北方水浒故事密集地,东平作家有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事实上,以自己熟悉的水浒故事为题材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水浒戏,正是东平杂剧作家鲜明的特征:元代创作水浒戏数量最多的作家为东平人高文秀(今见著录九种,其中八种以李逵为主角),而写出《李逵负荆》的康进之则是距东平不远的棣州人(今山东惠民)。
杂剧是北支水浒故事的主要载体,受其题材及体裁限制,它多以某个人物(尤其是李逵)为主角,铺张其替天行道的经历。杂剧难以完善水浒故事的整体结构,因此,北支水浒故事的主体仍然是松散而零乱的。与之相反,流传于南宋的水浒故事,今日所见资料既有单篇的话本(《醉翁谈录》),亦有连缀而成的长篇(《宣和遗事》),还有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尽管方家对三者的成书时间及相互关系莫衷一是,但从故事内容与形态看,说话是南支水浒故事主要载体,其体裁特性及说话人的叙事能力,促使更注重于融汇贯通的南支水浒故事日趋成熟。
我们之所以将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戏断为北支水浒故事,与宋元文献中的南支水浒故事相比较,这是因为元代水浒故事地域差异仍然明显。除信息交流缓慢及“南人”受歧视等原因外,还因元杂剧地域特色鲜明。元杂剧早期以大都、东平等北方城市为据点,晚期虽然转移到杭州等江南城市,不过,“杂剧虽然在元统一以后成为全国性的文艺样式,但它毕竟原产于北方,和北方的方言、音乐、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元代后期尽管有不少南方文人参与杂剧创作,但……南方最有才华的文人,并没有进入杂剧的领域”。这制约了南、北水浒故事的交流与融合。
三、南支水浒故事的成熟
若就故事的完整性着眼,似可将《大宋宣和遗事》所载水浒故事断为南宋水浒故事的结晶。但是,《大宋宣和遗事》“节录成书,未加融合,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胪列史料虽多,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因此,首尾已备的水浒故事雏形并未受到《大宋宣和遗事》太多束缚,而是脱离讲史成为单独的话题广泛流传,最终衍化成完整的长篇故事,从而为《水浒传》的成书揭开了重要的一页。
这个独立话题的出现,当然是《大宋宣和遗事》与今本《水浒传》中的重要一环,唯因文献无征,我们无法详悉具体衍化过程。不过,明人吴从先曾寓目过某个版本的《水浒传》(简称吴读本),代表了《大宋宣和遗事》向今本《水浒传》转化过程中,南支水浒故事接受北支故事影响后的新面貌。
就故事体系而言,吴读本从属水浒南支故事,原因有三:一是地点。宋金对峙,淮南属宋,而吴读本中宋江活动地点正为淮南,又言朝廷在杭州,将其活动时间后延至南渡,蕴含南宋民众对抗金前线的关注。杂剧作家所宣扬的北支水浒故事毫无例外以梁山泊为背景,对历史上的“淮南盗”不置一辞;二是情感。吴读本感慨于“宋室流离,金人相阨”而“誓清中原”,俨然如击揖中流的祖逖。水浒戏里的主人公,完全以强盗面目出现,替天行道,反抗各级昏庸残暴的官吏(“衙内”),称其“侠义”则可,称其“忠义”无据;三是内容。吴读本云“江啻失一张顺耳,不得已而招之降”,考《宋史·张叔夜传》云“擒其副贼,江乃降”,余嘉锡先生辨曰:“诸史皆不言‘擒其副贼’,独见于此传……若果稗史可信,则张叔夜所擒‘副贼’,当是吴加亮而非俊义也。”张顺的事迹,方家皆以为取自张贵、张顺驰援襄阳一役,他之所以在吴读本中被凸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襄阳之战为南宋存亡之关键,其事迹在南方广为流传。
尽管吴读本从属于南支水浒故事,但它明显受到北支水浒故事的影响。如吴读本中提到宋江妻子,这与今本《水浒传》大不相同。元时陈泰路行梁山地区,附近“蕖菏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这类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风物传说,说明这正是元代梁山地区的水浒故事传闻。另外,李逵本属元杂剧中出色人物,吴读本中的“李逵之虎”,应该是对北支水浒故事的吸收。
南北水浒故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即使是宋金对峙亦不能完全阻隔,靖康后北人南迁、金索南宋艺人入北,都可成为交流的媒介。至元时,大运河沟通南北,更增加了南北水浒故事交融的便利。就地理方位而言,梁山地区水浒故事向外扩散,南下自当以江淮地区为先。吴读本极重张顺,抗金色彩至为浓厚,是现实中民众激烈的抗元斗争的真实反映,这与江淮为南宋抗元前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吴读本水浒故事与淮南的密切关系,它是江淮地区流传的南支水浒故事凭借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吸取北支水浒故事的内容,而初步融合南北水浒故事的结果。
吴读本“其词轧札不雅,怪诡不经”,黄霖先生据此认为它“是元初出现的一种话本”。以吴读本反抗异族思想之浓,似乎也可以证明,它不太可能成书于入元太久。
就整个水浒故事体系而言,黄霖先生认为吴读本“与‘施耐庵的本’和《宣和遗事》是属两个系统的。后来,‘施耐庵的本’广为流传起来,它就逐渐被淹没”。侯会先生也认为吴读本是《水浒》古本,与《宣和遗事》是并行不悖的两派水浒故事,合流同为今本之祖。侯先生还进而比较二书,“《遗事》中的‘杨志卖刀’、‘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玄女庙授书’等情节,吴读本全未提到;反之,吴本中的‘李逵之虎’、‘时迁之甲’、‘武松之嫂’、‘智深之禅’,在《遗事》中又渺无踪迹可寻”。由于吴读本已佚,故而它与《宣和遗事》的关系不易确定。但将之与它本作细节上的比较,并不能令人非常信服,吴从先所记,只不过是他对《水浒传》有选择性地介绍,而不是吴读本的全部内容,否则,他何至于只字不提在所有水浒故事中都十分重要的晁盖?
王利器先生认为吴读本就是今本征方腊之所取资,但现有的资料似乎并不能予以充分的证明。
与《宣和遗事》一样,吴读本确实提到了征方腊,但吴从先并未详细论述。与此同时,他也提到征山东与河北,似乎并未见学者因此立论,认为它是《水浒全传》里征田虎、王庆的先声。
就目前所见资料,民间水浒故事更注重个人英雄事迹,这是前七十回的精华所在。对于民众而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属他们擅长的领域。征方腊是梁山一百单八好汉聚义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张顺归神、柴进使间、鲁达(武松)擒方腊等少数精彩片段外,少见个人活动。
今本《水浒传》中,征方腊几乎每役皆有英雄好汉战殁,揆诸人情事理,此必作者事先有全盘擘画,否则,便如《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三十六人”一样前后参差矛盾。这只能在一百单八将这个整体形成之后,而且,这种前后吻合如精细帐本的考虑,不属普通民众乐意思考的范围,更不可能成于众手。
从已有文献看,北支故事对征方腊不感兴趣,虽然杂剧里燕青也竭力把自己跟“洞庭湖方腊”区分开来;尽管几乎所有南支水浒故事中都有征方腊这个题目,但叙述都不详细。这似乎说明,今本《水浒传》中详尽的“征方腊”故事,应出自较晚的文人手笔。马成生先生认为,“朱元璋征伐张士诚的不少事迹,成为《水浒传》‘征方腊’部分的创作素材”。或许此为文人所本欤?唯文献无征,不能细论。
四、北支水浒故事对《水浒传》的影响
南支水浒故事重整体脉络,北支水浒故事重具体情节,这决定了它们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与地位。
南支水浒故事的整体性,使得它必然成为今本《水浒传》主干(这并不否认南支水浒故事在艺术性上的极大提高),而北支很难形成完整的长篇水浒故事,只能就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进行想象与修饰,从而成为《水浒传》吸取的素材。吴读本已经有了南北融合的基础,较《大宋宣和遗事》更为连贯、全面,它在水浒故事流传过程中的地位,似乎可以与三国故事中的《三国志平话》相较。
在吴读本及文人创作征方腊故事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完整的“施耐庵的本”?甚或今本《水浒传》作者即是征方腊故事的作者?这些疑问尚难回答。但从简单的梳理我们已经能看出,尽管尚不知源自何时,但南支水浒故事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吸纳北支水浒故事,而不是在编定今本《水浒传》时才一次性加以组织编排。
北支水浒故事有整体加入今本《水浒传》而成为其中重要事件的,如三打祝家庄。现存元杂剧中,晁盖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死于三打祝家庄,而严敦易、王利器两位先生认为,《水浒传》中的曾头市影喻金国——这应该属于南支故事。今本《水浒传》则是宋江先打祝家庄,尔后晁盖死于曾头市,南北故事兼收并蓄。
至于零碎的故事情节,元水浒戏中只有《黑旋风双负荆》被吸收进今本《水浒传》,是为“梁山泊双献头”,其它故事,由于缺乏文献证据,我们只能推测,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杂剧》里故事与燕青打擂、《鲁智深大闹黄花峪》与“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也许存在着血缘关系。而今本《水浒传》写卢俊义上山,则更借用了《梁山七虎闹铜台》同源的故事(甚或直接取材于杂剧本身)。
如果仅从文本角度看,元杂剧中的水浒故事较少被摄入今本《水浒传》中。这既与北支故事被南支故事吸纳的改编方式有关,同时也与水浒戏的特点有莫大关系。水浒戏无论内容如何,囿于体裁,基本上都是写梁山好汉上山之后的活动,以盗贼的面目出现,因此,想要将之改造成上山之前的活动,必须作较大的改动。我们看到,聚义之后,梁山众好汉便以头领的面貌出现,个人出场机会极少,唯一的例外便是李逵,而此时李逵故事更直接吸收了杂剧的诸多内容,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来,如双献头、乔坐衙等。
撇开细节,从总体上比较南支水浒故事(《大宋宣和遗事》及吴读本)同今本《水浒传》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北支水浒故事并非仅仅涉及今本《水浒传》的局部,从整体上来讲,北支水浒故事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今本《水浒传》的成书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加剧今本《水浒传》“忠义”与“侠义”的矛盾。
《水浒传》的主题,至今颇多争论,但宣扬反抗异族、忠于朝廷的“忠义”与反抗暴政、替天行道的“侠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固然有民间与文人价值观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也存在着内部矛盾。“说铁骑儿”在南宋说话四家中存在时间并不长久,南支水浒故事中的“忠义”色彩自有其局限性;在北支水浒故事里,梁山好汉多为纯粹强人行径。北支水浒故事大量补充进《水浒传》,更加剧二者间的冲突。因此,俞万春痛斥宋江“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在阶级偏见之外,确实指出了《水浒传》里无法调和的价值冲突。
第二,确立梁山泊的具体位置,却显示出鲜明的南北差异。
早期南支水浒故事,虽然提到了梁山泺,但更多与太行山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支水浒故事借鉴了杨幺故事中的八百里洞庭湖,因此,今本《水浒传》泛泛论及梁山泊,似乎烟波浩渺,仍有洞庭湖的气派。
但具体到细节描写则并非如此,欧阳健、萧相恺先生注意到了《水浒传》里梁山泊的规模偏小,“由朱贵酒店的水亭到梁山山寨,并不太远”,“由山寨过水泊到岸上,路程不远”。两位先生总结出的原因是,“自金以后,绝大部分时间,梁山泊是阡陌相连,垄亩相望,而无复宋时旧观了”。
南方民众讲述水浒故事,是否关心东平附近的梁山泊,并进而追究梁山泊的实际面积,尚属疑问。因此,今本《水浒传》里梁山泊的描述,应是吸收了太多北支水浒故事的素材,字里行间时时露出水浒戏里的山寨相。
北支水浒故事的地理背景,被明确为东平附近的梁山泊。元杂剧里泛泛介绍梁山泊,依《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中宋江上场介绍为据,仍是北宋末年“盗薮”的规模:
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然而,元杂剧描写的是占山为王的强盗,是山贼而非水寇,梁山泊实际上规模极小——有时候甚至“微缩”成一座山头。如《双献功》剧里李逵回答宋江,如何弄套庄家的衣服来,“您兄弟下的山去,在那官道傍边,候在一壁掩映着,等那庄家过来:哥阿,衣服借与我使一使儿”(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描述类似)。又如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里宋江上场云“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里阮小五上场诗同),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里宋江云“绿树重重映碧天,绕溪一派水流寒。观看此景真堪羡,独占人间第一山”。而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里宋江更是自称:“绣衲袄千重花艳,茜红巾万缕霞生;肩担的无非长刀大斧,腰挂的尽是鹊画雕瓴。赢了时,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若输呵,芦苇中潜身抹不着我影。”
当然,今本《水浒传》叙述北方梁山泊及周边地区时多有隔膜,甚至闹出许多地理方面的错误——此点已为诸多方家瞩目,马幼垣先生甚至还注意到《水浒传》里的气象描写也完全不符合山东梁山泊的实情,断定今本《水浒传》的编定者是“一个未曾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这似乎与南方叙事者的知识结构欠缺关系更为直接。
五、结 论
简而言之,水浒故事虽然源于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但源同而流异,南支水浒故事在南宋已盛传众口,而流传于中原的北支水浒故事,在众多题材中尚未脱颖而出,直至元时始凭“地利”因素得杂剧之力,盛极一时。就总体而言,元时南、北支水浒故事殄域仍在,但合流的趋势不可阻遏,其中尤以南北交界的江淮地区至为明显。最终,以说话为主要载体的南支水浒故事凭借其完整性,吸收民间传说与杂剧为载体的北支水浒故事内容,进而形成蔚为大观的今本《水浒传》。
值得说明的是,除说话及杂剧外,水浒故事是以多种艺术形式被民众讲述、传唱的。所谓南支、北支水浒故事,也仅就其大端而言之,在各地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活跃于民间的水浒故事面貌各异,内容十分繁杂。这些内容,并不能被今本《水浒传》编写者全部收集,更不可能为一本书尽数采纳吸收。鲁迅先生提到,“《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臂擒方腊》这些戏”,这便是擒方腊故事在民间的遗留。今天仍流传于民间各地的水浒故事说明,今本《水浒传》固然是水浒故事凝成的丰碑,但它只是一个“集大成者”,绝不是此前水浒故事的全部,更不是水浒故事流传的终结。
注:
①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由明新安刊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91页。
②吕乃岩《〈水浒〉故事在南北两地流传的情况》,《水浒争鸣》第三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③相关研究概况可参见王丽娟《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
④参见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69-70页;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2-114页。
⑤相较而言,说岳故事甚多,但《说岳全传》成书甚晚,并有明显摹仿《水浒传》之处,描写杨幺的《后水浒传》成书亦晚,民间影响极小。
⑥[宋]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7页。
⑦[宋]李若水《捕盗偶成》,转引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⑧关于洞庭湖事迹进入《水浒传》的考证,可参见侯会先生《〈水浒〉源流新探》(《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及《〈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⑨南北对峙,所处地域不同,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清人章学诚在辨析历代选择“帝魏寇蜀”与“尊刘抑曹”时便拈出地域为主要考量因素:“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见[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0—81页。
⑩㉕鲁迅《鲁迅全集》(第9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128页。
⑪《水浒传》中太行山系列故事,方家讨论极多,以王利器先生《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论述尤为全面。
⑫[宋]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⑬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洞庭湖方腊”,这个错误称呼本身,似乎也可以透露出民众认同二者一致性的某些信息来。在吴从先所记的水浒故事中,宋江事件的背景被推迟到南渡时,与洞庭湖的联系就更为明显了。
⑭[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页。
⑮北支水浒故事,如元杂剧,只强调为民除害的侠义精神,这固然囿于体例,但它所处的特定时空更为关键。
⑯[明]李卓吾《〈忠义水浒全传〉叙》,见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3页。
⑰㉙㉚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49、193 页。
⑱[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⑲[元]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7页。
⑳严敦易、胡士莹、王利器诸先生推测水浒故事在北方流行于抗金根据地,失之于以今度古。北方民众认梁山为忠义社,似乎缺乏心理依据。孙楷第先生以关汉卿《绯衣梦》中“比及拿王矮虎,先缠住一丈青”之语推断“梁山泺故事流传已久,故汉卿习而用之,则梁山泺事在金,固应早流传编唱矣”,作为夫妻的王矮虎与一丈青进入北支水浒故事,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具体论述可参看拙作《一丈青考》,《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㉑金国说话艺术远不如南宋发达,故此,女真贵族常向南宋索取艺人,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43页),而涂上“忠义”色彩的南支水浒故事甚至引起文人的赞叹与关注,有“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
㉒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复印),第25页。
㉓㊵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㉔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㉖从故事源头到今本《水浒传》成书,整个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重要环节,都因文献阙如而无法进行细致的考察。对其中某些环节的探讨,可参见陈松柏《〈宋江演义〉是连接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与〈水浒传〉必不可少的链条》,《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㉗[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41页。
㉘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33页。
㉛黄霖《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㉜侯会《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㉝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㉞王利器《水浒传的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㉟此处仅就整个征方腊事件的叙事文本而言,并不排除民间仍有关于征方腊的水浒故事流传。如前所述,今本征方腊中也有张顺归神、鲁达(武松)擒方腊等个人行动的精彩片段,这极有可能是民间故事的遗留。
㊱马成生《水浒传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另可参见《论〈水浒〉征方腊的地理描述:兼论其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5期。
㊲严敦易先生认为,《水浒传》里好像以梁山泊和曾头市来比拟赵宋和金国的斗争(《水浒传的演变》第124页);王利器先生根据曾头市里曾弄“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推断,此当即《中兴小纪》所说的“金众之在河北者”,《水浒》写打曾头市,即红巾抗金的缩影(《〈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耐雪堂集》第84页)。
㊳[清]俞万春《荡寇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㊴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24页。
㊶[美]马幼垣《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水浒论衡》,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4页。
㊷鲁迅《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04卷第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