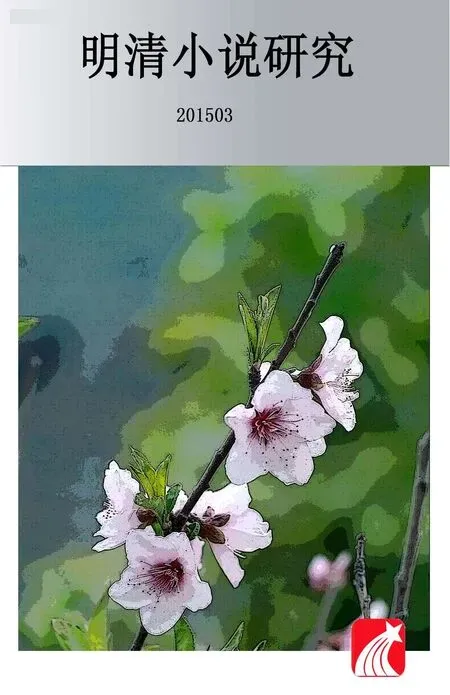明清戏曲小说中的氤氲神
·何艳君·
明清戏曲小说中的神鬼形象多不胜数,这既体现了普通民众对宇宙人生的朴素的认知和解释,也寄托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在婚恋题材的明清戏曲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便是婚姻爱情神,氤氲使正是其中之一。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氤氲使已渐渐隐退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当然也与他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属性有关。本文拟从此出发,对氤氲使这一婚姻爱情神及其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婚姻爱情神氤氲使
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信仰莫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种信仰往往不是为了获得所谓的终极关怀,而是更倾向于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其现实性和功利性不仅使人们无视宗教之间的界限,有神必拜,而且还自己创设出诸多名目,将诸多神鬼摆上祭坛,构建了一个极其庞杂的神灵信仰体系。人们希望神灵对自己的关照是方方面面的,自然也包括被视为人伦大事的婚姻。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受风俗、伦理和法律等的制约,它是使两性关系规范化的一种制度。董家遵先生指出:“很明显的,性关系不过是个人的生理上的要求;而婚姻是含有社会的意味,带着制度的色彩。性欲是生理的,婚姻是社会的,两者并不一样。”随着宗法制度和礼教文化的不断巩固加强,婚姻伦理逐渐被强化,而所谓的性与情都遭到了掩盖和压制。无血缘关系的男女除非结为夫妻,否则一定要严守男女之大防。在这种婚姻制度之下,人们对于美好姻缘的向往和在不圆满婚姻现实下催生出的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以及那无法被完全压抑住的生命冲动,必然会促使人们创造出许多的婚姻爱情神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古代民众信奉的婚姻爱情神有很多,女娲娘娘、月神、月下老人、泗州大圣、牛郎织女、月光菩萨、嫦娥、顺天圣母、和合神、华岳三娘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可以影响人们婚姻和爱情的神灵。在他们成为神的过程中,神话和传说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最为我们熟知的月下老人,现在可知最早便是出现在唐代志怪小说《定婚店》中,这种对姻缘前定的认定是唐人命定观念的一种体现,也对后世人们的婚姻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不圆满的婚姻做出解释,因为无力改变,所以只有无奈地接受。但是同时人们又相信只要相信并祭拜神灵,便会获得神灵的感应,从而使自己期待的事得以实现或对既定的事做出某种修正,于是人们在这种婚姻命定的故事之外,又创造出许多因神庇佑而获得美好姻缘的故事,使之成为对现实生活不圆满的一种补偿。氤氲神的出现正好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氤氲,古指阴阳二气交会和合之状,《白虎通·嫁娶》:“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此外,“氤氲”亦与“姻缘”音近。氤氲神,一般被称作氤氲大使、氤氲使、氤氲使者、氤氲大帝,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显示,其最早出现在宋人陶穀的笔记《清异录》中:
朱起,家居阳翟,年 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宠。宠艳秀明慧,起甚留意,宠尤系心。缘馆院各别,种种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诣都辇,起送至郊外。独回之次,逢青巾短袍担节杖药篮者,熟视起曰:“郎君幸值贫道,否则危矣。”起因骇异,下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济。”起再拜,以宠事诉。青巾笑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买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会,华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为子嘱之。”临去,篮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灵扇子。凡访宠,以扇自蔽,人皆不见。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绝。”起如戒,往来无阻。后十五年,宠疫病而殂。青巾,盖仙也。
《白虎通·嫁娶》对《周易》系辞的解释表明了在道德理性的压制之下,万物的交合繁殖行为被抽象成一种伦理思想,人们试图用更加文明的婚姻来为具体的两性行为遮羞。然而抽象的宗法伦理可以束缚人,却不能将人完全变成无生命的符号,人的七情六欲始终是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因此被称作“氤氲”的神灵就具有了双重属性。在《清异录》的这一则故事中,氤氲大使是掌管人间婚恋的神仙,乃缱绻司长官,凡合夙缘冥数的男女,便下鸳鸯牒使之成,这是姻缘前定观念的延续,也是氤氲使某种正统性的体现。而从“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买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会,华戎配接,率由一道焉”这句话来看,氤氲使除了掌管人间的正式婚姻,还会成全一切有违礼教之风月之事。而这一不正属性的凸显导致了氤氲使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成为了边缘化的婚姻爱情神。但是正因为如此,氤氲使就显得更有人情味,既可容人说情,亦会竭力成全痴男怨女。如清人王韬的志怪小说集《淞隐漫录》中有一篇名为《三梦桥》,叙聂君青新夫人本应死,但聂之前妻因怜聂在世孤苦,“故祈之氤氲使者,暂延鹤算,永结鸾俦”。泖滨野客所著《野客谰语》中有《梦仙》一则,叙陆生与刘梦仙互相爱慕,却无缘结识,后经氤氲使者帮助得遂欢娱。氤氲使者在梦中与陆生的对话颇值得玩味:
老者曰:“我氤氲使者也。世间才子佳人、痴男怨女,无不归我管理。其有彼此相悦,出于至情而限于境、隔于势者,我能合之。”生亟问曰:“然则婚姻之事,亦能主之乎?”老者曰:“婚姻之事,自有月老专主,我不与闻。月老之配合男女,悉视定数,守乎经者也。而我则参酌乎情与性之间,从乎权者也。如但有经而无权,则世间才子佳人、痴男怨女,不知枉死几许,亦造物者所不忍出也。”
在这一故事中,氤氲使者与正统的婚姻神月老是各司其职的,故陆生和刘梦仙也只能暂时欢会,最后只有忍痛分别,永不再见。但也可以看出,氤氲使者比“视定数”、“守乎经”的月老更具人情味,无怪乎作者在篇末借“野客”之口大发感叹:“……自月老出,不问妍媸,不论巧拙,但以一缕红丝,强为配合,则世间男女之情,因以不遂者多矣。藉非有氤氲使者为之代弥缺陷,窃恐离恨天不能补以片石,烦恼城难容无数众生。”氤氲使的出现使戏曲小说中才子佳人们的情感有所依归,其中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弹性和民间的宽容,即在对礼教的维护之外,还有着对情与性的包容。
阴阳二气交合而成的氤氲,原是没有具体形象的,但在各种故事传说中却逐渐地被塑造成一位人格化且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爱情婚姻神。《清异录》中的青巾道人虽身份不明,“盖仙也”,但将之视为氤氲使也未尝不可,故在后世的传奇、小说中,氤氲使多是幻化成道人给深陷相思迷局中的男女制造机缘,如《梦仙》中的氤氲使者便是“一老者,须发皓白,作道家装束,飘然而至”。而“坤灵扇”在一些故事中也成了氤氲使者的法宝,传奇《桃花影》中的氤氲使者即用这件宝贝将赵颜呼唤画中人的声音扇至天庭,让仙女真真听见并感动,终于下凡成全赵颜一片痴心。
陶穀《清异录》是一部类书形式的笔记,采录唐朝、五代时的新颖词语,分门别类,共计37门,661条目,“氤氲大使”在“仙宗门”。陶穀卒于北宋开宝三年(970),由此可知,作为婚姻爱情神的氤氲大使至晚在北宋初年已经成型。此后“氤氲大使”除了作为典故而存在,还频频出现在明清时期以情爱题材为主的戏曲小说中,凭借其神力影响着剧情的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形象。
二、氤氲神形象分析
明清时期,相对于杂剧,氤氲使更多地出现在传奇作品中。明清传奇的创作,承袭了南戏中生旦离合的叙事模式,其故事情节多与爱情婚姻相关。在明中后期兴起的以“情”反“理”的思潮更推动了风月题材的戏曲作品大量涌现,即所谓的“十部传奇九相思”。小说创作亦受此种思潮影响,才子佳人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争取爱情婚姻自主权的过程中,势必要遇到各种阻力,每当爱而不得或情海生波之际,总有外力相助使男女主人公得遂心愿或化解矛盾,而氤氲使便常常充当此类角色,为男欢女爱保驾护航,更为剧情平添一抹奇幻色彩。明代汪廷讷所作传奇《彩舟记》便是此中典型,氤氲使在剧中可谓翻云覆雨、大显神力,既可成就姻缘亦能拆散鸳鸯。该剧剧情大致如下:
太原江情随父在闽经商,两年后与父买舟同归,途遇氤氲大帝庙,遂求赐姻缘。其时福州太守吴治三年任满,携妻女往京城临安报政。氤氲大帝欲撮合江情与吴太守之女,兴风作浪,江、吴两舟只得候风于淮安闸。江情、吴小姐得以邂逅私会。后氤氲帝因被江情言语冒犯,半夜使顺风起,两舟解缆而去,江情不觉,仍留吴舟中,终被识破。吴太守见江情才貌双全,且恐家丑外扬,有辱门楣,遂认其为故人之子,将女儿许配于他,并遣张顺送其还家报知父母。途中张顺谋财害命,推江情落水。龙神为报江父先前修庙之恩,救活江情,送归太原,并助其秋闱夺魁,终与吴小姐再续前缘。
此剧本事可见《名媛诗归·吴氏女》《情史·江情》,冯梦龙《醒世恒言》之《吴衙内邻舟赴约》与此剧题材相同。汪廷讷于剧中增设氤氲大帝、龙神,使二者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之关键因素,亦使此一男女遇合情事变得更为曲折传奇。在第二齣《归舟》中,氤氲大帝第一次出场:
(末扮氤氲帝金幞头蟒衣玉带,杂扮二鬼使随上)(末)久署鸳鸯牒,长居缱绻司。朱陈如欲结,权柄我亲持。小圣氤氲大帝是也。掌天上之姻缘,成人间之匹配。欢偕二姓,也不问甚么野草闲花;契合百年,成就了多少旷夫怨女。主盟的是冰人月老,岂知他操纵难由。凑巧的是玉镜雀屏,都缘我机关暗设。那诚心祈祷我的,便薰莸异器,终教他胶漆绸缪;那出言玩侮我的,纵琴瑟和声,也不免参商阻隔。
此段说白点出氤氲大帝身份,虽然人间姻缘主盟的是月老,但是其实一切机关操纵皆由他来做主。最后两句更是埋下伏笔,暗示着江情与吴小姐这一段奇缘必定横生许多波折。因被江情的诚心祈祷感动,氤氲大帝才帮助他与吴小姐邂逅。此后江情竟敢出言不逊,于是被氤氲大帝施以惩罚,便有了父子分离、夫妻离散、被人谋害、妻聘他人等遭遇。最后幸为龙神点破,代诉哀情,江情亦知悔改,氤氲大帝才既往不咎,江吴二人终能再续前缘。由此可知,这一故事的起承转合皆是因为氤氲大帝,如果没有这一角色,剧情根本无法展开。
除《彩舟记》之外,吴中佩蘅子的小说《吴江雪》亦有提及氤氲神庙,那位“穿珠点翠、惯走大家”的雪婆,便是住此庙之前。雪婆在这一小说中的作用与氤氲大帝相似,即为江潮和吴媛穿针引线、排忧解难,在二人成婚之后则相别而去。第六回中,江潮为情所困,雪婆指点他到氤氲大帝前烧香拜祷,“求其一笤”,即可知姻缘成就与否。通过这两部作品的描述,可知似乎在当时,民间应是有奉祀氤氲神这一习俗的,但文学作品既经艺术加工,其真实性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因为没有更直接的史料证实在明清时期人们曾建庙供奉氤氲神,所以这一婚姻爱情神或许只存在于各种传说故事中,即使他当时在民间真的受人奉祀,也应属淫祀。江潮、江情,吴媛、吴小姐,《吴江雪》和《彩舟记》的男女主人公姓名相类,雪婆的角色又近似于氤氲大帝,其住址便是对其身份的一种暗示,而才子佳人的遇合故事大体如此。
在部分作品中,氤氲使者与月老的职务是相同的,即为有缘人系赤绳,如在王韬《淞隐漫录》的《华胥生》中,华胥生见一女子貌美,心向往之,其友朱昂青便说“此女郎与寒舍略有瓜葛,亦世家女,闻氤氲使者尚未系以赤绳,不知将来谁家郎有福消受”。许多时候人们相信人间的婚姻莫不由氤氲使者掌管,他与月老并无差别,如黄人在挽程稚侬的长联中便说道:“奈氤氲使者处,未注定正式姻缘。”《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结尾处的诗曰:“主婚靡不仗天公,堪叹人生尽聩聋。若道姻缘人可强,氤氲使者有何功?”因此,世上许多不完满的婚姻也是因他错配而生。明人西泠狂者之艳情小说《载花船》第三回,席公慕靓娘才貌,然靓娘已嫁作他人妇,席公叹曰:“可惜瑶岛奇葩,浪入狂夫之手,氤氲使恁差误也!”李渔在《连城璧》之《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的入话中说道:
世间惧内的男子,动不动怨天恨地,说氤氲使者配合不均,强硬的丈夫,偏把柔弱的妻子配他;像我这等温柔软款、没有性气的人,正该配个柔弱的妻子。……他偏不肯如此,定要选个强硬的妇人,来欺压我。
这些均在抱怨氤氲使者配合失误,致人间生出许多怨偶。《西湖二集》中有一故事为《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标题虽为月下老,但文中却只有氤氲大使。他于缱绻司中告知朱淑真,今生婚姻不幸,皆因前世作孽,且历数王昭君、卓文君、蔡文姬、薛涛、苏小小等人的姻缘报应,正在行使着《梦仙》中月老“视定数,守乎经”来配合男女的职权。毫无疑问,氤氲使者在此处与月老是重合的。
但是总的来说,氤氲大帝(使)在明清传奇、小说中的形象与月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便表现在二者的身份和职务上。明传奇《增广归元镜》之清乾隆钞本第三卷中增“祈天卜婚”一齣,叙月老为配合分别为仙童、仙女转世之田种文与蓝玉芳,特遣氤氲使者为二人牵聚良缘。清汪光被所作传奇《芙蓉楼》中,月老命氤氲使者勾取孟珩之魂魄,使孟珩与他未来的妻子杜弱兰在梦中相会。清慕真山人即俞达的小说《青楼梦》中,月老升座时,氤氲使和蜂蝶使随侍两旁。《樊梨花全传》第三十九回,氤氲使者蒙月下老人指引,往乾元山借迷魂砂、变俏符来帮助窦一虎和秦汉,使二人分别与薛金莲、刁月娥成亲。在上述故事中,氤氲使的地位应是低于月老。但在李百川的小说《绿野仙踪》第八十七回中,自称上元夫人之次女的月娟为诱周琏,这般说道:“……今早氤氲大使和月下老人到我洞中,着我看鸳鸯籍簿,内详郎君与我冥数该合,永为夫妇,同登仙道。”第九十七回,冷于冰化作福寿真人,“领氤氲使者和月下老人,口称奉上帝敕旨,该有姻缘之分”,在这里,二者同时出现,而且氤氲使者在前,月老在后,虽不能说明前者地位高于后者,但至少可以说明二者地位应是相当的。尹湛纳希在小说《一层楼》的第二回中则叙述了氤氲使者和月老二人在职务上的差异:
当时坐在玉栏旁边的司掌天下运数之氤氲使者,起身执笔过来,自百花仙子、月姊、织女等三人始,将在会上耻笑禽兽众仙或羡慕函香殿下的十五六位仙女,悉数载入缘分名册之中。又有月老见函香殿下与催艳玉女,在王母前敬献寿酒之时,见众仙女争看之态,相视放笑,早从姻缘袋中取出赤绳,在函香殿下与催艳玉女的足上系了;又乘着仙酒之力,将月姊、百花仙子、织女三人之足,与那所憎嫌的百鸟、百兽、百麟三仙之足系了。
此后仙女、仙童、仙子们的投胎,都是上帝传旨令氤氲使者操办的。由此可知,虽然氤氲使者也会系赤绳,但相对来说,还是月老牵线比较深入人心,而氤氲使统领缱绻司、掌管鸳鸯牒亦被视为其本分,大致符合二者在《定婚店》和《清异录》中的形象。《初刻拍案惊奇》之《感媒神张德龙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开篇的一段话亦点出了二者在职能上的不同:
话说婚姻事皆系前定,从来说月下老赤绳系足,虽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姻缘,眼面前也强求不得的。就是是因缘了,时辰未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够;时辰已到,要迟一日,也不能够。多是氤氲大使暗中主张,非人力可以安排也。
月老系绳是确定二人姻缘,而两人成就姻缘之时机、方式却是由氤氲大使来安排主张。月老被民间奉为婚姻神早于氤氲使,他是以老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作为一位人格神,月老在其神性之外也会被赋予某些与其形象相符合的人性,即虽然老成持重,但难免会因不知变通或一时糊涂而错配姻缘,导致人间出现不少怨偶。基于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功利性价值取向,人们在月老之外又创造出氤氲使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因此在人们心中,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当如氤氲使者在《梦仙》中的自述一样,他是喜欢将有情人配成眷属的,正所谓“风月场添彩色,氤氲使也欢欣”。人们希望他既能像月老一样有为人配合正式婚姻的权柄,同时又能参酌情性,给两情相悦的男女提供方便,这样便可减少遗憾,使更多的人获得美满姻缘。这也使得氤氲使的双重属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情爱和婚前的两性结合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为了解决情与理的冲突,便用婚姻作为故事结局,从而将违背礼法的程度降到最低。因此明清戏曲小说中的主人公多诚心拜祷氤氲使以求良缘,氤氲使也乐意帮助这些有情人,使他们得以终成眷属,而不像《梦仙》中陆生和刘梦仙那样只能够短暂欢会。
汪廷讷《彩舟记》和王骥德《题红记》中的氤氲大帝,因被称之为“帝”,具有较高的权力,如他在《彩舟记》中是“金幞头蟒衣玉带”,有两鬼使跟随,江情与吴小姐姻缘之成毁系于他手。《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中的氤氲大使虽不被称作“帝”,但是也是“带紫金冠,束红抹额,穿红锦袍,系白玉带”,这应该是他作为缱绻司长官的正式装扮。但即使如此,他也是“一尊神道”,而在其他戏曲小说中他也经常是以道士形象出现的,既是为了方便行事,也点明了其道教属性。《樊梨花全传》的氤氲使者便是“三只眼的道人,金面孔”。薛旦杂剧《昭君梦》中,王昭君见到氤氲大使时称其为“仙长”。传奇《天马媒》中的氤氲使者也是幻化为一道人向黄损求取玉马坠。就算没有直接描述氤氲使的装扮,但是这些作品也会将之与道教诸神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中国古代,因为人们比较关心的是神灵所能带给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并不热衷于区别信奉的神灵是自然神还是宗教神,所以民间俗神的属性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在俞万春《后水浒》的结子中,归元庵的一个老道婆被玉帝敕封为氤氲使者,足可证明这种复杂性。但是正如郑传寅在其《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书中所指出的,相对于佛教,戏曲与道教的关系要更为亲密。郑传寅先生认为原因之一便是“道教创生于本土,与世俗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其神仙故事、斋醮方术更为下层群众所熟悉。……道教以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为信仰核心。这种以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石的信仰,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当然比涅槃、圆寂的佛教学说更具有诱惑力。道教斋醮仪式和神仙方术与趋利避害的世俗心理相吻合,符箓禁咒、捉鬼驱邪、炼丹服食、吐纳导引,富有很强的实用性”。这虽然是在论述戏曲与道教的关系,但是也说明了道教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于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影响力。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吸收一些道教元素,以便更好地为中国民众接受。因此,相对来说,民间俗神的道教色彩要更为浓厚,氤氲使者即是如此。
当氤氲神被尊称为“氤氲大帝”时,他应该像玉帝、王母等神灵一样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某个具体的神明,而这也表明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至少在小说戏曲的世界中是受到普遍认可的。而当氤氲神被称作氤氲使、氤氲大使或氤氲使者的时候,就很容易地演变成了一个神仙职位,于是只要是有机缘的人便可被任命为氤氲使,俞万春《后水浒》中的老道婆便是如此。死后成为氤氲神的还有南唐女道士耿先生,在吴伟业的《秣陵春》中,花蕊夫人便托新掌了氤氲大使的耿先生撮合徐适与黄展娘。此外,也有普通人死后成为氤氲使的,王韬《淞滨琐话》中的《玉香》便有玉香之父死后署氤氲使者、掌姻缘簿一事,而玉香不过是寄住在舅家的孤女而已。
《彩舟记》中的氤氲大帝为撮合江情与吴小姐,特作风浪阻江吴两船的行程;《题红记》中的氤氲大帝则是遣鬼判起逆风将韩偓所题红叶送入上阳宫中,为翠屏拾得。可知“兴风”乃氤氲使的手段之一,因此他手中的法宝就有“扇”,如《桃花影》传奇中的氤氲使者就是用一把坤灵扇将赵颜的呼唤声扇上天庭。《怜香伴》中的氤氲使者也持羽扇上场,他在剧中用扇一挥,使崔笺云闻曹语花身上异香,两相爱慕,遂共事一夫。此外,氤氲使还有一面旗,在《一层楼》中,他便是“从袖内取出一面五色情思旗来,将众仙子卷起,往下一撒”,使她们各自投胎去了。孙郁在传奇《双鱼佩》中写氤氲使者用一大旗将柳生灵魂引入花想容梦中。这旗不知是五色情思旗,还是引魂幡,大致相类。摄取魂魄,使梦中相会,与其说是氤氲使的法力,不如说是文人们的绮思,这些虚构的人物就依靠这种被创设出来的神力,帮助现实世界的人们在虚拟情境中实现所有的愿望。
三、氤氲使和五瘟使
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红娘受莺莺所托去看张生:
【元和令】金钗敲门扇儿。〔末云〕是谁?〔红唱〕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风清月朗夜深时,使红娘来探尔。
五瘟使,王季思先生注曰:灾眚之神,“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意谓我来散播相思病也,此自合红娘声口;闵遇五以为当作“氤瘟使”,固有所本,然实不如五瘟使之本色也。且氤字平声,亦不合调。但张生已经陷入相思迷局,红娘奉莺莺之命来看张生,应该是为其排解相思,减缓病情,而闵遇五认为五瘟使当做氤瘟使,即是传说中可帮人成就姻缘的氤氲使。然说五瘟使比氤瘟使或氤氲使更本色,且合调,则确实如此,而五瘟使与氤氲使的关系也可由此看出端倪。
五瘟使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俗神,又有瘟神、五瘟神、五瘟使者、瘟神五帝、五福大帝等多种称呼,其前身是疫或疫鬼。王充《论衡》卷二十二“订鬼篇”云:
礼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
后蔡邕于《独断》中亦引此段话。《论衡》于卷二十五“解除篇”中记有禳解之法:
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
《搜神记》亦有同样的记载,关于禳解方法则云:“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疫,《说文解字》注曰:“民皆疾”,同瘟,指一种急性的传染病。医疗水平的低下使得古人们在瘟疫来临时常常束手无策。这种对瘟疫的恐惧与神鬼观念相结合,使得人们相信瘟疫是由疫鬼散播的,于是便希望通过祭祀或巫术的方式来祈求神佑和驱逐疫鬼。
疫鬼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定型,数量增至为五,应是与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相对应,统称为“五瘟使者”,且有具体姓名。元代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便有关于五瘟使者的详细记载:
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帝问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下方力士,乃天之五鬼,名曰五瘟使者。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为天行正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张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于是其年国人病死者甚众。是时帝乃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青袍力士封为显圣将军,红袍力士封为显应将军,白袍力士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封为感成将军,黄袍力士封为感威将军。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
明人编《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此基础上,点明了五瘟使者的姓名: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分别与前面所执之武器和后面所封之头衔一一对应。此外还在最后交代了匡阜真人收伏五瘟神为部将一事。
古时许多地方都有奉祀瘟神、送瘟神的习俗,而日期却各有不同,除了五月初五,亦有元旦、九月初三等等说法。本是散播瘟疫的五瘟使者,如何会在风月故事中变成了排解相思的角色?大概是相思一如疫病,人们一旦陷入其中,便神魂颠倒,难以解除。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疫病之生成和祛除都要经过五瘟使者,相思病也是如此。人们对带来灾害的疫鬼进行加封,奉其为神明,把他们纳入到正统的体制之内,瘟疫的降临也就不再只是疫鬼们的恶作剧,而是瘟神们奉天命行事。恶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人对神仙一般都会怀有敬畏之心,而对这些恶神更是如此。人们奉祀、讨好恶神,是祈求他们不要降灾于己,甚至还希望这些恶神会转变为保护神,如福建、台湾一带信奉的五福大帝,便是在属性上发生了某些转变的瘟神。五瘟使散播相思,亦会排解相思,这就和既帮人缔结姻缘,又不断为有缘人创造机会的氤氲使一样。虽然不能说氤氲使是由五瘟使演变而来,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二者之间是有着一定的相关性的,如秋瘟赵公明执扇,这就和氤氲使持羽扇的形象有着相通之处。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五瘟使者除了是瘟疫的散布者,也经常是以这种解相思、治相思的形象出现的,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隐喻式的借用,而并不落实为具体的角色,如华广生在《白雪遗音》中的《马头调·寄柬》一则中让红娘说道:“我是五瘟神,专治人间的相思病。”《金瓶梅》第八十三回,春梅便对陈经济说:“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在这里,是春梅将自己比作了五瘟使,此时帮金莲寄柬给陈经济便是干那五瘟使排解相思的勾当。在《醒世恒言》的《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则中,一枝被用作信物的凤头金簪便被比作了“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四、氤氲神的隐退
氤氲神频繁出现在明清时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大抵是因为此一时期的戏曲小说逐渐倾向于展现世俗生活和市民伦理,而被视为人伦大事的婚姻自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原本由纲常伦理设定的婚姻框架已无法限定人们内心的情感和欲望。但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以某种扭曲的或极端的方式来抵抗,而现实中的不圆满仍是难以弥补,于是人们只好在这些故事中寻求慰藉,即使这种慰藉是短暂而虚幻的。虽然这些戏曲小说经文人之笔而成就,但其实是当时民众心态的一种投射。氤氲神在戏曲、小说中为人们解除礼教所设置的障碍,使男女遇合成为可能,不仅使故事情节变得生动曲折,而且也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由爱情和美满姻缘的追求,以及隐藏在这种渴求之中的对现实的无奈。
明清戏曲小说中的氤氲神,虽然不一定都像在《彩舟记》里面那样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以这种实质性的角色出现以外,氤氲神也像五瘟使一样,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隐喻式的借用。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媒人、穿针引线者就常被称作“氤氲使”。清人捧花生的《画舫馀谭》中有如下记载:
雨芗取次花丛,独于玉香惓惓回顾。尝拉同木君、药谙、棣园、子白往访之,适姬赴约他出,踪迹之,盖为玉生明府所招也。玉生本夙好,闻余辈来,相强入座。同席为子春、弱士、孝逸、玉香并主人韵香、隐香两姊妹。洗盏更酌,几于达旦。两主人娟秀不俗,蔼然可亲。弱士谓余曰:“此《画舫录》之遗珠也?”余笑曰:“正俟君为氤氲使耳。为补小传,作孙兴公后序何如?”弱士乃喜色。
“俟君为氤氲使”,即是请弱士介绍引荐,以便深交。此外,在戏曲小说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说法:
【归朝欢】(生起沉吟介)当日里,当日里,草草未防,好教我迟疑着想。终非似,终非似,谩亲贾香,罢,待我去呵,与吾兄做一个氤氲的使长。明日里看太湖片帆移东向,门阑里喜气从天降,(合)整备着花烛迎仙返画堂。(沈自晋《望湖亭·再倩》)
(钟馗唱)兄权当冰人系一绳,权当个月老为媒证,权当个氤氲使巧撮合,权当个斧柯为盟订。(张大复《天下乐·嫁妹》)
瑞郎因无人通信,要他做个氤氲使者,只得把前情直告。(李渔《连城璧》外编卷之一)
拟请愚妹作一氤氲使者,与李家贤侄匹配良缘,愚妹也叨些喜酒。(《八剑七侠十六义》)
以上这些都是将原本是婚姻爱情神的氤氲使者生活化,使之成为人们世俗生活中普遍熟知的媒人的代称。方川在《媒妁史》中称:“官媒历来有媒氏、媒互人、媒聘、官媒婆、氤氲大使等不同叫法。”他认为自《清异录》中的故事流传开以后,氤氲大使便成为了媒人的代称。婚姻是人们世俗生活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古代社会中,婚姻大事是必须要经过媒人说合的,若是一桩好姻缘,媒人自然功不可没;若是缔结了恶姻缘,媒人也免不了被怨责。人们将媒人称呼为氤氲使,应是希望这些媒人能像通情达理的氤氲使者那样为自己觅得良缘。又因为氤氲使者常常帮助男女私下相会,虽达人情,却违礼教,故后来在旧上海介绍妇女幽会的“台基”中,其经纪人也往往自称为氤氲使者了。
婚姻爱情神氤氲使在现代已渐渐不为人熟知,月老祠犹存,而在戏曲小说中被提及的氤氲庙并没有实物遗存,史料中也没有关于民间建庙奉祀氤氲神的记载,不能为我们提供更为确实可靠的信息。但在《清异录》中的故事流传开以后,“氤氲大使”既作为典故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中,也经人们的奇思妙想和文人的生花妙笔逐渐丰满成型,民间俗神大多是依靠神话和传说来获得生命力的,氤氲使完全具备这种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被言说成神的条件。但从这些戏曲小说来看,作为爱情婚姻神的氤氲使是在人们的心理补偿机制之下产生的,因此其不正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而他做的事情就未免“有伤风化”。清人张泓的《滇南新语》中有记媚药合和草:
合和草生必相对,夷女采为末,暗置饮馔中,食所厚少年,则眷慕如胶漆,效胜黄昏散,不更思归矣。反目者宜用之。多生夷地深山中。余戏谓友人曰:此氤氲使者也,合和云尔哉。而或则资以逞欲,谬矣。
此处用氤氲使者来称呼合和草这种媚药,即表明了氤氲使的这种不正属性。氤氲使即使可以存在于复杂的民间信仰系统中,也无法被纳入官方的祭祀,因此也几乎不会被相关的官方文献记载。《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录清人宋士宗编撰之《学统存》,其提要为:
是书分二十四门,各为一卷。多摘录前人之说。……然书名《学统》,而中多杂引史事及说部诸书,庞杂不可枚举。至志异一门,尤多怪诞不经之语,如《清异录》所载缱绻司氤氲大使之类。岂亦有关于道学之统乎?
因此像氤氲使者此类“怪诞不经”、且有违礼教正统之神自然会被排除在正祀之外,如有信奉祭祀,也是民间私下为之,应属官方所禁抑的“淫祀”。随着氤氲神在人们生活中逐渐地被俗化,成为媒人的代称,其神性也就随之变淡了。而且在现代社会,女性不再被约束在闺房之中,男女交往也相对自由,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在婚姻中的作用也不再像古时那么重要,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氤氲神的力量来获得遇合的机缘,于是本不如月老正统的氤氲神就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世俗生活。《古今滑稽诗话》中有一条是记民国初年上海某报刊载的猷铎君代拟诸神怨诗十六首,其中“月老”一则云:“鼠交狗恋有前因,究赖氤氲使者身。今日红丝多不用,由他男女自成亲。”于此亦可见世俗人心之变化。今人王仁杰新编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又出现氤氲使的身影:
氤氲使者(唱)自古真情可动天,又何必鸳鸯牒下有夙缘。
吾乃缱绻司总管氤氲使者是也。只因董生、李氏有偷期之秘,虽鸳鸯牒下尚无名份,吾感其真情,特来乐助其成。和合二仙,你等行事吧!
在这一出新编古代戏中,人的情感和自然本真的生命冲动与传统的礼教规范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男女主人公最终打破了这种无形的束缚,获得了情感的自由。在这一过程中,氤氲使者正好可以借此还魂。
注:
①王承文编《董家遵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② 今本《易·系辞下》作“ ”,与“氤氲”同。
③[东汉]班固等《白虎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0页。
④[北宋]陶穀《清异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9-71页。
⑤⑫[清]王韬著,王思宇校点《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127、386 页。
⑥⑦⑧[清]泖滨野客《解酲语》(与《闻见异辞合志》合刊),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 年版,第40、42、40 页。
⑨[明]汪廷讷著,李占鹏点校《汪廷讷戏曲集》,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90、495-496、517 页。
⑩⑪[清]吴中佩蘅子著,司马师校点《吴江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5 页。
⑬唐子畏编著《现代名人名联鉴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⑭⑳㉑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7、55、348页。
⑮ 秋山、禾水编订《幻缘奇遇》,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⑯[清]李渔著,于文藻点校《连城璧》,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⑰⑱[清]李百川著,吕红点校《绿野仙踪》,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905、1003 页。
⑲㉖[清]尹湛纳希著,甲乙木译《一层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
㉒㉓[明]周清原著,周楞伽整理《西湖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271 页。
㉔[清]中都逸叟编次,欧阳健校点《樊梨花全传》(与《平金川》合刊),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58页。
㉕ 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㉗㉘[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5页。
㉙闽、台地区的瘟神属于五帝系统,当地人对瘟神的崇拜又与对五通、五显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五帝信仰。
㉚㉛[东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0、501-502 页。
㉜[东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9页。
㉝[元]秦子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明]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571页。
㉝[明]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㉟闽、台地区流传的五福大帝传说中的五位书生是以舍身救人的形象出现的,而江苏如皋民间传说中五书生却因被张天师误杀而成为厉鬼,故闽、台地区的瘟神是有着某种福神性质的。关于闽台瘟神信仰的研究,可参看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101页;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46页;宋怡明《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资料汇编》,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06年版;王振忠《历史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徐晓望《略论闽台瘟神信仰起源的若干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林立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民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㊱[清]华广生《白雪遗音(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b页。
㊲孙逊主编《金瓶梅鉴赏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㊳[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㊴李保民、胡建强、龙聿生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9页。
㊵方川《媒妁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㊶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十卷社会民情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4页。
㊷[清]张泓《滇南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㊸[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原著总纂,《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56页。
㊹ 范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会文堂新记书局1938年版,第30页。
㊺ 福建泉州市文化局编《泉州优秀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