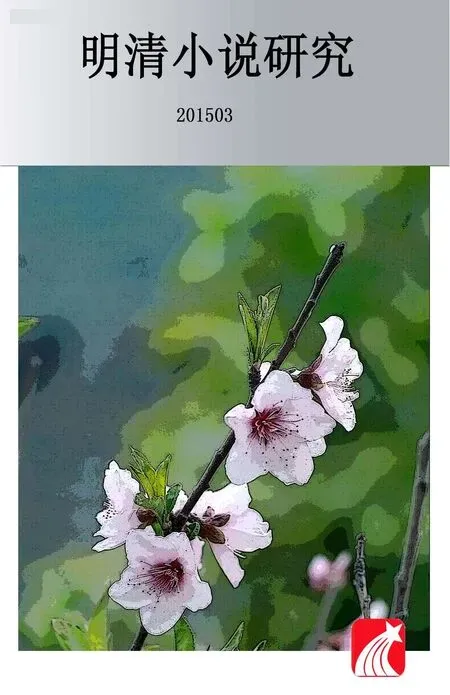“千里送京娘”故事的演变
·马健羚·
一、“送京”故事的最初记载
今存文本中最早记录“送京”故事名目的是明中叶的《金瓶梅词话》。在其书第六十五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中,有“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锣鼓地吊来灵前参灵,吊《五鬼闹判》、《张天师着鬼迷》……《洞宾飞剑斩黄龙》、《赵太祖千里送荆娘》,各样百戏吊罢,堂客都在帘内观看”的描述。
又,李玉《永团圆》传奇第四出“会釁”在描述一场各处村坊联合举办的“庆丰胜会”时,在【南普天乐】一曲中有“送京娘,匡胤名标”的“扎扮故事”记录。
沈德符著、成书于明末的《万历野获编》,其卷二十五“词曲”部将《千里送荆娘》归入“杂剧院本”条下,并评论道:“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闹东京》之属,则近粗莽。”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已有“送京”故事的呈演。
以上三则材料仅记录剧名,其文本及表演形态皆无从观之。《万历野获编》中“近粗莽”的评价,应是其文本散佚无存的原因。尽管如此,该故事形态并未消失,而是呈现于多种艺术样式中,且无论故事如何演变,“千里相送”这一可容纳丰富故事内容、具备极强戏剧张力的关目,总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文学理论的“互文性”概念中,此即同一故事所孳乳出的多种文本共同的“核心信号”。根据该理论,在不重合的前提下,产生于同一“信号源”的多种文本的“互文性”,体现着人们围绕某个“核心信号”所产生的精神活动。本文即采用这一概念,对“送京”故事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代表性文本进行梳理,分析这些文本如何围绕相同的“核心信号”,拣择不同的“非核心信号”以构成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表述各有千秋的故事内涵,而又是何种叙事方式及其故事内涵最受民众的青睐,由此分析支配该故事演变路径的历史文化动机和美学理念,及该个案所体现出的民众的集体心理。
二、小说中的“送京”故事
在迄今留存且形态整饬的“送京”故事文本中,年代最早的是明代冯梦龙所编订的拟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卷二十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严格说来,冯梦龙即是“送京”故事的写定者,因为我们已经见不到在他写定前的底本。但是,根据文中保留较多的“说话”口头语以及上文三则材料,可推测在此之前已有“送京”故事的说唱文本出现并长期流传,冯梦龙乃是据此加以修订而整理成篇。
整理后的“送京”小说,旨在表达宋朝的基业建立和辉煌之因乃是皇帝不好色。其“入话”写山间隐士谓宋朝“他事虽不及汉唐,惟不贪女色最胜”,而“宋朝诸帝不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因此,尽管小说花了大部分笔墨在赵匡胤的英雄行径上,但描叙“自他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也就是个铁铮铮的好汉,直道而行,一邪不染”的“拒美”关目方才是小说的意旨所在。
小说中多次描写赵京娘的绝世美貌,她也是因此而被响马盯上;但赵匡胤从一开始便标榜自己“不比奸淫之徒”,故对京娘时刻以兄妹之礼相待。这本已能表现赵匡胤的“不贪女色”,而作者还安排京娘主动表达爱意,无法直言便增加亲密举动,以更凸显主题,但赵匡胤终是不解风情;京娘终将心腹之言和盘托出,赵匡胤先是大笑婉拒,理由一是救女之心单纯,二是遵守“同姓不婚”的古训;而京娘仍言只望以妾婢身份服侍,引得赵匡胤勃然大怒,直言其乃“顶天立地的男子”,若京娘“邪心不息”则不再相送。京娘连连拜歉,赵匡胤息怒后方才道:
贤妹,非是俺胶柱鼓瑟,本为义气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与那两个响马何异?把从前一片真心化为假意,惹天下豪杰们笑话。
到此,赵匡胤“胸怀大志,不拘私情”的英雄形象已充分展现,但这对于话本小说而言尚嫌不够,因为无论其世情百态的描写有多么“离经叛道”,话本小说常常会以在篇首和结尾处进行一番人伦礼教说理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道德正确性”,而越是惨烈的结局,越能使其说理对人心有更大的冲击力,才能使读者回到社会律令的“旗下”。因此,小说以京娘自缢的惨烈结局收尾——归家之后,由于京娘父母的猜疑与撮合,又一次惹动赵匡胤的火爆脾性,暴怒而去。京娘因嫂子的讥讽而万念俱灰,决定以死证明自己和恩兄的清白。其后赵匡胤显达,敕封京娘为贞义夫人,立祠祭拜。
《飞龙全传》本“送京”故事的主要情节与《警世通言》本无大差异。稍有不同的是:《飞龙全传》本无市侩兄嫂角色,没有刻意于说理,京娘自缢是因自忖本就无以为报,又因父母之言激走恩兄,心中愧疚而求死;其后则有“阴送”情节,即死去的京娘化身鬼魂,为夜行的赵匡胤照明送路。赵匡胤探明实情后,为京娘的节烈之举不胜骇叹,许下若显达则为京娘“建立香祠,旌表节烈”的诺言,使京娘的魂魄稍得安息。
三、戏曲中的“送京”故事
对比其它文本可知,小说已基本涵括“送京”故事的所有“非核心信号”,如匡胤行侠、京娘爱慕、妹爱兄拒、父母撮合、兄嫂讥讽、京娘自缢、香魂阴送等等。戏曲在拣择这些“非核心信号”时,与小说产生了由文体的不同本质所决定的故事形态差异。
首先是叙述重心(即“次核心信号”)的不同:戏曲作品或重在展现千里路上的风光,或重在表现男女二人的情感互动,而少见小说中大篇叙写的英雄行径,即便是赵匡胤解救京娘的关目,在舞台上也多只是略略演过,甚至是置于后台,以一句念白带过。
其次是戏曲通过突出或减弱故事中的某些“非核心信号”,改写人物形象和故事结局:小说中所写京娘通过身体接触表达爱意,以及归家前直诉心声的做法,在戏曲中则多为含蓄的歌舞传情;而小说中赵匡胤火爆易怒的脾气,在舞台上只剩对强盗的嫉恶如仇,对京娘则多为怜香惜玉的温柔体贴;并且,戏曲或是安排京娘已被指婚,或是安排赵匡胤不入京娘家门,总之少见小说里京娘归家后遭人议论以至自缢的遭遇。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舞台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本质不同。虽然叙事性是小说与戏曲共有的重要属性;但小说乃案头文学,以故事为本位,不以作家的主观情感抒发为目的,追求故事情节本身的客体性,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时体现了强烈的“史性”,而戏曲属于场上艺术,以曲为本位,在表现形式中体现出了浓烈的诗歌韵味,极为强调抒情艺术中的主体性这一本属于诗歌艺术的创作原则,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上包含了强烈的“诗心”。基于这一“诗心”特质,戏曲往往倾向于重点表现那些适于以“剧曲”来“吟咏”的关目,而不介意其延缓甚至打断故事发展的进程。因此,小说中详叙的赵匡胤英雄行径为戏曲所略提,而小说中几笔带过的写景文墨,却为戏曲所大加唱演。
并且,戏曲作为一种重在抒情的艺术样式,“由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崇尚情感表现过程中的含蓄与节制,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戏剧,在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时,也总是趋向于使这种冲突在舞台上显得比较温文尔雅,比较‘诗意’,比较有分寸”。因此,舞台上的主人公以较为节制的方式表达情感;小说中京娘的惨烈结局被有意无意地避开,反倒是表现京娘鬼魂知恩图报、情深义厚的“阴送”情节多有展演。
基于此,文人传奇与民间小戏在表现“送京”故事时又各出机杼,以下分别详述之。
(一)文人传奇:提升故事审美品位
明代中期以后,大量文人投身传奇创作,使得戏曲文学呈现出浓郁的雅化倾向。这些传奇作家并不排斥来自于民间的故事题材,不过会“在艺术形式上追求一种相对完美、稳定的艺术格局和语言风格上实现一种与文人自身身份相合的雅化原则”。李玉的传奇《风云会》便是“送京”故事的雅化形态。
这部传奇尽力拢总历代有关赵匡胤的史料记载、民间轶闻,主要讲述郑恩、赵匡胤臣主相识草莽、四海行侠,之后投身军旅并夺得天下的过程。不同于话本小说旨在表现赵匡胤的“不贪女色”,该剧着重突出赵匡胤“义气凌千古,英风透九霄”(第一出《家门》)的大丈夫形象,加上场上表演“一出一事”的时空限制,使得作者的笔墨无暇旁及与主旨无关的儿女情怀,“送京”故事便被较大程度地压缩改编,只突出“山路风光”这一“次核心信号”,其它的“非核心信号”皆被舍弃——京娘虽被千里相送归家,但并无属意于恩兄,亦无旁人对二人一路行来“瓜李之嫌”的揣测议论。为了使这种改编具有“合理性”,作家给京娘预设了一个身份:她是赵匡胤结义兄弟郑恩的未婚妻。京娘既已被指婚,相送路上不动少女情愫,方才是合理的。
因此,在该剧第十五出《送路》中,京娘是戏份很少的配角。相比于赵匡胤大段的唱曲念白,京娘只有一段短短八句的【泣颜回】唱曲,几与京娘父母的戏份相当。主要剧情,乃是赵匡胤的即景生感。他一上场介绍送京之事的来龙去脉后,便赞叹道:
你看野花满径,山鸟呼人,好一派光景也!
接着便以一首曲子描写眼中旖旎的山路风光:
【北粉蝶儿】野旷天高、极目处野旷天高。只见那卷长空云霞缥缈,望几处草舍蓬蒿。种桑麻,栽竹树,迤逦有清流环绕。远近林皋,巧丹青也难传照。
在京娘上场以一曲略略叙事抒情后,赵匡胤又以一曲唱和:
【石榴花】俺只见一程程过一程遥,走不尽山径共荒郊。则看小桥流水,野渡空舠;深林鸟语,曲径花飘。只听得韵悠悠、只听得韵悠悠,樵歌儿唱和空山凹;高高下下,飞鸦声噪。见一幅酒旗儿、见一幅酒旗儿,招飐隐隐花枝杪;须索去半晌醉村醪。
在简单叙写打败强盗的过程后,作者又安排赵匡胤以一曲带过余下的路程:
【上小楼】闹炒炒征鞍跨,急攘攘脚步高。俺只见过着长亭、俺只见过着长亭,抹着长林,踏着长桥。俺只见荒径才穿、俺只见荒径才穿,荒溪才度,荒村才到,草萧萧竹林清奥。
这些曲子虽有推进时空的作用,但如此多在小说中一笔带过的精美笔墨,实是岔开剧作的主题;而原本极具看头的“拒美”关目却为作者芟除,就故事性而言不免有过分平淡之弊;且当为粗人的赵匡胤来唱演这大段的写景抒情文字,也不太“合理”。
这些“不合理”之处,原因之一是服从于作者对剧作整体的把握,以“立主脑”(李渔语),使这部传奇“止为一人(赵匡胤)一事(登基前的交游)而设”;同时也恰恰说明了长于以曲牌挥洒才情的文人传奇不以故事性、戏剧性为第一要义,其旨趣乃是藉由故事来欣赏一套载歌载舞的抒情诗,品味其中摇曳多姿、蕴藉深远的情致。这部传奇曲辞清丽、语言素净的特点,正是由这种文人的趣味所决定的,而它为“送京”故事所重构的戏剧场景,即千里相送路上的风光,使得剧中人物得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从而使剧作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美感,提升了故事的审美品位。
并且,笔者在比较《风云会》的两种存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和现行点校本,以及摘取全本而来的《缀白裘》、清宫昇平署档案、苏州张家手抄曲本中所录的《送京》昆腔折子戏本后,发现后出的文本,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互动趋于频密,赵匡胤对京娘从最初硬梆梆的使唤语气,愈往后则愈有体贴温柔的表现。不妨略举一例,即当赵匡胤打败强盗后,安抚京娘并提议速速赶路归家时:
《风云会》法藏本:(净)妹子上马,速速到家。(旦无言语)
《风云会》点校本:(净)妹子受惊。此去解梁不远,快些上马,待我作速送你到家便了。(旦)多谢恩兄。
《缀白裘》本:(净)吓,妹子,受惊了?(贴上)哥哥。(净)这里到解良(注:疑为“梁”)不远,作速上马去者。
《昇平署》本:(旦上)哥哥好英雄也!(净)妹子受惊了!妹子请上马,待愚兄速速送你归家便了。(旦上马)
张家藏曲本:(净)妹子受惊了!(旦)哥哥真乃盖世英雄也!(净)此处离家不远,义妹请上马,待愚兄送你到家。妹子,请上马。(旦)是,多谢恩兄。
这种现象,与折子戏在舞台演出实践中被演员不断精细打磨有关:历代艺人在“情通理顺”的前提下,为了照顾到戏的可看可听和生动有致,往往设法增加净、旦角的宾白并不断加工,使得这一出原本在戏剧性上不甚出彩、甚至可谓单调沉闷的折子戏,有更为细腻丰富的情感表现,人物的形象更为饱满,加强了整出戏的戏剧表现力。
由此也可反映出观众对“送京”故事的审美期待,因为不同于可在尚未搬演时便已刊印的传奇案头文本,折子戏的选本多是舞台演出的文字记录,以供观众看戏时对照参阅,因此它所记录的往往是演员根据观众的喜好打磨出来的场上之作。观众对折子戏的审美聚焦点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演员如何通过独到的舞台表演技艺,把剧本所提供的内容更好地表现出来,可以说,观众的欣赏口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故事形态的演变方向。由上述现象可知,即便是情爱因素连“非核心信号”都算不上的“送京”故事,其形态也往人性化的方向演变,可见观众有多么期待与欣赏男女情感互动这一关目。
(二)民间小戏:引人入胜的故事表现力
《送京》折子戏在昆剧舞台上被不断打磨,日趋精致,但它并不仅仅是昆剧的专利。在淮剧、川剧、豫剧、曲剧、潮剧、汉剧、徽剧等剧种中皆有的“送京”剧目,说明了承袭自民间说唱曲艺故事演绎路径的小戏路子一直没有中断,广受民众的欢迎。
民间小戏多是由民间歌舞或说唱曲艺演变而来,行当不像“大戏”剧种那样完整丰富,也少有文人阶层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雅化工作,其内容多为男女两性的相互思慕、调情与欢爱,唱词多为简单的上下对偶句,念白浅显。这一类“送京”剧目正是如此:它们的“次核心信号”都是小说中并不出彩、传奇中被略写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互动,曲辞宾白通俗易懂;相比于传奇中的《送京》剧目,有更为引人入胜的故事表现力,因为其京娘并非衬托赵匡胤侠义英雄形象的“绿叶”而已,整出戏从以旦角为配的净角重头戏,变为净、旦唱作兼重的“对儿戏”,呈现在舞台上更为赏心悦目。
然而,同一类演绎路径又会因不同剧种的表现之长有别及打磨程度的深浅,通过排列、突出或减弱不同的“非核心信号”而呈现出风貌上的外在差异。对比载录于《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乱弹戏《送荆娘》和江淮戏《千里送京娘》,即可见一斑。
乱弹戏《送荆娘》中的整体风貌,如《万历野获编》中所言“近粗莽”,京娘虽大胆而不免粗俗,对赵匡胤“动机不纯”,示爱言行颇有“调戏”的意味,可推测其保留较为原始的“送京”故事形态。戏中赵京娘是因目睹赵匡胤“龙眉凤眼”的仪态,在他下马饮清泉水时“只见龙来不见人”,想起“赵家有天下”的传闻才顿生好感的,之后便故意掉鞋并借口无法下马而让赵匡胤为她拾花鞋。此举在古代有很明显的诱惑意味,赵匡胤察其不妥,遂用盘龙棍挑起;可京娘竟还让赵匡胤仔细端详并问鞋上图案是哪种好看,赵匡胤怕京娘多想而从“花儿好”改称“叶儿好”,京娘坚持“花儿好”,且追问赵匡胤“为何见花不采?”赵匡胤闻此一语不发催马赶行。而后来到菜花地旁时,京娘吟诗以花关索和鲍三娘作比,赵匡胤则将其改为反问句回绝。京娘又举“隋炀帝月下戏兰英”之例,而赵匡胤则以关羽“千里送皇娘”言其心清如水,京娘虽反驳但终是无奈告终。
江淮戏早期的“送京”剧目应也是较为粗鄙的,《中国戏曲志·上海卷》指“早在淮剧处于‘香火戏’的雏型阶段,就有《赵匡胤日夜送》的忏词和剧目”。据参与编演江淮戏《千里送京娘》的筱文艳回忆,在此之前这出江淮戏的演出“还保留着说唱艺术的痕迹,舞蹈很少,手里拿着马鞭,亮相也简单,都是亮在舞台的中间”。1952年她与何叫天在改编这出戏时,首先是“删除了原来羼杂的迷信成分”,如京娘因目睹赵匡胤神迹而生发好感及其鬼魂“阴送”的情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剪裁,使戏集中在“送”上;音乐上发挥了以轻柔细腻的江苏民调传情达意的特长,其唱曲多为托物起兴、有景有情,旋律简单而节奏轻快;表演上打磨细致、多样、美化的身段动作,并注意营造赏心悦目的舞台画面感。去芜存精后,江淮戏《千里送京娘》呈现出较为清新的风貌。
在该剧中,京娘是一个温婉端庄的少女,她同样是在路过菜籽地时试探赵匡胤心意,首先将兄妹二人比作张君瑞和崔莺莺,羞涩而又大胆地说“当中缺少小红娘”,赵匡胤则稍显慌乱地回应道赶路匆忙。而后,京娘接连举了“吕纯阳调戏白牡丹”、“吕布戏貂蝉”的例子试探兄长,赵匡胤都是不予置评而催着赶路。最后当京娘举姜子牙垂老方才娶妻的例子,告诫兄长“错过青春空悲伤”,赵匡胤这才正面回应了一次,言他钦慕的是姜子牙“八十三岁遇文王”,打算闯关西的他认为“大丈夫何愁没妻房”。京娘终是明白了恩兄以抱负为重暂不考虑家室问题,不再追探,只是到最后分手时,泪眼汪汪地留别,赵匡胤宽解京娘道他并非铁石心肠,只是眼下要闯荡江湖,后会有期。
四、北昆本“送京”故事及其主旨变化
北方昆曲剧院新编的昆剧折子戏《千里送京娘》,其故事演绎方式与改编后的江淮戏本差别不大,都是采取寓情于景的表现方式,以同一片山水风光映衬男女的两种思绪——京娘因爱慕英豪、含情万千却欲言又止而“恨路短”,赵匡胤因志存高远、虽解风情但壮志未酬而“恨路长”。不同的是,北昆本以昆剧的曲牌体结构改写唱词,采用了【粉蝶儿】【山坡羊】【泣颜回】等适于表达细腻情感的曲牌,音乐优美动人,曲辞清丽晓畅,吸收了传奇作家对故事审美品位的提升努力;又吸收了演员长期舞台实践打磨之成果,在江淮戏所设计舞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成一系列聚散回旋的“双身段”、“高矮像”,将剧情本身的张力体现在美妙生动的舞台画面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饱满,情感表现丰富。因此,整出戏充满诗情画意的雅致韵味,十分耐看,被誉为当今北昆舞台上最著名的一出“新编古装戏”以及“不是传统戏的传统戏”。
其中,编排者对这出戏主旨以及主人公形象的定位及其变化,值得关注。
在陈均采写的《〈千里送京娘〉创演始末》一文中,叶兆桓先生作为北昆版《千里送京娘》折子戏剧本最后一稿的改编者,谈及这出戏正是取材于江淮戏,源于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赴新疆慰问部队的演出。当时许多牵涉到爱情的节目在审查时都不过关,因为“五十年代,部队里头,当兵的一年到头见不到女人,不许他们结婚,也不许他们谈恋爱。尤其是边防部队,少数民族地区,绝对不允许他们骚扰老百姓”。只有江淮戏的《千里送京娘》通过审核,领导的看法是这个戏“是主张为了国家大事拒绝爱情的……可以鼓舞士气,当兵的要英雄气概,不要儿女情长”。
北方昆曲剧院便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给侯永奎和李淑君“量身订做”了这出新编昆剧折子戏。一经推出,据说“红遍京城”,并形成“《千里送京娘》热”。据叶兆桓先生回忆,陈毅元帅特别喜欢该戏,在中南海紫光阁开会时,提议让部队的官兵都看看这出戏,原因是“要学习赵匡胤的这种胸怀,为了国家大事,把爱情拒绝”。因此,陈均分析,该剧的大受欢迎,除了艺术上的因素,切合时代氛围亦是重要原因——在六十年代的演出中,赵匡胤被“处理”成对京娘“无情”的英雄形象,就颇得好评。
虽然打着鲜明的政治烙印,《千里送京娘》在火红的年代退却之后,却仍活跃在舞台上,其艺术美感令演员爱演观众爱看,且对这出戏有了不同的理解。陈均一文中提到,“文革”结束时复排此剧,赵匡胤从“无情”被“安排”成对京娘“有情”,英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正常的儿女之情是否非得让位于国家大事,也不再确定无疑。这出戏的主旨以及主人公形象的变化,着实可令人深思。
五、“送京”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由上述分析可大致廓清“送京”故事的演变脉络:最初该故事的载体应为民间说唱曲艺,后由冯梦龙整理成为话本小说,收录于《警世通言》中;在此之前,民间小戏已将其搬演至舞台上,通过添加唱词和曲调、融入表演动作、补充必要情节等手段,转换为舞台叙事所擅长的表现形式;后又被文人传奇《风云会》所吸收,使其演绎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民间小戏的故事路径仍在多个剧种中呈演;今日昆剧舞台上的“送京”剧目乃是吸收民间小戏表现故事之长、文人剧作家对故事审美品位的提升努力和演员长期舞台实践打磨之成果,改编后使得民间小戏的演绎路径进入到“传统大戏”中,并以经典折子戏的艺术高度流传下来。
在“送京”故事的演变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文人传奇对该故事的演绎路径有较大程度的改写,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互动始终是最受欢迎的“次核心信号”,且不同的艺术体裁对这个“次核心信号”有着微妙的甚至是颇为悬殊的理解差异。这便必须从“送京”故事的外在叙事层面进入其内在的心理层面,考察支配“送京”故事演变路径的历史文化动机和美学理念,藉此理解为什么观众更爱看民间小戏而非文人传奇所演绎的“送京”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只有赵匡胤是历史上真实可考的人物。他与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一旦进入民间的叙事系统里,就不得不接受被“改头换面”式加工的事实:无论他生前有多么威严煊赫,无论文士有多么鄙夷、政府如何禁止这种“胡说八道”,即便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民间化的叙事想象也往往有意与正史中的记载“反其道而行之”,而这种“胡编乱造”却总以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代代相传,教被戏说者无可奈何。
相比于其他同样出身平民的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宋太祖赵匡胤属于民间叙事系统中不多见的“幸运儿”。尽管在他发迹变泰前,也是一个类似于“小混混”的平民,但广为流传的《飞龙全传》系列故事,并没有将其贬损,而是把他塑造成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形象,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
“送京”故事的广泛流传,体现的正是民众对赵匡胤的厚爱,因为它成立的关键,是赵匡胤“帮人帮到底”和坚决不以此换取自身利益的侠义精神。这虽与历史上关云长“千里送皇娘”的前例相似,但二位皇娘对关羽而言,既是“国母”,又是“兄嫂”,于忠于义,关羽都须当仁不让。但赵京娘之于赵匡胤,只是他路见不平时救出的一位弱女子,非亲非故,而愿千里相送归家,全程以兄妹之礼相待,相比于关羽,其侠义气概与君子风度体现得更为纯粹与典型。这符合古代社会对赵匡胤这位“明君”身为平民时的想象,该题材被文人整理改编的话本小说与传奇作品所吸纳以至重点刻画,便不足为奇。
然而,对底层民众而言,他们对“送京”故事的理解,绝不仅限于此。
不管“送京”故事孳乳出多少种文本,其内含的“核心信号”始终是赵匡胤千里相送京娘归家。这本就是一桩容易引起议论的奇事:因为在男女交往有严格界限的社会里,孤男寡女不论是同居一室还是同行一路,都容易引起大众无穷的遐想。更何况,救人者日后贵为天子,在一个皇权无处不在而天子又深居宫中的语境里,帝王的“神秘感”本就令民众对其充满好奇,当京娘“幸运”地与皇权的最高代表即皇帝“狭路相逢”,且还是在他一介平民的时候,京娘的“奇遇”足以成为一个令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对“幸运”的赵京娘而言,爱上恩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除了文人传奇,其它“送京”故事的文本皆有这段关目。但在处理赵匡胤如何面对京娘之爱时,则各有千秋:话本小说写的是赵匡胤毫不留情地“拒美”,甚至连原本无辜的京娘也必须在世人的讥诮声中自缢,可谓“大传统”所主张的压抑欲望的人格观念的极致体现,而这也与佛教据此做“匡胤君,送京娘,心正能做九五尊”的“戒色”、“节欲”说理是一致的;但在“小传统”的叙事语境中,故事的高潮才刚刚开始。更能代表民间叙事原始面目与观众真实诉求的小戏,在这个“次核心信号”中,精彩地展现了赵匡胤这位既是未来的开国皇帝又是当下的平民少年,充满人性内涵和人情气味的应对方式。
尽管民间叙事对赵匡胤颇为厚爱,但也并非将其塑造为一个完人,他在闯荡江湖时期身上的那些暴脾酒气的草莽习性,也被悉数写入“闹勾栏”、“打韩通”、“打董达”等故事中。他身上的诸多缺点却为民众所宽容,因为这样的赵匡胤,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宋太祖,而是一个普通如你我的人。
并非草木的赵匡胤,在面对美貌京娘的纯情示爱时,如何能不心头一动?民间小戏并没有掩饰他这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或装聋作哑,或转移话题,颇显几分少男在面对爱情突降时的惊慌失措;而此时他心中所烦恼的,是必须在自己的鸿鹄之志与京娘的脉脉衷情之间,做出难分对错的抉择。他的这种窘境,正是整出戏好看的关键。
民间小戏对此没有刻板于“英雄必须过美人关”的说理,而是有意将二者之间清晰的道德界限模糊化:赵京娘是一个性情纯真的美貌少女,而非水性杨花的风尘女子;赵匡胤则是一个有所担当的盖世英雄,而非贪图美色的响马强盗。二者不论外型还是品质都相当匹配,具有产生爱情的合理性,这便使得赵匡胤要过的这一道“美人关”,比“柳下惠坐怀不乱”、“关云长月下斩貂蝉”之类男性拥有道德优势的“美人关”要复杂得多。因此,赵匡胤的抉择才尤为困难:选择了京娘,则担心自己溺于私情而大志难伸;而若拒绝了京娘,则又不忍京娘为此伤心(或谓他心中也有几分惋惜)。当赵匡胤最后的天平还是偏向了自己时,他宽解京娘兄妹之情难忘、后会有期的行为,表现出不乏温情、诚挚坦荡的君子气度,给故事留下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而非惨烈的结局)。
民间小戏所刻画的赵匡胤,正是这样一个既刚强勇猛又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味地冷酷无情,他也有人性最温柔的一面。尽管他在“拒美”时有内心矛盾挣扎的看似不“完美”的表现,但从他身上所展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却使之成为一个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人物,爱护京娘的举动也丝毫不损其盖世英豪的形象,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是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处赵匡胤表现出来的常人的烦恼,自然更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这也便是为什么在戏曲作品中,表现男女二人情感互动的“次核心信号”比其它“非核心信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本就是与“核心信号”同属于赵匡胤的民间叙事系统中的。
另外,赵京娘与赵匡胤千里同行、爱上恩兄且设法表达的行为,在“禁欲”的社会语境里,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相比于其他个体情感和心理需求被基本遮蔽和牺牲的“美人关”(如西施、貂蝉)或“英雄救美”故事(如关羽皇嫂)中的女性,“次核心信号”所刻画的赵京娘,并不被视为纯粹生理性的存在,她拥有自由表达内心意愿的能力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而又“合法”地冲击了当时的道德戒律。
这一类叙写正常情爱欲望的“送京”故事,其实同民间小戏中常见的男女欢爱题材一样,是给在道德禁忌相当严厉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减压阀,在古代社会如此,在上世纪视个体爱情若“洪水猛兽”的时代亦如此。众所周知,人的本我欲求在文明社会中,总会遇到因外在的道德、风俗等的约束而产生的困惑,“大传统”对此往往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些在以“禁欲”为基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中所不能直言的话题,就只能在“小传统”的民间叙事中,以一种隐秘而充满活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补充“大传统”中所欠缺的对人性的理解与阐释,令心灵得到慰藉。由北昆本“送京”故事的主旨变化,笔者推测,即便是编演者与管理者将这出戏的主旨定义为“英雄必须以国家大事为重,拒绝儿女情长”,但在观众的接受视野里,很可能有自己隐秘的、基于天然人性与人情的解读。
这便是“送京”故事民间小戏演绎路径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相较于此,文人传奇的改编因芟除了赵京娘属意于恩兄的情节,故也一并芟除了赵匡胤内心矛盾的表现。虽然这种做法若置于整部传奇的框架来看无可厚非,但就单出而言,这种改编使观众欣赏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剧曲所描绘的山路风光,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皆扁平化了,牺牲了原本故事中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内涵。这也便是缘何传奇中的“送京”故事如今鲜见于舞台,即观众更爱看民间小戏所演绎的“送京”故事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改编后的江淮戏本和北昆本并不流于庸俗低下的格调,二者皆将“送京”故事中不雅的表现因素去掉,着力突出故事中的人性之美。男女主人公每一步的做法,都符合自身身份在当时不论是主流社会还是民间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含蓄委婉的情感表达也符合国人内敛持重的审美趣味,所谓“没有告别的爱情往往是最美的”,北昆本更是将这种人性之美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也因此,这一类“送京”故事获得了一张在社会中“雅俗共赏”的“通行证”,盛演至今。
最末,笔者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今人已不再像以往一样受严苛的礼教束缚和政治压抑,普遍承认了出于天性的自然欲求,甚至对女性长久以来作为男性“他者”(《第二性》)的地位提出质疑,那么,“送京”故事将会有怎样的演变呢?且待时代分解吧。
注:
①[明]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0-891页。
②[清]李玉《永团圆》,见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李玉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6页。
③[明]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页。
④参见董上德《叙事的互文性》,《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
⑤[明]冯梦龙编,严敦易校注《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316页。
⑥[清]吴璿编撰,裴效维校订《飞龙全传》第十八、十九回,宝文堂书店1982年版,第139-154页。
⑦⑨参见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
⑧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⑩[清]李玉《风云会》,见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李玉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668页。
⑪[未署撰者]《风云会》,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环翠山房十五种曲》抄本所收本,见《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二函。
⑫《风云会·送京》,见[清]钱德苍编选、汪协如点校《缀白裘》三集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8-143页。
⑬《送京(串关)》,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八八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549-51566页。
⑭《风云会·送京》,见中国昆曲博物馆编《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四十六册。
⑮此处所使用的五种文本的先后顺序是:《风云会》法藏本、点校本、《缀白裘》本、《昇平署》本、张家藏曲本。理由是:《风云会》法藏本所影印《环翠山房十五种曲》本,和点校本所用作底本的北京图书馆藏乾隆内府精钞本,虽并无直接证据判断二者的年代先后,但从文本自身考察,法藏本的关目、语言和情节总体较点校本粗疏,后者因是内府精钞本,作了诸多精细的编排处理。因此,可大体判断法藏本为先,点校本为后。而《缀白裘》是乾隆时期出版的折子戏曲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保留相对完整的是道光七年以后的昇平署档案,苏州张履谦家藏昆剧折子戏曲本抄写的时间跨度为清末民初。除了《风云会》点校本与《缀白裘》本属同一时段难分先后,其它文本孰先孰后,大致分明。
⑯此处的“小戏”概念,参见傅谨先生《“小戏”崛起与20世纪戏剧美学格局的变易》的定义,即“小戏”之名,乃用以“区别于那些有更悠久历史、在明清两代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音乐形态与表演程式、行当整齐丰富、能够搬演多种题材与类型的剧目的‘大戏’剧种”(《戏剧艺术》2010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傅谨先生在该文中将有结构完整的音乐体系的“乱弹腔系”剧种亦归入“大戏”剧种行列;但本文所引《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乱弹戏《送荆娘》”,由文本可知它保留较多的说唱曲艺痕迹,唱词念白浅显直白,并未形成完整的音乐结构,据此判断此处的“乱弹戏”概念应是沿用清中叶以后戏曲新老交织、纷呈繁盛时期对崑山腔以外的各种戏曲声腔的杂呼混称(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中所言“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因此仍将其归为“小戏”行列。
⑰《送荆娘 全串贯》,见首都图书馆编《清车王府藏曲本》第五册“乱弹类五代故事戏”,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84页。
⑱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事业管理处创作研究室整理改编《千里送京娘(江淮剧)》,《人民文学》1952年第11期。
⑲《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443页。又,“淮剧”即“江淮戏”,是江苏省的地方剧种之一,属于由田歌、民谣与清板小曲等说唱艺术,吸收花鼓、莲湘等舞蹈,衍化而成的民间小戏类型。它曾经有“三可子”、“盐城戏”、“江北小戏”、“江淮戏”等各种不同名称,直到建国以后,才正式定名为“淮剧”,一直沿用至今。参见邓小秋《淮剧的渊源与形成》,《戏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1-193页。
⑳高义龙、乔谷凡、张弛《筱文艳舞台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4页。
㉑根据1963年录音(侯永奎饰赵匡胤,李淑君饰赵京娘)整理《中国京剧戏考·千里送京娘》(网址:http://scripts.xikao.com/play/80000032),访问时间:2013年12月4日上午10时。
㉒侯少奎、胡明明、张蕾《北方昆曲经典剧目演变传承论——以《单刀会》、《林冲夜奔》和《千里送京娘》为例》,《戏曲艺术》2013年第1期。
㉓陈均采写《〈千里送京娘〉创演始末》,见《京都昆曲往事》,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99-305页。
㉔《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序》,《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卷一,清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