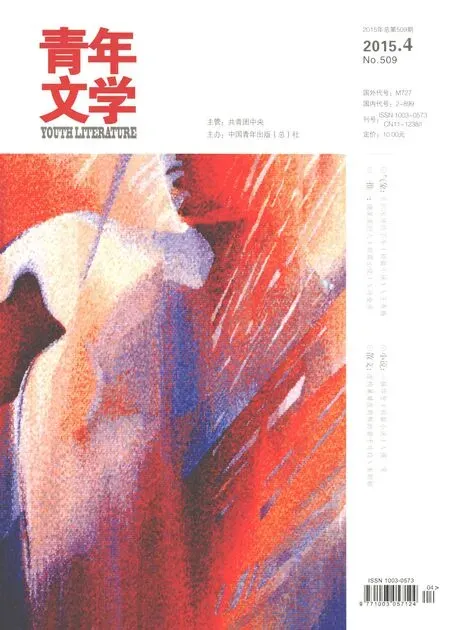来赋春,寻找远去的家园
⊙ 文/赋春小小
来赋春,寻找远去的家园
⊙ 文/赋春小小
赋春小小:本名吴细琴,一九八一年出生。热爱文学,多篇散文、诗作、新闻报道散见于《江西日报》《婺源报》《学习与思考》等报刊。
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哪里的一抹风景会牵动着心弦,哪里才是梦中的家园。当我们昂首挺胸行走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匆匆忙忙享受着便捷信息时,会不会在繁华中错过了精彩,会不会变得小心翼翼,相互防备隐藏了自我?
一
赋春镇位于婺源县的西南,交通便捷,商贸活跃。沿着蜿蜒小道前行,闻着扑鼻的芳香,恍若置身世外桃源,顿感豁然开朗。村庄隐现于青山绿水间,群山环绕,溪水欢腾,水口林处,一棵棵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依偎土地,张开臂膀,释放激情。枫香、樟树、红豆杉相处泰然,笑看世事风云。白墙黛瓦,高高的马头墙,缕缕炊烟绕心头。蓝天空旷无垠,白云自由惬意,一垄垄菜地,绿油油地生长。百年古建坐落村间,花虫鸟兽雕刻于门楼、堂前梁柱,珍藏着主人的美好愿望。散落的几间土坯房,简陋木门吱呀呀地响。五门同巷,邻里和睦。村民出出入入,笑容灿烂。
古驿道、徒步道纵横贯穿百个村庄,沿河流、穿山林、过田野,美不胜收。迎着冬日的暖阳,踏着厚厚的青石板,一步步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悠悠时光,岁月变迁,文化传承。来到赋春,放下匆忙的脚步,放下急切的心情慢慢游、慢慢品,你会惊喜、会心动。原来真实的情感一直都在,原来亲切平和的笑容如此温暖入怀,原来这里才是渴望寻找的家园,悄悄地你会爱上赋春这个美丽而风情的江南小镇。
二
如果不是友人带领,也许我会错过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盘坑村,沿着盘旋曲折的水泥路前行,路边竹木渐渐浓密,冬日暖阳透过枝头婆娑曼舞,平添一抹风情。透过车窗,我望见了最美的风光。
“这里就是徒步路口了。”友人用手指了指右方,“未通水泥路前,两个村群众都是沿着山道来回,从山外挑回生活必需品。”只见旁边有条山岔土路,一直通向山头,厚厚的青石板多了落叶遮掩仍依稀可见。友人是位乐观直爽的女子,前几年,刚从外打工回来,正遇上村里换届选举,她高票当选为村妇女主任。“昨天刚走了一趟山路,现在小腿还酸胀呢。”她笑着说。
沿山道从盘坑村至车田村有十里,上坡至山头步行一小段水泥路再下坡,友人踩着一双棉鞋,利索地前进。对于未探索的地方,心里充满了惊喜,习惯用好奇的双眼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山路渐宽,透过树林间隙遇见光的影子。阳光正暖,温柔明媚,树木千姿百态,不惧严寒,顽强生长。枯叶已落化为春泥,绿叶繁茂,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友人走走停停,不时回头望望。“慢些,别走得太快了呀。”我急切说道。她应了声,一会儿身轻如燕不见了踪影。
想必昔日来往的村民也是步履轻快吧,边挑着担子,边与同伴说说笑笑,担子里装满了粮食、干笋、干菜来到山外置换些生活用品,生活的期盼与幸福啊,如山道般弯弯长长。年轻的姑娘出嫁了,坐上花轿,过了山道就到了婆家,可心里多么不舍山里的家园,来年带上夫君翻越山头踏门看望年迈的双亲。当野果缀满枝头时,山间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跟随父母寻找着童趣。饱满的酸枣,风一吹哗哗掉落地上,孩子欢叫着,一双双透亮的眼睛盯着细小的果子,一颗又一颗,手拿满了,口袋也鼓鼓的,酸酸甜甜的滋味,像极了酸酸甜甜的生活。
三
我知道现代化平整宽阔的水泥路铺到乡村时,大人与小孩都是欢欣鼓舞的。可我不知道,盘旋蜿蜒的道路破山而过时,山会不会流泪,树会不会伤心,落叶下厚厚的青石板会不会愤怒。
山的那一方系着两个村庄:车田村和港头村。近几年,车田村村民陆陆续续搬迁至山外,建起了新房,远离了偏僻寂寞,与热闹相伴,高铁轰隆隆地响,忽地又拉近了现代文明。留在村里有年迈的老人,迟迟未婚的大龄男子。他们日复一日,心平气和地守护家园。最年长的老婆婆九十高龄,不辞辛劳养育三个儿子长大成人,老大老二成家后急忙走出了山村,小儿子五十余岁,智力不高孤身一人,母亲心疼小儿子,不顾老大老二好言相劝,执意留在小儿子身边。每天身体力行地烧菜做饭,照顾儿子起居。稍有空闲时就来料理菜园。
车田原名迎田,土地肥沃,群山环绕,村前山峦厚重连绵,似天然屏障,阻隔了城外的喧闹。山上种植苗竹,成片成林,节节拔高,葱葱翠翠。鸟雀栖息枝头,叽的一声飞入丛林,留下树叶哗哗地响。猴子身姿灵巧,来回跳跃,寻觅诱人的果实,村庄与竹林隔河相望,村民去山中采竹,有人卷起裤脚蹚过清亮的河水,有人踩着晃悠悠的木桥跨过河流。孩子们在河边玩耍,捉石子,打水漂,忘却时光。
车田是一方红色渲染的土地。据说,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与敌军日夜激战,获胜后红军部队曾在车田驻扎休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肩负着责任使命,挥洒青春与热血。热火朝天的生活场景,嘹亮的红歌悠扬回荡,在每个人心中荡漾澎湃。如今,硝烟已散,历史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村庄恢复了原有的平静。随意走在坑洼不平的羊肠小道,触摸低矮陈旧的土坯房,木门上闪闪的红星仍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好一处十里竹廊,好一个世外桃源。
诗歌
【汉诗·地方主义】
⊙ 皎洁心/徐俊国
⊙ 夏午的诗/夏 午
⊙ 厄土的诗/厄 土
特邀栏目主持:谷 禾
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话题绕不过当年的“京派”“海派”之争。且不说孰是孰非,“乡土”或者“新感觉”谁更接近文学之本质,“京派”“海派”造就了诸如沈从文、废名、施蛰存、张爱玲等个性鲜明的作家却是不争的事实。惜乎这样的争论,在诗歌领域并无太多笔墨的记载,轮转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时期,类似的争论却变幻成了“外省”对“京城”的集体反动,但无关写作立场和作品风格,而是话语权的强弱,它更多源于参与者的年轻气盛。今天回头再看,你也许会哑然失笑。
本期出列的三位诗人属于后辈,似乎没有这样的雄心,其作品却呈现了鲜明的海派风格。
七〇后诗人徐俊国若干年前离开他的“鹅塘村”,移居到了上海,变的是生存环境,不变的是他的“鹅塘之心”,他不关注都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而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更接近于自然的微小存在。恰恰这样的存在,才是更接近于他内心的。用《皎洁心》来界定他的诗歌写作也许再恰当不过了,当“月亮总是在最高的地方显现肉身/它让黑夜有了一颗皎洁的心”(《皎洁心》),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黑夜既是黑夜,也是沉浮在都市孤独里的诗人自己。如果说,《皎洁心》是自我安慰,《第三朵》则是对回到自然的感恩,唯如此,这白云方为肉体之家,这意外,才在“意料之中”。《夏末》写的是季节,是时间,更是人生况味。陶渊明的出现让诗歌有了纵深和沧桑感,但最后一句的“实现”一词也许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它过犹不及了。对于诗歌的表达,我主张浑然天成,书写生活的常态,呈现诗意的生活,而去除刻意。
八〇后诗人夏午则少了许多乡土的羁绊,书写更为任性和霸蛮。《不夜城》抛开了城,而专注于不夜城的人——“女人”,它不是城市史,而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夏午写得巧,写得开,写得干净利落。《大雨在早餐前来临》是一首回忆之诗,从眼前写到久远,通过“大朵大朵的泡桐花”,建立起了“我和祖父”“生与死”的联系,是以小见大,在“在意”和“不在意”之间,呈现感人的亲情。《为一首诗寻找读者》则几乎是宣言。美国诗人勃莱说“写诗就是在物质社会苦苦地坚持赠送礼品”,在我看来,此二者大约都是为自己的诗歌写作寻找坚持的理由。我想说的是每一首诗都如同一个人,它有自己的渊薮和命运,其知音迟早会来的。换句话说,你不用找,他(她)就在那儿。
同是八〇后的厄土的诗,具有典型的学院风格。不同于口语的“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类的诗歌从语言开始,或者干脆“语言即诗歌本身”“语言的诗意才是诗歌的唯一意义之所在”。读这样的诗,有时候需要一副“最强大脑”的大脑。不过有什么关系呢。阅读本身即是诗歌的一部分。作为读者,我想看一看他们究竟能把汉语的边界拓展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