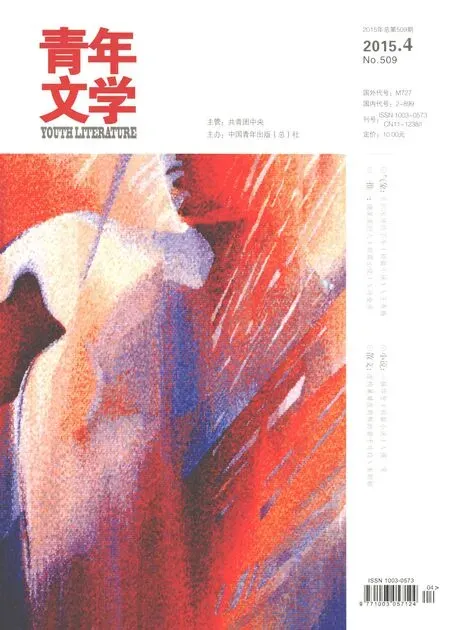静静的长河(访谈)
⊙ 文/赵 依
静静的长河(访谈)
⊙ 文/赵 依
赵 依: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硕士,现为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已在《当代文坛》《中华文化论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十余万字。翻译外国学者学术著作,译稿见《现代哲学》《美德与权利——跨文化视域下的儒学与人权》等书刊。
赵 依:先说说你自己吧。你的小说属于八〇后中的“乡土派”,我想你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对这种生活再熟悉不过,可否请你勾勒一下你生长的环境?父母、亲戚是怎样的人?你和你周围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生长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你是否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吃过苦、挨过饿、受过穷?
马金莲:说起八〇后的写作,我觉得自己的位置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一来是我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一个回族人,作品里自然会带有一个民族的特殊印记。二来,我生长于西海固并且书写的对象一直是西海固。至于西海固,它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地域偏僻,气候干旱,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而且基本都是靠天吃饭的那种农业生产。在我成长记忆里,可以说十年九旱,三年一大旱,两年一小旱,干旱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干旱倒是不正常了。
我出生在西海固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里,这个村庄就是我后来不断书写的扇子湾。二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在扇子湾生活,除了去学校上学,暑假都是帮父母务农,寒假在村庄里陪伴家人过着寂静的日子。村庄交通不便,小时候我们要去集市上,十多里山路靠步行和毛驴驮载,后来才有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靠的是村庄中间水沟里的一眼清泉。夏季用水量大,大家需要一大早排队去担水,冬季泉口结冰,厚厚一层,蹲着是舀不到水的,我们就给水瓢装上巨长的木柄,这样才能伸进泉眼去。我们这里极度不重视教育,女童教育更是薄弱,所以村庄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不念书。我们夏天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拔柴、割草、除草、放羊,冬天大家就在一起学习做针线。清真寺里遇到圣纪节的话,我们会成群结伙去寺里跟圣纪。总之,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是一种很自由很散漫的童年,就在大自然里接受着磨炼。我母亲等家人都是农民,亲戚也都是农民。我们把农民叫作泥腿子,想想其实挺形象,常年在土里劳作,两腿自然是沾着泥土的,这泥腿子很形象地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一个群体的艰难和苦难。所幸我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正是因为这个有利条件,才为我童年时候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也改变不了我的成长要经历一个被生计磨砺的过程。尤其像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母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在家里劳力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女孩子自然得像男孩子一样去挑起劳作的担子。
我很早就学会了女孩子必须会的活儿,后来还像男孩一样承担了一些繁重的苦活儿,比如赶着牲口犁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拉架子车,往车上抬粮食口袋,赶着毛驴去磨坊磨面,等等,都是需要比较大的气力的。家里孩子多,土地少,那时候没有挨饿,但是吃得不好,尤其九十年代初西吉连着几年大旱,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我们姐妹都在县城上学,家里开支很大,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和别的八〇后相比,我们西海固山区的孩子,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偏僻落后,还有苦难对生命个体的考验和磨砺。后来我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是中专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在家待业好几年,其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那时候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儿,因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要像每一个成年男女一样从事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相比之下,亲生父母还是比较娇惯我的,有些很繁重的活儿舍不得叫我们干,但是到了婆家,不存在这一说,我割麦子,跟着丈夫、小叔子、弟媳妇,一趟一趟,常常苦得站不起来。跟着婆婆做席面招待客人,守在寒冷的小厨房里一忙碌就是一整天,晚上洗完锅灶解下围裙,一双脚早就冻麻木了。西海固的生活,对我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了下来。
赵 依:能谈谈你那些年的个人心态吗?
马金莲:先说说小时候吧。那时候傻里傻气的,不知道生活的酸甜苦辣,大家都那么活着,我也就那么活着,有时候也觉得太苦了,尤其西海固山区的回族时兴早婚,女孩子不念书,十七八岁就说婆家了,二十来岁的人已经是好几个娃的妈妈了。看着这些姐妹的生活经历,我觉得不甘心,不愿意自己也走这样的路,所以当我有幸走进学校上学,我很努力,很小就懂事了,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所以一路念书,大人从不用操心我的学习成绩。
做了人家的小媳妇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具备文化知识的女性,我经历过中等师范学校的生活,通过读书,知道外面是一个和西海固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像我们这样地生活,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女人不仅仅是跟着丈夫过柴米油盐的日子、生孩子、操持家务,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比如看书、学习、写作。事实上我一直坚持着写作,就是苦得直不起腰的六月天,割完麦子的夜晚,我还是会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悄悄爬起来,坐在炕头上拿着笔在纸上划拉一些文字,表达内心对生活的理解。当然,这样的坚持,没有明确的宏大的目标,只是觉得文字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一个手段。通过阅读和书写,日常的辛苦变得可以忍受,苦涩的生活里好像有了一抹淡淡的甜味。我当然不知道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写作,并且写出了这么多作品,那时候我只是单纯地爱着文字,坚守着这种可以丰富内心、安慰内心的表达方式。
赵 依:你的小说总是围绕土地和乡里,书写苦难,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还是出于一种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悲悯?
马金莲: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写道:我的文字都是关于村庄的。我的灵感的源头,就是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写作写什么?这个可能会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困扰过我,因为我一开始呈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故事……童年时代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而这些,都是在我熟悉的乡村发生,所以,我的文字注定绕不开土地和乡里。而西海固乡村生活,总是和苦难难以分割,所以不管我是自觉还是无意,都不可避免地要书写苦难,因为苦难和生活是紧紧依附、交融在一起,是水和乳,是血和肉,绕不开,逃不掉,只能面对。
十八岁的时候,我开始文学经历,这时候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成熟到去考虑自己拿起笔写点文字的初衷,和需要承载的意义,我更对文学没有产生过什么宏大的梦想。我只是觉得扇子湾的人都活得太苦了,大家的故事活生生的就在眼前,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把他们在生计里的挣扎和苦难表达出来,如果可以算作初衷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初衷了。对于写作,我没有别的奢求,就希望这样一直一直地写着,用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内心朴素的想法,以朴素的方式面对世界。近来有很多对我的劝言说,摆脱苦难,不要再重复苦难,因为西海固作者的作品,给人第一眼就有西海固贫穷的影子,有千篇一律的印痕,更难以摆脱石舒清郭文斌等人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宁夏作家都是一个路子,鲜有新路。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
我以为,不是写苦难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我的笔触不够深入,远远没有挖掘出苦难背后的东西,仅仅浮于讲故事的层面,情节深处那些人性中闪光的鳞片,或者需要批判反思的诟病,都是需要往更深处开拓挖掘的。《绿化树》也写苦难,《心灵史》同样在写苦难。今天,我们距离文学前辈还有多远?跟在他们后面赶路,不能只是战战兢兢地去防备,避免踩上前面的脚印,刻意回避重复;而应是大着胆子,迈开步子走路。说不定,就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会不经意间超越了简单的重复,深化了自己。
赵 依:你后来离开农村,进入民盟固原市委员会工作。这种离开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如何?
马金莲: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我在乡镇政府工作了三年,眼界大大开阔,对社会有了一点比较复杂的认识。二〇一〇年秋进入固原市民盟,离开了乡村,在真正的城里工作生活了。离开了乡村,再回头看,眼界和从前有了差异。也许身在其中的时候,有些事物是看不清楚的,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一旦拉开距离,就能更冷静地思考,更成熟地表达,所以这几年我的文字比之前有了成熟和深度。当然,离开乡村,感觉与生活远了一步,幸好我的亲人们都还在农村生活,我一有空就往老家跑,婆家、娘家、亲戚,我需要关注农村的变化和人们内心的变迁,需要紧紧抓着生活的脉搏,不能与生活有隔膜。现在,感觉生活稍微比过去自由了一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和写作了,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从前想都不敢奢想的。所以我很感激,感激生活、命运、身边的人,感激遇上的每一个好人。我不敢懈怠,想趁着年轻再写几年,多写点比较好的文字出来。
赵 依:你和文学圈子里的作家、学者等来往和交流得多吗?
马金莲:说实话,不多。西海固本身偏僻,加之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是,疏于交流,不等于大家遗忘了我。相反,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我的写作,有很多事我一直铭记在心,感念不已。二〇一一年,我女儿高烧住院,我一个人带着她连续三天守在医院,这时候县文联打来电话,说白烨来西吉了,想要见我。当我带着一脸疲倦赶过去,才知道白老师的儿子马上要结婚了,而白老师为了见我特意在西吉多留了两天。很快白老师给我写的评论在《文艺报》登出来了。二〇一三年,《长河》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王干老师给我写了大篇幅的推荐语,并且在年终的评论里大篇幅论及这篇作品,而直到我去鲁院上学之前,我没有见过王老师并且连电话都没有通过。《长河》进入二〇一三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好几个老师辗转送来了祝福,而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面。所以,让我一再感受到了文学的温暖。
赵 依:最初出现的八〇后作家都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和城市色彩,这些年,包括你、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在内的,一批来自乡村、来自生活底层的青年写作者也逐渐成为八〇后作家的代表,你有参与创造这种不一样的八〇后写作史的感觉吗?
马金莲:呵呵,没有这野心。
赵 依:你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马金莲:有。我们回族作家石舒清就是我很敬重的人,不管是他做人的沉稳品格,还是为文的境界,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另外,喜欢迟子建的作品,喜欢作品里那种一以贯之的美好和纯粹。在作品思想深度上,我推崇张承志。
赵 依:很多人说你延续了萧红文脉,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马金莲: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作《蹲在洋车上》的小文,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她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如果要在我们之间寻找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我觉得肯定是我们都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凭着本能抒发和表达的愿望,并且将这一本能表现在作品里了。我们的写作,都完全地出于一片赤诚吧。
赵 依: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你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和创作小高峰,《长河》书写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信仰和一股力量,柔中带刚,平淡闲远。这既勾连着你的民族和宗教,又显示出你在更大范围内对人类命运所做的思考,那么这种旨趣具体是如何生发的?
马金莲:《长河》这篇作品和我的很多作品一样,是手写的,初稿写在一个旧教案本的背面。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上面划拉着,开始的时候连题目都没有,只是被村庄里新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触动了心弦,想表达点什么。表达什么呢?第一个故事,即伊哈的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是我小时候送过埋体的一个人,他死后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女人自然要再嫁,而孩子们活得很受罪,念书的时候他们和我一个学校,常常见到他们赤裸的脚板和一脸的泥土。伊哈的故事写完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是个男孩,从小心脏病,十二岁时按照医生预料的那样去世了。这样一个生命,匆匆地离去,我们除了惋惜,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一边琢磨,一边写。到了第三个故事,好像一发而不可收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明朗了,我就是要写死亡。——我们西海固的山村里的回族的死亡,朴素的清洁的简单的悲伤的死亡。这个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最初由五个部分组成,《民族文学》的编辑哈闻看了后建议我删除最后一个,同时给我分析了原因,另外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认真地思索了,并进行了修改。
作为一个回民,我很小就成长在一个信仰气氛很浓厚的环境里,可以说信仰已经成为一个不自觉的习惯和一股潜在的力量,深深地潜入我生命的深处。所以说信仰对我的作品来说就是一种本身存在的品质。宗教信仰影响了我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气质,我在作品里不用刻意去体现这种影响,但是会在作品中有反映,那是不自禁流露的。因为信仰以及信仰对心灵产生的影响,早就存在,信仰是生活里的盐,从来都没有缺失过;我只要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和生活就行了,这种影响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写作中的审美取向自然而然摆在那里。这种民族心理的影响流露在作品中,就呈现出《长河》这样一个风貌。而世界上所有的活着,最终都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所有的生命,最终都会死亡,死亡是所有生命不可避免的结局和悲剧。这么一延伸,自然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命运。而我最初写《长河》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很多东西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赵 依:你非常关注那些以柔弱顺从的姿态,去抗拒旧观念或者强大命运以及严酷自然环境的女性。在《碎媳妇》《风痕》《搬迁点上的女人》《绣鸳鸯》《离娘水》等作品中,你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自我生命关照。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这种女性关怀意识?
马金莲:西海固作家基本上都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作为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一分子,自然也会具备这样的写作情怀。这是那片土地和那土地上的生活赋予的一种生命的底色。这种底色会渗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西海固作家群有一个相对优良的传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文学很尊重,是以接近于痴迷的态度去对待的。相对落后的封闭的环境,造成了我们相对奇特的文学状态,我们集体呈现出一种内敛、安静的状态,远没有外界的浮躁和喧哗。而我作为一名女性,不自觉地就会更加关注身边的广大女性;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把她们写进文字,定格在纸上。就在这书写过程中也许就不自觉地流露了一种女性关怀意识。
赵 依:你的小说里总会出现很多娃娃,这些娃娃大多忧伤而平静,被伤害而不怨恨。例如《糜子》中法图麦在冰雹击落的糜子地里痛快淋漓地狂奔,你也常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马金莲:的确,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虽然后来为了避免单调和重复,也尝试拓展叙述角度,但纵观我目前一百多万的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儿童视角占据了一半之多。
我文字里书写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关于从前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另一类是关于八十年代之后的。
之前的时光,我是通过老人的口述加上自己的想象去体悟的。最庆幸的是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老人都健在。老人们本身就是一段故事,一段从岁月深处跋涉而出的经历,每一个老人的身上都带着个人的传奇和岁月的沉淀;而那些过往的岁月,含着我所向往的馨香和迷恋的味道。太爷爷当年跟着他的父亲拉着讨饭棍子从遥远的陕西到甘肃的张家川,再到西海固落下脚来,到后来经历了海原大地震。自然的灾难在上演,生存的课题在逼迫,这些目不识丁的人,依靠着什么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了那么纯真纯粹朴素简单的品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奶奶常来我家做客,来了就和我们姊妹睡一个炕,她的故事真是装满了肚子,一讲就是半个晚上。还有奶奶呢,这位饱尝了人间冷暖的妇女,肚子里更是塞满了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经历过的,说起来滔滔不绝,真是叫人佩服她那朴素本真却很迷人的口才。我喜欢听故事,听后就记住了。等我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这些故事自然冒出头来,我不得不打量它们,然后尝试着写了下来。《坚硬的月光》《老人与窑》《尕师兄》《柳叶哨》《山歌儿》等都是。这些文字里,自然都是已经逝去的岁月里的事情,当我要书写这些故事时,切入点自然是儿童视角,也就是童年的那个听故事的我。而如果换作成人视角,怀着虔敬敬仰的心态去写,我怕自己写不好。
另一类,是我所经历过的故事。书写和自己成长有关的故事,选择自己童年时候的角度,更好表达一些。
赵 依:你非常注重风物的描写和画面感的营造,不少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片段,例如《醉春烟》《手心里的阳光》,你的诸多作品中也不乏以画面来结尾的小说,例如《少年》《细瓷》《墨斗》。这种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是如何在你的创作中形成的?
马金莲:我喜欢沉默和观察。长时间静静地观察一些人和事,而眼睛看到的自然是画面,这些画面内化为文字,就会呈现出一种画面感较强的状态。语感、行文风格,都是在长期的坚持书写中磨炼出来的,是一种感觉,一种习惯;但是要准确描述出这样一个感觉或者习惯,我觉得是困难的。
赵 依:你已经来到城镇,是否正考虑逐渐将写作题材拓宽到城镇?小说《一个人的地老天荒》算不算对此做出的一种尝试?直言不讳地表达一下我的个人看法,相较于乡土题材的小说,你的城镇书写在语言和情节架构等方面稍显生疏和刻意了,似乎是独立于你以往小说的另一种美学风格,并不那么流畅自然和平静内敛。能不能请你谈谈今后的创作方向?
马金莲:首先,谢谢你注意到《一个人的地老天荒》这个中篇。它是一个尝试,是我第一次把故事从乡下搬到了城里,但是它无疑延续了乡土叙述的风格;在城市题材这方面没有探索更谈不上新的发现,所以它是有欠缺的,不成熟的。但是,随着对生活的了解、认识和感悟,我想,以后的写作不会狭隘地界定在乡村这样的一个范畴,而是会试着突破、融合。毕竟在当今普遍城乡一体化的社会里,就连我们这偏僻的西海固,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个作家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要不断尝试和突破。我也一样,需要努力,再努力。
气象
⊙ 王秀梅喜欢在作品中营造梦幻与现实暧昧不清的场景,这些场景质疑着我们素日苦苦经营的体面与斯文,指向我们内心混乱无名的潜意识。
——郑润良
⊙ 她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她进入现实生活的通道,有点狭窄,有点幽暗,却又有着难以察觉的执拗和敏锐。
——张艳梅
⊙ 王秀梅小说的引人入胜,多有赖于对真实与幻魅的辩证。
——马 兵
⊙ 我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靠文字才能发声的人。
——王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