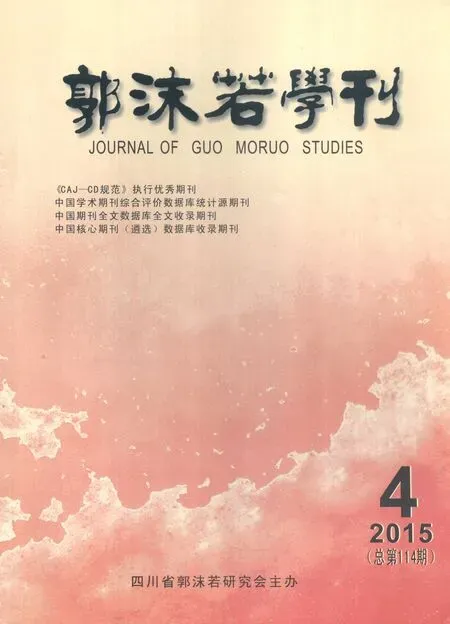创造社作家段可情与德语文学翻译
何俊
(西南交通大学 德语系,四川 成都 610031)
创造社作家段可情与德语文学翻译
何俊
(西南交通大学 德语系,四川 成都 610031)
创造社成员和“普罗诗派”代表人物段可情是为数不多的近代留德作家之一,译介了大量的德语文学作品,其中既有对非知名作家的昙花一现式的偶然译介,也对德语国家知名作家作品的译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就其翻译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来说,欧洲包括德国的书信体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对他的作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段可情;创造社作家;德语文学翻译
近代有留学经历的作家,留德学人实在是寥寥无几。这是因为近代留德学人中研习文科者甚少,而专攻文学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专门以作家名世、仅凸显创作成就者极少;因此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不如留学日本和英美的学人,更是远远落后于留法生。
有关民国时期的留德作家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情况,叶隽在其著作《另一种西学》里已经做了大量详实细致的爬剔梳理工作。吴晓樵在对该著作的书评中写道,叶隽的研究聚焦的尽是知名主流学者比如宗白华、陈铨与冯至等,对日渐淡出今人视野的边缘学者鲜有挖掘、缺乏关怀,并提出对近现代有德语国家留学经历的作家的关注至少可以扩大到李金发(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在留法期间曾长时间在柏林旁听)、段可情(创造社成员,曾留学柏林)、赵伯颜(文学研究会成员,曾留学维也纳)等人身上。笔者就将眼光投向这位渐渐淡出学界和大众视野、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的留德作家和翻译家——段可情,着重探究其在德语文学翻译上的成就。
一、生平经历
段可情(1899-1994),四川达县人,原名段传孝,学名传定,号白苑。笔名可情、白莼、锦蛮等,系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曾任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据一份由段可情本人证实过的年谱简辑,他于1919年留学日本,1922年3月负笈欧洲,先在巴黎住了一周,随后到了德国,求学于柏林大学,同学中有徐冰(邢西萍)等共产党人。来柏林后,经章伯钧介绍加入国民党左派。在留德期间,多次参加反帝运动,深受共产党人思想影响,其时与在柏林的中共旅德支部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夫妇交往甚密。其留学长达近四年,直至1926年初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提及段可情留学前苏联的经历,却没有考证出他此前在德国留学长达四年之久,故而误以为他的德语作品翻译有可能是经由其他语言(俄语,笔者注)转译。既然段可情的履历中完全存在他掌握德语的信息,那么也可以大胆推测他的德语文学译介工作直接借助的是原文德语。民国时期的德语文学翻译多半取道他国语言,尤其是经由英语和日语中转,有些即便译自德语,也常在翻译过程中参考和借鉴英语或日语译本,比如郭沫若的《浮士德》翻译即是一例。在从原文翻译德语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民国文人学者实属凤毛麟角,除郭沫若、郁达夫、冯至、陈铨、杨丙辰、宗白华等,这里可以加上段可情的名字。
段可情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翼——“普罗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社团活动方面的功绩也不容后世遗忘。他是文学团体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与成仿吾、王独清和郑伯奇同列为四大编辑委员。他在柏林留学时跟张闻天同校,跟当时在维也纳留学、同为川籍(江安)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研究会成员赵伯颜有过通信往来,跟宗白华、郁达夫等也有信件交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跟聂绀弩、孟十还同校,回国前就给郭沫若写信表达了加入创造社的热烈渴望,并对《创造月刊》的办刊内容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要多注重文艺理论及批评,第二创作短篇特别精选,第三多载国内及世界文坛消息,第四要尽量介绍本国文坛的佳作及完善译品(可附一短评),翻译不用文言,署真实姓名,反对重译。1926年底段可情从苏联回国,加入创造社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社刊《创造月刊上》。段可情还曾奉党的指示和郭沫若之托,与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一起专访过鲁迅先生,为消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大新文学社团之间的误会和分歧,并建立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奔波斡旋。段可情的这些文学社会活动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1927年11月9日《鲁迅日记》称,“午后,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1927年11月19日《鲁迅日记》又称,“下午,郑、段二君来”。这里鲁迅记载的两次访问即商议共同恢复《创造周报》、提倡革命文学之事。段可情对郭沫若素来心怀敬重,从苏联通信,到回国后共同战斗,俩人交情颇深。1992年正值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段可情赋诗一首,深情缅怀了二人之间既是巴蜀同乡、又是革命文学盟友的交情。诗云:“几渡西窗细读诗,乡情谊道早神驰。二贤孤竹联珠久,万里双鱼结网迟。归国欣参创造社,追随高举普罗旗。难忘最是春申夜,握手凝眸促膝时。”1979年6月11日,段可情在郭沫若逝世的次年在《成都日报》上撰文《忆郭老》。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段可情重返四川故里,担任省立三台中学校长并兼任语文教师,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及段可情本人翻译的海涅诗歌都是他的讲授内容。1956年他又担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与时任文联主席的李劼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具有较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
跟诸多创造社作家一样,段可情先是写诗,后转向小说创作。早期较有影响的诗作是组诗《旅行列宁格勒》(共6首),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有《铁汁》《杜鹃花》《火山下的上海》、《绑票匪的供状》《故乡之梦》等,这些作品克服了早期创造社以自我为中心、为艺术而艺术的弱点,展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
二、德语文学翻译
陆耀东谈及民国时期的德语文学译介情况,就把段可情与郭沫若、冯至、陈铨、郁达夫等同列为“译介、研究德国文学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人。就段可情翻译的德语地区作家的知名度来看,他翻译过一些不甚知名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如同飞逝而过的流星一般,仅仅被译介过一次就倏忽不见;为了迎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文学局势及国内读者接受情况,他也翻译过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
(一)对非知名作家的译介
据《段可情年谱简辑》,段可情的德语文学翻译活动集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硝烟四起、炮火连天,配合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左翼反战思潮,德国的战争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广泛传播。段可情不拘反战文学兴盛的时势,翻译出了德语国家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家,即使是在本国也不甚知名,时至今日更是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比如段可情翻译过德国自然主义作家哈尔特列本(Otto Erich Hartleben)的《彩色鸟》(Der bunte Vogel),刊登在1930年4月10日的《小说月报》21卷4号上。译者在译后介绍原作者“也是自然主义运动的一员,诗文均佳,诗主抒情,散文则充满讽刺和诙谐的气味”。
奥地利女作家埃布纳·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段译爱斯巴侯),创作倾向现实主义,段可情在《现代文学》1卷6期(1930年12月16日)上译出她的小说《犯罪的女人》(Die Sünderin)。在《现代文学》1930年第1卷第6期上段可情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两大文豪百年纪念》的文章,介绍了保罗·海泽(Paul Heyse,段译保罗·海士)和埃申巴赫,选择这两位作家的原因是恰逢这两位作家诞辰一百周年。不过后者系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可见文章标题称“德国两大文豪”有值得商榷之处。介绍海泽时自然不忘提及这位德国作家是1910年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并说他在德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的莫泊桑——同为“短篇小说之王”;介绍埃申巴赫则称其作品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受到了托尔斯泰不少的影响,尤其推崇她的作品《公儿》(Das Gemeindekind,今译《死刑犯之子》或《乡村里收容的孩子》。
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埃德施密特(Kasimir Edschmid)也引起了段可情的关注,翻译出其小说《曼冬梨的婚礼》(Maintonis Hochzeit),发表在《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1卷第3期。译文前有原作者的简单介绍,谈及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即是一本有关表现主义的理论著作,并介绍了收录该小说的集子《六个河口》(Die sechs Mundgänge)。段可情还翻译出现实主义作家克洛格尔(Timm Kröger,今译克勒格尔)的小说《一件不要人相信的故事》(Eine Geschichte,die man nicht zuglauben braucht),刊登在《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10日)。译文后有对原作者的简单介绍,称他是跟施托姆和弗伦森(Gustav Frenssen)齐名的北德乡土文学家,描写背景都是北德的荒野、海滩和小城,并赞誉他们的文字在德语文学花园内有其地位,虽不及那些“参天大树”一般伟大,却是在花园里“精巧夺目的琪花瑶草”。译后还介绍了原作者的几部其他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通行税》(Um den Wegzoll)、《旧箱子》(Aus alter Truhe)以及收入该翻译小说的集子《一个寂静的世界》(Eine stille Welt)。另外,段可情还提到原作者写过一篇儿童故事叫做《何处去》(Wohin),并说想近期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就现有资料来看,似乎未果,至少未公开发表。此外段可情还翻译过霍尔茶孟(Wilhelm Holzamer,今译霍尔茨阿默)的小说《窗边》(Am Fenster),发表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第4号,署名段白莼。段可情在译后介绍原作者为德国薄命文人之一,但其短篇小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提及他的其他作品比如诗集《光明》(Zum Licht)、散文集《在污秽的街上》(Auf staubigen Straßen)和收录《窗边》的短篇小说集《狂暴的妇人》(Die Sturmfrau)。1937年上海启明书店出版了施落英编纂的《德国小说名著》,其中就收录有段可请翻译的《窗边》。
段可情还翻译过奥地利女作家Vicki Baum(菲姬·宝蛮,今译鲍姆)的作品。这位女作家因为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暴政而深受迫害、饱经颠沛流离之苦。他翻译的具有某些自然主义特点的《大饭店》,连载于《文艺月刊》1934年第五卷第一至第四期。其实这部小说原名叫做《饭店里的人》(Menschen im Hotel),1932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时才改名叫做《大饭店》(Grand Hotel),段可情该书的译名可见是为了迎合观众口味。段可情翻译鲍姆的这部大作,不知有无声援她的政治主张之意,但更看重的恐怕是其一炮打响、大红大紫的名号——它自1929年横空出世后就受到好评如潮,1932年还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也正是这个原因,刊载《大饭店》的第一期《文艺月刊》扉页还印有原著者的照片及多张《大饭店》的剧照,并有简短介绍性文字《宝蛮女士与〈大饭店〉》,提及原著者为了体验生活,到柏林最大的饭店里做了三个月的招待。
段可情还翻译了德国女作家碧萝芙(Margarethe von Bülow)的小说《莪尔菲斯村的幸福钟》(Die Glücksuhr von Wölfis),发表于1931年《现代文学评论》创刊号(1卷1期)。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女作家,故而在同一期段可情又翻译发表了德国人巴斯特撰写的专文《德国短命女作家碧萝芙的小说》,向国人详细介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作家及其非同一般的短篇小说创作才能,为这位年仅二十四岁就阖然长辞的女作家扼腕叹息。《彗星》1933年第1卷第5期还刊发了段可情翻译的《小尼姑》,《流露月刊》1933年第3卷第1期则有他译的《刈草者》,原作者皆署名“瑞士查痕”,除译文外无任何附记,这就给原作家的考察带来很大困难。
以上较为小众的作家写作风格和从属流派各异,但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命运都相似,即就现有资料来看对其译介均无后继。就算是段可情本人对他们的翻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作为译者的段可情,其选择作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卫茂平认为出于偶然、并无偏好,否则“想必他不会初尝辄止、不断变向”。与以上作家作品命运相似的是德国新古典主义作家恩斯特(Paul Ernst),他的小说《寂寞》(Der Einsame,标题原意实为《寂寞的男人》)由段可情译出,署名段白莼,发表在《小说月报》1931年22卷3号上。译者在译后附记中评说原作者“是提倡新古典主义的”,又说“他为文古色盎然,但朴茂之中却夹有新意,并不是死学古典主义,而去作古人的傀儡”。惜乎段译之后国内翻译界应和寥寥,就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而言,其小说标题“寂寞”二字可谓一语成谶。段可情还翻译过德国另一位新古典主义作家苏尔池(Wilhelm von Scholz)的散文《少年时代的朋友》,发表于《橄榄月刊》1931年第15期,并在该译文的后记里提及了已在国内介绍的名剧《和影子赛跑》(Der Wettlauf mit dem Schatten)。1932年系歌德百年忌辰,其时国内的战火纷飞却没能阻挡各种纪念歌德的作品纷纷问世,比如同年《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就刊登了段可情翻译的德国作家赫寇尔的《歌德的死》。
此外段可情对德语儿童文学亦有涉猎,他翻译过波守斯(Waldemar Bonsels)的童话《蜜蜂玛雅的冒险》(Die Biene Maja und ihre Abendteuer),1939年由上海少年读物出版社发行。《彗星》1933年第一卷第六期则有汤增扬写的书评《“蜜蜂蚂雅的冒险”:德国波守斯著,段可情译》。段可情的德语文学翻译作品数量不可谓不可观,但绝大多数都发表在当时的期刊上,这本童话是他发行的寥寥无几的单行本之一,另两本是他翻译的海涅的诗集《新春》(Neuer Frühling)和施尼茨勒的小说《死》(Sterben)。
(二)对知名作家的译介
段可情还翻译过海涅的诗集《新诗集》(Neue Gedichte)的第一卷《新春》(Neuer Frühling),1928年7月由上海世纪书局出版。在翻译后记中他对海涅的“颗颗珠玉般的小诗”称赞有加,称其“低徊委婉的情调,流水鸟声般的音节,尤其是字句的构造,可算极尽艺术的能事”,比他“从前读中国古乐府,觉得是另具一个世界”。此外,段可情还计划翻译海涅《歌之书》(Buch der Lieder)中的《还乡集》和晚年革命诗集,可惜后来未能实现,至少未见公开发行。海涅后来从浪漫主义诗人转型为革命民主主义斗士,段可情译出其代表诗作《织工歌》(Die schlesischen Weber,今译《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表于《彗星》1933年第1卷第2期。
1946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裔瑞士作家黑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了段可情的关注。他在《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1卷第4期上翻译发表了《赫尔曼·黑塞评传》,原作者是德国人威尔赫谟·孔辙(Wilhelm Kunze),曾与黑塞保持长达十年的通信(1920-1930),文章介绍说黑塞是现代德语文学的常青树和领路人,对黑塞的作品评价颇高。同一本期刊后有段可情翻译的黑塞的小说《作家晚会》(Autorenabend),署名段白莼,这有可能是海塞中译的开端。
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是段可情在翻译德语文学作品时较为垂青的又一位作家,翻译过他的小说《死》,1930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原作者译名显尼志劳。颇值一读的还有段可情写的翻译后记,文章介绍原著者时别出心裁,不述其生平而先言其民族即犹太族,谈及该民族强大的经济地位,并与操纵上海经济大权的英国犹太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联系起来,展示出一段犹太人海外活动史,由此构建了施尼茨勒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关系。该小说非常畅销,1933年4月再版累印两千册。这也与当时国内文坛对这位奥地利作家翻译的蔚然成风不无关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丁西林、焦菊隐、袁昌英、田汉、赵伯颜等都翻译过他的剧本,除段可情外还有施蛰存、陶晶孙、周瘦鹃、刘大杰、叶灵凤、耿济之、林微音 等翻译过他的小说,虽然大多都系英语或其他外语转译。
民国时期对施笃谟(Theodor Storm,今译施托姆)的翻译呈现如日中天之势,他的作品经由大量不谙德语的文人雅士自英语、日语或俄语转移出来,也不乏通晓德语之人由德语直接译出,比如郭沫若、郁达夫、唐性天、赵伯颜等,这个名单还应添上段可情的名字。1933年和1935年,《文艺月刊》4卷6期和7卷3期分别刊登了段可情翻译的施托姆的短篇小说《一位沉静的音乐师》(Ein stiller Musikant)和《日光中》(Im Sonnenschein)。此外,段还翻译了施托姆的短篇小说《大厅中》(Im Saal),刊于《人间世》1936年第二期。
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消息经由瑞典科学院公布便不胫而走,甫一传至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界和翻译界就有了反应。段可情翻译的《到坟园之路》(Der Weg zum Friedhof)和《神童》(Das Wunderkind)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6期,署名皆为段白莼,后一篇后来被收录于1935年然而出版社的《世界短篇小名作选》,前面有关于托马斯?曼的传记。此外,段可情还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小说《殴打》(Wie Jappe und Do Escobar sich prügelten),发表于《文艺月刊》1936年第9卷第6期;《衣橱》(Der Kleiderschrank)译者署名段白莼,发表于1929年第20卷第12号。另外,《衣橱》也被收录进1937年上海启明书店出版、施落英编纂的《德国小说名著》一书。相比之下,托马斯·曼的胞兄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在中国的译介则显得寥落许多,这也许跟他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不无关系。1934年,段可情翻译出亨利希·曼的两篇小说《心》(Das Herz)和《奇遇》,分别发表在《中国文学》创刊号(1934年2月)和1卷2期(1934年3月)上。同年5月位于杭州的《艺风》杂志第2卷第5期还刊登了他翻译的亨利希·曼的《少女们》。
三、欧洲书信体文学对段可情创作的影响
就具有留学背景的近现代作家而言,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就是其留学经历、对外语的掌握以及对外国文学的涉猎对其创作产生了哪些可能性影响。留日的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及其中的情爱描写有借鉴日本私小说的痕迹,以戴望舒、李金发、艾青等为中心的留法作家接受并模仿法国现代诗派代表人物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等,留学日本却对德语文学情有独钟的郭沫若的诗剧创作则可窥见《浮士德》的踪影,这些实例都体现出留学背景对作家群体的创作会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并为其创作打上或深或浅的烙印。有过留德经历和德语文学翻译实践的段可情,其创作经历深受欧洲文学体裁书信体小说的影响。
欧洲书信小说的鼻祖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作家奥维德,他首创的诗体书简《女杰书简》(Heroides)对后来欧洲书信体小说的诞生起了间接的催化作用。16世纪中期,以爱情为题材的书信故事集在意大利发展迅速,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文学门类carte massagiere。这种文学形式很快传到了西班牙,胡安·德·塞居拉(Juan de Segura)创作除了欧洲第一部书信小说《书信往来》(Processo de cartas,1548)。继西班牙人之后,书信故事集这种形式被法国人采用,并在沙龙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继而在英国大受欢迎。17世纪的欧洲,书信体小说越来越受到推崇,18世纪后半期这一文学体裁则呈现空前绝后的繁荣状态。1741年理查逊创作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Pamela),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歌德1761和1774年相继出版《新爱洛依丝》(La nouvelle Hélo?se)和《少年维特的烦恼》(Der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就德国文学而言,书信体小说这一体裁在《少年维特的烦恼》时期抵达巅峰,但此前也有1771年的拉罗赫(Sophie von La Roche)的《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Sternheim),歌德承认其对自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正处于启蒙时期,人的主体性逐渐凸现和彰显出来,人们开始追求自身的身份表征以及个体的情感和共鸣。与此同时,人们也有了一种告知他人、向人倾诉的强烈愿望,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用来告白的文学形式,比如日记、自传、信件和书信体小说等。这些体裁的初衷是要表达内心深处的热烈情感,引发读者共鸣,甚至让读者潸然泪下。此后德国浪漫派作家也创作了一些书信体小说,比如蒂克(Ludwig Tick)的《威廉·洛威尔》(William Lovell),布伦塔罗(Clemens Brentano)的两卷本小说《郭特维或母亲的石像——一部野性的小说》(Godwi oder das steinerne Bild-ein verwilderter Roman)中的第一卷也是用书信体小说写成。至19世纪,书信体小说在德国虽已式微,但直至20世纪仍呈现不绝如缕之态,故而从这一文学体裁可以窥见德语文学史暗藏的一条主线。
1922年郭沫若《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问世,西方书信体小说进入中国,其后掀起上个世纪20年代的“维特热”,并催生了中国本土作家西洋式书信体小说的创作热情。书信体小说在国内呈现的热潮既与中国传统尺牍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深刻渊源,更与五四的时代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引进则对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大多通晓外语、崇尚西方文学,很多人也都具备留学经历,这些都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们不光欣赏外国小说展示的异域风情和新奇情节,也从中模仿习得新的创作方法与技巧,这就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变化和革新。几百年来的旧小说章回体与呆板的固定形式被最终打破,书信体小说在这样的文学时代背景下进入中国文坛,无疑是如鱼得水,很快扩展壮大起来。另外,五四时期的中国与18世纪的西方社会所处时代背景颇为相似,对人的启蒙成为时代赋予文学的首要任务,揭露和批判社会现状、塑造个体人格、追求个性自由、建构主体性话语则是中外文学作品母题中的共通应有之义。郭沫若在《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的引序中谈及翻译的动机:“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此书主人公维特之性格,便是“狂飙突进时代”(Sturm und Drang)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维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个伟大的主观诗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经验和实感的集成。”相似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背景,使书信体小说这种独特的文体一经引入就蓬勃生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结出累累硕果。
据研究统计,民国时期受到书信体小说影响而在国内出版的同题材作品计达到191篇 (部),除了郭沫若本人的创作,还有一大批作家也纷纷小试牛刀,尝试着驾驭这一舶来文学体裁。尤其是1926-1932年间共出版书信体小说139篇(部),占整个民国时期这类作品总出版量的73%,是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创作繁盛期。这股书信体小说热潮也直接影响到段可情的创作。他当年在文学社团创造社任编委时就在本社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即是书信或书信体小说:《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发表他于郭沫若的通信,《洪水》半月刊1927年第3卷第27期刊则有他与郁达夫的通信;《创造月刊》1927年第1卷第8期刊登《一封退回的信》,1928年第2卷第2期《一封英兵遗落的信》,皆为书信体小说。段可情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对这类文学体裁情有独钟,跟当时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传入的郭若沫翻译的歌德同体裁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
四、结语
时至今日,作家和翻译家段可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被人遗忘,他民国时期的作品似乎难见再版,迄今也未见他的创作和翻译作品全集。就一个学者、作家在学界的声誉变迁来说,抛开本人作品本身的学术和文艺价值,也有诸多权力政治等外部因素在发生作用。不少今日已经不再陌生的德语语言文学家的名字比如陈铨、杨丙辰、李长之等,也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才从积满灰尘的档案中走进大陆学术界——不仅仅是德语语言文学界。类似段可情这样著译并举且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近代学者,可纳入文学创作、翻译(史)和留学教育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视阈中来考察和探究,理当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责任编辑:陈俐)
注释:
①叶隽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20-21页附有《留德学人中任大学校长情况简表》,该表也可以加上段可情的名字。
②据咸立强的探究,赵伯颜还属于创造社的“外围同人”,参见:咸立强.寻找流浪的归宿者创造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1页。
③有些学者认为段可情是当时的“创造社”小伙计之一,对此咸立强表示异议,参见:咸立强.创造社小伙计若干文坛的考辨[J].郭沫若学刊,2013(3),第58-59页。
④《彗星》于1932年创刊于南京,由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任职的段可情联同宣传部总干事项德言和青年特约编译员吴云峰(又名吴铁峰)创办。该刊物虽与左联无组织上的联系,但暗中却遵循左联的文艺路线。终因内容进步,该刊出版四年后于1936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查封。参见:张效民、陈慈.段可情年谱简缉[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第55页。
⑤卫茂平在《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晴和民国时期》第149页考辨出林微音翻译过施尼茨勒的小说《莱森波男爵的命运》,该译文刊登在1934年《现代》5卷2期上,但称译者为“学界才女”,系将男性海派作家、诗人林微音误以为是集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一身的才女林徽因。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因姓名混淆困扰之故才改名。经吴晓樵提示,卫茂平在《维也纳现代派民国时期刍议》[A](收录于范捷平主编《奥地利现代文学研究——第十二届德语文学研究会论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中已作更正。
⑥信件在叙述中起关键作用的小说,且信件和叙述具有有机的联系,信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技法难以替代的,参见:Day, R.A.Told in Letters:Epistolary Fiction Before Richards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158.
[1]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吴晓樵.对民国时期留德学人的强光聚焦——叶隽著《另一种西学》读后[A].中德文学姻缘[C].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张效民、陈慈.段可情年谱简辑[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4]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晴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段可情.通信[J].创造月刊,1926,1(4).
[6]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陆耀东.德国文学在中国(1915--1949)——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讲演[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
[8][德]奥托·哈尔特列本,段白莼译.彩色鸟[J].小说月报.1930,21(4).
[9]段可情.德国两大文豪百年纪念[J].现代文学.1930,1(6).
[10]卫茂平.(主编)德语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1][德]迪姆·克勒格尔,段可情译.一件不要人相信的故事[J].小说月报.1931,22(9).
[12][德]保罗·恩斯特,段白莼译.寂寞[J].小说月报.1931,22(3).
[13][德]海因里希·海涅,段可情译.新春[M].上海:世纪书局,1928.
[14]吴晓樵.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A].中德文学姻缘[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5]李赋宁.序[A].(古罗马)奥维德,南星译.女杰书简[M].北京:三联书店,1992.
[16]李小鹿.《克拉丽莎》的狂欢化特点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7]Beebee,T.O.Epistolary Fiction in Europe,1500-1850[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19]叶隽.在理论维度与历史语境之间——读《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09(10).
[20]韩蕊.现代书信体小说创作繁盛成因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2008,36(5).
[21]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J].创造季刊,1922,1(1).
[22]韩蕊.现代书信体小说出版书目钩沉[J].华夏文化论坛,2010.
I046
符:A
1003-7225(2015)04-0059-06
2015-06-25
何俊(1979-),男,湖北武汉人,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兴趣与重点:德语文学汉译史(晚清民国时期)、德语国家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