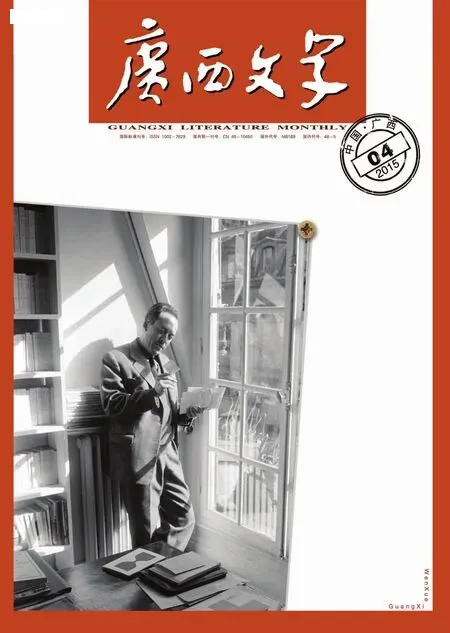《广西文学》2014年度盘点
韩颖琦/著
“繁荣文学创作,培育文学新人;构建八桂文学品位,反映时代现实精神”是《广西文学》杂志一贯的办刊宗旨。2014年度,杂志社在秉承这一宗旨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读”的理念,并呈现出两个新的亮点,一个是“广西80后小说专号”,另一个是“第五届广西诗歌双年展”。
《广西文学》在本年度第5期推出了“广西80后小说专号”。专号精选了八位广西80后优秀作者的作品,文体上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大类。三个中篇小说包括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侯珏的《立地成佛》与吴了了的《住在二楼的男人》。五个短篇小说分别是肖潇的《黄金船》、车海朋的《来自杨庄》、马中才的《关于很多很多小孩的想法》、韦孟驰的《美女来到我们村》和钟欣的《赔偿金》。整体来看,三个中篇抒写了现代都市年轻人“后青春”期的迷惘,五个短篇则主要将目光对准了乡村,现实性强,涉及留守老人、流浪汉、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矿难等社会问题。从文本内容来看,如果说当年韩寒等80后作者笔下青春少年们的孤独、寂寞、迷茫、脆弱、叛逆、冲动、渴望等诸种青春期独有的情绪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那么这三个中篇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初涉社会后的“后青春期”的主人公们在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巨大反差后的迷惘。与青春期的少年相比,后青春期主人公们的叛逆不再那么义无反顾,他们的疼痛也没有了往日的撕裂与尖锐。从人物气质及人物关系来看,三个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也十分相似。《我梦见了古小童》中的“我”出场时正颓丧地坐在电视机前,像一个得了病的老人,毫无青年人的生机。《住在二楼的男人》中的“我”则每天在狭小局促的出租屋里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无趣无聊。《立地成佛》中“我”的生活状态,用小说中的两个词汇来描述,就是“一潭死水”和“周而复始”。这三个中篇小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坏”女人的存在。与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相比,主人公们似乎都更喜欢“坏”女人,因为“坏”女人的共同特点是经历复杂、神秘莫测,总能给主人公们灰暗的生活带来未知的惊奇。其实所谓的“坏”女人,正代表了一种希望和渴求,一种摆脱无聊庸常生活的希望,一种体验激情与刺激的渴求。而这种“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生活,正是三个中篇的主人公们想要摆脱而又深陷其中的困境。在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三个中篇的主人公们也都表现出疑虑和恐惧,他们不缺少“性”,只是他们的“性”与“爱”无关。无论是对爱情的否定,还是对婚姻的怀疑,归根结底,都源于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而在自我怀疑与否定之后,主人公们自然会陷入深深的迷茫与忧伤之中,无法捉摸的未来让主人公们极度地缺乏安全感。伴随着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还有对大学教育的质疑。实际上,每当主人公们在现实中碰壁之后,都会习惯性地逃回到校园环境中。在小昌、侯珏和吴了了这三位广西80后作者的笔下,“后青春”期的迷惘、焦虑、彷徨、无措甚至愤怒,是一种弥散性的情感体验,映射出成长中的“80后”群体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和个体体验。三个中篇小说也都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短篇小说的写作对作者的要求同样很高,往往成为检验作者才情的文体。专号的五个短篇小说跳开了单一的都市与校园视角,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将城市叙事与乡村叙事加以链接,描摹出新时期的社会百态。这是80后文学除都市青春书写外的又一个走向。在视角的选取上,小说都回避了第一人称,不再关注自我的情绪与情感,弱化了人物的内心,加强了叙述的客观性。《黄金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父子之间的沉重的故事,构思精巧新奇,让人眼前一亮。孤独的老父亲为了唤回外出打工儿子的亲情,编织了一个关于黄金船的谎言,却最终让儿子送了命。随着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留守老人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聚焦老年人的孤独问题,读后令人嘘唏感叹。《赔偿金》写的是矿难遗属围绕赔偿金的使用和分配引发的悲剧。一笔矿难赔偿金,考验着本来就很淡薄的亲情。作者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失去了丈夫、儿子、父亲以及兄弟的不幸家庭中,苦难带给这个家庭的不是亲情的凝聚,而是对于赔偿金的算计与争夺,亲情淡漠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美女来到我们村》写了“寄命”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乡俗,其中的三仙婆颇像《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马中才《关于很多很多小孩的想法》则表达了家族兴旺、子孙满堂的传统理想。
可以说,80后文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在专号中都有所体现。“爱情”构成三个中篇小说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为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的主体,对待爱情的悲观主义,折射出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三位中篇小说作者都直面当下都市年轻人内心的迷惘和困惑,都擅长对于某种情绪的渲染和捕捉。关注社会问题的五个短篇小说视角则相对开阔。总体来看,这八位广西80后作者共同关注的是那些没有实现梦想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都遭遇了现实的困境。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他们直率坦诚的笔法,表达了对现实的理解。不足之处是有些表达和思考还停留在经验的浅表层面,难免给人一种单调重复之感,缺乏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今后如果能超越有限的生活和经验圈子,更深入地挖掘人性,将会锤炼出更有生命厚重感的文字。
配合“广西80后小说专号”,《广西文学》编辑部召开了作品专题研讨会。2014年6月1 8日,《广西文学》“80后小说专号作品研讨会”在南宁举行。研讨会阵容十分强大,来自自治区的相关领导、区内外知名作家评论家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专号展示了广西新一代作家的实力。容本镇先生在指出这批青年作家十分有潜力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给读者留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广西文学》主编覃瑞强认为,这八位80后广西作家无论是从生活经历、思考方式还是从写作姿态上来看,都与之前的广西作家有着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他们独特的文学景观,值得广西文学界去研究和发现。《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读完专号,整体感受到广西80后作家的创作实力及广西文学生生不息的文学力量,从作品方面则注意到大部分作品都比较关注日常生活,且不同程度达到了各自的审美表达。《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从人称的角度剖析了专号多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小说的原因。《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希望广西80后作家继续提高眼界和境界,并逐渐获得厚重感与深刻感。《十月》副主编赵兰振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专号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在主题的明确、细节的真实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严风华希望散文和诗歌也能像小说一样繁荣。唐春烨从专号中感受到青年作家青春的躁动。黄佩华在发言中高兴地指出广西新的一代作家已经正式诞生了。
从专号的推出和研讨会的召开,我们切实地感受到《广西文学》编辑部在培育广西文学新生力量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获得了丰厚的回馈。2014年度,《广西文学》发表的小说被多家权威文学期刊转载,转载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就包括“广西80后小说专号”中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被《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其他转载情况我们不妨来一一盘点:第1期晓苏的短篇小说《皮影戏》,被《小说月报》第4期转载;第3期周龙的中篇小说《谁是最可怜的人》,被《小说选刊》第4期转载;第4期蔡呈书的中篇小说《学校那堆糗事儿》,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6期转载;第6期陈然的短篇小说《把煤气打开》,被《小说选刊》第7期转载;第7期康健的短篇小说《温馨叨灯》,被《小说选刊》第1 0期转载;第8期王勇英的中篇小说《太阳花开》被《中篇小说选刊》增刊第3期转载。晓苏的《皮影戏》将目光聚焦于“租女友回家过年”这一颇有争议的社会现象,作家卞庆奎有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租个女友带回家》,后被改编成热播电视剧《租个女友回家过年》,可见这一现象已引起普遍的社会关注。小说题材不算新颖,但晓苏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皮影戏”这一媒介将传统与现代链接在一起,“皮影戏”这一饱含着深厚情感的传统艺术形式,与“租女友”这一没有感情色彩的交易行为之间的对比与冲撞,竟然迸发出奇异的情感火花,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与理想化,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小说向善的美好愿望。周龙是广西本土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谁是最可怜的人》通过主人公充满心酸与无奈的升迁历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官场某些层面的现实与现状,充满理性与批判色彩。蔡呈书也是广西本土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学校那堆糗事儿》同样聚焦现实,通过对一所中学中发生的一系列糗事儿,引发我们深刻反思中学教育的种种怪相。陈然的短篇小说《把煤气打开》写了一个患有强迫症的都市青年人的精神困境。强迫症这一精神病症,目前已被列为严重影响都市人生活的四大精神疾患之一,其形成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城市过密、居住空间拥挤、环境污染以及工作压力等。如何帮助都市年轻人走出这一精神困境,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从主人公彻底解脱的所谓解决之道,我们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康健的短篇小说《温馨叨灯》用荒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现实的故事,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通过主人公黑蛋的自述,我们了解到黑蛋和他母亲相似的命运,母子俩都曾被有钱人包养。黑蛋要用拿身体挣来的二十万给家乡修桥,却因为无法证明钱的来路而屡遭质疑和阻挠,甚至被抓进派出所,最后他把钱捐给了寺院。在放走了一个又一个呼唤亲人的叨灯之后,黑蛋梦见自己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故事充满反讽和隐喻。王勇英是土生土长的广西女作家,她的《太阳花开》带有儿童文学与女性写作的双重气息,“太阳花”意象在小说中象征着对纯洁、温暖与美好情感的渴望,王勇英对于隐秘的情感世界的探索,通过细腻而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读来令人感动、感伤。
从2005年起,《广西文学》开始了两年一度的广西诗歌创作双年展。“诗歌双年展”虽然不是2014年的新创,但其可贵之处在于编辑部十年一贯的坚守与执着。更为难得的是,本年度的第五届“诗歌双年展”对于诗作来源,定位在诗集选展,从地域性来划分,分别展出了来自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崇左、来宾、贺州、玉林、百色、河池、钦州、防城港、贵港等广西区内各市,及“扬子鳄”“自行车”“南楼丹霞”“漆诗歌沙龙”“凹地”“相思湖诗群”“麻雀”“天南湖”“南方诗人”等九个诗歌群落的诗歌。这种不拘一格选好诗的做法,正如冯艳冰女士在《断代回眸——诗歌双年展编辑手记 :广西诗坛十年》(《广西文学》2014年第1 2期)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是充分肯定和敬重诗人个性价值、体现互联网自联网时代艺术精品规律的创新之举”。回顾这十年的广西诗坛,冯艳冰指出,“广西新诗创作大面积地形成了一次更耐人寻味的诗群性的集体向内转。诗人们的写作目光和内心情境,离现实社会性的话题很远,离新闻更远,在李白和杜甫之间,他们似乎更多地选择李白的方式,在自己营造的精神王国里叙事或抒情”。在具体的诗人个体层面,则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诗人,如活跃于诗坛的实力派诗人“频、盘、非、春”,他们分别是“思想性、时代感和使命感较强的歌者”刘频、“李商隐式的抒情高手”盘妙彬、“冷静的寓言式叙事和寓言式格物风格一以贯之”的非亚和“最善于在平实的生活事件中有所发现的诗人”刘春。此外,从诗人代际来看,既有石才夫、田湘、黄鹏等充满社会历练及思考深度的成熟诗人,也有诗歌群落中那些虽稚嫩却清新生动的青春诗人。从性别归属来看,广西女诗人的诗作尤其引人注目,如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依靠爱情的感受,而是展现出更宽阔和悠远诗情的女诗人陆辉艳、黄芳;还有新鲜灵动的雪萍、铂斯、羽微微、唐女等女诗人的诗作,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广西诗歌虽然质量不俗,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和轰动还比较有限,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方面是诗歌文体本身在当下的尴尬处境,诗歌本身不是一种大众化的文体,其本身的小众化决定了读者群的小众性;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广西诗歌地区发展不均衡,尚缺乏引领诗人们突出重围的领军人物。但无论如何,通过2014年度的“广西诗歌双年展”这个让广西诗人整体登陆的平台,相信广西诗歌的明天会更好。
2014年已经成为过去,作为《广西文学》的忠实读者,我深切感受到这一年来杂志编辑部所做的努力。《广西文学》是广西最高水平的文学刊物,是本土作家走出去的必经之路,经由它将一批批本土作家推向了全国;同时杂志也吸引了区外一大批作家、评论家的关注。此番的年度盘点难免挂一漏万,愿《广西文学》走向全国,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