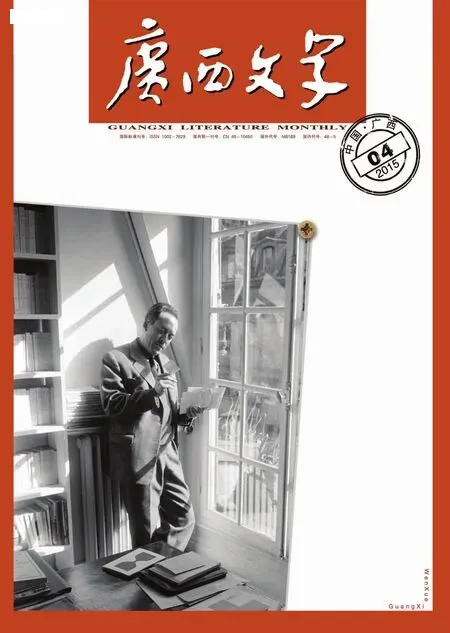母亲头上的乱发
何正文 / 著

本文选自《南丹文学》2014年第5期
在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就羽化成仙,别子而归了。四十多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宛如一尊露天的石雕,在年复一年的风化中,日渐斑驳,面目模糊,只剩下几道尚可辨认的轮廓。我的脑子好像也遭到风化似的,该记的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母亲头上那一蓬乱发。据寨子上的老人说,他们这辈子看见我母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成形有样的时候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和我父亲结婚时的那天,还有两次是我亲眼看到的。一次是母亲去金城江二医院住院,另一次就是母亲披着整齐的花白头发平躺在屋子中堂的棺木里。寨子上的人看见母亲三次梳理得十分整齐的头发都不是出自母亲的手,当年出门结婚的那一天是舅家姨母们梳理的(当地有个习俗,出嫁的人不能自己梳理自己的头发),去金城江住院那天是族嫂帮忙梳理的。我母亲逝世后,我经常去舅家,有次舅家的老人们和我谈起我母亲时,我随口问起我母亲的头发,他们都说我母亲在家当姑娘时是村子上最爱打扮的一个,衣着干净整洁,平时赶街走亲,吃红白喜酒,都穿上自己纳得非常漂亮的绣花鞋。一天要梳两次头,而且隔三差五地用茶麸煮水来洗头,她梳洗的头发连蚊子都爬不稳。至于母亲嫁给我父亲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舅家的前辈们没有一个说得清道得明。我长大懂事后,才弄懂其中的原因。母亲当姑娘时爱打扮,爱梳洗,主要缘于较好的生长环境和生活条件。母亲出生在车河镇车河村堂皇屯,寨子的附近有三条清澈的溪流,门前还有一潭四季不枯的呇水。坡上土地肥沃,种粮成粮,种菜成菜,种树成树,猪肥牛壮,鸡鸭成群。我小时候,一年四季很少能吃上一次鸡鸭肉,偶尔能吃上一只鸡棒腿、鸭棒腿都是母亲从舅家得来的。我家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与舅家有天壤之别,我家住在娘娘山脚下的洞颇屯,土地贫瘠,全是望天田,播种插秧要等天下雨,稻谷产量低,以食玉米、红薯等杂粮为主。无粮不养,这是农耕者千百年来的生存定律。所以,我们家那一带养牲难成,六畜欠旺。母亲嫁到我们家后悔不已,据寨上的老人说,我母亲为了挑水曾多次掉过眼泪,要挑一担水得往返七八里,枯水季节,就吃村头寨尾牛滚塘的水,水如茶色,牛屎和虫豸浮于水面,臭味难闻,母亲曾为此呕吐过无数次。平时,寨上的婶娘们挑水都是邀伴结队去的,鸡叫五更就得出门,住惯水边的母亲哪能适应这种生活,每次出门都是睡眼惺忪,根本来不及梳洗,而已适应这种生活的婶娘们经常嘲笑我母亲,说我母亲的头发比不上娘娘山这个石头人的头发,石头不会梳理,一年四季都是那样的整齐光滑。
我母亲无暇打理自己的头发,却把所有的时间用于打理自己的家。我家共有九口人,六个兄妹,男女各半,祖父健在却双目失明,既是一个大家庭又是一个困难户。那个年代的困难户和现在的困难户其性质、概念大不一样,现在的困难户有的是不会打算,有的是怕苦怕累,有的是因天灾人祸。而那时的困难户除了自然条件外,主要是因为人口多劳动力少。我家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实际上只有一个半,因为父亲常年患有肺结核病,三天两头不能出工。每年年终分配,我家不但得不到分红钱和分红粮,而且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的钱粮账。当时,如要过得好,必须靠劳动力多,靠工分多,社员的脑子没有用,全队一百三十多人只靠一个脑子,那就是生产队长。如果我家处在当今这个年代,生活也不会那么窘迫。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生活过得最好的是1 9 6 3年,那年国家实行政策调整,允许农民自由开荒种粮,允许农民利用富余的时间搞生意和经营自留地。当年,父母亲起早贪黑开生土、砍火炼、种旱谷、种小米,一年生产出两年多的粮食,年底还出栏三头肉猪,腊肉吃到第二年。每逢街日,母亲还做米粉、米糕、蒸糯米饭到大路边搭棚出卖。那年,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添上一两套新衣,买了一两对新鞋。如果是那个形势一直延续下去,我母亲也不会死得那么早。我母亲四十二岁就撒手归西了,我曾在她的墓碑上铭文:母亲的死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和贫困。说到吃苦耐劳,我母亲可评得上那个年代全村妇女的冠军,她从生到死,除了每年的大年初一外,没有歇息过一天。她每天除了完成集体工,还要砍柴、割草、舂谷磨米和缝补浆洗全家的衣裤,每晚煮完猪潲,都到深夜的一两点钟,天还未亮又要起床出集体工。一年四季,都是丑时睡寅时起,从来没有睡上四五个钟头的安稳觉。这个年代的妇女如果回到那个年代的生存状态,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活下去。我是家中的大儿子,数我读书最多,也是拖累母亲最多的一个。我家距离学校有七里,小学时只能早去晚归,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每天母亲都是早起五更,为我做饭煮菜,督促我吃饱后还要用口盅盛好饭菜装到我的书包里。我在学校的成绩优劣,母亲从不过问,因为她只字不识,也不知道怎样过问,她关爱我的唯一方式就是管好我的吃穿和催促我按时上学。当时,因为家里穷,无钱买鞋子,自己做的布鞋又不耐穿,母亲为了不让我打赤脚上学,经常到铁路火车站的工区附近捡工人子女废弃的解放鞋,把破烂的鞋面剪掉后,用破烂的衣裤布叠层为鞋面,重新上线给我穿。热天,她就用水带扎在解放鞋底上作为凉鞋,使我穿得舒服些。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母亲心中的牵挂。1971年8月,我接到瑶寨中学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全队有三个初中毕业生,只有我和一个军属家的男生获得录取),母亲为此高兴得一夜合不拢眼,半夜就起床为我打了一箱豆腐。我入学的那天,母亲递给我一包用手帕扎得严严的钱说里面包有十二块八角。母亲没有预料到我能读高中,她攒下的这包钱是每天卖菜积累的,原打算用它来买床棉被,因为母亲床上的棉被早已破成渔网。我到学校总务处将手帕打开,里面除了五张块票外,全是角角分分的,收费的总务主任叫我拿远点,他闻不得手帕和纸票散发出的汗水味。
我到瑶寨中学读高中还不满一个学期,母亲就突然病倒了,在本乡看了半年的中西医,毫不见效。无奈之下,父亲要我利用星期天和一个本族的小兄弟把母亲送去金城江二医院。动身前,呻吟中的母亲忽然想起自己头上的乱发,她吩咐我把族嫂请来,为她梳理一下。我说:你平时都不梳理,现在病成这个样子,还梳理它干什么。母亲觉得我不懂事,她白了我一眼就冲着我说:我平时不是不梳理,是因为没有时间,三刮两刮就了事,梳也等于没梳的一样。今天不同,你们说金城江是城市,进城市,人多多的,总不能披头散发,丢人现眼。母亲历来是一个发乱心细的人,到了金城江我又再次感觉到。来金城江前母亲已有几个月不能下地行走了,从家一路来,不是背就是抱的,到金城江火车站下车时,母亲突然内急闹着进厕所,父亲立即动手抱。母亲摇头制止并指着我和一个十三岁的小兄弟,要我们俩人把她抱进厕所去。父亲不理解母亲的意思,说我们俩年纪轻,力气小,俩人抱一个人太费劲。母亲骂父亲是猪脑壳,还责问父亲说:你打算抱我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父亲突然失语,接着母亲又开导说:正文和他的小兄弟都是男孩,属于不懂事的娃崽,抱我进女厕所,那些成年的女人不会见怪。母亲不但心思缜密而且还非常慈爱,她在住院期间,每个星期假日我都爬铁路货车去看她(因为无钱买客车票)。她在病房里,吃得比任何病友都要差,平时都是白饭、素菜,早餐吃的是白稀饭、粗馒头,从住院到出院只吃过两次肉。看到同房病友隔餐隔天吃肉,早餐有肉包子、牛奶和豆浆,母亲的清口水总在喉咙里打转转。母亲姓韦,有一个同姓的环江病友见她穷得可怜,就送给她三个肉包子,她只吃了一个,留下两个等我来。当我去看望她时,她高兴地把两个肉包子递给我,我立即将包子掰开,随手又把已经露馅的包子放到桌子上,第二个也是如此。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吃,我说中间的馅已经发霉变色了,母亲随手拿去闻一闻,顿时,只见她嘴唇动了又动,一颗颗泪珠不停地从眼眶中流出。
母亲在金城江二医院只住了三个多月,进院时,父亲只付了六块多钱,其余的费用都是姑父掏腰包。姑父曾经是国民党县政府职员,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到南宁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就业,分配到金城江二医院搞基建,工资少得可怜。好心的姑父每月省出一半的工资为母亲支付住院的费用,姑父家也穷,母亲住了三个多月的院,姑父已倾其所有,再也无能为力了。如果我母亲再留院几个月,病情可能得到彻底的好转。我母亲得的是肝炎和肺炎,进院前,头部和双脚已经浮肿,住院三个月后,浮肿基本消除并能下床行走。院方要求继续留院治疗,可是,父亲身无分文,亲朋好友该帮的已帮了,该借的已借了,无奈之下,只好要求出院。出院不几天,母亲的病又犯了,继续出现浮肿症状。父亲见状,又四处求医,请来的大多是土医、庸医,有的说吃煤油可以见效,有的说用银圆磨水喝可以见效,有的说吃金鱼可以见效。为了弄到金鱼,我还跑到瑶寨火车站找晏站长,好心的晏站长同意我把站前金鱼池里的十多吨水放光。人说久病乱投医,我母亲为了病情的好转曾听信庸医的胡言,喝下几个半碗的煤油。边远山区的穷人一般不信科学也信不起科学的,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了母亲病情的好转,除了盲目求医,还信神信鬼,请巫公来家烧犁头喷桐油扫家。庸医、鬼师都请了,还不见效,于是又请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我家房屋的置向与我母亲八字不合,所以克我母亲。父亲又遭到风水先生的愚弄,于是,在距离房子三十多米远的地方搭起一个茅棚,把母亲搬到里面去住,当时正值夏天,母亲的双脚已经溃烂、化脓,加之家中无蚊帐,一天到晚,蚂蚁和苍蝇爬到母亲的脚上。母亲住茅棚比犯人蹲监狱不知要难受多少倍,整天蚊虫肆虐,日晒雨淋,白天还好些,不时有寨上的人到茅棚看望她并与她说上几句话,晚上,没有一个人在她身边,口渴时连口热水也喝不上,一个人整夜躺在潮湿的床上不停地呻吟到天亮。每个星期天,我都从学校回来为母亲清洗身上的污垢和双脚的脓疮。每次见面,她总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崽啊,我不知道前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人们都在天天求生,我却在天天求死,连求死老天也不开眼,真是造孽啊!有一次,母亲要我找三炷香,我把香拿来后,便问母亲要香做什么?母亲说:崽呀!如果你可怜我,孝顺我的话,你就点燃三炷香,跪在地上磕三个头,祈求老天保佑我,放我一条死路吧!我说:母亲,我不能这样!母亲说:你若是还有点孝心,你就应该听我的话。结果,我真的按母亲的话做了。几十年来,我每每回想这件事,喉咙总是一阵阵发哽,心头总是阵阵的痛。世界上所有的人烧香都为母亲求健康、求长寿,而我烧香却求母亲快点死,走投无路的母亲让我从小就背上了一个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恶名。俗话说,好事难求,坏事易验,我为母亲祈死不到一个星期,她真的死了。母亲逝世在1 9 7 3年夏季的一个星期五早上,头天下午,已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不停地呼叫我的乳名。守候在她身边的父亲和一些男女亲戚都反复问她,是否拍个电报或派人到学校叫我回来?其实从学校到家也只是两小时的路程。每问一次母亲就摇一次头,口中还吐出不清不楚的“读书”两个字来,旁边的人终于明白她的意思。痛苦中的母亲还记得当天是星期四,怕我回来会影响星期五那天的学习,我得到消息已是母亲落气后。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愧疚,万万没想到,母亲在弥留之际还是那样的珍惜我的学习。按照我们地方的习俗,老人落气时必须由亲生儿子抱着,如果亲生儿子不在身边,同辈的族人可以代替。我母亲逝世时,二弟才五岁,小弟才两岁(生出时母亲就生病,无法哺育,一年前就过继给它村异姓了),只好由同辈的两个族兄抱着落气,作为亲生儿子的我没能尽到最后一刻的孝道而遗恨至今。
母亲出殡前,舅爷和小外公也赶来了,舅爷看见我们几个孤苦伶仃的兄妹心里十分难过,他拉着我和大妹的手说:你母亲的死是命中注定的,我和你母亲在小的时候,你外公曾请算命先生来为我们打流年,批八字,八字单上说你母亲过不了四十五岁,我过不了五十六岁。有次我到外公家时,舅爷从箱子里找出发黄的八字单,上面写的果然如舅爷所说。我母亲的命终于让八字先生蒙对了,她逝世时刚满四十三岁。而我舅爷五十六岁那年不但过了而且连感冒都没遭过一次,他今年已接近七十六岁,江湖骗子企图减少他二十年阳寿,根本做不到。如今七十六岁的舅爷还下地干活,挑抬百把斤轻松自如,寨上的人称他是“公老虎”。舅爷老来也曾生过两次比较重的病,每次生病时他都到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健康如初。而当年我母亲没有这种福气,眼看病情日渐好转却被迫出院,没有钱等于没有命。我从小就恨透了穷,恨透了钱,是铜臭夺去了我母亲年轻的生命。如果当年我家宽裕些,有足够的钱医治她,那个胡批乱蒙的八字先生只能见鬼去。
人们常说,好人命不长。这句话偏偏应验在我母亲的身上,我母亲确实是个好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母亲死了四十多年,我每逢年过节回家,还都经常听到寨上的人念叨她。其中有一个当年成分不好的地主子弟,他对我母亲的感激可以说是一生一世的。他曾多次对我说:有两件事如果不是你母亲的帮助,我不知要挨批斗到什么地步。一次是他在坡上烧草皮灰,我母亲也在离他十多丈远处干着同样的活,由于他年纪小,不懂得隔火路,便失火烧山,烧掉了集体的几棵树木,我母亲见状,立即跑过来同他一起扑火,帮他把火扑灭后,我母亲马上回到原位,在自己烧草皮灰的上方故意放了一把火,使火场连成一片,有意模糊失火界限。我母亲放火后又回头叮嘱地主子弟说:生产队的人来问,是谁烧的山,你就说是我烧的。地主子弟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母亲说:我担心你挨批斗,我的成分好不关事,我家成分是贫农,我烧山属于不小心大意失火,你是地主子弟,失火烧山就属于有意破坏。当生产队长赶来查问时,我母亲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失火烧的,生产队长也看不出其中的破绽。还有一次,也是这个地主子弟在坡上放牛,因为打瞌睡,牛跑到集体的田里去啃秧苗。我母亲也正好在附近放牛,她发现后,迅速把地主子弟看管的牛赶出田来,又将自己看管的牛赶进田去,故意搞乱脚印,让生产队的人无法辨认,又帮助这个地主子弟躲过了一劫。我母亲敢于这样做,是因为她的成分好。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文革”时期,那个年代,从上到下都看出身,唯成分论。出身不好,成分差的,如地主、富农之类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那时政治上的弱势比现在经济上的弱势更悲惨、更可怕,稍不顺眼或一不小心,就被人栽赃陷害,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我母亲是个只字不识的人,什么时候,她心中总有杆秤。“文革”动乱,人人都在乱,思想乱,行为乱,有文化的人乱,无文化的人也乱,唯我母亲她发乱心不乱。当时,很多人仇视和打击地主、富农时,我母亲不但不仇视、不打击他们,反而还帮助地主子弟渡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有一天,受过我母亲帮助的那个地主子弟斗胆和生产队长吵起来,起因是生产队长吩咐他通知我母亲晚上去开会,生产队长不说你去通知某某妈(我们村的风俗习惯用儿子名字来称呼母亲)去开会,而是叫他去通知“韦老乱”来开会,地主子弟觉得这是对他恩人的极大侮辱,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当时我也在附近,只见那个地主子弟冲着生产队长骂道:你说她乱,其实你比她更乱,她乱的只是头发,你们乱的全是五脏六腑,她因为子女多,生活困难,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头发,但她的心全用在打理自己的心肠上,她的心比你们哪个的都好。这几句话我一直珍藏在心,四十六年过去了,至今难以忘怀。
我母亲一生总是遭人议论,生前是这样,死后也还是这样。生前人们议论的是她那不爱打理的头发,现在议论的是她那坟上的茅草。我母亲坟头上的茅草特别茂盛,泥土全部被茅草覆盖,金黄金黄的,像染过的头发一样。同在一个坡,其他坟头生长的全是芭芒、刺藤。风水先生说:坟头长茅草是个吉兆。于是,附近的一些坟主做清明时,到处找茅草在坟头上栽,但不管怎么栽,都是稀稀拉拉的,总达不到我母亲坟上的效果。于是寨上的人说:何正文的母亲在生不打扮,死后天帮打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