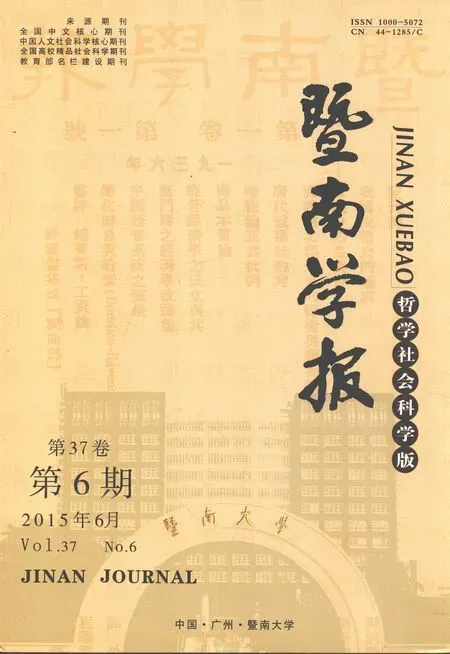“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悖谬
——论《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身体书写
潘敏芳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悖谬——论《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身体书写
潘敏芳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汤亭亭的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将族裔身体的表征编织进了小说的后现代叙事中。在惠特曼·阿新打算创作一部戏剧到戏剧最后上演的线性发展过程中,“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情感模式共时存在。“种族自憎”表达了对族群社群的摒弃,而“种族自爱”表达了作者希望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平等的多族裔社群的理想。但是“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之间显而易见的对立构成了悖谬。而通过思考其悖谬之处可见,汤亭亭在强调肤色差异性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多族裔共存的理想是一种“新种族主义”,它无助于华裔顺利归化进入美国社会。
汤亭亭;《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种族自爱;族裔身体
汤亭亭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一块丰碑,她的小说成为亚裔美国文学评论界关注最多的文本之一。在《女勇士》和《中国佬》大获成功后,汤亭亭于1989年发表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以下简称《孙行者》),“这部书获美国西部笔会的最佳小说奖”。小说充满了各种互文性的指涉,是一部后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葛莱思指出了其后现代性的诸多特征,如“文字游戏、自由形式的情节、自我指涉的叙事结构策略、详尽的互文指涉、妄想和怀疑的角度、历史和文化制品的商品化、戏仿和拼凑。”通过将这些后现代的创作方式同族裔视角相联系,作者“颠覆了族裔刻板印象,颠覆了大多数人看世界的单一方式”。
《孙行者》中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身体的描写,而身体的种族特征正是阻碍华裔美国人真正融入美国的障碍之一,正如小说中的惠特曼悲愤地声称他经常被人问的几个问题:“你是哪里人?”、“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你觉得我们的国家如何呢?”、“你讲英语吗?”但是评论界只是将身体的描写作为论述自己观点的佐证。
汤亭亭对华裔身体的认知和诗学表现在她的前面两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女勇士》中“我”和另一个华裔女孩遭遇的经历成为众多族裔批评理论的练兵场,如“种族的影子”、“种族忧郁”、“种族精神分裂”、“歇斯底里症”、“疑病症”等等;《中国佬》的开篇就是中国佬的身体被阉割的书写。在她的第三部作品,其实也是第一部虚构小说《孙行者》里,她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身体成为社会、文化、政治言说具身化的空间和政治争斗的场域。本文试图聚焦小说中的身体书写,指出汤亭亭在书写身体时呈现“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且共时存在,并思考其悖谬之处,以及作者在“憎”与“爱”中试图建构多元文化社区的努力以及其对华裔美国主体性建构的当下意义。
一、“种族自憎”:华裔美国人的生存之道
小说发生在1963年已大学毕业的华裔青年惠特曼·阿新身上,作为一名艺术家,他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并颠覆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但是生活在李磊伟所谓的“弃绝期”(Asian abjection),阿新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社会的和心理的隔绝与疏离,所以他甚至“每天都想着要自杀”,这种“胡思乱想”被台湾学者傅友祥(Bennett Yu-Hsiang Fu)称之为“居间的文化精神分裂症”(in between cultural schizophrenia),是处于“居间状态”的亚裔美国人在重组身份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首章里惠特曼·阿新在城市里闲逛时与新移民的正面相遇更加剧了这种精神危机:
迎面走过来一个华人,他来自中国,双手背在背后,弓形腿,宽松的裤子。他是出来溜达溜达的。……如此土里土气。如果说他们的裤子不那么短,运动袜不那么雪白引人,人们也不会厌恶他们的。新来者的风尚——短裤腿或卷裤脚。不可救药。土里土气。土里土气。
这里的华人一家人“是移民,新来美国。”新移民的形象在黄哲伦的戏剧得到最典型的再现:“FOB。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些FOB呢?笨拙、丑陋、贪婪的FOB。吵吵嚷嚷的、愚蠢的、架着副眼镜的FOB。大脚丫。欲火中烧的。就像《人鼠之间》中的莱尼。很好。有文学典故哩。特别短的长裤。更确切地说是吊杆裤。那种你不希望你的姐妹嫁的人。”惠特曼是“第五代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他个子很高,长得很瘦,络腮胡,加州大学毕业,是典型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说到底,这是ABC与FOB的正面相遇。
蒲若茜认为,汤亭亭“在描述中国人的体态、举止、打扮甚至脸色、眼神方面也都竭尽细腻白描之能事,‘他者化’中国人,以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她认为“汤亭亭对于中国人的‘他者化’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渊源,与美国主流的殖民话语几乎构成了一种‘同谋’关系,因为‘刻板印象’是一种先在的固定意识,并不受眼前现实的干扰。”李磊伟也认为这里“ABC”和“FOB”的相遇值得关注。他认为“将阿新与FOB外在的冷漠和内在的关系联系起来,不管后者看起来有多勉强,汤亭亭再现了一个对族群内交际障碍的更细微的描写。”
事实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阿新在这里遭遇的是黄秀玲所谓的“与种族影子的邂逅”,“种族影子”是独立于第一自我之外的“类我”,或第二自我,它与第一自我有亲缘关系,是阿新拒绝成为却又无法摆脱的族裔形象。这遭遇是一个自认为是美国人的华裔遇到了自己身份的他者的外在化表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外在的身体相同。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语言或肢体上的交流,但两者的相遇已经是敌意重重。在阿新看来,这些FOB们显得“土里土气”。因此,ABC与FOB的相遇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种族投射,也就是土生华裔看待新移民的态度。阿新长着华人的面孔,找工作受到歧视,在大学毕业以后和失业之前的这一年里,他所从事过的工作是“售货员、管理班学员、邮局拣信者,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奶油炼制工人”,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他的地位低人一等。在大街上,他遇见了长相与他相似的华人,在他眼里,他们代表着永远不可逾越的身体标记,代表着他无法成为一个同化的美国人的事实,他本能地采取了白人的评价标准,对新移民进行了“他者化”。这既是对新移民形象的嘲讽,也表现了阿新对自己族裔身份的憎恨。
种族自憎是华裔美国人面对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赵健秀称之为“自我蔑视”。他认为:“自我蔑视在于少数族群不仅接受了白人关于客观世界、审美观、行为准则和成就的标准,而且认为这些标准在道义上讲是绝对正确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认为自己不是白人,因而绝对达不到白人的标准”。对族群厌恶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他们拒绝与自己的族群认同,也无法建构一个属于本族群的核心正面形象,以至于他们在美国被主流社会建构出对自己身份认同非常有害的刻板印象。金惠经将其归纳为“好”的亚洲人和“坏”的亚洲人,坏人是“邪恶的坏蛋、粗野的魔军”,以傅满洲为典型;好人则是“不可同化的异族”,陈查理是另一个典型。在惠特曼出生长大的唐人街,美国白人累积了关于华裔的所有不切实际不可思议的想象。虽然唐人街的华裔经历了从最初的“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历史性转变,但最初形成的刻板印象难以改变。惠特曼接受了正统的美国教育,大学毕业于加州大学,他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叛和反战精神,经常以“嬉皮士”打扮示人,而他虽然求职受挫,但仍富有超越了物质限制的远大的艺术追求,因而在外表和精神上都有别于唐人街的主流群体,无法认同华裔群体,并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小说中普遍存在于华裔之间的“种族自憎”既不利于个体在美国的生存,更不利于群体的生存。惠特曼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通过戏剧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梨园乌托邦思想。南希·李在工作时饱受歧视,尽管资质出众,却只能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而种族群体内的自我厌恶只会加重这种情绪的发酵,不利于华裔群体为自己争取普遍的利益。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赵健秀(Frank Chin)与编辑弗兰克·程(Frank Ching)之间的辩论中。赵健秀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就我而言,无论是在文化上、智力上,还是情感上,十多岁来美定居的美国化的华人与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没有共同点。因为肤色相同,所有的华人因为肤色的原因都很相像,这是种族主义的说辞。”《桥》(Bridge)杂志的编辑弗兰克·程回信说“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只是加重了你担心白人将你与他们等同的恐惧。你希望作为美国人被接受、被承认—尽管只是华裔美国人—你尽量将自己远离这些新移民。看到一个人如此缺乏安全感,他靠背叛自己同祖的人们来证明自己这真是悲哀。”
而评论界公认惠特曼·阿新的原型就是作家赵健秀,赵健秀在辩论中将土生华裔与移民的华裔区别开来,从而也将自己与华裔社区疏离开来。文中的惠特曼在疏离自己社群的过程中产生了内心的惶惑:因为肤色的原因,他既无法归属美国,也无法认同华人,由此产生了弗兰克所称的“不安全感”。赵健秀在《甘加丁之路》中斥责关龙曼的行为为种族背叛,但是他自己鄙视新移民的行为则是对华裔美国群体的背叛。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弃绝了自己的族裔之根,这确实“悲哀”。但是,我们在认识到赵健秀思想的局限性时也必须认识到,是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制度让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产生了“种族自憎”的情感模式,正如黄秀玲所言:“亚裔美国人,像美国历史上其他移民和移民后代一样,参与并受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适应了与居住在亚洲的亚洲人不同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一事实往往被持反历史观的人们所忽略,这些人认为亚裔美国人身上永远刻有某种无法转化的异族因素的标志。”亚裔的“异族标志”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亚裔人群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其肤色外貌的显性表征,就将其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将其看作“异国风情”,“外来人”,这是对亚裔的彻底否定,是亚裔群体所不能接受,并坚决与之抗争的现实。
二、“种族自爱”:华裔美国人的自救之道
惠特曼·阿新的名字为众多评论者所考证,“惠特曼”毫无疑问,来自于美国最著名的本土诗人瓦尔特·惠特曼,不同的是名字的拼写。瓦尔特·惠特曼是毫无争议的美国著名诗人,汤亭亭的惠特曼是白人诗人惠特曼对应的他者形象。“阿新”则有多个来源,美国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布莱特·哈特在诗作《华人异教徒》中讲述的一个名叫阿新的华人形象,傅友祥则认为这名字直接取材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在林涧看来,名字来自于一百年前为华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呐喊的华人诺曼·阿新(Norman Asing)。总体来说,阿新的名字代表两重意思:它将遭受种族歧视的华人男性前景化并赋予其话语权。林涧所指称的阿新于1852年给加州州长毕格乐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他对华人的歧视性言论。他在信中写道:
“至于我们族群的肤色和表情,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人比你们略黑一点。然而,阁下会发现,我们和非洲种族、红种人的亲缘关系就如同你们和他们的一样。考虑到肤色的贵族性,我们的肤色可与大多数欧洲种族相提并论。我们也不认为阁下作为民主人士,会让我们相信您的人权宣言的制定者曾经提议创建皮肤的贵族性。”
诺曼·阿新在这里质疑了美国社会以肤色来判别人的肤浅准则,特别是以肤色来指认华人,并以此认为华人低人一等。但是他的质疑并没有被接受,因为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美国主流社会仍然以肤色定义自己,将华裔排除在主流之外。《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则接过了前任阿新手中的火炬,他要为华裔再立言,为此,他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我们可以称其为“种族自爱”。
“种族自爱”的核心思想是化种族特征的劣势为优势,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裔运动密不可分。黑人在民权运动中为反抗白人的强势话语而创造了“Black Is Power”,“Black Is Beauty”等震耳发聩的呐喊。秉承黑人民权运动的话语,汤亭亭所倡导的则是“黄就是美”、“斜眼睛就是美”,为此,她在小说中的不同语境下都表达了这种观点。
小说的第一章中,南希·李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中颇受挫折,去拍戏时,她被认为“你的发音不太对。你的声音与你的外貌不协调。你的外貌与你的言语不一致。”“不协调”、“不一致”的原因是她长着一副华人面孔,却讲着纯正的英语,不符合白人的期待视野。在做群众演员的时候,她的鼻子和眼睛会被额外化妆。华裔所遭受的这些不公正待遇都由身体而起。惠特曼因而对南希承诺说:“我正在为你写一台戏。在我为你写的戏里,观众会爱上你,因为你的黄皮肤、圆鼻子、扁瘪的身材、丹凤眼,还有你的口音。”阿新在此开始打算张扬华裔身体的存在,其种族特征被纳入新的审美规范中进行评价。
对于华裔刻板印象的描述中,最令惠特曼不满的是对于眼睛的描述。在“独角戏”中,惠特曼就尖锐地指出:“在我们的身体上,他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你知道是哪里吗?是我们的小眼睛。”惠特曼长着一双华人的“小眼睛”,“双眼皮”,在兰斯的聚会上,白人女孩直接问他“你能看见吗?你怎么会看见呢?”所以,惠特曼在独白中长篇累牍地阐述华人眼睛的美。他甚至呼吁:“为了我,卸妆吧,好不好?去那个女厕所,这儿有阿波灵洗面奶,洗了脸再出来。勇敢些。敢于不涂脂抹粉地生活。找回你的面孔。你的眼睛极大,不仅对于中国人而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显得大极了。”
而针对聚会中偶遇的日裔女孩小笠原洋子打算去做双眼皮手术的事情,惠特曼呼吁:“作为一个负责的导演,作为一个男人,我试图阻止我的女演员们不要去把自己切割得支离破碎。”双眼皮手术是亚裔女性归化美国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在诸如双眼皮手术、隆胸、隆鼻等手术中,亚裔女性所采用的是白人的审美规范,将白人女性看作美的化身,通过改造自己的身体来降低因身体特征而产生的种族歧视。这些美容手术,究其本质,是一种内部殖民的倾向。正如班纳瑞对眼部手术所做的评价中说“东方人摆脱种族主义的唯一机会是做眼部手术。通过这个手术,文化意义从身体的屏幕上移除,历史曾在其上书写它。双眼皮用来指代大熔炉的乌托邦。当种族自我只能栖居与白人对自己身体的投射中时,投射再一次既无所不包又一无是处。种族他者意识到白人的凝视最开始就将文化意义投射到解剖学的特殊部分,他们通过改变解剖学来作出应对。”华裔希望通过这个手术消解身体的族裔意义,归化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的认识过于肤浅,身体的手术并不能改变白人的种族投射,双眼皮也不能使他们立刻成为美国人。
惠特曼所采用的对抗策略是弘扬自己的种族身体之美,小说中,他引用自己的身体去对抗东方主义的话语,“我也要说我的长相—牙齿、眼睛、鼻子、侧影轮廓——完美无缺。仔细看看这眼。再从侧面看看。从另一边再看看。取个能看到脸的四分之三的角度再看。这脸不像鲁希莫尔山,是一个美国人的脸。”惠特曼将自己的身体前景化反击了华裔一直被认为是异族的看法,他着意于强调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正如素希·李所说,“惠特曼在大写的‘我’积极发声的同时展示自己的身体,他使自己可以被了解。”以这种方式,他也消解了关于“神秘”的华裔的刻板印象。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同时,惠特曼还表达了对肤色的作用进行重构的理想:“惠特曼要把那关于新英格兰西部的故事搞糟,把比尔、布鲁克和安妮描写成黑色和黄色皮肤。想象的新规则是:人普遍长得都像中国人。从现在起,每当你读到没有姓氏的人名时,就把他们当成黑皮肤或黄皮肤的。”林涧认为惠特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挑衅性但是严肃而重要的问题:“现代的阿新,作为现代美国文学的创作者,一定得皮肤白皙、胡子花白?还是得是一个长着亚裔的身材、有亚裔的姓氏的美国人?”林涧所追问的是:华裔能否超越身体的自然属性,成为美国文学的代言人。惠特曼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希望华裔的身体,同白人的身体一样,也是美国形象的代言人。
惠特曼的文学理想在美国现实的土壤里必然遭遇碰壁的命运,他首先面对的是美国主流文学对华裔的贬损,正如他的姓所暗示的一样。美国主流作家“垮掉派”的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称华人为“目光闪烁的小华人”,惠特曼对此愤愤不平,甚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凯鲁亚克。“听着,你这个目光闪烁的小法裔加拿大人。你知道什么,凯鲁亚克?你知道什么?你屁也不知道。在这儿,我是美国人。我是行走在这里的美国人。凯鲁亚克和他的美国之路滚一边去。”而对着美国主流文学开火也显示了华裔的边缘地位。如果说此时惠特曼只是通过语言甚至是内心活动来挑战权威,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话,在小说的后半部,惠特曼也不再含蓄忍隐了。他在餐馆听到邻桌的白人在开种族歧视的玩笑后,之前因为被称为“乡巴佬”的怒火在此一并点燃:“他挨个点着他们的鼻子。‘你们不要再开什么玩笑了。别让我再撞见你们笑话我们的民族。你们说外国佬的笑话,不论在哪里,我都要抓你们。明白吗?你们懂吗?’他抓着他们的桌沿,准备掀翻。”此时他俨然从语言的巨人转变为行动者,迈出了弘扬“种族自爱”的伟大的一步。正是这一步,连接了以前的语言天才和如今的行动派,并为“独角戏”中弘扬“种族自爱”的身体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阿新对于身体的“自爱”的建构类似于黑人民权运动者提出的“黑就是美”的文化运动。黑人民权主义者认为以往的“黑就是丑”对非裔美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表达出“内部殖民”的倾向,因此他们提出“黑就是美”的口号,来唤醒黑人对族裔、对肤色的自豪感。阿新生活在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呼吁将华裔的身体进行审美的修饰,表达了他的民权观。
三、“爱”与“憎”的悖谬: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探索
尓玛·玛尼(Irma Maini)认为《孙行者》是一部关于艺术家成长的小说(Kunstlerroman),小说中惠特曼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强调集体主体性以及族群对少数族裔的重要性。但是,小说的时间跨度不长,在惠特曼“工作—失业—结婚—找奶奶—创作戏剧”的线性发展过程中,无明显的戏剧冲突。而且惠特曼“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观点在第一章同时出现,笔者不认为“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两种情感模式属于线性发展序列,不存在明显情感转向,更准确地说,“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在小说中共时存在,有时甚至交替出现。作为一种共时的存在,它将叙述置于悖谬之中。既然是华裔,其身体不可避免具有中国性,与新移民的身体并不差别。但是对自己种族身体的厌恶性描写如何能同赞美自己身体的独特性并置?而且新移民的处于土生华裔凝视下的身体与土生华裔的祖辈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处于白人凝视下的身体并无不同,对于新移民的嘲讽是否也就是对于自己祖辈的嘲讽?
由前面的分析可见,“种族自憎”代表了华裔对自己族群的摒弃。而通篇惠特曼无畏无惧、大胆思考、大胆言说、大胆创作,最终创作了属于华裔的美国戏剧,采用了来自不同族裔的演员,建构了自己眼中的多元的美国社会。所以小说中的“种族自爱”,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则爱的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多族裔社群,各族群的差异性得以显现并处于平等的位置。
如何做到平等?对于华裔来说,主要要求的是对身体平等的双向凝视。身体的存在首先是视觉的客体,身体通过看与被看的方式去认知外界或被外界所认知。华人作为美国社会的他者总是处于被凝视的位置,而被凝视又强化了他们的他者身份,因为在凝视中,身体成为了一道景观。巴特勒曾说,在身体同精神相对立的时候,身体等同于女性,精神等同于男性。而在强调身体的时候,身体等同于男性身体,女性身体则作为他者被标记出来。将她的观点运用到华裔群体中,我们可以说,身体等同于白人男性的身体,华裔的身体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作为他者被标记出来。华裔的身体承载着异国情调的想象,成为白人凝视的客体。“种族化的凝视没有承认个体的反应/差异,在这种凝视中,个体的主体性消失了。脸、眼睛和其他面相学的特征明显意味着与文化标准化的族裔或种族多数群体的差异。通过凝视的景观性行为,‘少数族裔’的族裔主体被客体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种族身体,成为一道政治景观,一个空白的屏幕,种族主义的凝视在上面书写政治含义。而且,种族身体的景观特征对于白人的凝视总是适用,不管这个身体是否真的在移动,在表演。”华裔身体作为种族身体成为美国社会里的一道异域风景线,他们的行为被置于身体之下,身体的他者性被标出。他的肉体性超越了身体真正的行为。华裔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颠覆凝视与被凝视之间的主体区分,将被凝视转换为抗拒凝视。或者直接消极凝视与被凝视间的等级区分,取而代之以平等的互看。
而要做到平等的互看,华裔需要从各方面优化自己的形象,包括打破刻板印象的束缚。惠特曼的反叛行为主要表现在视觉和语言上。他首先使用自己的肤色作为武器,通过夸张的着装来挑战白人的视线。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母亲、阿姨们、朋友们以及化装师们都曾就他着绿色衣服的效果作过评点。‘别穿绿色的衣服,’有人像讲秘密似的说,另外有人像是提建议,又有人讲话时肯定得似乎傻瓜也懂。……‘你穿绿色不好看。’接着,宿舍里有人说,‘穿这颜色,我们显得更黄。’和种族肤色有关。当然,自此之后,他便懂得了他该穿什么颜色—绿色。”
所以,阿新穿着绿色的上衣,“从救世军那儿买来的外套”,配上一条“更绿的领带”,穿上“惠灵顿鞋”,头发蓬乱着,出门了。由此可见,阿新通过强化自己的种族身体形象,以造成凝视他的白人的视觉上的不快,借以对抗白人凝视的霸权地位。“他希望,他的这身打扮能侮辱那些看他的人。”此时,通过怪异的着装,他就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像美国主流社会带着歧视有色镜的妖魔鬼怪们举起了隐形金箍棒,将其偏见大白于天下,使其无处遁形。
同时,惠特曼通过不断言说打破了“沉默”的亚裔的刻板印象。一直以来,“沉默寡言”都是亚裔社群的刻板印象。张敬珏在《尽在不言中》对“沉默”进行“文化语境化”并探索“沉默”的积极意义。汤亭亭在小说中则一直赋予“沉默”以消极意义,在《女勇士》中,她通过叙述者对一个沉默的华裔女孩施暴表达了自己对华裔“沉默”的刻板印象的憎恨,在《孙行者》中,汤亭亭则直接塑造了一个颇有些饶舌的华裔青年形象来颠覆亚裔的刻板印象。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独角戏”中,惠特曼不再囿于自己丰富的思想活动里,他洋洋洒洒说了几十页,“这既是一场展现自我、伸张族裔权利的伟大的‘复辟’”,也挑战了美国社会的听觉系统。
惠特曼或者说汤亭亭所倡导的“种族自爱”强调的是“差异性”的身体。傅友祥在其论文中也归纳出汤亭亭所使用的差异的书写策略,突显美国文化内部差异的重要性,以重新构筑所谓的美国经验。确实如此,汤亭亭为凸显“差异性”,刻意描写华裔的身体,试图以此来抵抗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但是身体问题本身就带有种族主义的痕迹。葛莱思在《协商身份》一文中考查了“面相学”,她认为面相特征与种族差异紧密相连。而在安德烈·塔吉耶夫看来,当代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的。他认为:“在主张差别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文化差别的权利”的立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不明言的种族主义”,“这类种族主义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这类种族主义不援引纳粹的学说。这类种族主义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塔吉耶夫所谓的“新种族主义”其实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幌子下维持现有的种族差异,将少数族裔体现的文化看作正餐的佐料,目的是让正餐更有滋有味,对少数族裔施舍的正是赵健秀所称的“种族主义之爱”。而种族之间的差异的显性存在将极大伤害其成员,并阻碍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李磊伟认为“汤亭亭对少数族裔话语的理解的主要贡献在于她将笛卡尔的身体/意识二分状态结合在一起:在她看来,抽象的身份和具体的自我永不可能完全分开。物质性的身体(也就是种族、外表)和文化身体、象征和习惯,总是互相映照,去建构一个完整的亚裔美国身体。”汤亭亭将身体与意识结合,让身体成为思想的载体,凸显了作为亚裔美国主体的差异性身份,但她试图建构的“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社区势必会沦为一种全新的“种族主义话语”,这可能是她所没有想到的。
吉卜林被华裔美国学者所经常引用的一句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聚。”而一旦东西方相聚,则势必有高下之分。通过强调差异来消泯美国社会现存的种族偏见,其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本质主义。而且“种族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肤色的等级差异长期存在,很难立即消亡。所以,通过创作《孙行者》,汤亭亭所表达的与其是一种政治呼吁,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理想,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暗藏着深深的失望。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
A
1000-5072(2015)06-0017-08
2014-09-02
潘敏芳(1978—),女,湖北钟祥人,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亚裔美国文学、英美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再现、召唤、反抗——华裔美国小说中的身体书写研究》(批准号:14YJC75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