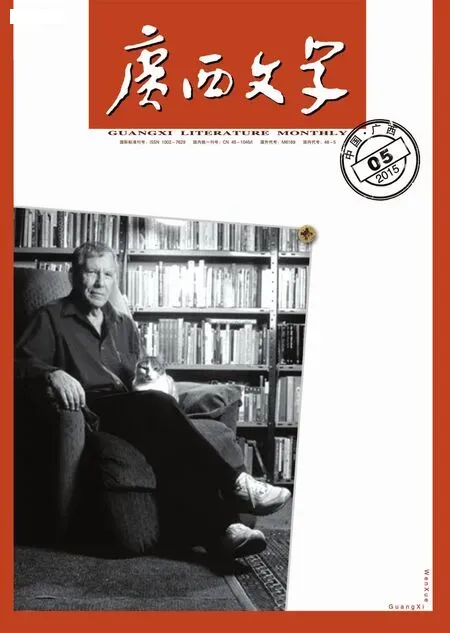旺根的守候
张 恒/著
全村其他户都在房屋拆迁意见书上签了字,只有旺根死活不愿签。
大伙儿不理解,七嘴八舌议论说,就你那破烂不堪的老屋和我们这些翻盖过的楼房一样的比例补偿,还不睡着笑醒了,咋不愿拆呢?旺根说,老屋咋啦?拆掉就没了。
真是榆木脑袋,转不过弯来。老屋拆了补偿新的,三室一厅的楼房,电梯上下,前后花园,住着和城里人一样的舒适,早先做梦都想不来的,咋碰到了这等好事还磨蹭呢?大伙儿摇摇头,想不通。
三奶奶说,旺根怕是想毛头想愚了。这些年他做什么事都没心情,心思一股脑儿地都牵挂在了毛头身上。
毛头是旺根的儿子,十八年前被人拐走了。被拐走的时候毛头五岁,刚晓得自己荡秋千,爬树摘柿子。毛头爬到柿树上总是对着自家的屋顶比画着,说我有屋高了。天真活泼的样子很可爱。
这时辰站在树下的旺根就傻傻地笑,毛头神气的模样让他感觉比吃了柿子还甜。即使毛头拿着柿子砸他,他也不躲,依旧傻傻地笑。
后来旺根懊悔得吐血。就在这柿子树下,许是在玩秋千的毛头被人拐走了。那会儿,旺根和媳妇挑着柿子去了镇上。旺根后悔没把毛头一起带去。平日里他去镇上都是把毛头一起带去的,唯独那一回没带。旺根懊悔得吐血。
旺根发疯似的四处找,镇上,县里,方圆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外省,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捕风捉影得到蛛丝马迹信儿说的地方也都去了,就是没找到。毛头像是被人锁住了身子,锁住了声音,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了音讯。
柿子落了又结,叶儿黄了又青,年复一年,就像旺根寻找毛头的脚步,来来去去。在家的时候,旺根就傻傻地站在树下,要么呆呆地看着孤零零的秋千,要么呆呆地望着枝叶稀疏的柿树,眼睛里总是晃动着毛头俏皮的身影。老屋没长,柿树也没长,年复一年的是旺根期盼的心绪在长。
村里人家一个接一个都在翻盖房子,土墙变砖墙,平房变楼房,唯独旺根家的房子是一成不变。不仅房子没变,就连在柿树下挂了多少年的秋千都没变。三奶奶有时过来劝劝他,说旺根啊,毛头虽然不在了,但可以慢慢找,自个的日子还是要过的。你看这村里就你家房子没翻了,刮风下雨不好住的。旺根说,没心情。
每次都这样,说得三奶奶直叹气。
村子要整体搬迁的消息传来,大伙儿在高兴之余又有些惋惜,都说,嗨,要早晓得搬迁,就不花那个冤枉钱翻房子了,还劳累烦神。转而便都羡慕旺根,说还是旺根有财运,老屋和我们的新房一样的比例得到补偿。人真是不长前后眼的,愚人自有愚人福。
可旺根却不签字,拆迁工作组的人好说歹说都不行,旺根是一百二十个不同意拆他那老屋。旺根说,我不想要你们的补偿。
只要一户不签字,这村子的屋就不能拆。屋不能拆势必要影响整个村子的搬迁,进而就要影响整个工业园的规划建设,这是上面断然不会允许的。于是,工作组的人便搬来三奶奶做旺根的思想工作。他们了解到,平日里旺根是最听三奶奶的话的。
三奶奶来了,旺根只得说实话。旺根说,我不是不想要那超面积的补偿,我是不能拆这老屋啊!
三奶奶说,怎么啦,老屋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搬到新楼住不是要比这好?
旺根说,新楼固然好,可毛头不认得,毛头只认这老屋呢。毛头被拐走的时候年龄小,其他的怕是都不记得了,但这老屋,还有这柿子树,树下的秋千他是一定记得的,说不准哪天毛头就找回来了……
哦,这下三奶奶和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了,旺根这些年来不愿拆老屋就是要等着毛头回来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旺根不愚,旺根心细着呢,只是这些年想儿子想得沉默寡言不愿多说话罢了。
工作组的人很同情旺根,但房子还是要拆的。想来想去,他们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就又带着人来到旺根家,对他说,把你们家的老屋,连同柿子树和秋千一起拍照下来,把照片保留着。
旺根说,保留照片有什么用?照片能一年到头摆在这儿?毛头能看到?
说的也是,工作组的人又没辙了。
这时随工作组一起来的摄影记者说话了,说把照片发到网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旺根将信将疑地勉强依了。
一个月后,在云南某户人家的一台电脑前,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到这张照片,立即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