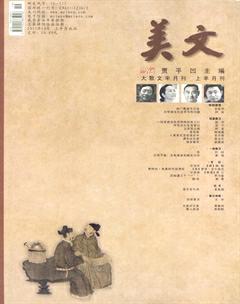苏
叶梓
手稿的东山
东山者,东洞庭山也,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半岛;手稿者,信笔涂来,不计章法,拥有个人书写时的体温与心跳。两者连在一起,名为“手稿的东山”,实乃东山之游的点滴记忆,不虚妄,不矫情,谨为一截时光之佐证耳。
先去了启园。
苏州的园林去了不少,启园还是头一次去。它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坐拥太湖,这是姑苏城里其他园林没法比的。启园也是私人的宅园,俗称席家花园。它的来历,是席家为纪念其祖上在此迎候康熙皇帝而建。这些年,见过一些人,喜欢把祖上与名人的照片拿出来炫耀,想想,这真是小手笔,那像席家那么出手阔绰大方,建个园子纪念以志其事。所以,园子里有“康熙皇帝御码头”。
我到码头跟前,里面站着不少人,拍照。
码头伸到太湖,我在边上抽了一支烟,看了一会游人,就折身返了。
陆巷古村也是第一次去。
有一次,在太湖边玩,上山采马兰头,一位同行者说,她小时候就在陆巷村长大,后来回去,不少人都问她,你是谁谁家的闺女。她看似不着边际的言辞,反倒让我喜欢上了陆巷村。为什么,说明那里的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这才是真正的古村,不像江南的不少水乡古镇,土著早就搬走了,大量的商贩们纷涌入驻了。
陆巷村的三十多条弄堂,一下子逛不完,就想着先去看看王鏊的故居。可拐来拐去,始终找不到。在一座老宅的门口打听时,老妇人说,这里就是,就进去了。王鏊是明代正德年间的宰相,是唐伯虎和文徽明的老师。他就是陆巷人。村子里至今保存的解元、会元、探花三座明代牌楼,皆与他有关。
从故居出来,经过一条巷子,见几位阿婆闲坐在家门口的小饭馆里,聊天。墙上挂一木质招牌,上书:吃饭、喝茶、食宿。这里竟然可以住宿,一问,包吃包住,一天150元,不算贵。离开时,有了个念想,寻个时间,在这里住几天,看书写东西,也挺好。写什么呢,我都想好了,写一篇《陆巷古村》,再把这两年关于苏州的文字,理一理。
从陆巷村出来,去万德山庄午饭。
朋友点了一桌子菜,太湖白鱼、太湖莼菜,皆为苏帮菜。我和诗人李满强喝了两瓶花开福贵,张家港产的。喝酒时,有湖风携带一丝清凉,吹在脸庞上。
下午去紫金庵,这是逛得最扎实的一个地方。
这得益于碰上了一位好导游。导游姓许,五十开外,这把年纪的导游,不多见了。始建于梁陈时期的紫金庵,有三宝,分别是“慧眼”“华盖”“经盖”。许导游讲得详细,听之,犹如读一册简洁明了的普及读物。这恰恰是一个导游的功力,既言之有物,又通俗易懂。我不敢说自己粗通泥塑,至少略知皮毛,因为家乡的麦积山石窟就是以泥塑见称,前些年每年去好多次,去得次数多了,就懂一点。
紫金庵的泥塑罗汉群像,有“天下罗汉二堂半”之一堂的美誉,言之有理。的确,大殿左右两壁十六尊相传出自南宋雕塑名手雷潮夫妇的泥塑彩绘罗汉像,“各显妙相,呼之欲出”,堪称古代雕塑艺术精华。在我看来,它的美德,其实与天水麦积山石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在哪里?就是给佛赋予了世俗的意义,每一尊罗汉,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真性情。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地方。
看着这些佛,我突然想念天水的麦积山大佛了。
在这个走马观花的年代里,一位认真的导游,能把一处景点讲得如此通透,通透得融合了历史、植物、宗教甚至天文地理,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临出门时,他还把我们带到一间房子,讲了一幅画,画系名家所作。上面的题款,写得真好,我录在这里,以求与读者诸君分享:
寒山问拾得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句句都是大实话,可世间俗人几人能为?
从紫金庵出来,去雕花楼。这次的导游,女的,年轻貌美,但职业得让人有点怕。或许,是刚听了许导游的原因吧,才有如此悬殊的对比。
雕花楼的名字,显然是因了这里“无处不雕、无处不刻”的砖雕、木雕、金雕、石雕,才叫它雕花大楼。不过,真配得上这样叫;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春在楼”这个名字。此名典出苏州清代诗人俞樾名句“花落春仍在”,有点雅致,有点惆怅,又有点人生无常的飘忽。
女导游的语速很快,像是急着下班似的。
她不停地强调着雕花楼独一无二的“进门有宝、伸手有钱、脚踏有福、抬头有寿、回头有官、出门有喜”。可她哪里知道,人世间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热衷于追求福禄。比如我,倒是对后院里的孩儿莲更感兴趣。前段时间去江西婺源看油菜花,在李坑古村碰到了一棵怕痒树,很喜欢。这次见到的孩儿莲,本是西南一带的树种,偏偏求生于江南,颇为神奇。更神奇的是,据园艺专家考证,云南等地的“孩儿莲”已在上世纪绝迹,而雕花楼的“孩儿莲”偏偏在异乡生长得枝繁叶茂——我从西北南迁江南,我也希望拥有这样的命运。
“你们来得幸运了,孩儿莲今天开花了。”导游说。
抬头一望,果然是。花的形状似莲花,色微红,花柄弯垂,呈倒挂形状,如红灯笼一般。一株迁徒异乡的孩儿莲,在江南的四月举着一树的小小的红灯笼。天下的草木虫鱼,得慢慢认识,都认识了,人情世故也就差不多都懂了。
时间的关系,三山岛没去成。但经过渡口时我留意了一眼,游客如云。据说,岛上花果繁复,一派田园风光。其实,东山的不少地方都没去,比如裕德堂,比如藏有文徵明《东西两山图》的轩辕宫,比如有“东山雕花楼第二”的文德堂。
但我并不遗憾,为什么?
不为什么。
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我想,大抵是粗略看过的这些足以让我有了终老于斯的念头,所以,不必遗憾,留着以后慢慢看。家乡谚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些年游荡了不少地方,让人徒生终老之心的地方,似乎只有东山。也难怪,早在明代就有那么多的文人雅士风雅地生活在这一带,看烟波太湖,写隽秀文章。
鸡头米的赞美诗
江南苦夏。
这苦,是风吹不散的燠热。好在苦尽了总会甘来,桂花香的秋天就在不远处等着。不仅如此,在桂香抵临之前,鸡头米携着款款温情已经来了,像是怀着菩萨心肠给熬过苦夏的人送清凉来了。鸡头米与鸡无关,就像昆曲跟昆明不搭界一样。鸡头米,又名水鸡头、鸡头苞,学名芡实。古代的药书里,说它“补而不峻”“防燥不腻”,是“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的佳品。鸡头米是“水八仙”之一——水八仙就像是一支活跃于水底世界的小分队,由茭白、莲藕、水芹、茨菰、荸荠、莼菜、菱以及芡实组成,它们大多在秋天上市,用各自的风采丰富着江南秋天的味蕾。中国古代历史上,喜欢用八仙称谓一个小群体,比如饮中八仙,而水八仙是江南水底世界里的一个小小村庄,有着人间的温情。
鸡头米是荷藕的高邻,叶圆且大,边角向上微翘,像一个绿圆盘平铺在水面上,但不似荷叶那么光润平滑,叶面有些凹凸皱起。鸡头米的花儿也很好看,颜色呈浅紫色,浮在水面,一派紫云英的清艳。等花谢后,花萼并不脱落,随着生长时间慢慢地闭合和膨胀,形成如鸡头般大小的果实球——果实球里孕育着的坚硬果实,就是鸡头米。
今年的江南出奇的热,气温屡创新高。在这难耐的暑热里唯一让人念想的,就是喝一碗新鲜的鸡头米羹。
我是北人,之前没喝过鸡头米羹。去年,在苏州的太湖边第一次喝,有点初恋般的美好。微风吹过太湖水的时候,我在临湖的一家饭店里,与一碗鸡头米羹不期而遇。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一碗新鲜的鸡头米羹,以刚上市的鸡头米为主料,辅以桂花糖、燕窝、银耳、玉米粒,淡而幽远,淡得如同洗尽铅华,远得回味无穷,仿佛一段深藏岁月深处的往事。喝上一口,跟苏绣、评弹给你的感觉一样,软嫩、细糯、甜润。如果没有南迁,也许,我的味蕾世界里永远留不下鸡头米的微甜与软糯。当它一勺一勺地抵达舌尖时,内心里有一丝小小的悸动。我坦言:“这是我第一次吃。”
她坐在旁边,微笑,不语。
在她的记忆里,每年夏末秋初的苏州街头,都会有小摊贩聚集在树阴下,一边剥一边出售鸡头米。他们的面前,是堆起来的鸡头米,白白嫩嫩,圆圆溜溜,煞是可爱。老底子的苏州,最有名的是南荡鸡头米——而正宗的南荡鸡头米种植在葑门外一带。南荡鸡头米又叫“南芡”,果实硕大,结籽六七十粒,清糯可口,相比之下其他地方的鸡头米就有些点瘦弱了,结籽最多也就是二十余颗,这样的区别颇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味道。
苏州美食偏重时令,南荡虾仁就是其中一款。看似没有鸡头米的名字,实际上,是鸡头米炒虾仁了。新鲜的鸡头米配以新鲜的虾仁,鲜美遇上清香,仿佛一场秋天的艳遇。清朝的沈朝初在《忆江南·姑苏四时食品词》里深情地描述:“苏州好,葑水种鸡头,莹润每凝珠十斛,柔香偏爱乳盈瓯,细剥小庭幽。”苏州之好,竟然不是虎丘,不是园林,而是“葑水种鸡头”,这样的夸张足见“葑水”一带的南荡鸡头米有何等的好。其实,我倒喜欢“小庭”一词,形象,生动,能给人这样的错觉:每一粒鸡头米,都是一个小小的家。
据说,一代影后王丹凤在香港请客,宣布甜品上桌,大家吃了一惊:竟然是鸡头米!当时冰箱很少,航班也不多,要吃到上市时间很短的苏州鸡头米,几乎不能想象。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王丹凤委托苏州朋友采购,连夜送到上海寄放在冰箱里,上午专人从上海送到香港,才赶上了晚宴。
而我,怀念去年的鸡头米,如同怀念一个人,甜蜜里渗着点点忧伤。
承天寺巷
一
这是夏日的午后,我从人流攒动的苏州平江路七拐八弯地来到了承天寺巷,仿佛完成了一次身不由已的撤离。可我又在拒绝和回避着什么呢?也许,拥挤的人群、躁杂的市声以及那些挤在一起显得极为逼仄的咖啡店、茶室、精品小屋,早就让平江路不堪重负了。
当然,我之于平江路,也是多余的。
精致婉约的苏州,像南方大地的一座后花园(更是中国的后花园),它所提供的小巧细美的园林、纵横交错的流水、风姿绰约的小桥以及生生不息的风雅传承,是大地与历史联手赐予的精美篇章。而我偏爱这里的小巷。苏州的小巷像是一位不动声色的世外高人,把苏州的美景紧密地联接在一起。除此之外,它不同于我见过的北方胡同,苏州小巷的静谧,既有静若处子的清纯,亦有深藏闺房的雅静,而这种静恰好依托于形制上的窄与小——它窄得撑油纸伞的姑娘只能一个人通过,窄得两个人只能擦肩而过,窄得横亘两边房檐上的竹竿只能晒一床被子。一条条小巷,宛似苏州老城身体里的道道血管,流淌的是一座千年古城的精魂与风雅。
承天寺巷就是这样一条古巷。
它在苏州小巷的排行榜上名气并不大,不似山塘老街那么如雷贯耳,可是它洗尽铅华,低调内敛,仿佛要低到尘埃里。我与它最初的亲近,来自于曾经静静聆听过一个人对它的讲述与回忆。也许,这就是我从平江路辗转而来的唯一理由吧。
可是,我几经打听来到这里,到底要寻找什么呢?况且,在城市变迁的大浪里,它就换了容颜。
二
其实,要进入承天寺巷的肌理,承天寺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词。
第一次听到承天寺巷的时候,条件反射地想到了苏轼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这次彪炳史册的夜游被苏轼简洁记录在案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任职,大概是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所以,当听到“承天寺巷”四个字时,我心里猛地一惊,莫非,与苏轼的那个承天寺有点关系?然而,我终究错了,普天之下以承天寺命名的寺院多了去了,苏州有,其它地方也有。
不过,苏州的承天寺说来话长——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承天寺。
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梁武帝萧衍以佛治国,一时间上行下效,全国佛事大兴。某日傍晚,住在长洲县衙西北二里处的官员陆僧瓒,见其官宅上祥云重叠,遂突发奇想,奏请梁武帝主动建议舍宅建寺——不仅如此,他还给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闻之,大悦,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重云”被误为“重玄”,这是奏章转抄上递过程中出现的阴差阳错,于是,“重云寺”变成了“重玄寺”。
中唐时期的重玄寺十分兴盛,时任苏州刺使的唐代大诗人韦应物游览此寺后,写过一首《登重玄寺阁》。白居易也在寺内书写了《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碑文,认为“石经功徳契如来付嘱之心。”后来的五代吴越王钱镠时代(公元908-932年),对重玄寺进行了大规模修葺,规模更加宏大,殿阁更加富丽,而且,因寺前有两座土山、两块异石立于庭前,有人给它重新命名:双峨寺——据说,当时有一尊高丈余的无量寿佛铜像屹立于中央,十六尊罗汉环立两侧,另有盘沟大圣祠、灵佑庙和万佛阁等别院五座。
大约在宋初,重玄寺才易名为承天寺。
而此时的承天寺,已经易址于苏州城东了。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运动突然爆发,朝廷对僧人展开了残酷的迫害,苏州城里的大量寺庙被毁,僧人纷纷迁出城外,有的在别处另建新寺。于是,苏州城东的唯亭镇草鞋山附近出现了一座新的重元寺,它是对承天寺的一次遥远致意与守望。这大抵也是多年之后的今天,重修之地选在现在的工业园区的理由了。
范仲淹任职宰相时,曾与同僚章岷游览过承天寺,那时候好像已经叫重元寺了,但他在诗名里还是叫承天寺,诗题为《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其诗曰:“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晩意烟乖草,秋姿露滴苔,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读这样的句子,分明能看出他内心几近放浪的愉悦。
宋徽宗宣和中,因朝廷禁止寺观、桥梁名字以“天、圣、皇、王”等为名,所以重元寺又改名为能仁寺。元代时,重玄寺又将宋代的两个名字合二为一,称“承天能仁寺”。从初名“重云”误为“重玄”,到后来相继以“承天”“能仁”“双峨”“重元”等为寺名,这大抵就是承天寺的漫漫历史了。
在搜读有关承天寺的史料时,偶然碰到了一则僧人的故事,颇有意思。
唐代的承天寺里,有一药圃,是喜好种植名药的元达僧人专门到各地采集药种后在寺内栽种。一日,文学家皮日休专门到寺里访问,并题诗以赠,诗曰:“香蔓口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牙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今朝种一麻。”皮日休的诗在唐代诗坛属于中等偏上,但这首诗却把药圃之事写得风流蕴藉,我一下子对他有了好感。
可能的话,与我心底里偏爱这座消失的古寺有关吧。
三
承天寺的原址在苏州接驾桥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承天寺前36号一带。自唐代易址唯亭之后,这里因为少了一座香火繁盛的寺庙而有些“此处空余黄鹤楼”的寂寥与落寞。但是,就像江湖上没有了身影但传说仍在一样,承天寺的名字却留了下来,而且,这一带以承天寺巷命名,就是对它的一次遥遥致敬。
毕竟,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这里香火极盛,也是苏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年古刹。
然而今天,当我拖着孤独的身躯穿行在以这条古巷为中心的街区时,四处的高楼大厦铺天盖地,甚至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这样的场景,让我多么怀念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承天寺巷的街景——尽管我不是亲历者,但我能转述出它当年的模样:青砖铺就的路面,因为年代久了,春天的水气又足,好像脚下稍一用劲,就会挤出水珠来,两边的房子鳞次栉比,虽然高低参差,门窗的朝向略有不同,但是清一色的石灰粉墙,简约朴素,粗糙而有质感,鱼鳞黑瓦,房檐处只用白灰简洁地一抹,比起砖刻浮雕着花鸟鱼虫的瓦当来另有一番创意。小巷两旁,是一户户江南人家,推门而入,天井、木格子的窗、红色的棱框一应俱全,江南人特有的谨慎、含蓄、简约、超脱和秩序,从这样一条寂静的小巷中一览无余。
四
命运派遣我来到江南,仿佛就是为了让我认识一个承天寺巷长大的女孩。常常,她有意无意地给我讲述自己在承天寺巷度过的时光。这段时光其实是一个江南女孩的少女时代,忧伤多愁的日记本、初潮的疼痛、快乐的郊游,都是以这条小巷为背景展开的。她讲述最多的是在附近的苏州花线厂去玩的旧事。那时候,她家的门口有一眼古井,井水清冽甘甜,她常常扶在井栏对着蓝天发呆。不远处的小桥流水,是她看惯了的街景。偶尔,她会跟一个叫杨柳的女孩子一起,从承天寺巷出发,跑到附近的园林去玩,以至于后来她想当然地以为别处的城市里都有园林可玩——如此天真无邪的念头需要怎样一颗单纯的心灵才能承载呢?
终于,有一天,她带我去了承天寺巷。
我们不是去寻找旧时的风物,因为已经找不回来了。可是,这个一直栖身于苏州城里,上班下班弹琴喝茶的女子,对这里的记忆永远新鲜如初,如同昨日。她仍然记得,外公让佣人从家门口的那口井淘出了不少瓷器,那口井神奇的是遇旱不减,遇涝不增,永远那么多,甚至,有人说井水一直通着虎丘泉水。还有,小巷及边上的东海岛西海岛传说是吴王的别院遗址,东西海岛住着他的两个妃子。这些看似遥远的传说,其实是一个女人少女时代的温暖记忆。
我还参加过一次在承天寺巷长大的孩子们的聚会。
如今,这些人已经跨入中年的门槛,他们齐聚一堂的别致之处,在于不似一般的同学聚会,张口闭口不是金钱、女人,就是权力房子,他们在饭桌上讲述的全是小巷的点滴记忆,谁家的盆景最好看,谁家的桂花树最香,谁家的天井里水最清澈,没有飞长流短,只有风花雪月,真正意义上的风花雪月。
当他们回忆时,我却刚刚步入这条小巷——刚刚开始,也是刚刚好。
五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刚好是一个立夏之日:2013年5月5日。这个夜晚,我孤身一人,仿佛陷入一场夏日的大梦中。秋叶静美,夏花烂漫,是芸芸人生里的诸种美好,可我,在这个初夏时节会迎来生命里期许的美好么?我不知道,所以无端地怀念起承天寺巷来。我承认,我有些遗憾,遗憾自己经过你的过往时你已经离开,但我也很庆幸,庆幸尽管你已离开,而我还能经过你的过往,穿过时光的隧道看到了少女时代的你,看到了那个喜欢捧着一册《廊桥遗梦》在木格子的窗下静静阅读的女孩。
夜已经深了,我该睡了,让我借着星辰的嘴唇给承天寺巷道一声: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