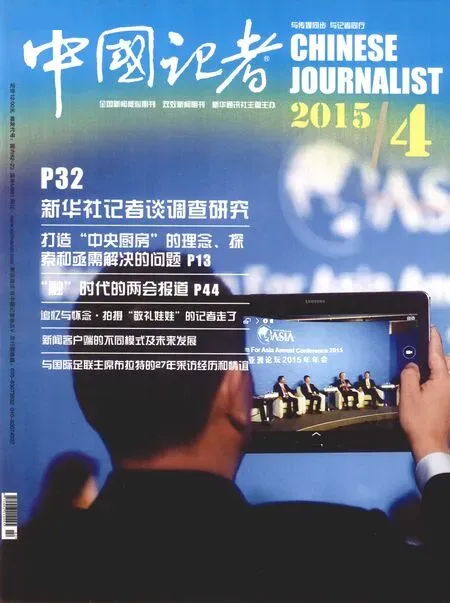吕厚民,从未放下过手中相机 ——吕厚民在扬州兴化的7年事
吕厚民,从未放下过手中相机
——吕厚民在扬州兴化的7年事
□ 文/王 鑫
提要:2015年3月9日,摄影大家吕厚民逝世,享年88岁。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看过吕厚民拍摄的毛泽东照片。他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瞬间。吕厚民对中国摄影做出巨大贡献,曾任新华社江西、江苏分社摄影组长。为怀念这位著名的摄影大师,《中国记者》特邀《扬州晚报》记者王鑫采写此文。
关键词:吕厚民 怀念 追忆 摄影
2015年3月9日,摄影大家吕厚民逝世。
几乎每名中国人,都曾看过吕厚民所拍摄的毛泽东照片。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摄影师,吕厚民定格下很多幅毛泽东的经典形象。“文革”期间,吕厚民被下放到扬州兴化农村,在这里,他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虽然贫苦漂泊,但吕厚民都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相机。
“我叫吕厚民,今天来这里报到”
所有的往事,如今都藏在8旬老人王虹军的脑海里。吕厚民在兴化的7年多时间,基本都在他的陪伴下走过。患难见真情。
1967年的初夏,新蝉初鸣,第一次看见吕厚民的场景,王虹军还是历历在目:“那是1967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当时正在兴化县文化馆工作,首当其冲被批斗了。但是,总要有人干活,特别是开展摄影工作时,又都离不开人,军代表就让我重新开始拿起相机。因为需要拍摄的内容很多,我就提出来,需要找一个帮手。他们问要找谁,我就提出了吕厚民。”王虹军回忆道,“当时,我还没有和吕厚民见过面,就是知道他下放到这里的农村来了。之前,我都是在《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上看见吕厚民的作品,虽未谋面,内心早就对他很是敬仰。”
王虹军的要求得到了批准。第二天,吕厚民就来到了兴化县城。听说他来了,王虹军连忙丢下手中的活,迎上前去。站在他面前的吕厚民,个子不高,身形单薄,面色苍白,憔悴不堪,只是说了一句:“我叫吕厚民,今天来这里报到。”

摄影大家 吕厚民
沉默、寡言,这是吕厚民留给王虹军的第一印象。最开始的时候,吕厚民的话不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时候,还会长久望着一处水面发呆。
“如果调一下快门和光圈,效果会不会更好?”
吕厚民下放的地方,是兴化县海河区钓鱼乡杨家大队第四生产队,距离县城几十里路,条件非常艰苦。王虹军到过吕住的地方,泥巴糊起的墙面,茅草盖成的屋顶,屋内烂泥裹足,屋外垃圾堆积。从北京到兴化,从中南海到农村,其中的落差,可想而知。更何况,吕厚民还带着妻子刘钟云和三个孩子,看着他们的生活,王虹军心中不忍。
好在,只要吕厚民拿起相机,他的话就多了起来,脸上的神情也活络多了,眼睛里就有了光泽。一开始,王虹军还以为,吕厚民肯定会带着相机。谁知道,他竟是两手空空而来。王虹军手上有一部别人用过的二手德国罗莱福莱相机,两个人就共用一部相机,穿行在兴化农村的阡陌之间。
兴化是鱼米之乡,两人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粮食入仓。长长的传送带,将稻米运至高处,再从上方倾泄入仓,场面十分壮观。吕厚民总是让王虹军先拍,自己在一旁观察。王虹军调试了一下,用了“快门1/125,光圈F8”的系数拍摄。一会儿,吕厚民在一旁建议说:“如果调一下快门和光圈,快门1/30,光圈F16,效果会不会更好?”根据吕厚民提出的系数,王虹军再进行拍摄,获益匪浅。
在两人的交流过程中,吕厚民从未以著名摄影师自居。他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和王虹军说话,很多时候,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后,都会十分谦逊地说上一句:“虹军,你看呢?”
“摄影技术,就是写实、求真、传情、表意”
随着交往,吕厚民越来越放松。在农村,尽管生活条件大不如前,但是当地农民的质朴纯善时常让他们感受温情。在这里,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邻家在河里打捞起来的小鱼,放上咸菜熬煮,都会送来一小碗。渐渐地,看着妻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吕厚民的心,也逐渐踏实了下来。
一次在电厂拍摄,王虹军看到吕厚民使用灯光。在吕厚民手中,灯光的灯位高低,
主灯辅灯之间的光比,光线的强弱,都是丝毫必较。
照片冲洗好后,王虹军看到成品时,才发觉吕厚民对于灯光的理解。人物脸部的亮度和暗度恰到好处,每一幅人物照片,都显现出肤色质感。“吕厚民对我说,摄影技术,就是写实、求真、传情、表意,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王虹军回忆道,“拍摄人物时,吕厚民特别讲究细节的捕捉,往往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体现出人物的性格来。”
有一次,两人走在乌巾荡中,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游荡着四只渔船。看到这样的场面,两人不约而同想到登高取景,湖边正好有一处废弃的砖窑,两人就相互搭手,登上窑顶。吕厚民站在高处,大声招呼着湖面上的渔民:“渔船上的老乡,你们从哪来啊?”渔民也在船上和他应和着,就在对话之间,吕厚民拍下好几幅照片。水面上波光粼粼,小船上渔民撒网。每一张网,都捕获着希望,还有那天吕厚民的高声笑语。
“吕厚民每拍摄一张照片,都不会随随便便按下快门,他都会来回走上几次,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王虹军说道,“特别是他对被摄者充满了尊重,无论是百姓工人,还是农夫渔民,他都非常礼貌地和对方攀谈,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走过这么多地方,这里的垛田风貌是独一无二的”
兴化地势低洼形成了独特的垛田风貌。农民开挖网状深沟,或用小河的泥土堆积而成垛状高田。或方或圆,或宽或窄,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春暖花开,油菜花开,千垛万垛一片金黄,十里八村阵风飘香。当吕厚民第一次来到垛田边上时,看到“船在水中走,人在花中游”时,不由惊呼:“走过这么多地方,这里的垛田风貌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拍摄好眼前美景,吕厚民特地拿出了一卷过期的彩色柯达胶卷,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一卷胶卷只有12张,每一张的构图用色,都费尽思量。他们在金黄色的垛田中穿行,乘小船,走独木,乐在其中。最后,他们拍摄了一组彩色照片,名为《垛田春色》。
“文革”结束后,全国举行了首届摄影展,他们就选送了其中一幅作品,顺利入选;此后,在《中国摄影》恢复创刊的首期中,这幅《垛田春色》被用作封面;建国30周年摄影艺术作品展,这幅作品再次入选。在当年,这幅照片成为了中国乡村景色的范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刊用这幅作品的出版物上,这幅《垛田春色》的作者,均署名为“吕厚军”,取了“吕厚民”和“王虹军”两人名字。“当时,我们都想署对方的名字,结果谁都说服不了对方,结果,就取了‘吕厚军’这个名字。”王虹军笑道。
“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的,曾问了三次我的下落”
几年过去了,吕厚民在兴化边走边拍,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吕妻刘钟云常年居住在北方,来到兴化后,气候很难适应,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雨天气,就酸疼难忍。王虹军看到在县城文化馆后面,有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面积只有8平方米,但是好歹要比农村的条件好。经过他争取,吕厚民一家住到了兴化县城里。
但是,就在这时,根据当时有关文件,说是吕厚民这批下放的,不得回京。大家知道消息后,都很为吕厚民着急,却又不敢泄露文件内容。王虹军故作随意地问他:“你都下来这么久了,毛主席知道吗?要不要写封信给他,汇报一下你的情况?”吕厚民听了之后,当即写信。没过多久,就接到了毛主席要接见他的消息。
从北京回来后,吕厚民激动地告诉王虹军:“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的,曾问了三次我的下落。”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吕厚民调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并在第二年调回北京工作。
在临行之前,吕厚民把王虹军请到家中,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木箱,里面珍藏着一本小影集。里面都摆放着毛主席的珍贵照片,还有一张是毛主席跟吕厚民握手的照片,那是吕厚民在古巴举办个人摄影展归来时,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他。7年多来,这本小影集,无论吕厚民身在何处,都把它放在了最妥当的地方。
当晚,王虹军也把心中的疑问一股脑都问了出来:“给毛主席他们拍照,你紧张吗?”吕厚民说:“开始当然非常紧张,但是毛主席人非常随和,就和普通人一样。”王虹军又问:“这么多年来,你拍摄失误过吗?”吕厚民想了想后回答说:“拍照就是要随时做好准备,我一次失误也没有过。”
“他忽然大声喊道,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冥冥之中似有安排,2015年3月9日,吕厚民逝世的当天上午,王虹军编著的《运河与扬州百年影存》正在扬州进行首发仪式,其中收录了吕厚民的两幅摄影作品。一幅是《放鸭图》,反映了扬州运河上放鸭的场景。一幅是《精雕细刻》,是一位扬州工艺大师正在雕刻漆器花瓶的图片。首发式上,噩耗传来,王虹军情难自抑,放声大哭。
“我特别记得,拍摄那张《放鸭图》的场景。那天,我们从扬州行署第二招待所出发,到南门车站坐车,准备去江都,并肩坐在靠前右侧的位置上,车子开过扬州大桥时,他忽然大声喊道,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我也没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司机说,下车后就不能再上来了。他也不管,停车后就赶紧往回跑,我跟着他,到了桥上,忽然看到水面上成千上万的鸭子,正在水中游弋,场面非常壮观,他立刻用那台罗莱福莱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照片拍到了,班车却走了,我们就一路走回了招待所。我特别记得,那天的吕厚民非常高兴,一脸的兴奋和满足,像个孩子一样。”王虹军回忆道。(作者是《扬州晚报》文娱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