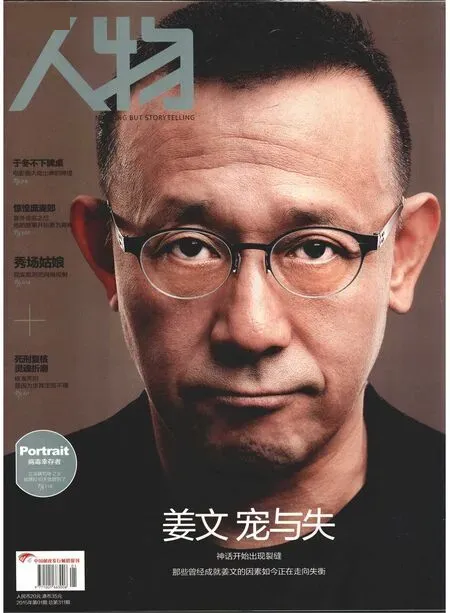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
文|思郁 编辑|鲁韵子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
文|思郁 编辑|鲁韵子
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耳语者》关注的就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毛俊杰
类别:历史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2010年4月,著名苏俄史学者奥兰多·费吉斯被发现数年间不断匿名登录亚马逊网站,对同行的作品进行恶毒差评。行径暴露后,费吉斯公开道歉,并辩解自己因对苏联历史研究过度而心理失衡,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两年后,美国学术杂志刊登了对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以下简称《耳语者》)一书的评论,重提旧事,还列举了他著作中不少“硬伤”,比如所采用口述者的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有出入、书中的描述过于文学化等等。
提及学界旧事并非为了质疑或者辩护。坦白说,真相扑朔迷离,早已远去,我们只能试着理解书中的那段历史。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对斯大林时期苏俄历史的了解,仅仅建立在各种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上,而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缺乏认知。关于那段历史,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档案等着我们去发掘。但对费吉斯来说,《耳语者》的写作与出版迫在眉睫,因为当年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已经步入老年,其回忆弥足珍贵,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此鲜活的故事样本。
《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家庭档案,主要是信件、日记、回忆录及家庭照片等。书中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年事已高的幸存者的口述中获得。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正来源于此,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如果考虑到当年的现实,尤其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就能理解很多幸存者的恐惧已烙在心灵深处。如何让他们打消疑虑讲出真相、如何分辨其中真假,都是难题。
费吉斯认为,“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耳语者》关注的就是流放者背后的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在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耳语者”这个词汇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也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
家庭是我们保留私人生活的最后场所。但在斯大林时代,统治者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效忠并服务于国家和集体。在这一统治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只要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反对者流放至古拉格。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正在此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耳语者的世界。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在那种极端恐怖、随时可能被搜查和逮捕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偷偷写日记。1936年,作家普利谢维恩因在新年晚会上作尖锐评论而受到作家协会的攻击,他担心地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利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利谢维恩由此撤出公共领域,遁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思想的暴露。对他来说,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斯大林以及苏维埃大众文化的异议,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普利谢维恩的选择并非个例。《耳语者》就借用了大量的幸存者日记和回忆录。如同“耳语者”本身就具有双重意义一样,幸存者的回忆往往与虚构交织在一起。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掩盖了更多真相的人。他们活在阴影中太久了,自己已变成了那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他们讲述它,又反抗它;认同它,又恐惧它。讲述的永远没有沉默包含的多。《耳语者》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