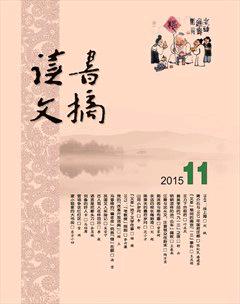冯雪峰的“编者按”究竟“错”在哪
汤莹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甲午年,因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份。批判 《文艺报》 是这一系列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现在我们得知,当时之所以突然对 《文艺报》 进行批判,一个主要的源头是,《文艺报》 在转载李希凡、蓝翎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这则“编者按”令毛泽东“怒火中烧”。问题在于,这则“编者按”是由中宣部审定通过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撰写这则“编者按”的冯雪峰与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私交,这是当时文艺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则由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究竟“错”在哪里?
一、令毛泽东“怒火中烧”的“编者按”
李希凡、蓝翎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是195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源头之一。这篇文章刊发在 《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中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进行了学术商榷。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让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找邓拓转载该文,以期引起争论。不过,在转载的过程中,经过研究最后达成一致决定由《文艺报》 转载。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文艺报》第18期在转载该文的时候,时任 《文艺报》 主编的冯雪峰特意加了一个“编者按”。
这则“编者按”共两段。第一段是:“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 《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 《红楼梦简论》 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 《红楼梦》 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第二段是:“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 《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p262)
针对这则不足300字的“编者按”,毛泽东在批阅时写下了4处严厉的批语。第一个批语是“不过是小人物”,是针对“编者按”中“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而写的。第二个批语是“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是针对“编者按”中“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 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而写的,并在“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第三个批语是“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是针对“编者按”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而写的。第四个批语是“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是针对“编者按”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 《红楼梦》 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以及“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而写的,并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
《文艺报》 被批判的命运由此注定!
二、毛泽东一度没有注意到这则“编者按”
问题在于,上述批语具体写于什么时间呢?一般的叙述是这样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28日闭幕后,毛泽东也相对有了处理其他事情的时间。他利用料理军国大事的余暇,又耐心地将 《文艺报》 转载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和 《光明日报》 新发表的 《评 〈红楼梦研究〉》 及‘编者按仔细读了一遍,并在上面加了不少批注。……10月16日,毛泽东奋笔写下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并将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 〈红楼梦研究〉》 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正式发出了他要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先声。”(孙玉明,《红学: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p77—81)这一叙述大体是正确的,但一个可商榷的地方在于: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中仅揭出《文艺报》 的罪状是,两个“小人物”“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判俞平伯,被置之不理”,而没有提及《文艺报》“编者按”的“问题”。
新近出版的 《毛泽东年谱》 进行了如下解释,该书第二卷1954年“10月16日”条载:“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致信各同志。……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和 《评〈红楼梦研究〉》 两篇文章。对 《文艺报》 转载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毛泽东年谱 (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p297—298)由此而言,《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中所言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经毛泽东批阅过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 《评 〈红楼梦研究〉》,因而《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中不必重复提及这则“编者按”的问题。
这一记载的问题在于,如果毛泽东批下去的是经他批注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应该即刻做出反应,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举措。据冯雪峰说:“主席指示下达后,作协党组是很快开过一次会的……会是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的。……对于我写的已经发表的 《文艺报》 编者按语的严重错误,在这次会上(以至 《人民日报》 发表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之前),我也确实没有听到过什么人提到过 (我是指作协党组和周扬等),我自己更没有意识到。……十月二十八日早晨邵荃麟打电话给我,问我看了 《人民日报》没有。我那时确实还没有看。他就叫我很快看一看,立即到作协去开会。……我记得先说话的是周扬,他说,《文艺报》编者按语,他先也没有注意,主席指出之后,这才注意到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只记得这次党组会决定了《文艺报》 和 《文学遗产》 赶快组织稿子,批判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 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时决定作协古典文学研究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和讨论。”(冯烈,方馨未,《冯雪峰外调材料 (上)》,《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如此来看,在1954年10月28日袁水拍发表 《质问〈文艺报〉 编者》 之前,毛泽东“指出”“问题”之前,周扬等人并没有“注意”到 《文艺报》 所加“编者按”有任何问题。
由此而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毛泽东在写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的10月16日还没有对 《文艺报》 所加“编者按”进行批注,否则难以解释文艺界有关负责人何以没有就此进行任何的反应。
三、“错误”或许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圣意”
如果上述推测大体不错,冯雪峰的“编者按”的“错”究竟在哪里这一看似复杂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还得从毛泽东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说起。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毛泽东虽然对两个“小人物”“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及 《人民日报》 方面以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和“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理由拒绝转载两个“小人物”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一文等情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当他得知 《文艺报》 转载此文后,“《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 一书的文章”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他还对那些“大人物”下了严重警告:“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和 《武训传》 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然而,就在毛泽东乐观地估计“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之后——大约在1954年10月26日,一个“明目张胆”的、“违抗圣意”的“编者按”进入到了他的视线。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的另一处批注中得到印证。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 《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一文。文中说:“我在处理李、蓝文章的问题上,第一个错误是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表现了我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第二个错误,更严重的,是我贬低了他们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也是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冯雪峰论文集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P265) 不过,毛泽东在读到这篇文章时并没有对冯雪峰检讨的这两个错误进行任何批注,而是在该文“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一语旁画了“点睛”作用的竖线,并批示:“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由此来看,其他的“错误”都不是“主题”,一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终于点到“问题”的实质。冯雪峰的“编者按”究竟“错”在哪里?“错”就在这里!
(选自《党史文苑》201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