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轰鸣中的诗与歌
陈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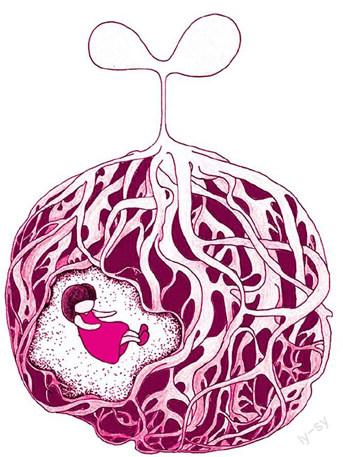
穿着深粉色吊带裙的邬霞紧张得要死,她抿着嘴唇,听着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大门马上就要打开,外面闪光灯亮个不停。
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接下来就该《我的诗篇》剧组出场了。这是由财经作家吴晓波策划的一部反映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现状的纪录电影。邬霞是其中一名写诗的女工人。
若不是电影的导演之一、诗人秦晓宇在网络上看到了她写的诗歌《吊带裙》,邬霞可能一直待在深圳市宝安区那个一点儿也不闪亮的世界里。
邬霞现在要从幕后走向台前。和她一起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还有刚刚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去年去世的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据秦晓宇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
“以前也有许多写工人的电影,都很难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不是演员,没法通过表情来呈现内心,但诗歌绝对是表达内心最合适的一种方式。”秦晓宇说,“现在都在说后工业化,实际上我们的时代还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而工业化的一些弊端正在展示出来,如何面对它们是全人类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工人诗人的忽视
前短后长的裙子挂在瘦弱的身体上,这就是诗歌里写到的那件吊带裙了。那是她最喜欢的一条,也是衣柜里最贵的一条,花了70元从地摊上买来的。除此之外,邬霞还穿上了几乎没穿过的银色高跟鞋。
红毯只有50米,她还是把脚磨破了。
平日里邬霞是不太有机会穿这些衣服的。从14岁到深圳打工开始,邬霞上班时间必须套上铁灰色、水桶样的厂服。制衣厂“加班是出了名的”。
要想写作,她必须在凌晨回到宿舍以后,拉起上铺的床帘,用几乎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
其实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窘迫。爆破工陈年喜倒是有大把的时间,他总是沿着山脉往深处行进,最长的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但是在深山里爆破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稍微不留意石头就会掉下来砸到人。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才能打开头上的矿灯,在巴掌大小的灯光照射下写诗。
大山深处没有纸,陈年喜就写在烟盒背面,有时候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等到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再一点一点誊写到网络博客里。邬霞写作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有一种薄薄的黄纸是从父亲打工的厂里找来的,“都快要透明了”。为了节约,她还要尽量把字写得小。
她的那首《吊带裙》,也写在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上:“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工厂和角落里的诗句,很容易被机器的轰鸣声吞没。读过许多中文诗歌的秦晓宇,是在一次号称没有门槛的网络华文诗歌大赛上当评委时,才意外发现还有一些“写作非常成熟,但自己又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工人诗人”。
曾经多次走进工厂,被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陪着,从这些工人身边快速走过的吴晓波,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他记得自己是一次在南京出差时报摊上买了一本《读书》杂志,才在其中看到了秦晓宇对工人诗人的介绍。
很快,他就给素不相识的秦晓宇写了一封信:“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我们似乎找到了这根线头。过往30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
本来吴晓波的建议,是让有编选中文诗经验的秦晓宇为这些工人诗人编一部诗典,但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资料的丰富程度超越了预期,他们决定再拍一部电影。
拍电影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这部电影的另一名导演吴飞跃记得,他曾拿着先期制作的一段宣传片到广州纪录片提案大会寻求支持,获得不少人的赞扬,却鲜有实际支持。
“这集中表现了大众对诗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工人诗人的态度。”吴飞跃说。
由于缺少传统渠道的支持,摄制组决定用网络众筹的方式。
“我们选择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秦晓宇说。虽然在决定进行众筹时,“很多人表达了十分悲观的意见”,但是在众筹进行的3个月里,共有1304人参与,共筹集到216819元。在影片的结尾致谢部分,1304个普通人的名字被一一打在银幕上。
2015年初,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导演们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几名工人诗人聚在一起,在北京五环外的边缘地带皮村,举办了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
秦晓宇是这场朗诵会的主持人之一。他记得在朗诵会结束时,有人告诉他,自己以前觉得诗人就是牛鬼蛇神,说着莫名其妙的疯话,但是现在“确实被这些工人诗人打动了”。
诗人杨炼也参与了那次朗诵会的主持。常居德国的他为了这场朗诵会专程来了趟北京。在朗诵会的开场,他一字一顿地说:“这些诗是活的中国,真的中国,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
在吴晓波看来,“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有点像是穷人
抵抗现实的方式
陈年喜这个初中时曾向《萌芽》杂志投稿的少年,因为家里太穷,3个兄弟都要娶媳妇盖房子,便早早放弃了学业。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写了七八百首诗,只是几乎很少投稿。
在他位于陕西商洛的家里,父亲早已瘫痪在床,母亲也衰老到没法下地干活。农家的活计由妻子操持,全家所有的收入,都靠陈年喜爆破所得。
他努力工作。有时候爆破需要进入几千米深的山洞,陈年喜弯腰前进,空气稀薄到几乎没办法呼吸,可即使如此也没能为农村的父母妻儿换来更为宽敞舒适的生活。
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一处矿山工作时,刚从巷道里出来的陈年喜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在县城医院查出来食道癌。
“当时就像身体里有炸药要炸裂一样,但是又不能炸裂。”这个跟雷管打了15年交道的汉子回忆。
当天晚上,他回去写下了诗歌《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
“首先所有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但是表达是有形式限制的,比如音乐绘画,都要有一定的基础,可是诗歌几乎是没有门槛的,零成本的,有点儿像是穷人抵抗现实的方式。”秦晓宇说。
在包装车间工作不久,邬霞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通宵加班。到了凌晨四五时,身边一起工作的小姐妹实在受不了了,一边干活一边哭喊:“妈妈呀,妈妈呀,我的妈妈睡得很香,不知道女儿在加班受苦!”可是邬霞不敢喊,妈妈就在离她不到5米远的地方加班,她怕喊出来妈妈跟着难过,只能忍着。
泪水被留在了下班后,邬霞每次流泪都会在纸上记一笔,后来算了一下,4年哭了200多次。她曾经试图自杀,一只脚已经跨到了窗外,又被母亲狠命拽回来。
在工厂的日子里,写作几乎是她休息时间的惟一消遣,她曾写道:“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
电影拍摄时,剧组让每一个工人诗人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写作?至今仍让吴飞跃印象深刻的,是煤炭工人老井的回答。
“地球上200年前没有煤矿工人,200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老井这样说。
我们就是地气本身
在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的角逐中,《我的诗篇》成了最后的赢家,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电影节计划内的两场放映票一售而空,剧组向电影节组委会提出加映申请,票又很快售罄。
其实从放映到现在,电影也受到不少质疑,复旦大学政治系一位专家发文说,“此片从未从诗学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恰是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还有媒体认为,“工人诗会”是知识分子和资本阶层对工人阶级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集体玩弄”。
吴晓波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些质疑,“邬霞显然无法回答,我也无法回答”。
在北京的放映现场,一名工人诗人看完电影激动地告诉秦晓宇,“我是真正的农民工,也写诗歌,里面有很多就是我的生活!”然后顿了一顿,这个在北京打拼十几年的农民工说,“我现在有一些困惑,我还想写诗,可是现在孩子要上学,还有很多压力,导演有没有什么建议?”
“诗歌可能真的很难给你的生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导演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说。
很快,邬霞就要重新开始找工作了。今年33岁的她不知道充斥着90后农民工的工厂还能不能接纳她。她并不准备利用电影给她带来的名气,还要努力隐藏自己写诗的历史。
陈年喜的生活甚至开始急转直下。山洞里的弯腰劳作让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一场手术之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回到矿山继续爆破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可是家里的农田显然不够养活一家老小。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怎么办。
来自新疆的工人诗人乌鸟鸟倒是继续在找工作,可是他决定做一些改变。在《我的诗篇》结尾,他对着镜头告诉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希望她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
“你为什么要加这么一段?”电影首映会结束,一位从烟台到北京来打拼的女孩儿拦住了秦晓宇问,“我爸爸是个工人,他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我把它写进作文里以后被老师批评了,说我太悲观。”
秦晓宇一时语塞。“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吧。”他想了想,一字一顿地告诉面前这个80后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