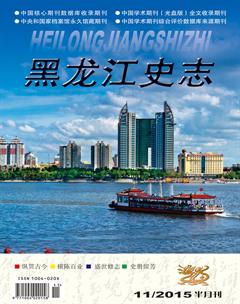羌族“泰山石敢当”造型变异成因探析
蒋楠楠
[摘 要]作为一种信仰习俗的泰山石敢当,经传播移植到羌族聚居区后,其外部造型经选择变异后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集民族性、民俗性、历史性、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等于一身的羌族“泰山石敢当”。本文在对羌族“泰山石敢当”变异后的造型进行深描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并试图揭示泰山石敢当传播移植后造型变异的成因。
[关键词]羌族;石敢当;造型变异;成因
立“泰山石敢当”的习俗是我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是我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其历史悠久,早在明清之际,习俗便已繁盛且传播广泛,不仅传入以汉族为主的内地和沿海地区,同时也传播到西南地区的羌族、彝族、侗族、土家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保存石敢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体态完好。但从外部形态上来看,羌族泰山石敢当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异。
一、泰山石敢当的基本外在形态
信仰内涵外化的外在形象对于信仰本身十分重要,学者叶涛认为,“作为一种信仰习俗的泰山石敢当,外在形态是其内在信仰内涵的外化。”石敢当最初的外化形态仅为简单的“石敢当”三字形。受其影响,至今我国的广东沿海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石敢当仍以刻有“石敢当”的三字形为主,且外部的碑制形态有桃形、人形和葫芦形等多种样式。相比之下,在北方诸多地区,石敢当外部形态受泰山文化影响,多为刻有“泰山石敢当”五字形的条状石碑。因为人们认为加上“泰山”二字,可增加石敢当镇宅、驱鬼、保平安功能的威力。
除字数不同外,在石碑的整体布局上,个别字体的书写位置也存在差异。例如,在日本和中国北京的一些地方,把“石敢当”三个字横写,有些地方则把“泰山”二字横写,“石敢当”三字竖写。另外,篆写字体也各有不同,如“泰”写成“太”,“当”写成“當”或“挡”、“擋”,在古代石敢当的这些字均为通假字。尽管不同地区的石敢当碑制上的文字布局及书写方式各有不同,但都还属于基本样式、基本形态的范畴。
二、羌族“泰山石敢当”的变异形态
泰山石敢当经传播移入羌区后,除继续保留有原泰山文化中相关元素如碑文“泰山石敢当”和石质材质外,还融入了羌族自身的原始信仰、白石信仰、羌族建筑文化、西南傩文化中吞口面具造型以及门神文化,可以说是集民族性、民俗性、历史性、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于一身,经选择变异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羌族“泰山石敢当”。
在羌族地区,泰山石敢当一般被百姓称之为“泰山石”、“吞口”、“解救石”等,多放于羌族碉房大门左侧,立于宅门、寨门、要冲之处,以保羌寨及羌族人家平安之用。其外部造型的典型特征是上端多为圆眼鼓出、怒目而视、血盘大口,獠牙突出、满脸横肉、口中衔有一宝剑等面目狰狞的吞口形象,下端多为“泰山石敢当”几个字,偶见左右刻有“日、月”或“敕令”等字样。其夸张的吞口形象实为傩文化中的面具形象,是傩文化的一种艺术表达和象征。
三、羌族“泰山石敢当”造型艺术变异成因探析
1.西南巫傩文化的象征性表达
傩是一种请神逐鬼、驱疫求吉、祈福免灾的世俗文化现象。傩文化包括对从天到人、从神到鬼、从请到逐的若干构成要素既相互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包括傩戏、傩舞、傩仪、傩祭、傩神话以及傩面具等内容。其中羌族“泰山石敢当”中,傩面具的吞口形象正是傩文化一个象征符号,成为傩文化的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傩文化里镇宅傩俗中的重要内容。
吞口,实为民间艺坛面具变异,起源于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教,分为镇宅和镇墓两种,汉代以前,多为镇墓吞口,汉代之后多为镇宅吞口,而悬挂吞口以避邪驱鬼的形式在西南各民族地区颇为兴盛。其造型历经时代不断变迁与西南门神文化、巫傩文化、图腾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为一种民间文化信仰之物。吞口口头衔一斩妖利剑,样式受汉道教影响,因为剑是道士作法的必备之物。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力无边把一切妖魔吞下的吞口造象的原型为“饕餮纹”,周星在《中国和日本石敢当》一文中就将吞口定义为门前的虎头牌,民间也就称其为吞口或饕餮的转音。饕餮纹源于商周时期,是当时青铜器上和玉器上主要的纹饰之一,实为一种贪食的恶兽。多以龙、虎、狮等头部造型夸张的兽面造型和变异的鬼脸之形的人面造型为主。
吞口乃面具文化变异,面具本身带有驱鬼性,造型夸张恐怖的吞口形象也正是由于驱鬼的需要,而在其夸张狰狞的造型、无穷威力以及艺术魅力背后,实则隐含着一种宗教力量的存在和变形,特别是饕餮纹饰眼部特征夸张直观,是神圣与神秘的暗示象征,似乎可看穿一切,让人很自然产生一种恐惧与敬畏心理。石敢当信仰习俗本身即为镇宅傩俗中的一部分,而吞口又为傩戏面具的变异物,石敢当上加吞口形象更是增强了其神力和威慑力。
在有些羌族的“泰山石敢当”,不仅面部吞口形象夸张,而且面部额头上有火纹或龙纹造型,并蓄有胡须,更加凸显其威严。当地人认为这或许与羌族崇拜火和崇拜龙的文化有关,与羌族文化及宗教信仰、图腾崇拜一脉相承,而这种一脉相承更符合羌族本民族的特点。
2.固有信仰和崇拜的表达
在原始信仰中,羌民族同其他华夏族群一样,在不断的繁衍生息中始终坚持着自己朴素的原始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羌民族崇拜和信仰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认为天、地、山、树等一切皆有各自的神灵主宰,对山与石更是有着特殊的信奉。这些被羌族赋予了灵性而加以崇拜的万事万物皆无塑像,均通过供在屋顶及角落的白石来来作为崇拜物来祈求平安、避免灾祸,从而形成的独特白石崇拜。
陶思炎认为,石敢当信仰本身即是一种原始山神信仰的物化遗存。作为灵石崇拜物的石敢当,保留了万物有灵山神信仰的印迹,担负着帮助和传递人们对神灵信奉的任务,石敢当信仰无论是石敢当的材质、文字、符号,亦或是保佑平安的功能,都带有原始质朴的气息和原始信仰的烙印。这与羌族原始信仰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不谋而合,同为原始宗教信仰,来源于灵石崇拜的石敢当信仰与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白石崇拜、释比文化存在共性,达成共识,逐渐成为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羌族民众并非一味全盘接受,而是在其中加入了具有艺术性、宗教性、审美性的吞口形象,从而建构出了一个更加符合自身需求和审美特点的羌族石敢当。
有学者认为,符、咒、文字是人与神灵通灵的语言,文字图像及夸张造型本身都是民间大众驱鬼避邪意识的直接载体,有着强大力量。羌族石敢当正是将三者结合起来,使其驱鬼避邪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羌族石敢当外形上既有适用增加神性复合原理,增加各种神力的元素,又有因审美、时代变迁和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各种元素。叶涛认为这是民间信仰神性相加原理,是乡土社会的现实主义支配民间信仰中镇物相互结合关系的原因。也正是这种民间信仰的复合构造原理才使得石敢当各种变异形象得以呈现。
四、结语
石敢当及其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传播,其功能、外部形象等开始演化成多种变异形态。这种变异是羌族人同族群在文化、信仰及习俗等方面不断碰撞、交流、认同、吸收、融合的结果。羌族“泰山石敢当”是羌文化纳入汉文化独特的一面,是汉区石敢当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其外在造型的变异也正是是对羌族对石敢当文化的跨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1]陈跃红、徐新建等.中国傩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邓廷良.羌笛悠悠: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3]冯桂香.羌族石敢当与汉族泰山石敢当的民俗内涵[J].大众商务,2009(10)
[4]顾朴光.中国面具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
[5][美]C·恩伯-M·恩伯,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6][美]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7]王镛.移植与变异——东西方艺术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
[8]尹浩英.浅析“泰山石敢当”的民俗内涵[J].科教文汇,2007(11)
[9]叶涛.泰山石敢当[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守神和祈愿[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0
[11]张■.羌族“泰山石敢当”现象的文化成因[J].民族艺术研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