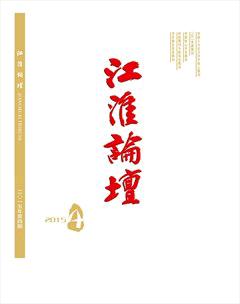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廖诗评 李若楠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廖诗评李若楠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实践情况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之间,以及普遍性和专门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都有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不同措施。国际法规则创新和国内法规则在国际法领域延伸运用,能有效避免和解决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国际争端解决;管辖权冲突;管辖条款;国际合作;既判力;未决诉讼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界定,管辖权指的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事所行使的普遍性权力,法院判决案件或者作出决定的权力,政治权力或者司法权力发生作用的地域范围,政治权力分支或司法权力分支发生作用的地域范围”[1]。为了实施国际法规则,各国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许多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处理国际法律争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核心含义与管辖权的上述界定并无太大差异,主要指的是国际争端机构解决争端的能力或者资格。具体而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否有权审查争议,是否有权指示临时措施,是否有权对裁决进行复核等,都属于管辖权的范围。在这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中,有些机制具有司法性质(如国际法院),有些具有准司法性质(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些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如常设国际仲裁院),有些则只是作出无强制约束力的建议(如各类条约监督机构)。由于国际法立法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化,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可能会对同一个或同一类案件同时行使管辖权,进而导致不同机构对相同或相似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这对国际法治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泛。从机构职能角度看,可以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分为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和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前者处理国际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争端,如国际法院;后者则处理特定领域中的法律争端,如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庭。从机构的地域性来划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划分为全球性争端解决机制和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这些不同类型机制的管辖权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冲突,以下仅择要述之。
(一)全球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相比于区域性和专门性争端解决机制,全球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的数量不多,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以下简称PCIJ)、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以下简称ICJ)和常设国际仲裁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以下简称PCA)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从历史上看,ICJ与PCA之间并没有发生管辖权冲突的情况,加上近年来通过任择性声明方式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数量增多,两者在今后发生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践情况看,司法程序与仲裁程序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绝非毫无关系,在特定情况下,争端国可能会通过国际司法程序来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在“1989年7月31日几内亚比绍与塞内加尔仲裁裁决案”中,几内亚比绍提请ICJ审查关于两国海洋划界的仲裁裁决,ICJ对此认为,只有在仲裁庭明显违背仲裁协议授权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对仲裁程序进行干预。ICJ的此种立场表明,其还是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对仲裁裁决进行干预的,这也为两种程序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不过总体来说,承认在先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一直是PCIJ和ICJ在司法实践中所奉行的重要原则,这使得全球普遍性司法程序与仲裁程序在管辖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全球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与全球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国际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简称ITLOS)之间在管辖权上可能存在的冲突。这是因为ITLOS所处理的国际海洋划界等争端同时也是ICJ的管辖范围,海洋纠纷在历史上也构成ICJ最为主要的案源之一。此外,在人权法领域,个人在人权机构或者人权条约体制中所提起的程序,也可能与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存在事实上的重合。如,针对法国再次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核试验,新西兰于1995年再次向ICJ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法国的核试验行为违法。与此同时,对法国进行核试验同样表示不满的一些个人分别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为人权理事会)和欧洲人权委员会控告法国进行核试验的行为侵犯人权,居住在进行核试验区域附近的居民也以法国的行为违反《欧洲原子能条约》为由向欧盟委员会提起控告。在这些案件中,尽管案件的原告方分别为主权国家(新西兰)和个人,但由于所要求处理的问题事实上相同,上述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实际上是有冲突的。
(三)全球普遍性争端解决机制与区域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这种情况的冲突在实践中并不多见,但确实存在。如,国际法院审理的“某些财产案”主要涉及德国与列支敦士登之间就关于列支敦士登汉斯王子私人财产所发生的纠纷。在诉讼提起之后,汉斯王子本人又以相同事项向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以下简称ECHR)提出诉讼,ECHR于2001年驳回了汉斯王子的起诉。[2]尽管两个诉讼中的当事方不尽相同,但由于两个程序涉及的是完全相同的法律问题,如果两个程序同时进行,考虑到其所适用的法律不尽相同,有可能会在判决结果上存在差异。
(四)全球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从目前的国际实践来看,这方面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人权法和经贸法领域中。如,联合国所制定的一些普遍性人权条约,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反酷刑公约》、《消除一切形式妇女歧视公约》等,均规定由相关条约实施监督机构负责处理违反条约的相关指控,这类程序所处理的事项,与历史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设的人权委员会程序具有重合之处。除此之外,该人权委员会程序在实践中也曾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程序发生竞合。如,加拿大国内的一个贸易团体曾多次向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提出动议,指控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所制定的劳工法违反国际人权法规则,委员会受理了该申请,并发布了两份报告。但在第三份报告发布之前,该贸易团体理事会的若干成员又以相同理由将情势提交给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强烈不满。[3]
而在经贸法领域中,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著名的“金字塔案”和“智利与欧共体剑鱼案”。在“金字塔案”中,南太平洋公司和南太平洋(中东)财产公司与埃及政府就埃及政府取消其在埃及的投资项目发生争端,前者将争端提交给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埃及政府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被仲裁庭驳回,仲裁庭嗣后作出了有利于前者的裁决。埃及随后在仲裁地——法国向法国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获得法院许可。与此同时,南太平洋(中东)财产公司向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中心(以下简称ICSID)提出仲裁申请,ICSID不顾之前国际商会仲裁院已经就案件作出裁决的事实,仍然对申请行使了管辖权,并作出了同样有利于公司的裁决,导致ICSID与国际商会仲裁院事实上对同一争议“一事再理”。[4]在“智利与欧共体剑鱼案”中,欧共体先将争议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请求成立专家组;智利随后以争议不具有贸易性质为由,将案件提交给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其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阻止了不同机制管辖权之间冲突的扩大化。
(五)全球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与区域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这类冲突仍然主要集中体现在贸易和人权领域,如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项下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程序与区域性人权争端解决机制程序间的冲突,等等。
由于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往往也是WTO的成员方,在出现贸易争端时,争端方就有两套解决机制来选择。在GATT时期,有两个案件被同时提交给GATT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争端解决机制,即“加拿大冷冻鲜猪肉补贴税案”和“加拿大影响软木进口措施案”。不过,GATT与NAFTA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都没有提及争端解决程序竞合的问题,在审理第二个案件时,GATT的裁决甚至还在NAFTA争端解决程序中作为证据出现。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理的“墨西哥对美国玉米糖浆出口反倾销调查案”中,美国认为墨西哥所采取的反倾销调查措施违反《反倾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玉米糖浆出口商也向NAFTA仲裁庭提出了仲裁申请。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美国提出墨西哥在NAFTA仲裁程序中的抗辩理由与在WTO中不完全一致,以此证明墨西哥没有善意履行其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而墨西哥认为这两个争端解决程序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持不同的抗辩立场是完全合理的。DSB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证据,但认为两类程序是否有区别在本案中并不重要,更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此问题进行裁决。[5]
在人权法领域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所处理的绝大部分申诉都属于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的管辖范围。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与个人来文中指控情势相同的事件已经处于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委员会不得审查该个人来文。但这项规定并没有禁止个人将在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中已经处理完毕的情势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韦恩伯格诉乌拉圭案”、“亨德里克斯诉荷兰联合王国案”等案件中,申诉人所指称的情势已经先由其他人权机构程序处理,随后又再次被提交给当时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只有在前述程序没有审查案件的实质性问题时,其才对案件进行处理。[6]
(六)区域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这类管辖权冲突往往要以该区域法治一体化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条件,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以下简称ECJ)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在管辖权上的竞合就属此种情况。例如,欧盟成员国如果制定违反欧盟劳工立法方面的法律,就有可能同时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违反,上述两个法院对此都具有管辖权。在ECJ审理的“胎儿保护协会诉格洛甘案”中,原告胎儿保护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禁止被告散发关于堕胎服务的广告。欧洲法院认为,本案涉及《欧洲人权公约》中所载明的相关权利,不宜对案件主要问题作出判决。[7]而在胎儿保护协会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的同样诉讼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禁止散发这种广告,会构成对言论表达自由不必要和不合理的限制。[8]
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原因
上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与国际法不成体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管辖事项发生重叠,这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上文中列出的很多管辖权冲突都表明了这一点。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规范的领域逐步扩大,诸如环境保护、人权的国际保护等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所无法完成的事项被纳入到国际合作规制的范围中,现代国际法开始越来越呈现出“合作法”的特征。此外,国际强行法和“对一切义务”等新型国际法规范的出现,导致了国际法规则的价值等级发生变化。[9]国际法的这种发展趋势使得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调整事项彼此交错,不同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在管辖问题上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扩散化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重要原因。冷战的结束使得建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体制性障碍得以消除,诸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国际海洋法法庭等诸多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纷纷建立,这些机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处理的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一定的重合性,这无疑增加了不同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管辖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此外,部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了获取更多的案源,提高本机制的国际影响力,往往倾向于通过对争端内容进行解释,扩大自身的管辖权,但这同时也可能带来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在管辖权上的重叠与冲突。
第三,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各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没有类似于国内法律体系形成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明确审级关系,这也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这种明确审级关系的缺位,使得在不同机构管辖权发生冲突时,无法参照既定的审级规则确定不同机构管辖权在适用上的关系。
第四,各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倾向于依附自身具有自足性的条约体制。这导致其在审理案件时经常只适用本体制内的国际条约,从而排除了其他领域或体制内国际条约的适用。如,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就规定,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简称DSB)应该根据WTO协议以及解释国际公法的一般规则处理本谅解中的争端;联合国体系中各个人权条约监督机构也主要是根据国际人权条约体系中的规则对申诉和来文进行处理。国际法多个领域中的这种自足性质,在一定程上度阻碍了不同条约规则之间的融合和借鉴,也容易引发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
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所发生的上述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相同案件的裁决结果迥异,而且会给争端当事方提供“挑选法院”的机会,选择对其较为有利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逃避国际条约或者国际习惯法规则所设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采取冲突发生前的预防措施和冲突发生后的救济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对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进行协调,对于维护国际法治有着重要意义。
(一)管辖权冲突发生前的预防措施
所谓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对管辖权进行“二次分配”,预先设定管辖权冲突时所应该参照的“争端解决机制选择条款”,以达到解决管辖权冲突的目的。具体而言,这些方法包括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专属性管辖条款以及规定争端解决机制选择条款等。除此之外,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不同争端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也是预防管辖权冲突的重要途径。
1.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专属性管辖条款
一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会在本机构基础性法律文件中规定,本机制对相关争议具有专属性管辖权,以加快争端的解决进程。这种专属性管辖权事实上也能够起到消除管辖权冲突的作用。从实践情况来看,采取这种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往往是区域性或专业性争端解决机制,由于这类机制的成员方地缘相近或者相关诉求相同,它们更倾向于在本区域或领域内解决冲突,避免争议或冲突的“外溢”。如,原《欧共体条约》第292条就规定,除本条约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之外,成员国不得将源自于本条约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争端提交给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相似的规定也见于《欧洲原子能条约》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中。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因为欧共体法的起草者们认为,将关于欧共体的运行和其基本文书的诠释提交给一个外部的司法机构将会具有反作用,因为这些机构不可能充分了解欧共体的法律,并且不能对欧共体的广泛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此外,诉诸于外部司法机构将会导致欧共体法律实施的前后矛盾,这将会减损法律体系的有效性。除了欧共体的基础法律文件之外,《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安第斯共同体条约》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中都有这类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除了区域一体化争端解决机制之外,一些专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倾向于确立本机构对争端的专属管辖权。如,《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中心公约》第26条就规定:“当事各方根据本公约规定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即应视为排除其他任何救济措施……但本公约另有规定的除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专属性管辖规则以争端方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仲裁为前提,如果争端方没有选择将争议提交ICSID,那么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也无需尊重ICSID这种专属性管辖权的规定。
在条约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属性管辖权,是预防管辖权冲突的有效方法。但是,由于各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设定本机构对争端的专属管辖权必须征得主权国家或争端当事方的同意。
2.规定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条款
相比于直接设定专属管辖权,也有一些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争端当事各方可以选择本机构作为争端解决的方法之一。这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不同的模式:
第一,直接规定争端当事方可以选择本机构作为争端解决方法之一。如《联合国宪章》第95条规定,本宪章不妨碍成员国通过既存或将来可能包括的协议,将它们之间的分歧提交其他法庭处理。但这种规定事实上赋予成员方自由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其结果是增加了管辖竞合的可能性。为了减少管辖竞合的情形,国际法院倡导成员国通过任择性管辖声明的方式接受ICJ的强制管辖权。
第二,规定本争端解决方法具有“剩余”性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2条所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一种事实上具有“剩余”性质的管辖权。根据该条的规定,作为有关该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定或以其他方式达成协议,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将这种争端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程序,该程序应代替本部分规定的程序而适用,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
第三,规定争端当事方可以选择本机构所提供的多种争端解决方法,但这些争端解决方法之间不具有替代性。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条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应有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方法,以解决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按照附件Ⅵ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按照附件Ⅶ组成的仲裁庭,按照附件Ⅷ组成的处理其中所列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争端的特别仲裁法庭。
第四,规定争端当事方可以选择本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所提供的争端解决方法,但只能在这些机构中选择一种方法解决争端。如NAFTA就规定,如果争端同时可以由GATT和NAFTA管辖,那么申请人可以自由选择管辖机构。但是,一旦选定争端解决机制,该机构就享有专属管辖权。不过,如果NAFTA的两个成员方意欲对其他成员方提出相同诉讼,两个申诉方必须先就管辖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则通常由NAFTA来行使管辖权。据此,NAFTA明确允许原告选择争端解决机制,但是限制原告选择多个争端解决机制。在NAFTA的实践中,对于成员国之间关于环境、自然资源保护以及健康安全的某些争议,一旦被申请方坚持将争议提交NAFTA,申请方就无权将争议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如果成员方已经向WTO提起争议,则必须将争议撤回。NAFTA的这种处理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在成员国选择诉讼自主权与特别领域特别保护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
3.加强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国际合作
考虑到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明确隶属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缺乏统一最高司法机关的事实,加强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国际合作在实践中可能更为可行。首先,尽管现行国际法规则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同争端解决机制应该以司法礼让作为处理管辖权竞合方法,但在不同争端解决机制实践中推广礼让原则的适用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处理已经由其他机制受理并等待审理的案件,或者对一个已经在其他程序中有待裁决或裁决终局的案件重新判决,可能会被视为不符合司法礼仪。其次,不同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应该建立定期的信息交换制度。实际的信息交换可以通过各种特别机制来进行,如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的非正式会议、各个争端解决机制的信息公开等等。实践中,联合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就达成了双方定期交换信息的协议。
(二)管辖权冲突发生之后的解决措施
一旦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已经发生,争端解决机制之间需要就争议的审理进行协调。除了强调机构之间的这种合作外,各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还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司法技术,避免管辖权的实际冲突。这些司法技术主要包括承认其他机构裁决的既判力效力,以及尊重其他机构的未决案件程序。
1.承认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裁决的既判力效力
既判力(res judicata)是源于罗马法的一个古老法律概念,指的是民事判决在实质上的确定力。该判决一旦获得确定,其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由于既判力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很多国际法学者认为其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10]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也多次确认既判力的一般法律原则地位。[11]
在“商会社团案”中,比利时希望国际常设法院判决执行对比利时公司有利的仲裁裁决,希腊并没有质疑裁决的效力,而只是声称裁决金额应当被视为外债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适用很长的偿还期)。法院认为,仲裁裁决是终局判决,不得上诉,法院无法对此进行审查。因此,法院在该案争端当事国的请求范围内,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废除部分或整个裁决结果。法院似乎倾向于认定,在没有当事方具体授权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够对当事人已经明确接受的有终局约束力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仲裁裁决因而在该案中被视为具有既判力作用。而在“西班牙王国仲裁裁决案”中,尼加拉瓜要求法院推翻50多年前的一份对洪都拉斯有利的仲裁裁决,法院认为尼加拉瓜不得质疑终局性的裁决结果,同时认为法院可以审查裁决是否无效,并因此审查了尼加拉瓜提出的两项请求,即仲裁人有越权行为以及裁决中具有本质性的过失,但这两者都被判定缺乏证据。
由上可见,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都认为,法院只是一个具有有限审查能力的法庭,而不是具有重新审查争议事实能力的上诉机构。这无疑是对在国际案件中适用既判力原则的有力支持。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发生竞合的情况下,灵活运用既判力原则,是相关机构解决管辖权冲突过程中一项有效的司法工具。
2.尊重其他机构的未决案件程序
如果说既判力处理的是已决案件在其他程序中的效力和地位问题,未决案件原则(lis pendens)处理的则是尚未中止的案件在其他程序中的地位问题。与既判力原则一样,未决案件原则也被认为具有《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是国际法中的重要渊源。
未决案件原则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运用广泛。如前所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的规定,事实上就确立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处理个人来文时将遵循未决案件原则,不过该规定并未明确禁止同一情势审结后再次向委员会提出申请。《非洲人权法院议定书》第4条也规定,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时申请非洲人权委员会与本法院处理同一请求,那么本法院将不会提供咨询意见。相类似的规定在《保护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程序规则中也都有反映。
除了人权法领域外,未决案件原则还大量运用于其他国际法领域。《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第14条就规定,争端被申请方或被告方应该将与申请方或原告方发生争议的事实通知北美环境合作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已经就相同争议启动行政或司法程序,此类程序应该中止。而在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中,一旦面临并行程序,委员会也会中止本程序,直到并行程序完成。《欧共体法院规约议定书》第47条也规定,当欧共体法院与欧洲初审法院受理的案件涉及对相同事实作出解释,或者质疑同一问题的合法性,或者案件寻求相同类型的救济措施,初审法院应该在听证后中止程序,以便欧共体法院作出判决。
与既判力原则一样,尊重未决案件程序也能起到解决管辖权冲突的作用。除此之外,上述两项一般法律原则在促进国际诉讼中的司法经济,保护被告利益使其免陷讼累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12]
四、结论
现代国际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带来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扩散化”,并造成了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固然会给国际法治建设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于相同案件或者实质上相同的案件作出不同裁决,也会削弱国际法的整体性,损害争端当事方的预期。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冲突:一方面,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恰恰反映了现代国际法蓬勃发展的事实,正是因为现代国际法在所调整事项的广度、深度等方面的不断扩大,国际法在争端解决方面的规范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国际法已经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很多解决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有些属于国际法规则创新,有些则是国内法规则在国际法领域中的延伸运用。尽管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学界都曾担心,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会引发案件判决在结果上互相矛盾或冲突,还有国内学者甚至认为现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规范存在缺陷[13],但从目前总体情况来看,这类矛盾或冲突在实践中并未频繁发生,也并没有构成影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的实质性法律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冲突的规则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1]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2009,p.920.
[2]Prince Hans-Adam II of Liechtenstein v.Germany,42527/98 ECHR 10(2001).
[3]Comm.118/1982,JB v.Canada UN GAOR,41st Session,Supplement.40,para.151.
[4]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Middle East)Ltd.v.E-gypt,3 ICSID Report 112(1985)and 3 ICSID Report 131(1988).
[5]Mexico—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of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from the US,WT/DS/132/R,para. 185.
[6]Comm.R.7/28,Weinberger v.Uruguay UN GAOR,36th Session,Supp.40,p.114-116.Comm.201/1985,Hendricks v.Netherlands UN GAOR,43rd Session,Supp.40,pp.230-235.
[7]Case C-159/90,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born Children in Ireland Ltd.v.Grogan,ECR I-4685(1991).
[8]Open Door Counseling Ltd.v.Ireland,15 ECHR 244(1992).
[9]王秀梅.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1).
[10]C.Parry et.Eds,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p. 339-341;Bin Cheng,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336;H. Lauterpacht,The Development i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p.325-326.
[11]Interpretation of Judgments No.7&8 Concerning the Case of the Factory at Chorzow,A11,PCIJ,27(1927);I.C.J.Report,1960,p.192;ICJ,Report 1999,p.31,p.39;I.C.J.Report,2001,p.318.
[12]August Reinisch,The Use and Limits of Res Judicata and Lis Pendens as Procedural Tools to Avoid Conflicting Dispute Settlement Outcomes,3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2004,p.37.
[13]吴卡,宋连斌.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的解决路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3).
(责任编辑吴兴国)
DF9
A
1001-862X(2015)04-0072-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廖诗评(1979—),广东东莞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李若楠(1991—),女,河北沧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