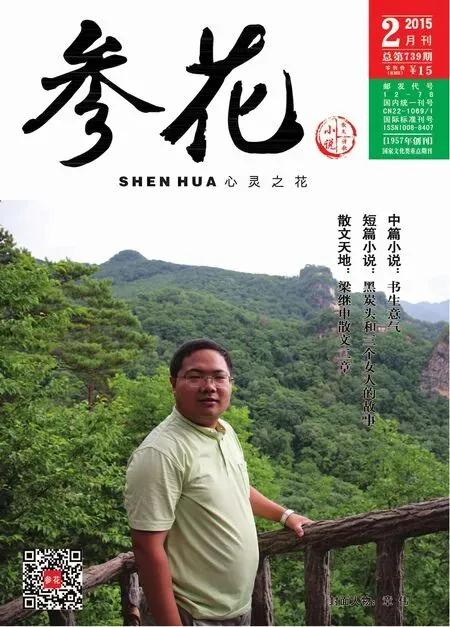黑炭头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吕丰平
黑炭头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吕丰平
2013年9月底,壶镇中心卫生院的老汪退休了,他是老卫生工作者,加上插队落户的时间共有43年工龄,曾担任过基层卫生院的院长职务,单位给他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茶话会。
老汪皮肤黝黑,人称“黑炭头”,最好杯中物,由于今日心里高兴,在家多喝了几杯,略显醉意。在同事们大谈了他的贡献和美善为人后,忽有一知情女同事叶鸣调侃相问:“老汪,据悉你年轻时艳福匪浅,能否交代一下你的风流韵事?”大家齐鼓掌。
黑炭头眼睛笑眯成一条线:“反正那些年,那点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既然大家有兴趣,就听我从头讲来。”
一、难熬的一夜
1976年5月,24岁的我结束插队落户的农村生活,被安排进三和公社卫生所当学徒。3年后我出师,不知不觉间到了“晚婚”的年龄,虽然五官没有长歪,头脑也不笨,可是由于个子偏矮,肤色如碳,找对象出现了暂时性困难。青春如火,孤阳独亢,深夜屡屡梦见美娥入怀,男人那玩意自然而然如鼎湖峰般坚挺起来,居然在内裤里画起了地图。
关心莫过于莫逆相交的朋友,县公安局的郭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张罗着给我牵线搭桥。在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他骑着侧三轮摩托急急赶到卫生所来,悄悄告诉我:“黑炭头,我在武义的‘杨家萤石矿’给你物色到了一个女工人,小你一岁,肤色比你可白多了。快,换上新衬衫,马上跟我去相亲。”言罢不由分说扒拉下我的旧汗衫,并将带来的白色“的确良衬衫”给我穿上,拽拉我上了摩托,一溜烟驶向武义。
到了萤石矿已是傍晚,郭庆带我来到女方的单身宿舍。那房间12平方米大小,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双人木沙发,外加一个小梳妆台和一张双抽屉桌,塞得满满当当的。床沿上坐着位不胖不瘦的姑娘,皮肤白皙,圆脸,柳眉,单眼皮,剪短发,外穿一件黑白相间的圆豆点图案紧身连衣裙,胸部显得特别饱满。见我们到来忙起身招呼让座,递过两把蒲草扇后,又斟满两杯凉茶,红着脸说:“这天热的。郭叔,你们还没吃晚餐吧?我先去食堂买些馒头和红烧肉回来。”言罢不经意间与我打了个对眼,她忙将眼光移开,低着头轻盈地出门而去。
郭庆和我并排坐在双人木沙发上,他一边喝着凉茶一边轻声告诉我:“姑娘叫王莉,在矿山的筛选车间工作,是办了顶替手续而招工进矿山的;她的父亲在部队时是我的老排长,转业后被安排在萤石矿工作,数年前因患重度矽肺而病退,到矿山的疗养院治疗,不幸于去年病故;她的母亲在家务农。王莉很孝顺,因为一直忙于工作和照顾父亲,所以耽误了谈恋爱的最佳时机,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姑娘。吃了晚饭后,你们单独聊聊,以增强了解,培养感情。我还要去武义县城会个朋友,半夜回来接你。”
白馒头夹红烧肉味道确实不错,那年头这就算是极其奢侈的晚餐了,我不用紫菜汤润喉就轻松地吃了三个。郭庆匆匆吃了两个馒头就借故骑摩托走了,临走前高深莫测地笑着对我眨了眨眼 。
在狭窄的空间里只留下孤男寡女,素昧平生,几乎都听到了彼此局促的呼吸声,好生尴尬。我咂吧着嘴里的馒头渣,试着轻声道谢:“真好吃。谢谢你的馒头!”
“好吃就再吃一个。”王莉笑着又递上一个夹好了红烧肉的大馒头。
我不好意思推辞,伸手接过馒头,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她的手指,似乎触了电一般,变得语无伦次:“你的手也和这馒头一般白,真好看!”
“其实馒头也不要太白,漂白过的面粉营养差,黑色好,黑色的食品营养丰富。”王莉仍旧笑着回话,脸上漾出一对酒窝。
平生第一次听到说黑色好的姑娘,我感动得由衷言表起来:“真的?可是我这黑炭头皮肤却成了心病,姑娘们看了一眼就投否决票,不然我怎会至今打着光棍呢。”
“亏你还是医生,其实人的皮肤何必计较它是白是黑,只要人们内脏好、心眼好就行。你如果在非洲生活,人家还嫌你太白了呢。”王莉依旧笑得那么甜。
“对,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无论白男人黑男人,能劳动赚钱,会疼女人育儿女就是好男人。”我飘飘然借题发挥起来。
“你能疼女人?”
“当然!”
“会育儿女?”
“还没试过。”
……
俩人畅谈时,房间门是半开着的,趋光的蚊子不断涌入,“嗡嗡”作响。因为我穿着西装短裤,所以小腿时不时被蚊子叮咬上几口,只得一边拍打蚊子,一边尽兴聊着。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到了午夜12点。我想郭庆应该回来接我了,可是门外始终没有传来摩托车的响声。
“时候不早,你该睡觉了。我还是到门外等郭庆吧。”
“门外蚊子更多,请把门关上,免得蚊子再进来。你就在房间里等吧。”
她说得在理,我也求之不得,站起关门后,回坐到木沙发上。仔细品味坐在床沿的王莉,顿觉其端庄贤淑、温柔体贴集于一身。见她也时不时举手拍打蚊子,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若不是我在,她早该放下蚊帐歇息了。于是大胆上前放下单人床上的蚊帐,诚恳地说:“夜深了,你先躲进蚊帐内歇息,我就斜躺在木沙发上等郭庆来接。不然,我宁愿到门外去等。”
也许是为了不使我到门外去受罪,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她顺从地和衣躺进了蚊帐内。我斜躺在双人木沙发上,看看手腕上的锺山牌手表,已是深夜一点钟,听听门外,依旧不闻摩托车声。唉,这该死的郭庆做媒也确实用心良苦!怪不得他临走时笑着对我眨眼呢。房间内的蚊子像一架架轰炸机,“嗡嗡”空袭,分批次轮流叮咬着我,我拍罢小腿拍脸颊,“啪啪”连声。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赏过床上的睡美人,也从没享受过与女人深夜同处一室款款交谈的温馨,皮肤上的痛痒,被内心的甜蜜掩盖着,脸上露出了美滋滋的笑容。
“你也躲到蚊帐内来吧!”突然耳畔传来一声略带羞涩的细语,而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声春雷。
人们对春天的向往与生俱来,面对鲜花的召唤,蜜蜂从没考虑过拒绝。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胆量,我上前轻轻地撩起了蚊帐,和衣上了单人床,傻傻地坐着不敢躺下,伸手搔着小腿上的痒疱,心里却默默地感谢着蚊子。
“躺下歇息吧 ,明天还要赶路呢。郭叔说话不算数,真坏!”王莉轻声吩咐,话语中充满关怀。
我早坐不住了,面对单人床,最合理的躺姿应该是分头睡,可都到了这火候,我于心不甘,既然她有没有明白叫我躺在哪一头,于是假装懵懂,和衣侧身与她同头共躺。她侧身朝里,我侧身朝外,贴背而睡。
我尽管心旌摇动,但也不可贸然造次。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俩人不知不觉就迷糊起来。也许人类本来就会在睡梦中自动调节睡姿,也许是青春的烈焰在作怪,待到一觉醒来,俩人竟面对面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那不听话的玩意自我胀挺着,全身弥漫着一股强大的一醉方休的冲动。王莉浑身发烫,眼帘微合,不作推却。
天已蒙蒙亮,正当我即将冲垮理智堤坝时,她轻轻地问我:“我接替父亲所干的工作岗位是极其高危的,矽肺发生率很高。你想好了吗?”
是啊,那年代如果要实质性体肤交欢女人,前提必须是承诺过结婚。我想好或准备好了吗?如今初次相会,显然还没有。我只得如实相告:“还没完全想好,但你确实很可爱。我回去征求一下父母意见后,再告诉你吧。”那玩意依然胀挺着,着实难熬,胜过蚊子叮咬之难熬岂止千百倍!
二、有心种花花不发
从武义的杨家萤石矿回来后,我如实向父母汇报了情况,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那时矿山劳动保护条件差,我想想王莉父亲的短命,确实也不寒而栗,于是只得浅尝辄止。但没有老婆总不是过日子的办法,于是又利用休息日跑到县公安局找郭庆喝酒闲聊,其实是想看看他还有没有鹊桥可搭。
朋友毕竟是朋友,对于上次的相亲,郭庆非但没有责怪我没主见,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晓晴,在壶镇医院药房工作。
说起这晓晴,其实是我在读卫生班时的同学,本来认识,她小我三岁,长得身材窈窕,皮肤白里透红,秀发披肩,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瓜子脸上镶嵌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双眼皮上排列着长长的睫毛,不愧班花一朵!由于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如今朋友鼎力促成,再看看古往今来,鲜花插牛粪,癞蛤蟆吃成天鹅肉的事例确也不乏,不禁喜出望外,于是振奋精神,有事没事就往湖镇医院跑,找机会与晓晴套近乎。
晚上约四人打红五(扑克),我尽量争取与她搭档,如果输了,我宁愿独自出钱,不让她破费,赢了两人有份。渐渐地她基本都认定与我搭档,就连院长邀她搭伙也委婉推辞了。夏日的某一个下午,湖镇医院组织篮球赛,我应邀参加。抢球、运球、传球,跑步、跳跃、投篮,盯人、阻截、摔倒了爬起来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底,且屡屡得分。场外观众喝彩和评论声不断:“黑炭头厉害,加油!”“黑炭头坚韧,像蚂蟥一样。”晓晴也在观看球赛,不时为我鼓掌。
球赛结束了,我汗流浃背,湿透了短裤和背心。“汪冠翼,先到我宿舍擦一下汗水,吃碗面条再打扑克吧。”在球场的出口处意外传来了晓晴的甜甜招呼声,仿佛一阵春风扑面而来,凉爽宜人,沐浴心田。“好啊,谢谢!”打一个贬义的比喻,就像大灰狼见着了小白兔,口水直流,紧跟不舍。
“我去煮面条,你先擦把汗。”进了宿舍,她打来一脸盆自来水给我,并递上一条带有香味的毛巾。我也不客气,脱下背心,对着镜子擦洗裸露的上身。看着镜子里的我,由于白天紫外线的照射,原来裸露的黑皮肤愈加黑的光亮,而背心包裹着的黑皮肤反而显得特别白净。
“汪冠翼,你身上的皮肤也并不黑嘛!”她一边煮面条,一边斜睨着我。反差,人世间的大反差,原来桃花运来了,黑的也可以变白,男女间的情事是最讲不清楚的了,只要打心眼里喜欢,是可以黑白不分的。
“真的?”我又不自信地多往镜子里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自己成了奶油小生,不觉沾沾自喜起来:“平时说我黑的人都是色盲,你才是火眼金睛,是世界上第一个说我皮肤白的人!”
“臭美!面条煮好了,吃吧。”她端上两碗葱油鸡蛋面,放到餐桌上,与我面对面地吃着。
“好吃吗?”
“好吃极了!”我头也不抬,狼吞虎咽。
“如果喜欢吃,以后不要客气,可以再来找我。”
“当然喜欢!真希望今生今世都吃你煮的面条。”我抬头正眼瞅她。
“贫嘴。要想我永远给你煮面条,我父母那一关恐怕就过不了!”
“事在人为,天下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峰。”
“别太自信。你的背心我帮你洗一下,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免得你光着膀子回家。”她放下筷子真的就帮我洗涤背心。
当晚我俩没有去打红五,继续聊了一会儿体己话后,背心也干了。她亲手给我穿上温馨的背心,她那柔滑细腻的小手不经意间在我的胸部轻轻滑过,我不免春心荡漾,不知哪来的胆量,情不自禁地搂抱着她亲了一口。她满脸绯红,轻轻将我推开:“我母亲肯定不会应允的。你先回去吧。”犹如一盆凉水将我从头泼到脚。我冷静了一下后,满怀心事地走出了她的房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父母这一关,这一关?别太自信,太自信?”
知母莫若女,后来事实证明,晓晴的担忧是对的。我托郭庆带上礼品去向他父母提亲,结果被她母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其实她母亲看不上乡卫生院的小医生,但借口是:“这人皮肤也太黑了,我们这里是亚洲,不是非洲。”更要命的是,晓晴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女子,母亲说东,她不敢往西。于是春天种下的玫瑰刚刚绽放出花蕾,还没来得及怒放,就在霜风中夭折了!郭庆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在撮合你俩前,我是征求过晓晴本人意见的,岂料阴沟里翻船?唉,你这黑碳头的媒难做!下次只能帮你去非洲寻找配偶了。”
“去非洲找婆娘?那里的人又嫌弃我太白,千里迢迢的,你更没办法弄了。我还是打光棍算了!”我像霜打的茄子。
“别灰心。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不过还没有发现。我再帮你找找。”郭庆摇了摇我肩膀后,陷入了沉思中……
三、无意插柳柳成荫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对于讨老婆的事更加不自信了,心里凉了半截,为了压抑灵魂深处的青春欲火,把时间打发在了诊治疾病、学习业务和专业进修上。经联系我去台州市医院进修,一年后回到原单位上班,由于工作小有出息,半年后被县卫生局调到白柳乡卫生院任副院长。
郭庆特地开来侧三轮摩托,将我的铺盖送到了新单位。当晚,我俩就着狗肉喝了一瓶半“二锅头”高粱烧。酒到酣处,郭庆犹豫地开口了:“黑炭头,我又物色到了一位与你般配的姑娘,只是没有先前给你介绍过的女子漂亮,但稳实勤劳,心地善良,一眼看去也极其顺眼。”
“唉,高度和低度都是酒,只要是正品,能喝就行!”我喝着老酒吐着酒话。
“此话当真?”
“高度酒喝多了就醉,醉得心痛,醉得发狂,醉醒时两眼昏花;低度酒多喝不醉,醇味绵长,渴了当茶,乐了添欢,忧时解闷,最适宜寻常百姓居家过日子。”我酒后真言毕露。
“好,有见地!”郭庆咕咚咚喝干杯中“二锅头”又道:“来,换啤酒来,每人再各自喝一瓶 。”
数天后的傍晚,郭庆给我送来一张电影票,说是湖镇大会堂今晚放映故事片《小花》,坐在你右侧的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姑娘,联络暗号:双手交叉抱胸。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穿着中山装走进大会堂,找到自己的座位后,双手抱胸坐了下来。电影开始放映了,右侧座位还是空着,等到第一次换片时,仍旧不见伊人来。我的双手抱得酸疼不自觉地松垂下来,心想:“没戏了!”不过经过前两次的历练,心情甚是平淡,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的,并不抱过高的期望。突然有了想小便的感觉,于是离座走出大会堂的边门,在围墙内的菜地边就地解决。谁料刚将尿撒出去,忽然下身那玩意有触电般的感觉,抖动了两下尿又憋了回来,继续再撒,情况如前,尿又憋了回来。我纳闷至极,忙划一根火柴看个究竟:原来大会堂的围墙残缺不全,管理人员为防止有人不买票而翻墙入内偷看电影,在围墙内的菜地边拉上了铁丝低压电网,我的尿撒到了铁丝网上。唉!人到运气背时,连撒尿也遇到了电击!赶快调整方向,总算解决了内急,然后匆匆回座继续观看影片。
第二片又开始放映了,好在刘晓庆演得精彩,恋爱故事也引人入胜,于是心情也不觉得特别纠结。正当我看得入神时,右侧空位前来了一位穿着红毛衣,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姑娘,她就座后,双手抱于胸前。我一下醒悟过来,忙恢复双手交叉抱胸的姿势。两人不约而同地顾首相看,却又都默默无言。为打破僵局,我大胆地用右肘触碰了她一下,轻声问:“你是郭庆给的票?”
“嗯。你呢?”她的回话羞涩而甜润。
“一样。”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没事,没事。”
看完电影后,我们出了大会堂,一路走,一路轻轻地聊了起来。于是知道她叫丽英,在县城的工厂做工,父亲是县电力公司的革命老干部。月光下映衬出她那圆圆的脸庞和匀称的身材,令人有敦厚而温顺的感觉。她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打了个踉跄,我忙上前抱扶住她:“路黑,小心!”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她的胸部乳房,感觉绵绵胀胀的,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向我袭来,不觉浑身臊热起来,忙不好意思地将双手移开:“请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没事。”她的声音有些轻微颤抖。
“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我厚着脸皮相问。
“就凭你今晚在大会堂久等不离开、无怨言的一份诚心,我乐意与你交朋友。”她笑着应允。
桃花运来了的时候,你躲也躲不开,而且特别顺利。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征得双方父母同意,我们定在元旦结婚。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再过十天就是大喜的日子。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郭庆匆匆赶来,告诉我一个惊天的讯息:“晓晴特地跑来告知,说是母亲转变了看法,同意她和你处朋友了,要我赶快告诉你。看我这媒人当的,搞得这头红红火火,那头又死灰复燃,这却如何是好?”言罢直搓手。
晓晴貌如天仙,情深谊长,是我有意种过的花;丽英温顺善良,敦厚诚实,是我无意插下的柳,而且已经到了铺排婚嫁仪式的关头。对于男人追求女人而言,说实在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时我也乱了分寸:“要说喜欢,我内心肯定喜欢晓晴,但说良心和道义,我不能辜负丽英。郭兄你说如何是好?”
“主意你自己拿捏,哪有做媒包生儿子的?”其实郭庆也为难。
“这样吧,我马上写一封信给丽英,就说我要求她结婚后调到湖镇轻机厂来工作,以利日后家庭生活。如果她打消以前要求我调到县城去工作的想法,同意调到我身边来,那我是决不能变卦了;如果她不同意,那我和晓晴的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提出了一个听天由命的机会主义想法。
“唉,由你便吧!你这黑炭头原来也是鬼精灵。”郭庆摇了摇头。
信发出去了,三天后收到了丽英的回信,她说愿意放弃以前的想法,同意调到湖镇来工作,因而断了我对晓晴的最后一丝念想。我特地跑到湖镇医院药房,将事情原委五味杂陈地告知了晓晴。她眼眶潮红,哽咽着说:“祝贺你。到时我给你铺喜床,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心愿,切莫推辞。”
到了举办喜事的前一天,晓晴真的来到了我的新房,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埋头拉直绣花毯、叠铺大红被、置放鸳鸯枕。她铺好了喜床后就悄然离开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这场景却使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也是我长到成人后的第一次。
第二年夏天,晓晴也接受母亲的安排,和一个陌生男子结婚了。在婚后的日子里,那男子疑心病特重,老是怀疑晓晴和院长有私情,经常吵闹。晓晴忍受不了污辱,竟然留下两封遗书,吃下一瓶安眠药,决然离开红尘,以示清白。
噩耗传来,我惊呆了!丽英却拉着我的手摇了摇,凄楚地说:“去送送她吧。”
据说她的尸体还停放在湖镇医院的手术室,我满脑子空白,骑上自行车急急赶去。我不顾一切地推开手术室的门,只见她的身体赫然停放在手术床上,几个法医正在给她作解剖,里面的工作人员忙将我推了出来。她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悲惨。我想到她以前给我铺好喜床的情景,忍不住嚎啕着究问苍天:“红颜薄命,悲喜无常。老天啊,你怎么如此残酷?!”
经历过大喜大悲后,我愈发感悟到人生苦短,真情难得!男女之间的相识、相交、相知更是特别难得的缘分。于是有一日在与郭庆同饮时,不由自主地问起了王莉姑娘的近况。郭庆告诉我:“她前年已与同矿的李某结婚,生了个儿子。因年度体检查出早期矽肺,经疗养后已经调离原工作岗位。”
“哦,矽肺是很难根治的毛病。我这里有个中药方专治矽肺,拜托你转交给她。衷心祝福她幸福平安!”
“真看不出你黑炭头还是个多情的种子。来,干杯!”郭庆举起满杯的“二锅头”,邀我一饮而尽。
“黑炭头,你都当爸爸了,还吃着碗里,想着锅里。当心蚊子叮死你!”丽英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笑着接茬打趣,接着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中药方递给了郭庆。
(责任编辑 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