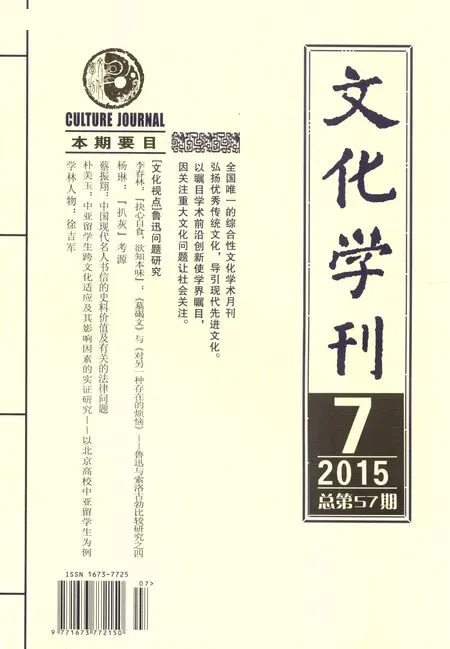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记忆的符号建构
——以浦江郑氏宗族文化再造为例
李文茂
(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1)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记忆的符号建构
——以浦江郑氏宗族文化再造为例
李文茂
(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1)
宗祠、祖陵、书院、碑亭、古宅等构成家族记忆的场所,这些场所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符号要素,时时提醒着集体成员的身份。文化记忆在民间社会力量的主持下,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断在国家和市场的攻势中抗争、妥协,在变通中寻求平衡与发展。作为城镇化推动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对待文化记忆,不仅要从历史文脉延续的角度去保护,更重要的是,应在尊重其自身发生发展逻辑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造就独具地方特色的城镇文化。
城镇化;乡愁;文化记忆;宗族
当很多地方以大拆大建的方式推进城镇化的时候,包括官员、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随着某些能够唤起人们怀旧情感场所的消失,人们的某些集体记忆也正逐步退出日常话语。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使用了“记得住乡愁”这样散文式的语句,这既是对当前城镇化存在问题的一种纠偏,也为未来城乡规划建设提供了宏观指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是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注重人文建设的重大部署。本文以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宗族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再造为例,阐述文化记忆的传递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此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宗族符号建构的想象共同体
法国历史学家Pierre Nora认为,记忆的场所包括博物馆、纪念馆、墓地、教堂、纪念碑这样的地方或实物,以及典礼、仪式、格言等这样的行动。记忆的场所是处在现代时间的特定现象。[1]德国的埃及学家Jan Assman提出“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概念。文化记忆指向的是远离当下日常生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是文化记忆在过去的时间流中固定的点,它们的范围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2]文化记忆是被再次使用的文字、图像和仪式的总合。通过对这些文字、图像和仪式的培育(cultivation),群体的自我形象得以固定和延续。
(一)宗祠祭祀
根据《郑氏祭簿》的记载,古代的郑氏宗祠主要有祭祀、集会、宴饮和议事四项功能,其中,郑氏家族的祭祀活动大大小小就有108种。如今,郑氏宗祠仍然是郑氏后裔祭拜祖先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郑氏宗祠曾一度被供销社和文化站占有,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历经磨难的宗祠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
祭祀活动在20世纪50~80年代是被政府完全禁止的。随着政府意识形态管控的变化,祭祀活动逐渐恢复,宗族成员小心地试探政府的敏感神经。在“文革”结束后没多长时间,各个分号的郑氏子孙就采取了板凳龙进祠堂的方式,即灯尾巴进入祠堂,偷偷地祭奠祖先。板凳龙是当地的民俗活动。
三献礼是郑氏族人祭祀祖先的隆重仪式,自新中国成立到1994年,已有四十多年没有举行。1994年农历二月初八,是郑氏同居始祖郑绮诞辰876周年的日子,三献礼在郑氏老人们的努力下,终于正式恢复。据调查,三献礼仪式由丰产村85岁老人郑锦宗口传,郑兴均、郑隆牛、郑新贤、郑可斌、郑可思、郑期补、郑修坚、郑文山等人反复回忆,冷水村郑文涛老人提供资料,郑定财、郑秋珪、郑健民等对照《郑氏家仪》进行核实,经祭祀人员反复演练,三献礼得以重新与世人见面。
在祭祀仪式完成后,郑隆锦赋诗一首:“赞礼都爱听,郑家古有名。定可期恢复,才能比宝灵。英勇爱第一,明朝又来临。”一方面是对郑氏辉煌的同居历史的赞美,对今天给予期待,另一方面通过这首诗来赞美郑定财个人。郑定财在古礼的恢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祭祀仪式恢复后,在郑宅能见到的祭祀活动主要有春节祭祖、立春“春祭”、正月初十祭昌四公青琏府君、二月初八大祭同居始祖冲素处士郑绮、十月十三日宋濂诞辰等。
(二)墓地追源
荷厅又称悬柏园,是在郑氏宗族同居第一祖郑绮的墓地上的建筑,位于郑宅镇义门路和玄麓路交叉的地方。处在繁华的商业街道上,荷厅有碍交通,也与商业环境不协调。从镇区的整体规划着眼,镇政府做出迁移荷厅的决定,但作为同居第一世祖郑绮的墓地,是郑氏后裔追根认祖、祭祀祖先的主要场所,迁移是有阻力的。
郑氏以文史研究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迁移同居第一世祖墓地荷亭的意见,意在使政府同意修建东明山祖陵,并给予一定的支持。“重建东明山祖陵,有百利而无一害,郑氏后裔必定会举双手赞成,从而减少迁移荷厅祖墓的阻力,也是一项造福郑宅人民之举,谨请镇委、镇政府领导审时度势,给予考虑。至于重建经费,我们除请求政府划给我们一点土地,拨给重建荷厅祖墓的资金外,其他建设资金均由我们自筹解决。”[3]
同居第五世郑德璋的坟墓被称为夹板茔①据当地传说,郑文融在为父亲郑德璋三年守墓期间,夜间总听到演奏的声音,乐器独缺夹板。于是建造了夹板状的巨壁,演奏声音停息。夹板茔是独具一格的墓地设计。,建在东明山,已经遭到破坏;郑德璋之兄郑德珪的墓碑还暂放在东明书院收藏;同居第一世祖郑绮的墓位于繁华的街道中心,而更多郑氏家族中有功德之人的坟墓已经湮没难寻。义门郑氏宗亲会理事会数次开会商讨修建东明山祖陵事宜。
宋濂在郑氏大家族的同居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仅是他作为东明书院的教师,培养了很多郑氏子弟,参与郑氏家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在他成为朝廷近臣的时候,郑氏的同居事业得到了皇帝的承认。郑氏家族也成就了宋濂,他的儒学修养离不开郑氏宗族的丰富藏书。郑氏后世子孙除了祭祀自己祖先之外,也不忘表达对这位外姓人的感激和崇敬。《郑氏祭簿》中记载着,逢十月十三日合族前往青萝山祭奠宋濂,行三献礼,称宋濂为“先师翰林承旨潛溪宋公”。
宋濂曾长期居住在青萝山,在这里著书立说。宋濂故居和墓地现已荒废,那里的土地也已归属个人。[4]由宗亲会出面,付人民币3.5万元从安山村张伯成那里购得土地468.44平方米,用来恢复宋濂及其妻贾氏的墓地。宋濂的墓碑年代久远,现在看到的碑文是重新刻上去的,“明故宋文宪公之墓——义门郑氏宗亲会,己丑年春立”。宋濂并没有葬在这里,这里的墓只是衣冠冢。贾夫人的墓是嘉庆年间郑家人重修的,现在看到的是断裂成两节被镶补起来的样子。这两块碑在“文革”的时候被抛到了青萝山上。
宋濂故居和墓地都属于青萝故址,是文物保护单位。宋濂故居现今只剩下杂草掩映中的一赌破败的墙。除此之外,宋濂故居项目还是同济大学“江南第一家”保护与开发方案中的一个子项目,包括贾夫人坟墓和郑濂衣冠墓的恢复。还没等政府行动,宗亲会已经先行建设了。
(三)同宗联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外地的浦江郑氏后裔来认亲,这需要查找宗谱和相关文献予以确认。共同的祖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祭祀仪式表达了这种血脉的联系。
2008年二月初八,在郑氏宗祠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同居始祖郑绮的活动。韩国瑞山郑氏宗亲代表团110多人,湖州双林镇郑氏宗亲130人,诸暨金鸡山10人来郑宅祭祖。二月初八和初九两日,在昌七公祠举行了“江南第一家”首届书画展览。韩国瑞山郑氏后裔的祭祖安排在二月初八,遵照他们自己的仪式,浦江郑氏三献礼祭祖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为了此次祭祖活动,宗亲会多次召开理事会,安排筹备祭祖活动。摘录2008年2月27日上午在郑氏宗祠召开的会议记录如下。据当地传说,郑文融在为父亲郑德璋三年守墓期间,夜间总听到演奏的声音,乐器独缺夹板。于是建造了夹板状的巨壁,演奏声音停息。夹板茔是独具一格的墓地设计。
讨论事项:
(1)二月初七前联系落实、悬挂、布置书画展。(2)初六前把柏树移来宗祠内、初步栽好。(3)贡品三桌:前陈、枣元、后溪,每桌100元。(4)邀请腰鼓三队(镇队、前陈、后溪),每队红包200元。上郑锣鼓班,前陈时调班。(5)郑真牛负责联系录像、摄影。(6)郑新蓝负责胸章、礼品袋。(7)郑志法邀请旅游局马局长参加。(8)标语、横幅、邀请书。(9)联谊、祭祖由宗亲会承办,秘书长主持。邀请镇领导、各村二委参加。会长讲话由文捷拟稿。(10)初七下午去塔山宾馆会见韩国宗亲。初八上午带领腰鼓锣鼓到牌坊群前迎接韩胞。参观牌坊群、白麟溪。再到祠内植树、祭祖。双方会长讲话。到昌七公祠参观书画展。到塔山中饭,联谊活动。(11)赠韩胞礼品:《江南第一家》圆谱录像、胸章。
在欢迎辞中,义门郑氏宗亲会会长表达了对韩国瑞山郑氏宗亲的亲情。“千山万水隔不断,枝枝叶叶总关情。血浓于水,亲情是永远隔不断的,也是任何感情所无法替代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我们永远心心相连,我们殷切期望兄弟之间不断增进相互往来,真诚地欢迎韩国宗亲多来祖地走走。”
在2002年签订的《归源金禧书》中,徙居到韩国瑞山的郑臣保被确定为浦江始迁一世郑淮之后的第六代,其曾祖、祖父、父、子都确立了在郑氏世系中的位置。而且,韩国瑞山郑氏与浦江郑氏一同载入《郑氏族系大典》,确定了在全世界整个郑姓世系中的位置。“虽曰贯异、国异、文异、语异,其根源侧一也,其血统侧同也,携手共进,溯以之睦、之歙、之荥阳,以至受封太始祖桓公侧,岂不大事伟业哉!是亦继往祖开来孙之时代的使命也夫!”[4]
2003年,韩国瑞山100多名郑氏后人来到郑氏宗祠祭祖。2004年,浦江郑氏40多人到韩国访亲。在续修的族谱中另立“瑞山郑氏谱图”。
浦江郑氏同居第八代的义十一公郑湜在明代洪武年间任福建布政司左参议。他的重孙郑章跟随母亲王氏避难外祖母家,定居在洪家村。义十一公祠在2003年夏重建,2004年秋竣工。作为祖地的郑宅派人参加祠堂的竣工仪式,并致祝贺词:
宗祠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它能充分体现一个家族的兴旺和发达。这次“义十一公祠”的重修竣工,更加增强宗亲们的凝聚之力。为振兴义门郑氏,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义十一公祠修建期间,洪家村郑氏邀请郑宅有知识的族人审校拟定的楹联,为祠堂内文字资料的书写提供帮助。
1983年春节,郑宅受邀派4人到义乌洪家村作客。通过座谈、访问和查阅宗谱等,证明洪家村郑氏是义十一郑湜后裔的一支。1985年春节,郑氏族人用迎灯的形式,在义十一公祠庆贺洪家郑氏归宗。①见“义十一公裔孙归宗记”,载郑可淳编《义门郑氏资料汇编》,1985。
据郑可淳的记载,浦江桃源口村派人于1983年春节到郑氏宗祠祭祖,自称是义二十六郑渊后裔。当年8月郑宅郑可淳、郑隆汼派人回访桃源口村,比对两边的宗谱,并根据之前郑定榴的考证,确认桃源口村郑氏为义二十六郑洽后裔(郑渊即郑洽)。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桃源口村已经多次派人来郑氏宗祠,请求认祖归宗,但未果。
其他联谊活动还有:浦江郑氏派人参加玠溪村、蟠溪村郑氏②这两个村的郑氏子孙是浦江郑氏始迁祖郑淮的二兄郑涚的后代。见郑余欢编《江南第一家郑氏义门源流考略》,2003。的圆谱典礼;邀请安徽遂安的郑氏宗亲参加义门郑氏续谱圆谱大会③浦江郑氏始迁祖郑淮的祖父、父亲在遂安为官。;参加义门岳阳仰科郑氏续修谱典礼;等等。
二、宗族符号在国家话语中的流变
对于郑氏同居历史,国家并没有坚持一贯的态度。“文革”在1966年开始,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为此作了准备。像其他地区一样,郑宅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在这期间,党委在郑宅公社派驻工作队。在工作队对四清运动所作的总结中,工作队认为当地人对郑氏同居历史的传扬意味着封建势力的威胁。
郑宅公社以往是一个封建势力比较严重的地方,“九世同居,千柱落地,百犬同槽,江南第一家”是这里流行的俗语,也是封建势力真实的写照。[5]
在四清运动中,与宗族有关的建筑、宗谱、画像等被大肆破坏。
短短几天时间,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被斗得一败涂地,大快人心,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据不完全统计,捣毁牌坊五个、石牌五个、大小菩萨750个,灶君200多个,香炉灵牌7 500个,各种容图500多幅,各种宗谱1 240本,龙灯20套,花轿二顶,黄色书籍7 000多册,其他迷信品为数不少,无法统计。
宗祠祭祀祖先的功能在追根问祖之风兴盛之时得到恢复。宗祠古老的建筑构件以及其承载的家族文化被作为保护的对象,宗祠是陈列和展示郑氏家族文化的博物馆。
家族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孝悌、忠义等,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对象,而并不成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在保护中被撤销。政府要做的是把家族文化请到寂静的博物馆,把它放回历史,只保留它的历史意义,而不去追随它的价值观念。[6]
政府出于特定的目的操控过去,试图做到“古为今用”。对待传统文化,政府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只是精华与糟粕的定义和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左右摇摆的。郑淂的行为可以当作批判封建主义愚忠的典型,也可以作为克尽职守的楷模,而政府却是把它作为廉政的典型。郑氏规范中有关妇女、生育的规定,可以作为旧时压迫妇女的例证,为倡导男女平等提供反面教材,然而这样的道德要求没有出现在这里。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关注郑氏文史研究的郑氏后人试图亲近这种要求,但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
1994年,中央政府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之后确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中小学生推荐阅读爱国主义教育图书,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学唱爱国主义歌曲。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尤其针对青少年。“江南第一家”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地方政府响应中央政府要求的行为。
2001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被确定为治国方略。“德”不仅指官德,更重要的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
惩治腐败是历届政府都要做的工作。而今,廉政建设被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话语当中。郑氏家族历史上为官者的事迹成为教育官员廉洁的素材。
郑氏的过去总能和当下的政治话语联系上。今天,郑氏后人仍然在郑氏宗祠祭祀远古的祖先,但已经失去集会、宴饮和议事的功能,它被政府征用,用来作为展示郑氏古老家族文化的博物馆。
三、多元社会力量在符号重构中的博弈
家族的记忆成为公共文化并不是国家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多元力量参与的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变,意识形态管控放松,全能主义国家的权力逐渐退出基层,家族逐渐从潜伏的状态走向公开。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力量借宗族的名义在增长,这种增长发生在与政府的不断妥协之中。面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和政府主流话语的变化,地方精英不断通过符号和仪式的变通与国家政治话语接洽,不断试探国家的接纳程度,为宗族活动寻找合法性的文化逻辑。[7]国家符号始终出现在宗族活动之中。
在敏感的恢复早期,宗族就主动把文史资料整理这样的活动纳入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话语之中,对祖先的祭祀也只是作为民俗活动来开展,进而,接待韩国宗亲的认祖归宗也被赋予招商引资的目的。当国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宗族将同居时代的郑氏家族称为“和谐大家庭”,认为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与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不同时期的政治话语都接纳宗族的历史,而宗族共同体也主动去靠近这些政治话语,为宗族存在寻求合法性。
民间社会从来都不是与国家针锋相对的,而是巧妙地周旋,尽管存在彼此力量的消长。如今民间社会正在壮大,国家权力继续从基层退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政府并没有一味地打倒旧传统,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是作为民族遗产来保护的。实际上,即便是在共和国短短60年的历史中,破坏文物、给传统文化贴上“封建糟粕”标签的做法,也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的。文物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得到贯彻。如果剔除那个短暂的年代,对待传统文化,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
20世纪80年代后,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话语几经变化,有的还在持续,有的已经失去重要性,郑氏宗族历史的面貌随之发生变化。宗族的历史被征用为公共文化,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文化的公共性往往为国家所垄断。
受国际思想与学术界后现代转向的影响,中国参与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部分郑氏宗族的记忆作为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其成为公共文化物品,而国家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并非为弘扬郑氏治家中的儒学思想,也不关心家族管理制度对当代的意义,国家恰恰是要把同居时代的道德要求剥离开来。国家只是要把它们辨认出来,然后请进博物馆,加以保护,在这个层面上,被保护对象的价值体现在收藏和研究上。[8]在不同时期,国家给予这些宗族历史、宗族活动和宗族思想不同的名分,封建糟粕、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向的是同一事物。除此之外,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情感的征用,使之成为公共文化,体现了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国家意志。
地方政府将郑氏家族的过去作为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并不是为了复兴、光大传统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而是以此为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惊诧”来吸引游客,以赢得旅游经济的发展。通过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也会被带动起来。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在衡量它的标尺上取得一个好成绩。而作为文化资源的郑氏宗族,借旅游开发之际,进入了公共的视野。
这些文化资源主要来源于地方精英提供的文史资料,地方精英是这些文史资料价值的虔诚的信奉者和真实的掌握者。地方政府是宗族共同体之外的人,难以有效地把丰富的宗族历史中的内涵传递给旅游者。
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诸多人的利益,在影响到居民个人利益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工作也会遭受阻力。面对这些阻力,地方政府仰仗地方精英的权威予以化解,地方精英站在本族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去协调,以族人的让步换取公共的利益。借政府征用,一方面,家族的辉煌得到承认,并广为人知;另一方面,本族人当下共同利益得到实现。村容镇貌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村民更加富庶。
通过旅游开发,更多的游客知晓“江南第一家”的伟业,即便是没有亲自到过,也可能从媒体的宣传中听说过。祖先的荣耀因此不再沉寂,这是郑氏子孙所期待的。而且,郑氏子孙并不满足于仅仅让更多的人知晓“江南第一家”,他们更希望通过名声的扩大吸引更多的学者去研究祖先的辉煌历史。
经历全能主义政府时期的民众,仍然对地方政府予以很高的期望,在政府不能如他们所想象那样行动的时候,他们批评政府无能,然而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削弱很多,他们越来越依靠地方精英的力量。
宗族的过去从私家的记忆转变为公共的文化,是国家权力、地方政府利益、民间共同体意识等多种力量互动和共谋的复杂过程。
四、文化符号重生与再建的逻辑
Schwarts(1996)把记忆作为一种有序的符号构成的统一体,共同体成员就是在文化系统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发展知识,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过去的样式——如书面叙述、图片、雕塑、动画、音乐、歌曲等,与当下的体验联系起来,来判定当下的事件。共享记忆成为思考和比较当前事件的背景。[9]
一般的郑氏家族成员对于祖先的辉煌历史的认识并不明朗。带有神秘色彩的有关祖先的传说故事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是他们日常话语的组成部分。一些地方精英注重文史的考证,对祖先的文化记忆来自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这样从历史文献中重建起来的家族共同体的过去,以仪式、图书、影视等形式呈现,成为一般的家族成员对于祖先的记忆,加强了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
文化记忆指向远离日常生活,它有固定的点,这些点的范围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这些固定的点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浦江郑氏家族文化记忆固定的点,就是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到明天顺三年(1459)间,家族中发生的事件。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郑氏的祖先创造了同居共财的家族历史。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延长至分居之后义十一公后裔创造的后同居时代。躺在历史文献中的历史事件,被整理出来,以牌坊、仪式、绘图、文本等形式被重新构造。
那是一个以儒学治家的大家族,在浙东儒士柳贯、吴莱、宋濂等的参与下,宋明理学在合族同居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家族子弟生活在忠义孝悌的儒家伦理关系之中,这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通过祭祀、训诫、诵读等方式被不断强化。[10]在历代同居实践中,郑氏家族逐渐形成成熟的家族管理制度,设置完整的家族事务管理机构。同居共食不分家,持续300余年,除了儒家伦理的贯彻和成熟的管理制度的执行外,家族产业的良好经营也是重要的缘由。
家族同居取得的成绩得到南宋、元、明三个朝代朝廷的表扬。在以儒治国的思想里,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放大。明代的法典甚至参照了郑氏的家规《郑氏规范》。
郑氏是望族,郑氏子弟接受东明书院的儒家教育,往往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被朝廷选用为官。郑氏子弟出仕为官的有170多人,有关这些人的记载散见于宗谱、地方志、诗文集等。
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构被置于当代的参考框架之内进行。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构成不可改变的记忆形象和知识库,文化记忆就根植于此,但每个当代的情境与此相关联的都不一样,有时征用,有时批判,有时保留原样,有时改造。文化记忆通过再造来实现,它的知识与现实情境相关联。今人的文化记忆虽然固着于那段无可质疑和不可更改的辉煌形象,但在现代性的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下,这些形象被置于不断地分析、保持和改造的关系之中。
通过修谱、联谊、祭祀,族人确定了在连绵不断的世系组合体中的位置,与那些显赫的祖先发生关联,他们对过去的记忆,是一个连贯的郑氏子孙的谱系,他们依此构成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文化记忆的保有让浦江郑氏获得整体感和独特感的知识库,对认同感的需求让人们去获得和传递这种知识。正是浦江郑氏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同居事迹,得到朝廷多次旌表,而不是其他人的祖先。郑氏后裔中的地方精英在思考祖先的遗产对处理家庭、邻里、村庄关系的借鉴意义,甚至作为民营企业家,也在思考家族的管理制度对于企业管理的参考价值。
五、结语
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宗祠、祖先的陵墓、书院、碑亭、古宅等构成家族记忆的场所,这些场所的存在时时提醒宗族成员的身份。在新的际遇之下,这些作为家族记忆场所的建筑得以从宗族这个共同体的视野进入到公共文化系统之中。附着于这些实物之上的家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情感也被选择性地征为公共文化。随着政府话语的变化,郑氏宗祠以不同的主题被征用。政府不仅征用已有的文化记忆的场所作为公共文化物品,而且还基于历史记述再造公共文化。这些新造的公共文化物品反过来又成为宗族新的记忆场所。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记忆的存在、传播和创造处于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宗族成员等组成的多元社会力量的挟裹之中,地方政府只有尊重并顺应文化记忆发生发展的逻辑,才能塑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城镇文化。

泥模艺术——狮子滚绣球
[1]Pierre Nora.“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de Mémoire.”[J].Representations,1989,(6):7-24.
[2]Jan Assmann,&John Czaplicka.1995.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New German Critique,1995,(65):125-133.
[3]张文德.江南第一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22.
[4]郑厚永.瑞山郑氏远世系谱序[A].郑余欢,编.江南第一家郑氏义门源流考略[M].金华: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2003.56.
[5]梁敬明.走进郑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3.
[6]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7.
[7][8]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J].社会学研究,2006,(1).
[9][10]Barry Schwartz.Memoryasa Cultural System: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5):908-927.
【责任编辑:周 丹】
G120
A
1673-7725(2015)07-0065-08
2015-05-05
李文茂(1978-),男,河北顺平人,经济师,主要从事城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