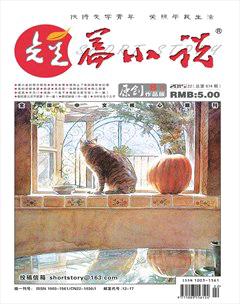等
林书羽

(一)
十年前,我还在念小学时,这个女人就坐在那里。阿强是我家茶楼的一位年轻的服务生,听他说,是他第一次接待了这个女人。
“两个茶位。”女人的语气很轻,漂浮到耳朵时,阿强觉得她是在对他耳语,她踏上了木楼梯,阿强本想叫楼上的阿红接待的,想开口的一瞬间,又闭上了,尾随女人上了楼。很久以后,他才明白,那一瞬间,一定是她的背影把他的嘴给封住的:这是个特别的女人,我想了解她。她径直走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阿强在她脸上多停留了一秒,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强利索地拿出两套餐具,例行公事地问她:“请问要点什么茶?我们这里有普洱、铁观音……”“我要玫瑰花茶。”“抱歉,我们这里只有茉莉花。”“我这里有,你拿去冲。”“这个——”阿强在这个有些名气的茶楼做服务生也有半年了,见过不少大款,也见过不少吝啬鬼,但从没有人自带茶料的。女人从头到尾目光都不曾在他身上停留,眼神云淡风轻,似乎要把人拒之千里,阿强把两朵花抖入壶里,打了一壶开水,饶有兴致地看着花从壶底摇摇晃晃地飘起来,似乎比有根的玫瑰花更妖娆、更恣意,在水中更显丰润烂漫。
阿强生怕冲得不好,忐忑地注意着女人的表情。女人为对面的空座位倒了一杯茶,才给自己倒了一杯。五个大小不同的小月牙指甲对着一袭发旧的青色旗袍,指甲透明的白与手中的泛着微光的白瓷小茶杯相得益彰,女人用中指和大拇指捏起茶杯,中指和大拇指的手指微微泛红,她把杯子凑到颜色寡淡的唇边,略略噘起嘴,徐徐吹着茶杯上的水蒸气,阿强忽然想,要是自己是这杯子里的一朵玫瑰多好,转眼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住了。白瓷小茶杯缺了一个小角,被两片薄嘴唇含住了,女人抿了一口茶,进而喝了一口。女人的脸好像红润了一些,她是不是把这杯玫瑰的红都吸收到自己脸上了?阿强摇了摇头,好好工作,都想些什么了?
阿强把早餐车推来,对女人说:“请问,您要点些什么?”女人摇摇头,一直看着楼下。当阿强把车推一圈回来的时候,他又问了女人:“请问,您要点些什么吗?”女人说,加水。阿强加水回来时,女人把一碗水晶饺端到了自己桌上,把酒水单递给了他,他找到六元的一栏,画了一笔。女人又叫他拿了一壶白开水,仔仔细细地洗起了两套餐具,把第一个水晶饺夹到了对面的碗里。后来她又点了一笼金沙包,一碟红豆糕,一碗猪肚,第一筷子总会夹到对面的碗里。她就这么坐到夕阳西下,余晖照到她的身上,她才离去。她自己碗里的食物都会吃得很干净,而对面堆起来的食物,她动都没动,服务生问她要不要打包,她摇了摇头。
第二个星期一,晨光还未消散,女人又来了。“两个茶位”。她的皓腕扶在棕色的木扶手上,翡翠手镯在她的手臂与扶手之间晃动,女人轻轻提着旗袍,又小心翼翼地从木梯上楼去,径直走到上个星期一的角落边上。阿强跟在她的后面,待她入座,问:“请问要点些什么茶?有普洱、铁观音……”“我要玫瑰花。”“抱歉,我们这里只有茉莉花。”阿强想起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以后,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阿强都能看见这抹动人的绿色规矩地涂在二楼的角落上,一个人买两个茶位,一坐一天。
一个月后,这个女人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二)
中午人闲的时候,阿红指了指那个女人,神秘地跟阿强说:“你知道这个女人一直等的人是谁吗?”“不知道。”“我猜是他的情夫,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被有钱男人抛弃了,每天没什么事干,就只会想着以前的事,看她那眼神,总是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说不定就是跟那男人有过什么约定。”阿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可能是吧。”阳光谄媚似的爬到了女人的脸上,阿红又半嫌弃半讥讽地说:“你看她眼角的细纹,啧啧啧,都一把年纪了,还学别人穿旗袍。”阿强因为这句话就开始讨厌起中午猛烈的阳光,他觉得中午白晃晃的阳光就像一把手术刀,冰冷得很,把女人的年纪都切割得清清楚楚。很快,这个猜想就钻入了形形色色的耳朵中,阿强知道,阿红喜欢跟许多结伴喝早茶的女人们咬耳朵,嘴和耳朵一相接,就会滋生出无数流言。
“估计是她的男人喜欢这套旗袍,不然这年头,还有谁穿旗袍。”
“看她连椅子都拉开了,还夹了满满的一碗菜,还挺痴情嘛。这种见不得人的关系,男人给你一笔钱,甩掉你了高兴还来不及,会回来赴什么约。”
“女人想犯贱,谁也救不了。”尖锐而细碎的笑声散在空气中,突然增加了空气的重量。
“嗡嗡嗡”,一群恼人的苍蝇趁着热闹停留在餐桌上,再把细菌散布出去,阿强蹑手蹑脚地走近它时,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人还是坐着,偶尔托托腮,居高临下地欣赏着来往的人群,任由食物渐凉,阳光渐凉。
都等了一个多月了,她的心上人还没赴约吗?她还要继续等下去?真是个痴情女子。阿强莫名地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同情心。女人离去后,阿红嫌收拾“贱货”留下的东西脏,总是推给阿威,阿强发现,阿威总是会仔细地看一遍这些没动过的一碗食物,才依依不舍地收拾。
阿强好像渐渐喜欢上了周一,每周一早晨,他会精神抖擞地站在门口,他知道,他这套工作服西装把他的英姿勃发衬托出来。他期望那个略带陈旧的清新身影出现,跟随她的背影上楼。重复了然于胸的几句话。偶尔他还会喃喃自语“两个茶位”,“玫瑰花茶”……
因为女人,每周一茶楼的生意竟渐渐红火起来,女人在人们的嘴里出了名。茶楼老板发现了这个玄机后,总会乐呵呵地对女人说,下周一见啊!女人好像从来没听到一样,淡漠地走开了。
有一次,阿强偷偷坐在女人一直坐的地方,把头摆成跟她一样的角度,欣赏楼下的风景。着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值得看一天,一个卖簸箕炊的老妈子,一个戴着头巾边卖编织绳边看孩子的异乡女人,一个卖石榴的老大爷,还有形形色色四面八方把道路挤满的人。难道星期一会有什么不同之处?阿强决定星期一仔细观察一下,他没有发现,他坐着这个位置的时候,一直有双眼睛盯着他。
又是一个周一,还是那个位置,那个女人。有一瞬间,阿强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老去过,他一直在过同一天。他假装无意,频繁地从女人身边走过,朝楼下看了无数次,还是那个老妈子,那个异乡女人,那个老大爷,他们连吆喝的腔调都跟昨天的他们一模一样。
“这女人住的地方听说不怎么样,怎么会有钱每周都来茶楼消费?肯定是跟什么男人勾搭上了,又怀念过去的情人。”
“我看她这是故弄玄虚,专门来这种高档的地方,沏好茶,点好吃的,还把椅子拉开,吸引大老板的注意,谁坐下就是谁的女人了。哼,也不想想,男人怎么会喜欢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幸好我们家死鬼从来不来茶楼,以后我们也要常来,好第一时间发现。”
炎热的夏季阳光很刺眼,把乌黑的苍蝇照得格外明显,这群女人看到苍蝇就尖叫起来,“你们的卫生是怎么搞的?苍蝇到处都是。”阿强赔着笑脸说,对不起,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消灭它们的。
阿强看见有一只苍蝇飞到了女人的面前,女人却无动于衷,他用手挥了挥,差点把女人的茶杯碰倒,千钧一发之际,女人及时扶住了茶杯,两只手碰到了一起,阿强感到一段温热的丝绸滑过自己手背,女人的手真光滑,似乎从来没有干过粗活。难道真如外界所说,她是被人抛弃了?阿强感觉自己似乎跟女人亲近了不少,尽管女人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
“听别人说,那女人出身地主,我猜也是,根据我这么多年做服装的经验,那身丝绸,绝对是上品。”
“这么说后来斗地主的时候家道中落了?看来她人老珠黄了,还是没舍得褪掉这种大小姐做派。”
“人总要接受现实嘛,这么久了还看不开,自己害自己。”
“那只手镯的成色也很不错,估计以前还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娇生惯养的,一打击,精神崩溃了。”
“看来后来嫁得也不错嘛,每星期都上茶楼,这种富贵病很难戒的。”
阿强想起了那一瞬间的丝滑质感,以前的她一定很高贵。
(三)
即使是夏季,风还是责无旁贷地把八卦带到各色各样的耳朵中。女人像往常一样刚入座,一个小报社恭候多时的记者带着录音笔面带微笑地问:“这位女士,听说您每个周一都在这里坐一天,一个人来还买了两个茶位,能告诉我您是在等谁吗?”女人的目光还是飘散在楼下,一点没有理他的意思。“噢,那你能讲讲为什么您一直穿着旗袍过来吗?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女人好像一直与这个世界不在一个时空,记者的言语在她的耳边被打散,支离破碎,落下一地尘土。她还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楼下的世界,像圣母玛利亚一般俯视着这个车水马龙的世界。记者自讨没趣,拍了一张照片,次日在报纸不起眼的豆腐块有一个女人的侧脸和“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欠你——旗袍女人的无尽等待”。
看来是有心人看到了这篇报道。下个周一,女人出现以前,有个脖子上戴着金项链的中年男人坐在了女人常空的那把椅子上,女人入座后,男人开始发起攻势:“我虽然不知道你在等谁,但是我希望从今天起,每天你的等待都不落空。”他希望女人给他一个反应,但是女人的目光还是游离于楼下,男人好奇地往楼下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他接着从包里拿出一串项链,说:“这是见面礼,每个星期一,我都会来跟你约会的。”女人还是正眼都没有看他一下,男人一直坐着,坐到中午,实在忍不住了,落荒而逃,阿强后来再也没见到那个男人,听说那个男人一出茶楼,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神经病。”
女人走后,阿强忽然记起有一张单子放在一张桌子上,回头却不见了,可能是阿威不留神收走了吧,他到潲水间找阿威,刚进门,与阿威的眼神对上,他的眼里全是惊恐,阿威手中的碗碎了,食物落了一地,阿强看了一下,那一碗,全是女人留下的!阿强大吃一惊,“阿威,你……”“阿强,你不要说出去好不好?老板会炒了我的,我自己买不起,这一碗满满的没动过,倒了觉得太浪费,太可惜,所以就——你不要告诉老板啊!”阿强心中一阵怜悯,“嗯嗯,我不会说出去的。”说完,心里却堵得慌,他多想吃那一碗食物,尽管他买得起。
“听说有个大款追她,她连看都没看一眼,于是人家再没有理过她,现在可不兴欲擒故纵的把戏了。”
“一把年纪还装什么矜持,受不了,听说还有不少男人打赌,谁追到她谁赢钱呢,真是便宜这种女人了。”
“男人也真够傻真够幼稚的,幸好她只是星期一来,要是每天都来,在这里盯着她都难受。”
“啪!”阿强狠狠地朝一只苍蝇拍去,却什么也没拍到。
一个夏天过去了,女人还穿着那件发旧的旗袍。
她会不会冷呢?阿强想着想着,一直担忧地看着女人,女人又乘着晚霞下楼了,阿强鬼使神差地跟着这个背影走着,跟着这个摇摆的青柳下了楼,走出了茶楼,老板叫了他好几声,他竟一点没听到,他只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觉得他与她是有距离的,而且必须是有距离的,他似乎没有了思维,一直走着,走过了哪条街哪条巷哪条路他一概不知,他只是走着,像一个扯线木偶,时间都停止了,声音都消失了,颜色都不见了,世界只剩下飘扬的柳枝。一不小心,这抹绿色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阿强慌乱地寻找,猛然惊醒,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是一片陈旧的平房,破碎地分布,毫无美感。他渐渐想起来自己是跟着女人来到的这个地方,但此刻他却不知道女人进了哪个屋,他注意到自己还穿着笔挺的西装,自己竟出了茶楼!他心里一想:糟了!他疯狂转身离去,一激灵,意识到这个地方完全是陌生的。阿强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到处问人,终于走出了那片灰色的建筑。
“我听那个卖元宝的大伯说,那个女人买了很多呢,估计是她要等的人过世了。”
“那是不是她每星期一都跟这个人的灵魂约会?看她灵魂出窍的样子,很像呢!”
“这么说那碗吃的和那杯茶是给那个死去的人的?”
“真晦气,下次别来了,要是让那个鬼知道我们在说她,来找我们就糟了。”
阿强感到背脊凉飕飕的,想起了那片废墟般的平房。秋天了,苍蝇都少了,阿强很想弄出些声响,提醒自己不是做梦。
茶楼周一的生意忽然急剧下降,老板干着急,后来一打听,原来是这些少奶奶们嫌这个女人晦气,都不敢来了,连嘴上也忌讳不少,伴随着秋天的到来,谣言的温度似乎也下降了。
老板发愁了,那怎么行?因为一个人整天的生意都黄了,老板吩咐阿强,女人要是再过来,就不要让她进茶楼,说今天盘算,不待客。阿强心里很难过,却笑着对老板点点头。女人果然来了,“对不起,我们——今天盘算,不待客。“阿强面露难色。女人微微一笑,她就转身离开了。这是阿强第一次见到她笑,也是最后一次。从此,阿强再也没见到那个女人了。
(四)
阿强下班回家,途中经过了一家花茶店,平时他是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但他忽然想尝一尝玫瑰花茶的味道,进店里买了一点,冲了一下,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喝。
我问他,你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长得……像白开水一样,即使我仔仔细细看过她的眼睛、鼻子、嘴巴,但我还是一转眼,还是想不出她长什么样。”
半年后,干了三年的阿威辞职了。阿强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茶楼,名字叫“等”,老板就是那个女人。他曾去过那个茶楼,女人还是穿着绿旗袍,在二楼看着一楼的世界,而她的对面,坐着的竟然是阿威。有人问她,你是不是等到了要等的人。还有人问她,你是不是还在等?她都只是重复着上一个季节、上一年抑或是上辈子的表情。
问的人多了,她就叫人在店里挂了一句话,等,没有终结也不是循环,只是一个圈套。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