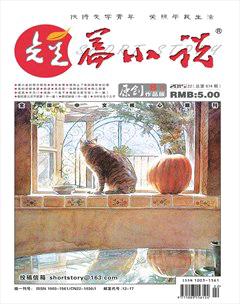脸谱
陈柳金


小雅
醒来已是九点,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像慵懒的猫摔到沙发上。啪嗒点着火,她诡秘地看着摄像头,慢悠悠地吐出一个个烟圈,愈飘愈大,终于散乱成一片烟雾。她就是要让这个别墅成为云山雾海,叫老杜找不着人。每次他飙车离开时,她心里就蹿起一股无名之火,噌地燃着了香烟,一圈一圈地吞云吐雾。有一阵子,她觉得自己就是这烟盒里的烟,老杜想抽的时候便抽出一支来,直至抽完一盒,把空盒子扔在这别墅里。烟盒是烟的别墅,而她,是别墅里的一支烟。什么时候开始收藏起空烟盒的?大概有两年了吧。
这烟盒的空、别墅的空和心里的空一起稀释着本就稀薄的空气,连呼吸都是急促的。她不敢走出去太远,也不敢走出去太久,这是老杜的限定。要是违背了,像他这种敢以三百公里时速飙车的人不知会怎样处置她。摄像头像宫廷里的锦衣卫,以鹰隼的眼睛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她成了透明的宫女,随时接受老杜的检阅。
老杜是不是从古代宫廷里转世的?他收藏的宫廷仕女图,听说有上百幅了,全是那些忧郁、沉思、凝神的,脸呈笑意的一概不收。就连找回来的她,也是一脸的忧思,仿佛是从仕女图里走下来的,他说他就是要找这种类型的冷美人。正如他脸上的表情,一天到晚的肃穆,好像在他的表情谱系里压根就没有微笑的概念。但仍掩盖不了他身上的气场,宛若书香墨韵萦绕着他,走到哪里都有一股子儒雅气,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里蹦出的都是专业的书画评析。他的生意就是这样旺起来的,已有些年头了。他做的是书画交易,在广州开了个艺术馆,但这两年书画市场受到了反腐潮的影响,官员藏画一下子锐减,交易量小了很多,他便更卖力地开画展啦,找藏家啦,跑全国各地参加书画交易会、拍卖会啦,简直比日理万机的皇上还忙。一月两月才能抽个时间开着跑车飙回三百公里远的县城,用男人的温暖排遣她后宫式的寂寞。
到底还是放不下心,这么漂亮的人,这么奢华的别墅,换了谁也一样。一次温存之后,老杜用一贯轻缓的口气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装上摄像头吧!貌似商量,其实是抛出决定。她没接话,她能说什么呢?于是就装上了。房前屋后,楼上楼下,客厅寝室,差点连洗手间也装了。后来老杜也许考虑到有悖于他书画商的身份和儒雅吧,便放过了。但他不轻不重地对女人说,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在手机上看到屋里的情况。女人当然能掂出这话的分量,没开口,只轻微地扯了扯嘴角,毕竟她的生活费、化妆品费、汽油费等一应费用都是从他口袋里飞来的。
只逗留了两天,一个电话又把老杜催走了。他是在凌晨五点离开的,上车时在脸上戴一只黑白相间的脸谱,保时捷911发出一阵轰鸣,门前凤凰树上的鸟四处窜飞,红彤彤的花瓣簌簌飘落,好像在以惊恐状欢送一个神秘之人。而树下,停着女人的白色宝马。
女人的愠怒终究架不住沉重的眼皮,转了个侧又熟睡过去。她是被微信提示音吵醒的,从枕头下摸出iphone6。是一张图片,广州的早茶餐厅永远人头攒动,餐桌上摆着虾饺、蛋挞、烤肠、酥炸鱿鱼须和两杯咖啡。跟他一起喝早茶的,也许又是一个美眉。老杜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但身边从来不缺女人。她从心里诅咒起他来,喝水呛死,吃饭噎死,走路摔死,开车撞死。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七点,便拉上被子蒙住头。她不想让老杜和另外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在广州的茶餐厅边喝早茶边欣赏她的睡姿。
再次醒来时,眼睛对上了房间里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她感到自己全身都是赤裸的,被老杜剥得一丝不挂扔在了冰冷的后宫。她连睡裙也懒得换,踱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抽起了烟,一个个烟圈飘向客厅天花板下的摄像头,很解恨,仿佛是哪吒的乾坤圈,在抗议老杜的旨意。眼睛落在了壁挂电视旁边的水族箱,一尾金龙鱼正孤单地摆着尾巴。她觉得自己就是水族箱里的鱼,透明的玻璃永远阻隔不了盯梢的眼睛。无所谓了,把身子都交给了他,还有什么不能屈服的呢?什么隐私权,什么私人空间,全都拉倒吧,像我这种女人,连最隐私的地方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就算穿得再严实也是透明的。
把早餐省略了,她多年来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用烟对付过去,简洁,倒是嘴唇干干的。走向水族箱旁的饮水机,一按,下了小半杯水就停了,倒立的桶已经空置,便给水店打了个电话。
大概等了十五分钟吧,期间她把那半杯水分几次喝干了,又等了十五分钟,一辆电动三轮车出现在门口,女人心里有一丝不快。门铃叮咚响起,好一会儿女人才从沙发上直起身,这才意识到米黄色的睡裙太稀薄,她的透明能给老杜看,老杜却不允许给他以外的男人看。想去换衣服,门铃却又急促地响了起来,送水员已看到了她的身影,她这时闪开显然是不对的时间,便索性拉开门,重又坐回去,把身子埋在沙发里。这样,透明的成分才不会过大。
一个新面孔,一脸的微笑。肩上扛着一桶水,还把身子躬了躬,说,您好,让您久等了,我是新来的大娄!
女人被他脸上的阳光照亮了,按捺着的火气顷刻消弭,却依然忧郁着脸,没回答。这是她一贯的姿态,她不想因为一位陌生男人而有所改变。
客厅大,摆设又多,这位自称大娄的送水员在烟草味里四处巡睃饮水机的位置,站着久久没动。女人只得开腔,喏,鱼缸右边!
大娄终于看到了那个硕大的鱼缸,要不是女人提醒,他还真没看着饮水机。因为从他站着的位置看去,饮水机刚好被一株茂盛的巴西木挡住了。他朝前走去,拿下空桶,扶着桶装水倒立在饮水机上。刚想挪步,眼睛却被墙上的脸谱吸引住了,红蓝赤紫,喜怒哀乐。大娄只大概地知道是戏剧里的传统脸谱,还有几个是罩在眼睛上的新款面具。
大娄的笑在这些复杂而神秘的表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转过身往出走,笑眼对上了女人忧郁的眼神,目光迅疾地滑过她薄如蝉翼的透明,落在烟灰缸里杵着的两只浅黄烟蒂上。大娄躬了躬身,说,下次有需要请随时联系笑笑水店!
早晨的阳光穿过凤凰树照在地板砖上,折射着桶装水,客厅里流淌着粼粼的波光,驱散了笼罩在屋里的阴郁。这天的白开水居然喝出了一种新的味道。她拿起茶几上的空烟盒放到书房的木架子上,上面摆着国内外款式各异的烟盒,有北京的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湖北的红金龙、黄鹤楼,福建的七匹狼、石狮,浙江的大红鹰、利群,上海的大熊猫,湖南的芙蓉王,广东的五叶神,台湾的阿里山、520,香港的好万年、金香港,甚至美国的总督,英国的约翰王,法国的大卫杜夫,荷兰的黑魔,加拿大的淘金者……
几乎都是老杜带回来的,他满世界跑,每去一个地方,必定会买一盒当地的品牌烟当作礼物送给她。刚放上去的这盒烟,是老杜去苏州参加名家书画展带回的苏烟,烟味里总有一种婉约绵柔,仿佛还闻到了他身上残留着的江南女子的韵味。
女人说,小雅,下次老杜会给你带回什么烟呢?
大娄
笑,也许是上天留给大娄的唯一资本了。一天到晚都是笑眯眯的佛爷样,好像伤心事从来不会光顾他。即使原来上班的电子厂毫无征兆地倒闭后,他仍然一脸笑意,其实他很担心下一顿会不会端着破碗到大街上乞讨。这么危急的信号还是压不倒笑,他就这样如一只笑眯眯的流浪猫游走在大街上。幸运的是,笑笑水店老板看中了他的笑,二话不说招聘他为送水员。
那天,他给对面海龙湾别墅区的海公馆208送第一桶水。一走进那个高楼林立、绿树参天的小区就迷路了,问了好几个人,全是脸无表情,爱理不理,他像无头苍蝇兜了几大圈才找到。他惊讶于她别墅里的豪华摆设,更惊讶于她漂亮脸蛋上忧郁的表情。大娄走出门时,门前那棵树上红彤彤的花把他的笑渲染得活色生香。而树下,停着一辆白色车,车身上的花红艳灼目。大娄想,好美的婚车。拧着电子打火开关,呼呼开出老远,心里还在犯迷糊——怎么会那么忧伤,一点都不像要出阁的新娘!
回到水店,老板坐在木雕茶几旁,招着手说,来来来,大娄,喝杯观音笑,这是新上市的茶,以后你要多喝!大娄接过薄陶瓷杯,觉得这名字忒好听。轻吹一口气,青绿色的茶面皱起圈圈涟漪,如大娄的笑,随阳光投射在码成墙一样的桶装水上,这个水店便成了一个晶莹的水族箱,地板和白墙漾着跃动的波光。而大娄,是一条微笑的鱼。
他微笑着钻进地下室。拧亮灯,墙上的湿渍洇成一个世界地图,伸手沿湿渍轮廓画了一圈,手指蘸满湿软的墙灰。还有一些扑簌簌地落在墙根和地板相交处,一条白线在昏暗的灯光下异常刺目,如延伸的海航线。湿漉漉的地板,在灯下波光闪烁。大娄躺倒在床,感觉自己睡在海面上,成了一条自由畅泳的鱼,正往海龙湾漂去,一直漂到海公馆208,那个穿米黄色睡裙的女人依旧忧郁着脸,蜷在沙发里喷出一个个散淡的烟圈。太美了,要是笑起来,一定跟他的偶像林志玲一样美……
大娄,送水!
地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娄额头爬着笑,眉毛簇着笑,眼眸蓄着笑,鼻尖亮着笑,嘴角堆着笑,两唇溢着笑,下颚盛着笑,电动三轮车在早晨的阳光里呼呼地开向对面的海龙湾。才一天,海公馆208又叫送水了。穿过一条条忧伤的鱼,愣是不明白这些鱼住在宫殿一样的房子里,为什么还总是板着脸,好像这个世界亏欠了他们什么。他想起胖墩墩的老板娘说的话,现在的人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风不愁雨,就是成天脸上不见笑,把个城市弄得像阴曹地府。大娄,我们就喜欢你成天笑眯眯的佛爷样!这正是我们招聘你的原因,把笑送给了千家万户,还愁生意不好吗?
这样想着,他又迷路了,七拐八弯才绕到目的地。那辆白色婚车还在,大娄的笑被车身上喜人的红衬得生动有姿。不锈钢门关着,透过门棂隐隐约约看见那女人在客厅走台步、甩水袖,咿咿呀呀地传出一段哀怨的粤曲:
思飘渺、梦迢迢。空楼静悄,风寒料峭。暮暮朝朝,凭栏凝眺,但见冻云残雪阻长桥。烽火弥天鸿雁杳。愁对残山剩水,怕听管笛笙箫。两载伴我空楼唯冷月,夜夜君眠斗帐听寒刁,两地凤泊鸾飘。
大娄就那样定定地扛着桶装水站在门口听。唱曲戛然而止,换了一身乳白色连衣裙的女人打开门,大娄看到她的眼睑挂着泪痕,说,真好听!女人没回答。便径直把桶装水扛进客厅,倒立饮水机上。女人拿了个大水勺去接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接满了,走向门前的凤凰树。哗啦,水洒在树下,洇开一层浮土。
大娄说,拿这么好的水去浇树啊?
女人破例说了一整句话,梧桐栖凤凰,凤凰落梧桐。没有什么水比梧桐泉更适合凤凰树了……
仍是一丝微笑也没有,倒是起了一阵微风。旁边车身上喜人的红簌簌飘落,原来是花瓣,这婚车便被揭去了面纱。大娄心里一阵喜悦,这女人不是新娘!想着她会在这别墅里长住下去,他就有了踏实感,往回开的三轮车特别平稳。路过文具店时买了一张红纸和林志玲挂画,顺便要了几张旧报纸。
大娄半躬着腰站在水店逼仄、阴湿的地下室,要是稍微把身子挺直一点,头就碰着楼板了。此刻,他心里很潮湿,他不知道女人住在那么豪华的别墅里为什么一点都不高兴,自己哪怕躺在这负一层的地下室喘气都是顺溜的。他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心里的潮湿发酵起来,幼稚地想,女人脸上的忧郁,会不会与这阴暗地下室里的世界地图有关?顺着老板娘的话说开去,这不是把个世界弄得像阴曹地府吗?他要让世界上的人都挂满微笑,于是用几张旧报纸贴在墙上,把世界地图全盖住了,思谋着每天用红纸剪一个简洁的笑脸图形贴报纸上。轻轻剪下第一个红色笑脸,蘸了胶水粘上去。又把林志玲挂画贴在报纸旁,她明媚的笑映衬着报纸上的笑,地下室一下子有了阳光。
新的一天,老板又叫大娄给海公馆208送水。半路上,大娄掏出一个红色笑脸贴在了梧桐泉桶装水上。
门前的凤凰花如燃烧的火焰,树上的知了在使劲聒噪,把五月的气温吵上去好几度,空气里流淌着暖烘烘的湿热。女人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烟圈却在知了声里狼奔豕突般躁乱,才离开嘴便飘散开来。大娄穿过烟雾把桶装水倒立饮水机上,那个红色笑脸正微笑地看着忧伤的女人。
大娄正要转身离开时,女人忽然递过一支烟来,幽幽地说,抽支烟吧!大娄怔在那,他不抽烟,但还是踌躇着接了。女人又递过来打火机,接了,握在手里一看,却是一把龙头刀。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刀刃发着寒光,把大娄的笑照得刷白刷白。好像接了一只烫手山芋,慌乱地摆弄了几下,却找不着开关。女人把手伸过来,按了一下龙尾处的银色按钮,刀刃自动弹进了刀削里。再摁一下颌下的龙须,啪嗒一声,一团火苗腾地从龙嘴里喷出来。大娄并没有把烟凑前去,而是插在耳根处,躬着腰说,谢谢您的烟!
掏下烟耸着鼻翼闻了闻,另一只手握着三轮车手把,车子左摇右晃,迎面走来的男人失魂大叫,要不是大娄猛然一拐,准定撞个正着。哗啦一声,却连人带车掉进了一旁的水池里,水一下子淹没了头。大娄的意识也许正是这时从美好的幻想中切换回并不美妙的现实,他的笑也就僵硬了那么几秒钟,从水里探出脑袋时又粲然恢复。幸好水不深,吃力地站直双腿撑起身,像一只微笑的水獭抖着水珠。
也顾不得擦脸,伸手握紧三轮车,猛一用劲,右脚却一软,重又掉回水里,大娄手足无措。还好,岸上的男人往物业中心打电话叫来俩保安,他们卷起裤腿下水来,一人握手把,一人托后架,三轮车终于离开水面上了岸。大娄攥住浮在水上的空桶,刚一挪动才感觉右脚酸痛,俩保安伸出手,把他拉了上去。
疼痛感已越来越清晰,他强忍着爬上车,摁着电子打火开关,居然还能跑。在十来米处忽然停了下来,爬下车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在俩保安和那男人不解的目光下,坐在池沿用两手撑住身子往池里探去,双脚好不容易触到池底,半个身体淹没在水里。用雪亮的眼睛搜寻着水面,待看到那根在水上浮荡的烟时,一把攥在手里,惊喜得双唇嗫嚅。对着烟轻吹几口气,插回耳根,忍着疼痛在保安的搀扶下上了岸。
自始至终,俩保安和那男人都是板着脸孔的。而大娄,却总是微笑着,好像掉到水里的并不是他。
老板不在,老板娘站在柜台后低头按着计算器。大娄缩起右腿跳到地下室,拧亮灯,墙壁上林志玲的笑带着一种嘲讽味儿,这才看到她两只眼睛上染了褐色的湿渍。大娄点燃打火机烘烤那支湿透的烟,火苗舔舐着烟根,白色慢慢变成焦黄,一股香味让大娄忘了右腿的疼痛。把烤干的烟捧在手里,久久不忍点燃,重新插回耳根。躺倒在床,湿衣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蜷缩着爬起来换了一身干的,穿裤子时才发现右腿脚踝异常红肿,疼痛一阵接一阵。又顺势躺下,心里说,也许睡一觉就好了!哪怕再痛,在大娄想来都是美好的。把烟掏下来放在鼻尖深呼吸,眼前全是那女人忧伤的影子。睡眼惺忪中,大娄又变成一尾鱼,微笑着游向海公馆208,他多么想把笑传递给坐在客厅朝摄像头喷烟圈的女人……
大娄是在一阵刺痛中醒来的,摸了一下脚踝,痛得叫出声来。望了一眼墙上的笑脸和林志玲,说,大娄,你不能失业!把那根烟藏在行李袋的衣服口兜里,咬着牙沿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蹦,跳出地面时,却看到老板回来了,笑着说,老板,能借我两百元吗,我想去看医生!老板和老板娘这才注意到大娄的伤腿,大娄只淡淡地说送水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事件的性质便基本等同于工伤了,老板递给他钱。
果真是脚踝崴了,上了药,用白胶布缠了好几重,医生交代他至少一个月不能乱动。心里有了一种要失业的恐惧,但他并没有把惊惶挂在脸上,还是一如既往地笑。
回到店里,老板递来一杯茶,说,来,喝杯观音笑!大娄接在手里,惶恐不定。他缩起缠着胶布的右腿,身体微微晃动。浅浅地喝了一口,完全不是味儿。
老板终于又说话了,大娄,这几天你休息一下,我来送水!
大娄一惊,忙说,老板,我行的,我还有左脚呢!
老板说,你是不是想把左脚也弄崴,我还指望你以后送水呢!
大娄算是吃了颗定心丸,浑身是劲地跳到地下室。用红纸剪了很多个笑脸,一蹦一蹦地跳出地面,往摆成墙一样的桶装水上贴。胖墩墩的老板娘说,大娄,这是干嘛?大娄用老板娘说过的话回答道,把笑送给了千家万户,还愁生意不好吗?这正吻合了笑笑水店的经营策略,老板和老板娘听着很是受用。
只要回到地下室,大娄就会掏出那支烟,虽然有些干瘪,但仍散发着香味,放在鼻翼间,深深地闻了闻,觉得地下室憋闷的空气通畅了许多。大娄当然不会忘记每天早晨往墙上的旧报纸贴一个笑脸,他焦急地渴望脚快点好起来,已有三四天没见着那个抽烟的女人了。
大娄去医院换了药,右脚已明显没那么痛了,试着踮在地上轻轻用力,居然能走上几步。这天晚上,老板不在,三轮车停在门口,而老板娘站在柜台后按着计算器。大娄说,老板娘,我去送水!老板娘也许算账太投入,没听清大娄的话。他抱起一桶梧桐泉,所有重量基本靠左腿撑着,拖沓着右腿,一高一低地靠近三轮车。待老板娘反应过来,车已开出老远。
把梧桐泉抱下来,才发现宝马车不在。客厅亮着灯,大门紧锁,大娄按了好几次门铃,最终失望地坐回三轮车上。而那桶蹲在门口的梧桐泉,在灯光下发出晶莹的光,贴在桶上的红色笑脸,像弥勒佛一样呵呵地笑。
大娄沮丧地开着三轮车往回走。高楼群车道的一边一顺溜停着很多车,一辆白色宝马在路灯下异常扎眼。他停了下来,发现前座的车窗没关,探头瞧了瞧,粤曲声中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男一女眼睛罩着面具在车上吸烟,那女的,穿着乳白色连衣裙。而那男的,鼻子里喷出一个个烟圈!
他大惊失色,赶紧开着三轮车逃离。这一晚,大娄怎么也睡不着。
老板
笑笑水店的老板万万没想到新来的大娄上班没几天,会冷不丁摔跤崴了脚,要不是大娄有一张生动的笑脸,他也许就把他炒了。笑笑水店需要有一个活广告,大娄便是最好的广告代言人。没办法,再请一个人是不现实的,老板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一户一户地开着三轮车送水。
在开水店之前,老板惊奇地发现海龙湾的人几乎都不开心,脸上乌云密布,好像阳光从来没有照耀过这个小区。他意识到,生活中客户除了需要纯净水,还需要微笑。于是,他的店取名为笑笑水店。在店门口贴出招聘启事,竟然没一个人符合条件。那天,店里来了一个小伙子,老板一眼就看中了他的笑。
大娄的笑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开始以为他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其实不是,他心态好,属于有一口饭就能维持一天,有一锅粥就能维持一个月的人。而海龙湾里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恨不能白天开着直升机上班,晚上躺在金矿里睡觉。
知了在头顶的凤凰树上吵翻了天,拉长了南方五月的闷热白昼。按了门铃,一个穿着乳白色连衣裙的女人手夹香烟拉开门,脸上满是忧伤,老板对这样的表情早已见怪不怪,但他还是脸挂笑意,尽可能笑得自然一点。倒是女人迷惑了,怎么又换了一个送水员?他的笑,远远没有上一个送水员的笑好看!她没说,这点小事犯不着说。
老板一眼就看到了饮水机的位置,走过巴西木,利索地换了水,那个红色笑脸异常灿烂。他的目光也被墙上的脸谱吸引了去,粤剧里的生、旦、文武、武生、公脚、小武、六分、拉扯,中间夹杂着几只西方狂欢节的男士和女士面具。
女人坐在皮沙发上抽烟,嘴里喷出的烟圈朝天花板飘去,一圈一圈,仿若要套住那个神秘的摄像头。老板有二十年烟龄,这在他眼里是个小儿科,便笑着说,你会用鼻子喷烟圈吗?女人愕然,好像她从来不知道有这个高招,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他,老板接了。女人又递去龙头刀打火机,老板熟练地摁了一下龙尾处,雪亮的刀刃弹进刀削里。又按一下龙须,火砰地点燃。老板深深地吸了一口,再蓄着劲用鼻子呼气,只见一个个烟圈变魔术似的徐徐而出。女人看呆了,很快又恢复常态,看了一眼客厅的摄像头,轻悠地说,改天我们一起抽烟!
老板走出门时还热血沸腾,有这么漂亮的女人约他抽烟,当然求之不得。他老婆一天到晚站在柜台后算账,边按计算器边喝蓝荷,其实来来去去也就几百元,没什么好算的。她那半堵墙一样的身体老横在那,很影响他喝茶的心情。他曾喝骂,天生的水桶腰,减肥能减成黄蜂腰?喝那蓝荷还不如喝几杯观音笑!老板娘也不是省油的灯,红腮怒目地骂道,喝喝喝,一天到晚就知道喝,没听说铁观音有农药残留?难怪一到晚上就软成了狗塌皮!
观音笑真的是铁观音的弟子吗?老板不想考究,但老板娘却真的不是他喜欢的女人。
大约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坐在木雕茶几旁喝茶的老板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女的,问他今晚有没有空。老板的心都要跳出来,是她,居然是她,他激动得语无伦次,找个借口走了出去。
女人已坐在别墅门口的宝马车上,看到他远远走来,便把车开了过去,让他坐副驾驶座。老板心里犯狐疑,抽个烟怎么还要开车去,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车绕海龙湾开了一圈后,停在了高楼群的车道旁。摁下前座的玻璃窗,把主副驾驶位调成仰卧状。女人递给他一个狂欢节男士面具,只罩住双眼,鼻子以下的部位像往常一样露着,一点都不影响抽烟。女人自己戴上一个狂欢节女士面具,拿出一包猫头鹰,用那把龙头刀打火机点燃一支。另抽出一支给他,他想伸手拿火机,被她挡住了。吧嗒一声,火苗亮了,他把嘴巴凑前来,深吸了一口,鼻孔喷出肆意的烟圈。两个猩红的烟头在夜色里闪闪烁烁,女人手里总握着那把龙头刀打火机,刀刃在路灯和烟头下发出鬼魅的光。
两人就这样仰卧着抽,一个用嘴巴喷烟圈,一个用鼻孔喷烟圈。车载音响飘出红线女哀伤悱恻的粤曲《香君守楼》——
望断盈盈秋水,瘦损婀娜宫腰。夜夜枕边红泪泛春潮,楼门紧闭不许风情扰,待等候郎归日,再度花朝,怎奈马阮差人似狼嗥虎啸,欺我烟花弱女,欺我烟花弱女,薄命飘摇……
好像眼前秋水迷茫,寒烟渺渺,为这夜色徒添了几分萧瑟。
男的问,为什么要到车上抽烟,别墅里不是更好吗?
女的说,我喜欢外面的夜色,这样可以无拘无束。
男的问,你的男人呢,怎么不跟你一起抽?
女的说,他满世界跑,踪迹无常,却老是用眼睛盯着我!
男的问,那在别墅和在车上抽烟不是一样吗?
女的说,只有在车上的这半小时才是自由的,我可以不在他的视线里。别墅里的摄像头让我感到恐惧。
男的说,你恨他!
女的说,我抽的烟,都是他送的,这猫头鹰,是他从越南带回来的。我抽烟,还收藏烟盒,你说我恨他吗?
女的问,那个叫大娄的送水员怎么没来?
男的说,脚崴了,等伤好了后,还是他来送。
女的说,那就好!
……
抽完一支,男的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拿打火机时摸了一下女人娇嫩的手,再凑前来,大着胆子往她胸前摸去。女人用龙头刀挡住了,说,别乱来,这刀是不长眼睛的!锋利的刀刃使男人不得不老实,女人啪嗒点着火,男的用力吸了一口,嘴巴憋了好长时间,烟圈才从鼻孔里喷出来。女人又说,别瞎想,就这样在夜色里吸烟,多好!
男人的烟吸得七零八落,一点章法都没有。他看着戴面具的女人,左手夹着烟,右手攥着龙头刀。烟圈正从她嘴巴里悠闲地喷出,往窗外飘得老远。
这时,男人从后视镜看到一辆三轮车远远开来,在车前突然停住了,一看,是大娄!他脸色大变,赶紧把憋在嘴巴的烟从鼻孔里喷出,要是呛着,一咳嗽就被他听出来了。他把戴着面具的脸转向一旁,幸好大娄很快就离开了,这家伙,腿还没恢复就跑出来送水。
女人其实也认出了大娄,说实话,她打心眼里喜欢他的笑。她加了男人的微信,说,今晚就到这吧!
老板回到店里,发现大娄和三轮车还没回来,而他的女人又站在柜台后一边喝蓝荷一边按计算器,好像水店的账永远也算不完。他问,大娄呢,去哪了?老板娘说,刚才接了几个客户电话,送水去了!从这天开始,腿还没恢复的大娄又开始送起水来。他的双腿高低不平,而脸上的笑却灿烂如常。
老杜
过了几天,老板接到女人的微信,约他一起抽烟。这一次,抽完半小时的烟后,女人递给他一张票,是本县古代仕女图展览的门票。
也就是那次,他看到了女人的男人老杜。一个近五十的人,梳着一头有点潮男的发型,却身穿一件浅黄色对襟唐装,眼睛非常有穿透力,说话中气很足。老杜在开幕式上讲话,台下是本县的父母官、书画家和应邀嘉宾,他表达了应本县文联主席之邀首次展览收藏的上百幅仕女图这层意思后,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我去过很多地方,经常在外面跑,每到一个地方都想办法淘一些字画,这上百幅仕女图就是这样收藏起来的。但每一个仕女都不是脸带笑意的,全是忧思、伤感的神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年在外,看过太多献媚和嬉笑的女人,早已厌倦了,唯独对忧伤的冷美人情有独钟,这算是我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吧!我又想,人生是一个又一个未知组成的,今天你春风得意,明天也许就成为风中的一粒微尘……
笑笑水店的老板听不进去了,一个男人怎么这么悲观,要是地球人都是忧伤的,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便移步去看画,每一个仕女的脸上真的没有一丁点笑意,全是怨女,他打心眼里排斥。话讲完了,人流涌过来,竟然连观画的每一个人都是蹙眉哀伤的。老板觉得像在开一场追悼会,空气里流淌着一股腐朽的气味,他再也呆不下去了,正想转身离开,迎面碰见了老杜和挽着他的女人。老板一阵心悸,老杜却递过来一支烟,脸无表情地说,感谢观赏!说着又递去一张名片,老板也递给他一张名片。就这样,“笑笑水店”和“忧忧艺术馆”在展厅里戏剧性地相遇了。他们各自揣上名片,不动声色地擦肩而过,到底是背道而驰的陌路人。老板啪地点燃了烟,鼻孔里喷出一个个烟圈。影影绰绰中,仿佛看到所有观展的人脸上都戴着脸谱,在与上百个仕女们说着千百年前的话。
回到店里,不浅不淡地喝着茶,手机响起微信提示音,打开一看,海公馆208女人发的两张图片,一张是一包漫天游版黄鹤楼,另一张是几个摆满了国内外款式各异烟盒的大烟架。哪怕很想跟女人抽烟,他也知道今晚不是时候,老杜也许正搂抱着属于他的女人。
老板这晚辗转反侧,老板娘几次挑逗,都被他拒绝了,她恨恨地说了句——狗塌皮!
小雅
清晨六点半,睡梦中的大娄被巨大的轰鸣声惊醒。接着,是警报器的紧张鸣笛。这个觉算是无疾而终,索性起床。一群人从店门口急急走过,一打听,才知道前面国道拐弯处出了车祸,一辆疾驰的蓝色保时捷跑车撞上了大货车。
大娄尾随着人群追上去,警灯闪烁,保时捷车头凹陷进去,而大货车侧卧在国道旁边的花圃上。好像开保时捷的男人还有一口气,一个女人嘤嘤啜泣地搂着浑身是血的他。走前一看,那女的是海公馆208的女人,而那男的,却戴着一只黑白相间的脸谱!
——他气若游丝地说,小雅,你一定很介意我在别墅里装那么多摄像头,其实只有房前屋后的摄像头在用,其他都是摆设,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家……
——他缓了缓气,又说,小雅,给我唱一段粤曲吧!女人做出一个甩水袖的动作,唱出满腔哀愁:
血痕一缕在眉梢,镜里朱霞残照。点点绯红留扇上,空有个闲情写照。添上枝叶夭夭,这桃花似我伤情,朵朵春风懒笑。这桃花如人薄命,片片流水浮漂……
——他翕张着唇,小雅,帮我把脸谱取下来……女人小心地摘下,他挤出一丝笑,说,我以前喜欢你忧伤的神情,在我离开时,还是想看看你微笑的样子……女人擦干泪,脸上居然绽放出如花的笑靥。老杜手一松,在她的微笑里走了……
大娄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叫小雅,也第一次看到她笑的表情,真的,她笑起来比林志玲还好看。他掏出女人那次给他的烟,已在衣兜里藏了好些日子,皱巴巴的,一直舍不得抽。啪嗒点燃,深吸了一口,喷出一团烟雾。早晨的太阳已在海龙湾的高楼之间升起,阳光穿过凤凰树叶,照在这片忧伤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