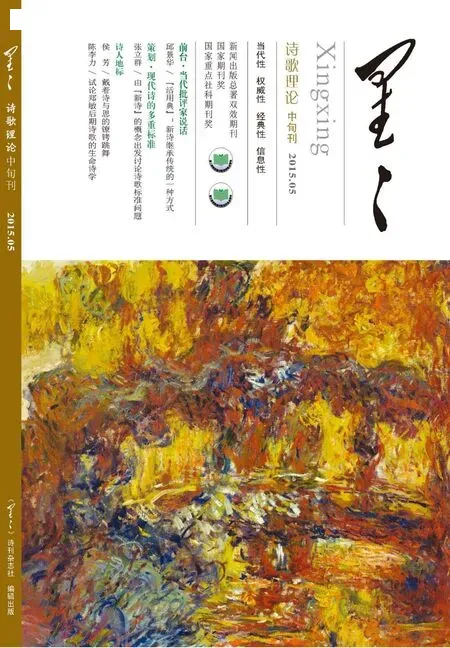宿墨诗写:关于于明诠的诗歌创作
欧阳江河
宿墨诗写:关于于明诠的诗歌创作
欧阳江河
我在认识于明诠之前,一直比较关注作为书法家的于明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搜于明诠书法的时候,搜到了他一首关于书法的诗。那首名为《点画呻吟》的诗,给我留下了非常独特的印象。于明诠先生字写得了不起,诗也写得与众不同。后来,我就向山东的朋友打听,好像正是张清华兄相告,说他诗写得还不少,算一个诗人又算一个书法家。
我觉得,像于明诠先生这样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同时又是一位将很多时间和心力花在严肃创作中的诗人,这样一种双重性质的艺术家诗人,在中国不多。或许,能在写诗和写字两方面都取得独特成就的,就他一个。我本人也是又写诗又喜欢书法,但书法于我,主要还是自然书写,是心性舒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书法列入与诗歌写作平行的创作序列之中,构成创造性意义上的对应物。于明诠现象,从大的历史格局来理解,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书法的面貌,能够找到于明诠这样的人物,用诗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当代人,这也是大家的一种幸运吧。因为找不到这样一个人的话,在书法向度上
珍藏的某种感性与知性相混合的文化元素,作为当代诗歌的独特材料、对象、主题的东西,就有可能完全不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会消失,因为当代诗歌对此茫无所知。好在于明诠将自己对诗歌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与他对书法艺术的原创性理解和高蹈实践,做了两相辉映的合并。他将历史的、当代的、生命的东西,以及他个人的一些东西,合并在一起。他是一个思者,一个观者:他睁开诗的眼睛,去观看书法镜像,观看日常生活,观看心灵世界。
因为明诠近期要出版个人诗集,我得以系统地阅读他精选出来的诗。我发现,他的写作意识和格局,深深触及对中国古文化、古诗词曲赋的转化和处理。这既是种种包容和吸取,又在写作时幻化为资源和心智的溢出。我特别注意到于明诠对京戏元素的提炼,他真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京戏迷。这样一些传统的东西,有人认为是遗老遗少的东西,他把它拿来放到一种当代的情怀和关注里面,像是施了招魂术般使之活了起来。总括而言,从诗歌写作的当代格局来看,于明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认真关注的一个原创性对象。
于明诠的书法和诗歌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为写字而写字。他的诗和书法创作,有一个对自我镜像的确认,有一个认知的确立,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当今很多写诗的人,有一个毛病,他们相互在修辞游戏中写作。所以,读者会觉得纸面上那些外在的东西是如此漂亮,但却往往经不起深究。
明诠写作后面,有一个自我的追寻确认。而且,他的自我
追寻和确认,可以通过它所投射的镜像,以及他对这些镜像的描述和吟咏,而不是他主观的表现和抒情,去感受到。他的这个自我是一个特别的,跟中国古代的文人形象和心智接通了气息的。他把自我的边界扩展到了古人那边,无论是书法的角度,还是在写诗方面。但是,他又明显具有当下感,无论是他的书法气息,还是诗歌语言。他不是从当代先锋诗歌的修辞游戏里去寻找自己的风格元素,而是寻找语言后面的气息和诗意。他的写作里有一种气息感,有一种独特的放松的节奏感。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的诗歌里有古诗、古词、古戏曲和当代诗歌、当代节奏、当代白话意象的混用。这样一种不留痕迹的、这样一种衔接和变容的、一种富于活力的混搭。其实,这里的混用,也是他在寻找,在通过镜像来确认自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张清华兄所讲的,三十来岁的他曾想确立一种无边的或者繁复的,从众多的镜像中寻找一个自我的、确切的自我边际。他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写作途径:通过写作来确立自我,把自我提高到一个认知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一个抒情。当代诗歌有一个特点,要么是抒情,要么就是反抒情、反讽。反讽啊、抒情啊,这些东西在于明诠的诗里,也淡淡的有,但他更多的是想确立一个自我的呈现方式。
要是深入梳理一下于明诠写作特征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写作里面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对话关系,一种潜对话关系。他这样的写作模式跟很多先锋诗人不大一样,在他的写作和书写里面始终有他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你感觉到他的写作,与他这人,存在一种同构的关系。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本性的东西,呈现在他写作的字里行间。比如他的对话,他常常引入当下的语
境,当下的用语,当下的话语节奏,包括口语的东西以及新闻的乱象,当下这种盛世与乱世混杂的东西,等等。他的题材也十分独特,比如他这首《望真如草》,这个既属于传统的也是当代的书法面孔:
体内长满点画线条
不肯轻易吐露心声
一笔一划
端端正正
把心事梳理的井井有条
这不是正楷
这只是从篆隶到行楷的
叙事方式之一
毛笔不癫狂
但中锋侧锋癫狂
手腕不飞动
但家事国事飞动
人们围拢过来
端着传统文化的水杯
篆书是红茶
隶书是乌龙
楷书是绿茶与青茶的混搭
一种所谓国粹就这样
越品评越肤浅
望真如草就是望一望书法的面孔
黑黑白白的倒影飘着油花
左边吻一下是轻佻
右边吻一下是滑稽
就这样,他把当代的东西引进来,但是面对的那个镜像般的对话者,显然是一个固有的中国传统形象,而不是西哲的镜像和声音。这有助于话语的直接呈现、直接成像,构成固有的对话板块和语言团块。
梳理明诠诗歌写作的独特性,会给当代诗坛带来一些启示和提醒。在这个时代大家写诗,风格越来越雷同,这真得有点讨厌。明诠他突然就出现,带着很多不一样,这真得值得关注和借鉴。他没有混迹于诗歌江湖,不在任何圈子里,也没有跟诗歌批评界发生联系。他是独立的,自在的。而他的阅读与写作,他观看和对话的对象,也就是他确立自我的镜像,是来自于我们认为当下诗人应该避之唯恐不及的古代文人、传统文人。并且,他写作的材料包含大量的古诗、古词,比如他有好几首诗是在着力处理词牌,由此形成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个语言团块,就是那种固有的东西。他处理这一切的时候,尽可能地将之还原到原生态,回归天真的释义。比如说像水调歌头,他把它分成“水调”和“歌
头”,用很现代的构词法把它分离。
谈到明诠诗歌写作的方向、对话的对象和写作的对象,我们认为过时了的、不具现代性的传统元素,甚至直接是传统诗句,他却经常使用,采取混搭的办法,改写的办法,还有潜对话的办法。这些东西影响了、规定了他写作的范围、性质、状态和语境。于明诠写作的整体语境状态,正好跟当代有些东西是相反的。当代语言狂欢里出现的戾气、语言的暴力和碎片,他没有。那戾气来自什么地方?来自我们每天谈论的东西,关注的东西,媒体意识形态所传播的恶、残暴,那种筛选过的恶。当你在谈论和关注暴戾事物的过程中,难道有一个非常优雅,非常超然物外的东西吗?不可能。那么,我再说于明诠关注的东西。他对话的源头,就在中国古代诗歌、古代文人中间,特别优雅,特别高明的东西。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华文明这么一个精细的文明,落入这个现代之恶的,撕扯、撕咬以及媒体意识形态控制的世界,好像一切都脏得要命,残暴得要命,而于明诠的诗呈现出优雅的、超然的诗意,出现淡淡的嘲讽、淡淡的批判、淡淡的忧伤所构成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状态,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于明诠的这种呈现,是从源头上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一直在担心和焦虑的,就是中国古典诗歌这么好的一个文化资源,怎么跟当代中文诗歌的创作衔接。怎么从文化资源上做一个衔接,这是一个困难的历史课题。这样的东西,被美国大诗人庞德拿去了,变成英语现代主义诗歌革命的源头;但在我们这里,却变成是不能碰的东西了,好像碰它就是没有时代感,就是在躲避当下时代直面人生血腥的东西。于明诠的写作,其实是
从对话的角度,把当代的东西带到和古人的对话深处。他呈现了这样一种心态,和庞德是不一样的。庞德更多是语言本体的角度和真正的天才的角度,用中国的古典诗歌、用中国古人的眼睛来打量英语诗歌,考虑英语诗歌写作的历史命运以及未来的去向。
回到我所说的于明诠第三个写作特点,就是他写作的源头。对话的镜像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正是那些我们认为已经死去的优美、文明的东西。明诠诗歌的语感非常90年代,也有可能是一种惯性。他的语感里面有一种识别度很高的独特语速。明诠写作不是与时俱进。当然还有一点,明诠的写作有一种感觉,就是用“宿墨”在写。用一种旧时风格在写。于明诠写作的宿墨成色,涉及细致的词义变化。种种变化,在极致处会构成措辞的墨色渐变和虚实笔触感。这一格外讲究的写作追求,与他多年书法创作中持续追求的“书法味道”是相通的,两者都带有宿墨性质。而他诗歌里出现的文本时间,他的当代感,是在某一瞬间唤起所有时代的那样一种“同时代性”。这是他对当代的定义,就是说当下只是时间的一个缩略,一个压缩,而不是时间本身的自动展开。于明诠的诗歌里,有一个时间的反过来被打开。无论是书法还是诗歌写作,他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左右腾挪。这里有时间的消逝,所以他有现代感而不是当代感,没有末日在里面。于明诠的时间感里面没有末日,就没有弥撒亚的那种无限的时间被推迟的缩略,没有终结性,没有末日审判。所谓更多的他的自我,就是在他三十多岁确立自我的过程中,那个三十多岁可能变成了他的四十多岁。这可能就是真正的中国性,舒放有度的那种空间感,不追求那种末日审判式的极端。
作为诗人,实在本身已是虚渺的一部分了。明诠写陶渊明这首诗,他重复了五棵柳树,一棵柳树、一棵柳树、一棵柳树、一棵柳树、一棵柳树,而不是一棵、两棵、三棵,这里有一种元书写性。还有《会开花的鸟儿》这首:
鸟儿从土地里长出来
长出来就向往天空
鸟儿鸟儿
就这样飞起来
鸟儿的声音
和我儿子撒尿一样自由一样透明
点点滴滴都绽放在蓝天白云里
看那潇潇洒洒的情节
让一百杆枪管
都优雅地折断
鸟儿就是这样开花
一朵一朵地开花
鸟儿开花
花开在情人的额头
花开在诗歌的腿部
从此我们的眼睛
长出鱼和水草
呵,鸟儿鸟儿
我的会开花的鸟儿
我觉得于明诠的第四个特征,是他诗作里那种接了地气的小小的禅意。而这个禅意、佛意,与他的书法也有一定的联系,是他的书写性的一个部分。你看他写的“鸟儿从土地里长出来,长出来就飞向天空”,是一种地里长出来的飞翔,是接了地气的。然后他又说“鸟儿的声音和我儿子撒尿一样自由”,这在修辞上非常现代,但又极为久远的接到他的儿子,传宗接代,递到了下一个自我。他的自我衔接,不光是跟古人,也跟儿子这样的未来意象衔接。“鸟儿的声音和我儿子撒尿一样自由,点点滴滴绽放在蓝天白云里”。非常有现代感,但是又充满禅意。他有不少有禅意的诗,像《一尾鱼和两尾鱼》:
一尾鱼
喜欢坐在书桌旁
静静地思考平面与角度
两尾鱼
喜欢躺在床上
欣赏天花板和它的耳朵
一尾鱼
常常把生活的片段红烧
制成书籍的彩页和封腰
两尾鱼
生活常常把它们放进汤锅里
表演花样游泳
一尾鱼
为自己的游荡苦恼
两尾鱼
为自己的世俗兴奋
一三五
我是一尾鱼
二四六
我是两尾鱼
周日我就和庄周对话
围着他的南溟和北溟
一边吃一边聊
禅意,其实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智慧。从点点滴滴,从眼下的每时每刻,从眼下的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场景飞升,小小的飞升或广阔的飞升都可以。他这样写,不像别的诗人,要获得禅意和佛
性的时候,一定是面对一个虚无,面对一个伟大或永恒。于明诠的禅意是世俗化的,他随便拎一个小孩撒尿的意象,跟鸟儿这样一个意象弄在一起,那么天然。他有一首写刷牙的诗,从刷牙引出禅意,好像还很深奥,带着神秘感的演绎。老鼠刷牙这样的衔接很有趣,李商隐有“不知腐鼠成滋味”的诗句,在当代的语境里有鼠标啊、米老鼠这样一种当代卡通形象,老鼠已成为一种中产阶级消费的对象了。于明诠把它与刷牙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太有意思了。琢磨生活却不刷牙,就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中秋》这首诗:
上午10点37分
我和大家一起
准时到大街上串门寒暄
提着月饼扮着笑脸
兜里揣满无奈的友情
下午4点05分
大家和我一起
到大街上拥堵
提着寒暄换回笑脸
满街的车水马龙
一起伸长脖子仰望天空
白花花的阳光里
看不见月亮和嫦娥以及
玉兔
傍晚6点49分
我站在阳台上看天
天上什么也没有
看看左邻右舍
差不多和我一样
似乎等待着什么
甚至一个民族
都被赶到阳台上
仰望
等待某个节日升腾
等待某种黑暗的降临
等待期盼多年的神话故事
出现
终于什么也没有出现
天气预报不说
我们也感到了
云彩太厚
阴天是预料之中的一件事
中秋夜,我们大家使劲地要望中秋月,要跟古人衔接,那么多诗人写过那么多优美的中秋诗,中秋之月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了。乡愁啊、永恒啊,“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推开窗子望,使劲儿地望向月亮。从现在的生活中,从各种肮脏的、疲倦的、残缺不全的生活中去望这个月,望了半天,月最后没出来,给你一个嘲讽。就这里面,其实充满了禅意,真正的古意:就是想从日常生活,去望一个千古诗意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嘲讽,和古意构成了微妙的禅。像《中秋》和《刷牙》这样的诗,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诗意、禅意,它背后的日常性,都是随意捡来的,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当你使很大地劲去望中秋圆月的时候,月亮便不出来了。月亮不是人们望出来的,也不是诗歌写出来的。这首诗非常透气,非常的口语化,在那么多写中秋的当代诗里,这首诗是非常突出的,它衔接了中国众多经典中秋诗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现在于明诠规定我们看月亮的地方是阳台上。为什么是阳台呢?第一,我们现在住在筒子屋里或者商品屋里,已经不在自然里了,这是第一个反讽意象。第二个,是不是阳台离天近一点,比地面高一点,整个民族都被赶到阳台里,高,实在是高。太反讽了。
明诠不应该把自己定义为“票友”性质的写诗者,完全可以从专门写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的抱负还不够。他写书法是有抱负的,在他表面的谦虚和限定后面,蕴含了巨大的抱负和骄傲。他说,当代书法不就是那一点点趣味吗,那一点点与众不同
的趣味而已。表面上很谦虚和后退,但是里面包含了一个巨大的美学抱负。就诗歌写作而言,我对明诠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减少镜像的折射,增加一点展现自我的东西,就是直接表现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再现和折射。如果我们要讲讲明诠下一步写作格局的变化的话,那我想应该就是他要有一点抱负。
因为张清华兄的引荐,今年我认识了几个山东诗人,也读了他们的诗。山东诗人构成了一个有一定地方特色的格局,但这个地方特色的格局其实可以折射一个很大的格局。山东诗人的诗作里,常常洋溢着古风和现代感相互辉映、相互呈现,这样一种既有点别扭、又带来张力的气息。我觉得山东诗人身上的古风,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现象,而是跟生命有关。或许,山东地域文化的古意太浓厚,幽灵性质太强。如果你想体现当代性,但同时却不被唤起的话,那很可能是个假的当代性。这个意义上的当代性,就是一个幽灵性质的,一个考古学性质的当代性。
于明诠今年才五十多岁,才活了一半,写作的路还很长,我发现他写作和书法上的气息很悠长。他没有那种“憋”的感觉。他的写作不管怎么处理都是很愉快的,很有节制的一种行为。这个节制感、这个写作的快意里面,出现了一种气息,就是“轻”。这个“轻”很重要,它和禅意一样,一定得是接了地气的。否则,飘在半空,那是真得“轻”。接了地气,无论多轻,都是在大地上伸展的,都是在世俗性,在日常生活中,在真实自我的喜怒哀乐中,在人类的局限性里面,找到了诗歌写作的根源。这样一种“轻”,你把一个有千军万马之力的东西变成轻的,像踩在一片树叶上一样,你可以在一片树叶上把整个楼房放
下,那是什么概念?这种“轻”,是我们在诗歌里,在书法里力求企及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神一样的境界了。这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最好的书法家一直都想抵达的境界。其实,写作、书法,就是我们在“家”里。也就是找到是语言古已有之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能够“诗意地栖居”,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