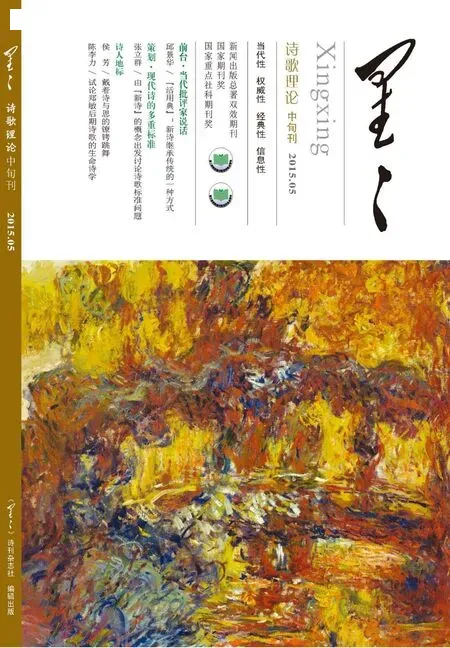诗与新常态生活的和解以及抵抗
张厚刚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诗与新常态生活的和解以及抵抗
张厚刚
诗与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联。当下社会消费主义取代理想主义,社会生活进入到平静的新常态。诗与时代精神、个体存在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位移,诗歌关注从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转移到人与自我的观照关系。
华万里《我的母亲》、马行《阿尔金山之夜》、广子《礼物(或春天的会议)》这三首诗,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诗歌对当下生活的关联、和解与抵抗。诗在与当下新常态生活的和解中,也没有放弃它的反向运动,即诗对社会生活中的庸常成分的抵抗,指认“历史的终结”,就中国当下语境而言显然为时过早,但消费时代的庸常对理想的消解已成不争的现实。诗人面对日复一日的乏味的常态生活对诗歌的侵蚀,柔性反抗已经取代了以往的激进手法,这构成新常态生活诗歌精神的时代内质。
华万里《我的母亲》一诗,从主题上看属于一首悼亡诗。开首起句:“我的母亲,坐着马车走了”,这古典性的、带有怀旧意味的马车意象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具有平静、内敛的唯美形质和伤感情绪。作者抑制住感情泛滥对诗歌表达精微的伤害,给文字背后的所指预留空间。母亲“被扬成一阵尘埃”,从
大地的沉重中被命运的必然性“扬起”,诗人从淡紫色的梧桐花移情到母亲自缢的紫色伤痕,隐忍了尘世间不可克服的悲伤。作者进一步对母亲的死因做出了解释:“她承担不了生活的重和男人的脏”。生活压力带来的绝望,因母亲的“干净”使得沉重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在这里,“死”成为个体尊严和自由意志的拯救者。生活压力淘尽了一个人自我持存于世的信念。每一个母亲或者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这人类的宿命,但母亲之死尤具独特的讽世意味。“我只在梦中,一遍遍地/做她的儿子”,当母子的现实关系被解除之后,在意愿和情感上,诗人不停地确认着母子身份,表达自己对“美之死”的无奈与心痛。“我又看见母亲了/她在花间,淡紫淡紫地闪烁/或者轻轻地摇曳”,母亲已融为泥土、融为万物的普遍存在之中,突显出“我”在浮世上的孤独、留恋与悲伤。
马行《阿尔金山之夜》写一次工亡事故,一个仪器工人坠崖身亡,具有直击人心的现场感。马行这首诗题材上是一个工人之死,但他避开了类似一般打工诗歌的道德诉求或对劳动的抒情,意在呈现个体在死亡面前的精神。我们无法确认这个仪器工之死的原因是不慎失足还是自戕,“他头盔里留出的血/怎么看/都像月光”,“月光”是故乡、宁静的标志,这种意外之死终止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的结束。作者把一桩惨痛的死亡写得克制、内敛、冷静。这本是生活中并不稀少的事件,老班长“一会哭一会笑,一会又骂邱小华还欠他/两包烟”,把淳朴工友情谊表达得哀婉、低回,使之获得了动人的情感力量。
广子的诗《礼物(或春天的会议)》,朴素、平静,带有
隐喻性质,对乌鸦(在中西文化中,乌鸦都是不祥之物)装模作样的“春天的会议”提出了质疑和嘲讽。作者拒绝装腔作势的修辞,呈现出诗歌写作的从容境界。诗歌写生活,本就是对生活的反思、观照和扬弃,并借助于此,收获一种与生活异质的属于诗的另一种生活,最终达成对庸常生活和世故人情的有限度和解。广子的诗,文字洁净,节奏舒缓,不让过度抒情伤害了诗的基质,这在当下诗人中是相当有特色的。广子在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中坚守着自己的诗歌路径。
这三首诗是诗歌进入“小时代”乃至于“微时代”的心灵呈现,诗歌形式由“重”转“轻”。当下诗歌放弃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宏大主题之后,转而朝向个体内心取索,当然人所能感觉到、思索到的外部世界,又都是被自我意识所统摄的,也就是说,这个外部世界之种种,无不是个人内心的外化,从这一点来讲,这些诗歌在缩回到内心的同时,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