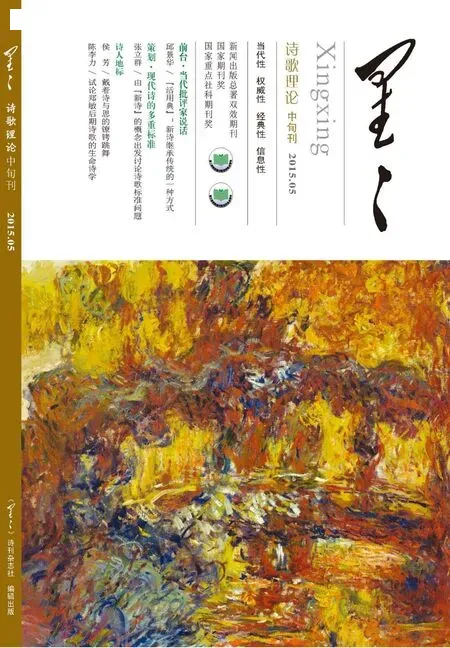朴素哲学与隐喻追求
——郑兴明诗歌论
朴素哲学与隐喻追求
——郑兴明诗歌论
董迎春 覃 才
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不断提供一个复杂而严肃的哲学命题。无数的诗人、诗歌研究者开始思考和反思诗歌与个人、诗歌与生存、诗歌与时代等等各种错综复杂而又关联一体的诗学问题。层出不穷的书写主义、诗学观念,或主流或边缘的诗歌态度、趣味,成为每个汉语诗人所追求与表现的艺术取向与探索。诗人们这些充满差异的诗歌实践,反过来让原本“诗人何为”写诗思考、写诗担虑远远超出了诗歌与写作本身。如今,诗歌的艺术问题,俨然已经成为诗人们真实生活、生存与思维意识相当实质化的一部分。
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四川诗人郑兴明,经历过中国诗歌史上最有歧义的“朦胧诗”时期与80年代“第三代诗歌”的出现、发展与成体过程,并且是在场性的身处于各种新诗观点、新主张冲突最活跃的“腹地”——四川成都。他的诗歌写作倾向必然地与“第三代诗歌”颠覆宏大叙述介入、回归现实生活思考为主,又或多或少地遗留有“朦胧诗”抒情叙事影响。这种诗歌倾向符合“第三代”诗人整体的倡导平面化的诗歌结构、遵循日常化的
语言规则的诗学特征。同时,也是由于他个人朴实、沉潜的生命姿态和自我意识,让郑兴明表现出朴素哲理追求和隐喻写作的特征。这两个鲜明而重要的诗歌写作特征,反映在诗人郑兴明现实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艺术审美及生存思考当中,是其诗歌艺术的整体价值。
一
郑兴明个人朴实、沉潜、反思的生命姿态和自我意识为其建构起了朴素的哲学关怀。面对个人成长的彭州和川地、亲人和家人聚散、城与乡居住转变,艺术知觉灵敏的郑兴明,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着一种持续的“自画像式”的哲学态度与反思写作的追求。处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思考、写作状态中,郑兴明个人深刻的哲学观察与发现就成为一种平静的可能。
诗人在《我希望以一匹马的样子》以“马”代表的自在的存活姿态,喻指而真诚地坦白写道:“更多时候,一个草坡/我们选择爱的向阳的一面/舔舐粗糙的生活,咀嚼朴素的哲学”。在诗人所坚守的朴实、沉潜、反思遭遇现实的诸多变化、差异、不解之时,生命的朴素就作为一种哲学超越与回归自我的面目存在。诗人常常以一种“漫步者”和“思考者”的身份游离与存在于城市、乡村及自我之间。
对亲情的感知、思考是郑兴明朴素哲学的最主要一面。在他的诗歌中,母亲、父亲、二姐、奶奶、女儿作为一种最为朴实、最为宁静的生命本真体验,是他的诗歌写作和朴素性情的一个巨大“展面”。海德格尔说:“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1],诗人真切而自然的处于此种状态,以一种冷静的眼光
体悟出日常存在、常人存在的朴素本质。而对生命与人情朴素本质的发现、追问与探究形成他的生命思考与哲理化的审美态度。“女儿,你搀扶我一时/就搀扶了我一生/事实上/我就是靠回忆和想象/轻轻搀扶幸福和宁静。”(《搀扶》)郑兴明有着一种将朴素日常事实、事件哲学化的透视、聚焦能力,他能从自己女儿带有日常性或淘气性的“搀扶”行为中透视而过,这种对短暂性、日常性行为的透视能力,就是一种对哲学本质与常态的发现能力。在很多感知、思考亲情的诗歌文本中,郑兴明继续展示出他的这种朴素哲学。“老家瓦上的霜。披星戴月/总在那本打开的家书的背面//读到这页,已开始/化了”(《母亲》),“一撮荷叶茶/开水一冲。我就看见/父子俩月下摘荷的情景”(《荷叶茶》),“我发现她一下子拐进黄昏/暮色很快在她背后关上门来”(《二姐》)。不管是对于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母亲、父亲、二姐,还是细节、微小的生活场景、片断,郑兴明自然会在他的诗歌当中,感知、透视出生命本质化的哲学意味与审美态度。
陈述是一种最朴素的哲学发现与思考,它能够很好地完成对日常表象与真理性存在的双重“道示”。这个过程中,道示就作为一种诗歌风格与诗艺特征被呈现出来。“哲学本身就是道路,是陈述着的表象的通道。这个通道的运动必定取决于陈述所跟随的东西,取决于现象意识本身,也即取决于实在的知识——后者乃是自然的知识的真理。”[2]在郑兴明陈述性明显的诗歌写作中,陈述的展开方式是随着与他日常相关的事物、现象、观念等内容。这些或知识,或认识、或感觉、或直观、或能指与所指的内容,就构成了郑兴明诗歌写作当中生活性、自然性的哲学思考来源。“我等着时光 /等着某个黄昏/把我注满”(《陶罐》),
“路领着自己行走”(《路》),“芦花,你嫁给风、嫁给无依无靠的时候”(《芦花》),“一些芬芳的灯、明亮的花匆忙地谢了/空间还在。风,已在远处吹”(《风,已在远处吹》)。在诗中诗人直接体验或间接观察到的人、事、物的意义,被他已然生命习惯化的哲学“悟识”轻易地进行由此处至彼处、由“我性”至“他性”转换。这些夹杂着感性和理性的情感色彩所表现出的艺术特性,无疑指向了多样日常事物背后意义朴素的哲学守护、认同感。
二
“第三代诗歌”一个重要的写作转向是从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现实关怀。郑兴明充满哲学悟识的朴素陈述无疑是根植于现时生活之中,回归生活并表现生活构成了郑兴明诗歌写作重要的一面。阅读他的诗歌文本而发现,郑兴明对平静现时生活和周围真实世界的一切并不是一味地进行哲学维度上的提升。很多时候,他是在运用隐喻式的思维进行一种关于现实与时代的再现、还原、综合及否定。在新历史主义哲学家海登·怀特看来,隐喻还有换喻、提喻、反讽三种同类型,“隐喻是再现的,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转喻是还原的,强调事物的外在性;提喻是综合的,强调事物的内在性;而反讽是否定的,在肯定的层面是证实被否定的东西,或相反。”[3]面对当下复杂、迅捷的时代环境,及现代人看似极为正常的物质生活、消费生活状况,朴实、沉潜、反思的郑兴明萌生出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崩溃意识”,这是其诗歌具有隐喻写作特征的来源。“日子一天天好,生活一天天远/玉米都开始跑了”(《蜷缩的玉米》),“当黄昏埋下夕阳和父亲/村口
没有升起月亮和新娘//蝙蝠的碎片从檐口掠向空中/老家和祖先的魂魄正在崩溃”(《崩溃》)。郑兴明要通过诗歌表现这种现实与时代,自我和实在的“崩溃感”,必然需要进行一种可能与必要的再现、还原、综合及否定。
郑兴明善于运用现实生活中多种植物,作为隐喻写作的切入口。这点可以从他大量植物性命名的诗作题目看出,比如《这朵荷》、《柑花初开》、《川芎》、《秋天的李子园》、《芦花》、《油菜花》、《草药》、《石榴》、《柳絮》。这些植物性的诗题,实际上喻指、再现、还原的是诗人经历或感知到的各种情感、历史、时间、现实等等。在诗歌《木槿——怀念二姐》中,郑兴明写道:“红一丝,就洋盘了点/紫一丝,又像有心事似的/在红与紫之间,一迟疑/就是一生啊……木槿//……//今天看见你,是在城里的花台里/你从岁月深处探出脸庞/贫血、殷殷,倔强而忧伤 //我想起小时候,摘下你的叶/在溪边揉搓的情景——/我突然觉得,那是我的二姐/在我手上抹上泡泡,捏着我的脏手搓呀搓//木槿……”。“木槿”作为诗人的“二姐”隐喻。它在一年四季的形态变化,所喻指的就是五年、十年时间中,在城市和乡村中二姐的变化。在诗人的记忆里,二姐是善良、勤劳、朴实的,代表着人的一种原始状态。所以才有进城之后各种遭遇及作为乡村长大的女性善良、勤劳性格不切合之处。诗人对木槿花的叙事,并非仅是怀念他的二姐,还可以解读出再现、还原时代变化的意图。
我们当下的现实与时代,所取得的进步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无疑是超乎想象的。这种“大进步”背景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怪异、乖张、荒诞感,强烈地震颤诗人朴实、平静的内心和灵魂
的深处。人性的各种美好、安宁、原始、和善被当下的冷漠、戾气、娱乐、浮躁所代替。面对这种无法挽回的历史变化,郑兴明在诗歌中,常常表达出个体内心深处的一种反讽思维。“冬至不冷/吃饱喝足的时代,啥子都热/谁,还会去冷呢?//只有棉花冷/只有狗呀羊呀冷//它们挂在架上,剥了皮/肋骨,是上天堂的梯子/而它们,头,朝下”(《冬至》第2节),“雪化了。//那么多忠实的狗,吃素的羊/被风吹散//雪,化成春天/而这场雪,化成//骨头”(《冬至》第4节)。诗歌叙述是有温度、温情的,所运用的“棉花”“雪”的意象表达也是美好、高雅的。但是郑兴明固有的“植物性的诗歌隐喻模式”所反现出来的实则是刻骨的现实问题,是他本人相信的那种好的人、好的时代的消逝不存。
“植物性的诗歌隐喻模式”是郑兴明多年诗歌写作形成的一个个人化的隐喻话语空间,
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他的审美栖居于这种植物性的隐喻话语空间当中。这个“隐喻话语空间”就像有着“特殊银行”存在。在诗歌《二十年前的报纸》中,诗人这样自述,“你让一个信封大着肚子/一挺身就是二十年/在一个特殊银行,你存下特殊的银两/浪迹江湖,你埋下自己的心腹//……//谁能摸索着读出——/在一个特殊银行,他存下特殊的银两/浪迹江湖,他埋下自己的心腹。”在此可以看出,“特殊银行”里面存储的“银两”是诗人的生活、情感、审美和各种现实,在这个空间里面,诗人为他们好安排一种合理的存在秩序,即隐喻的结构。因而,在郑兴明进行诗歌写作时,隐喻的结构就附着于他所要表达的诗歌内容之上,成为隐喻的诗歌。这种隐喻性,成为诗人表达情感的艺术符码,也让诗歌多了蕴涵与回味。
三
在郑兴明的诗中,可以归纳出明显的朴素哲学和“植物性的诗歌隐喻”的写作特征。为了传达他个人平面化的诗歌结构、日常化的诗歌艺术追求,必然地需要选用某种语言策略达成。诗正是这种语言策略必然的生命追求与诗学趣味。
瓦莱里说,“语言所包含的情感能力与它的实用性,也就是直接具有意义的特性混合在一起。在日常语言中,这些运动和魅力的力量、这些情感生活的精神敏感性的兴奋剂与平常和表面的生活所使用的交流符号和方式混为一体,诗人的责任、工作和职能就是将它们展示出来并使它们运作起来。”[4]从“第三代诗歌”语境所认为的“诗从语言开始”(他们)、“诗到语言为止”(非非)、“语言发出的呼吸比生命发生的更亲切,更安详”(“海上诗群”)等各种语言观来看,郑兴明同样持有一种日常性的语言观,并以此作为其诗歌写作叙事的话语策略、内容与意义载体。他非常注重表现日常语言情感能力和实用意义,让语言既有实指,同时也朝向诗歌艺术的本体追求。
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瓦莱里语),诗学它研究语言的结构、意义、结成等问题,所以可以把诗学看成语言学的一部分。而“语言学旨在提供一种程序,用这种程序来描述语言。提供描述语言程序就是引入一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各种语言。”[5]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学提供的“这种程序”中话语、结构、组成对诗歌写作有很大的益处。诗人可以用语言学程序中的语素、义素、词语、言语等架构诗歌,展开诗歌,聚合诗歌,目的是能够顺利地完成一首诗歌。郑兴明的诗歌写作就明显地表
现出运用“语言学程序写诗”的这种特性。“我知道,踩着一架诗歌的梯子/就可以成功越狱/但此刻,我更愿意将一首诗拆成句/句拆成词、词拆成字/字拆成一地笔画——/成为草、成为我的胡须和头发”(《囚徒》)。诗中,诗人完全地通过不断细化的语言成分,即句、词、字、笔画把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延展开来。这里的语言成分所具备的意义和表述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语言本身,是被郑兴明重新定义和创造过的语言成分。
以语言学的程序架构诗歌,展开诗歌,聚合诗歌的能力特征,常态化的出现在郑兴明的诗歌写作中。在诗歌《荷叶茶》)中,诗人把生活喝茶“嚼茶叶”的体验对等为一个汉字的具体体认:“我常把偶尔喝进口的茶叶/嚼成一个汉字//我从来没有把某些字/咀嚼得如此具体”。在《这小小的空间》中诗人把平时自身所处的空间布置当作汉字的“部首”、“偏旁”具象化的认知:“你是织机边上的部首/我是田边小憩的偏旁”。在《这场雨》中,诗人把偶然的或是长久性的雨的认识,更为形象的看成中国古代“竖排的诗句”,所以在诗人审视天空掉落的雨时,能够看出语言的长句和短句、韵脚和小注。“仿佛是珠帘,仿佛是柳丝/这场雨是竖排的诗句/我不知该从左边还是右边读起/该从远处还是近处读起//一把伞漫无目的飘到哪里/哪里的长句就被裁成短句/我们的脚,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韵脚和小注”。由此可见,郑兴明擅长的叙事策略,就是“运作语言”,运作“语言学程序”提供的或大或小的话语。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兴明诗歌叙事的语言观,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语言学话语的使用,他守护的朴素哲学和“植物性的诗歌隐喻”也是一种叙事的语言观外现。阅读、感受郑兴明的诗
歌,他或平面化的诗歌结构,或日常化的诗歌语言观,都显现出他个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在成都彭州、甚至在四川的诗歌写作群体当作,都具群体的、地域的考察价值。
从郑兴明朴实、沉潜、反思的生命姿态和自我意识当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彭州、四川地域所存有的自由、放松、诗意的栖居状态。这种生命、生活的自由、放松、诗意,带给人的其实就是一种临近哲学的栖居状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朴素的人,就是一个“源始”的人。当朴素个体的存在如此的“源始”,如此地亲近哲学,产生朴素的哲学和植物性的隐喻是合情合理的。哲思和隐喻,在郑兴明的诗歌中,既是表达,又是语言,这在第三代诗歌写作中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诗学意义。
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51页。
2.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3.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序,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4. [法]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1,182页。
5. [丹]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程琪龙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