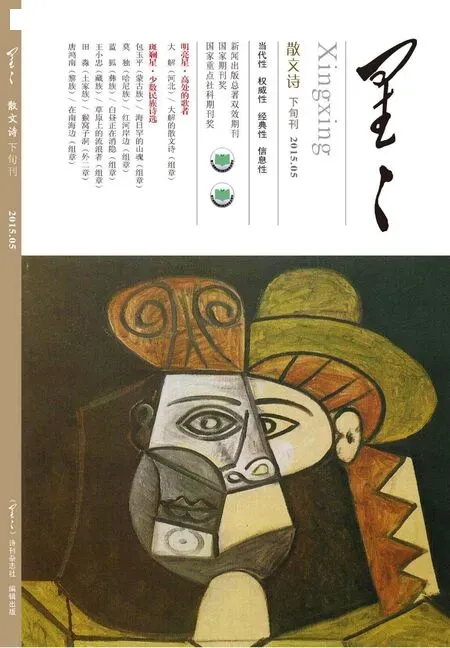广东行纪
若 非贵州
广东行纪
若 非贵州
巨轮之下。旧事已沦为史书中泛黄的鳞片。
歌吟者作诗,弹曲。把生涩的词汇着满岭南万山神色,流水温情。
如今车流滚滚。历史的足音,于缥缈处讲述着不老的传说。
在南粤大地,每一句难懂的方言,都是一首史诗……
01
大地褶皱,被矫情的色彩绘成一幅画卷。
观音山,从名字里透露出骨血深处的意味。
把黑暗之夜都点亮,把沉睡之人都唤醒,把迷途之人都唤回……佛在,这一切都轻而易举。
在观音山,适合打坐,谈心,独自发呆,或者和心爱的人,把爱重新谈上千万遍……
趁着日出正好,观照年轻的身体;
趁着日头当空,看看壮年如斯;
趁着黄昏来到,想想年迈后夕阳红灿灿,把人生看个遍……
一天,即一生。
在美好的风景中,我们足以成为美本身;
在美的关照下,自身的美应该自内而外,贯穿所有。
在观音山,陌生人如是说。
02
名字足够霸气,但此刻它就在脚下了。
渺小卑微者如你我,高居其上,只为看一眼这浩瀚人间,烟火是如何盘旋而上,又是如何消失于虚无。
地王大厦69层,足以俯瞰这一片土地——
车流来回,穿梭如同浮游之物。它们有各自的远方,但并不被自己所知悉。它们的义务无非是做一台听话的机器,在合适的时间里,启动,或停止;
人流快成为油画上需要放大镜才能辨别的尘粒。像攀附巨大时代里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他们转动,从不停息,把财米油盐酱醋茶的人生,转成了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虚空的黑洞。他们少部分在此高处,自傲地指点江山,笑谈他人的人生;大多数流连这城市中,从此及彼,从饥饿到饥饿,从生到死亡;
只有浩荡大江,是真正壮烈而又无所畏惧,不会回头的。流水并不允许自己回头,即便大海,也不是重点。它来自远方,深山之中的鸟鸣和絮语,都已经丢失在沿途。只剩下浑浊一身,像疲惫的游子,落魄却又毫不悔改地寻找自己的梦想。
地王大厦,是谁有意铸造这样的高点,供无知者虚拟自我的高度?
其实,身在其中才更清醒地自知,谁都渺小如蜉蝣。
03
炮台还在。
排列岸上。乖巧,沉默。像扎紧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排好队列,等待祖国的召唤。
像故乡深山之中,冬日里深守田野,等待回家的每一堆草垛。
流水滔滔。万物都不言语。
但我知道,历史上的滚滚浓烟和嘶喊,已经敲响古老族群的耳朵。
低下头,这坚实土地,叫虎门;
抬眼,远方云烟浩荡,叫历史。
04
“色如渥丹,灿若明霞。”
一抬眼,这丹霞山就是日落。
我们来得不巧,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它一起醉;我们来得太巧,一抵达,就遇上这最具媚态的南方姑娘,正妩媚地展现面容。
这一刻可以毫无声响。
但耳朵会被震撼——
好比万山庄严肃穆,在朝着我的方向怒喊;
大地深处有呼之欲出的喷薄之气,在等待被时间唤醒。
是有人在高处呼唤吗?
一眼望去,这些红色的山峰,都齐刷刷地奔了过来。
05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枪声是时间的五线谱上一枚最不起眼的小符号,轻弹起一曲悲壮的歌谣。
但此刻是足够安宁和祥和的。
这是大时代里的黄花岗,是现代文明里仅供赞扬的一小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土地。
但它的厚重无限绵长。比这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传说,都真实可靠;比这岭南任何一首谣,都沉重悲伤。
游人只有应接不暇的眼睛,导游只有麻木应付的舌头。
黄花岗能看见的一切,都是生硬。
看不见的一切,还活在时间不死的记忆中。
06
在河之洲,高楼呈现日益疯长的模样。
时代并没有多余的时间理会一条远道而来又将奔赴大海的河流难以抑制的悲伤……
我突然想——
逆流,顺珠江而上,一定能回到家乡的深部,在水的根部,把前面路上的风景给出发的打工仔细说一遍;
或者顺流而去,在大海深处,向每一滴珠江水,讲述它们走后故乡的模样。
当夜游的船,穿过灯火辉煌。
我像深处时光隧道的小偷,头晕目眩地,感染了流逝的悲伤与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