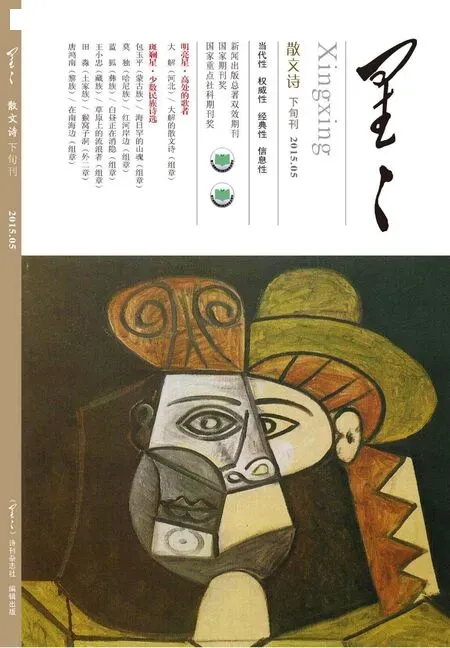风吹故乡(组章)
王崇党上海
风吹故乡(组章)
王崇党上海
清明雨
那些父亲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现在都空着。
我看见风呜咽地围着那些空打着旋,卷起地上的香樟树叶,像在抛洒着若干年的纸钱。慢慢地,那些忧伤的风抬着那些空,就像抬着父亲的灵柩,越来越远……
一场适时而下的清明雨,滚烫地下着。
我们兄弟埋放在父亲身边的柳树棒,在淅淅沥沥的雨里,长出了新芽。
风吹故乡
风吹过屋后的小竹园与吹过庄稼地,声音是不一样的;风吹过母亲的乱发与吹过村后的坟场,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故乡的每一个物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调弦的乐师,每次都能恰如其分地调出乡音。
每次我擦拭完父亲的牌位,都会恭恭敬敬地放回原处。故乡在随处等着你,清晨出去随便走上一趟,鞋就湿了。
母亲已看不见了,但我每次从城里回家她都知道。一次是母亲睡着了,我回来后静静地立在床前。她醒时,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这孩子,咋不叫醒娘呢”。
回城时,路过山岗,我听见风吹过坚实的山壁时,像河流在父亲裸露的脊背上欢快流淌;风吹过有空洞的山壁时,像失去老马的小马驹在泣声嘶鸣。
忙 音
我每天都要给一个人打电话。
可是,不是号码按到一半,突然被事情打断,就是电话忙音,多少年来一直都没有打通。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忙碌。我想问候一下他,让他幸福的时候要提防厄运,痛苦的时候要想想彩虹和父母,思乡的时候不要读李白的《静夜思》,失恋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在河边遛达。
终于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替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看着自己的手机响个不停,泪水哗哗哗地流。
方 言
有方言的人,是有故乡的人,也是幸福的人。
家乡的寂静也是一种方言。
家乡的寂静,站着听与俯下身子听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你的身心和它紧贴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察觉到寂静从乡土里泛上来的体温。
如果你能和草木一起静立不动,寂静的方言就会在你身上结满露珠。
寒冬里,我们提着方言的小火炉,穿过童年的时候,更多跌落的寂静会从梦里苏醒过来。
异乡再大也是航行的船。
在异乡,我的心总是荡着的。只有在家乡,心才是平的,世界也是稳妥的。
漂泊在外的人,很容易与操着方言的老乡喝个大醉——
醉眼里,对方只是一块小小的乡土。
寂寞长出丛丛木耳,每一只都努力竖着,朝着家乡的方向。
丢 失
我的第一声啼哭,让家乡的寂静大吃一惊。
慢慢地,我就与家乡的寂静融为了一体,成为家乡寂静乐器的一个部件,一个发声的簧片,我的站、坐、卧、侧的各种姿势都参与着寂静的发声。
我的漂泊远离,让家乡的寂静响起连绵的幽谧思念。
在繁华的都市,我走着走着,就丢失了脚步声,丢失了悄悄话,丢失了喃喃自语,丢失了爱的私语……
那些声音,要么没入了噪音的水位下,要么懒得再说出来。
油漆工
有些事物是命定的。
春天正在生长,却忽然把嫩芽憋了回去,想流泪的人忍住了悲伤。
我到处寻找适合粉刷的东西,母亲用破的抹布,父亲用旧的木尺,一只半埋在歧途中的鞋子,都被我涂上鲜艳的颜色。
后来我又找到霉黑的王氏族谱,找到孤寡的二胡,胎死蛋壳的鸡雏,甚至找到阳春三月刚备好的棺材,我把它们全部刷成好看的颜色,还画上花草、蝙蝠和仙鹤等装饰纹样,画上神灵的庇护和乡村的乐器。
我累了,蹲下来,鲤鱼一样在冰冷中弯起身子。
漫山遍野的迎春花忽然开到了我脚下,我假装很开心很幸福。
爷爷,可能是你在土里翻了个身,突然之间——
我哆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