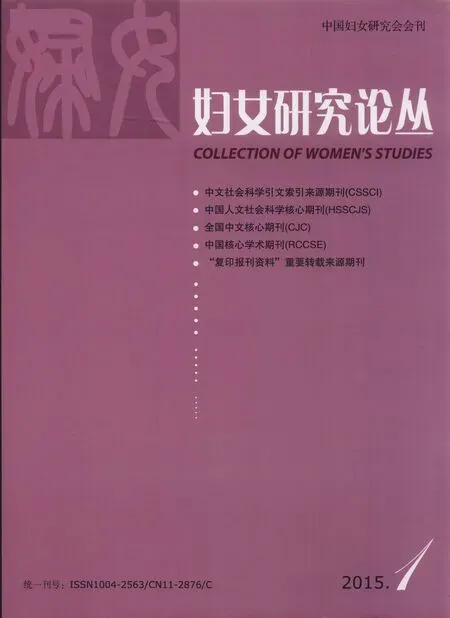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
胡莹 李树茁
(1.2.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
胡莹1李树茁2
(1.2.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第六次人口普查;婚姻迁移;迁移模式;性别比失衡
大规模跨省婚姻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重要的人口迁移社会现象之一。文章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时空模式及变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水平与性别结构失衡具有一定关联性。性别结构失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在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中的叠加效应开始初步显现。大规模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的同时,也推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婚姻挤压程度。
一、背景
婚姻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社会现象,是指通过婚姻途径进行的与自然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直接相关的社会流动。[1][2][3][4]婚姻迁移一直是中国女性实现迁移的重要形式之一。[5][6]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婚姻市场信息缺乏以及婚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女性的婚姻迁移距离通常都比较短,基本上在同县乡方圆20里范围内。[7]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巨大变迁,人口迁移和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女性婚姻迁移规模和迁移距离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5-1990年全国直接报告以婚姻为动机的跨省迁入女性高达140万人,占女性跨省迁入总人数的28%。[8](PP41-45)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推算,中国省际迁移女性人口中婚姻迁移所占比例仍然高达20.7%。[9](PP13-28)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近10年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规模爆炸式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5%。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当前中国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原因,这直接导致婚姻迁移人口在中国总流动迁移人口中比例的快速下降。2005-2010年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人口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到8.39%,但总量相对于第四次人口普查(1985-1990年)和第五次人口普查(1995-2000年)仍然分别有34.2%和14.6%的增长。[10](PP85-98)
从迁移效应来看,相对于迁移距离较近的省内婚姻迁移,大规模远距离跨省婚姻迁移对促进地区文化交流和融合具有积极影响,对于保持人口婚配动态平衡也具有积极作用。[11]但远距离跨省婚姻迁移可能会使女性婚姻迁入者在家庭福祉、社区参与、人际交往、就业、生育和社会支持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可能造成外来婚姻迁入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当地女性。[11][12]中国女性的婚姻迁移特别是跨省婚姻迁移具有高度的地域选择性,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的大规模婚姻迁移会加重迁出地的婚姻市场挤压程度,可能导致经济落后地区出现大量大龄男青年终身未婚和养老困难。[13][14][15]相对于学术界在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流向、规模、后果、城镇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的研究成果,[16][17]18][19]近些年对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现象的研究则薄弱得多。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从时空特征、动因、机制、途径和后果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8][20][21][22][23][24][25]但绝大部分研究从经济视角展开,更多关注经济驱动下的中国女性婚姻迁移水平和模式特征。在当前中国性别结构失衡和婚姻挤压程度加剧情况下,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水平、态势和特征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不断增长的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规模和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存在关联性,婚姻挤压在全国范围伴随婚姻迁移如何传导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和回答。本文利用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经济、制度和性别结构等角度综合来考察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态势、特征、模式及其变迁规律,为有关部门有效引导和促进婚姻迁移女性社会融合以及迁出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态势、模式与特征变迁
婚姻迁移现象的主要测度变量包括态势、迁移水平、模式和个体特征。态势主要用于描述婚姻迁移人口规模变化。迁移水平则反映婚姻迁移人数占当地户籍人口的比例或全国迁移人口的比例,可以揭示各地婚姻迁移的活跃程度。婚姻迁移模式关注迁移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分布情况,与迁移水平相结合,可更直观描述婚姻迁移空间模式和变化规律。年龄、户籍、教育和职业是描述婚姻迁移女性最常用的个体特征。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及变迁进行研究。
1.态势分析
表1给出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数据变化情况。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态势变化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跨省婚姻迁移女性人口占全部迁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但其绝对数量仍在不断增加。随着从事经济及相关活动的流动人口规模爆炸性增长,跨省迁移女性人口中婚姻迁移比例在快速下降,从20年前近1/3下降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5.02%。这说明跨省婚姻迁移已不再是当代中国女性实现远距离迁移的主要原因。尽管比例在不断下降,但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规模仍然在快速增长,相对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绝对数量分别增长了34%和16%。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劳动力流动迁移更加自由和频繁,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规模仍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第二,在全部婚姻迁移女性中,跨省婚姻迁移女性所占比例在快速增长,省内婚姻迁移比例在降低。跨省婚姻迁移所占比例从1995-2000年的12.0%上升到2005-2010年的18.0%。这表明伴随年轻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中国女性婚姻市场和通婚距离也在不断扩大。这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所揭示的趋势是一致的。[26](PP40-47)第三,跨省婚姻迁移男性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从第四次人口普查8.99%增加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4.35%。这说明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婚姻迁移现象已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在当前婚姻挤压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伴随着外出务工经商规模不断扩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接受远距离跨省婚姻迁移。

表1 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跨省婚姻迁移女性数据比较
2.空间迁移水平与模式变迁
首先用各省迁入率来描述女性跨省婚姻空间迁移水平和模式。迁入率定义为各省跨省婚姻迁入女性占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总人口数的比例,可度量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空间比例分布。为了较为全面地揭示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空间模式变迁,利用第四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绘制了全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率的分省GIS图。(见图2)从第四次人口普查GIS图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空间流向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S”型曲线。[20][21]第五次人口普查GIS图表明,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S”型曲线开始断裂,女性跨省婚姻迁移逐渐向北京、苏沪和广东聚集。近10年来女性跨省婚姻迁入率最为显著的变化则是上海和北京在2005-2010年超过广东并直逼江苏,成为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最活跃的热点区域。第六次人口普查GIS图显示了21世纪前10年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地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其所占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比例接近全国的60%。传统的女性跨省婚姻迁入大省河北和山东则迅速下降,逐渐与安徽和四川等省处于同一水平,不再是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的热点区域。从近20年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入率的空间演变历程来看,女性跨省婚姻空间迁移模式最大变化是加速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原本较为分散的东部沿海地区的“S”型集中迁入地近10年逐渐分裂并快速聚集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中国女性跨省婚姻空间迁移模式的这种变迁,与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和城市化进程是一致的。[27]

图2 女性跨省婚姻迁入率时空模式变化
由于各省既有婚姻迁入也有婚姻迁出的人口,因此还需综合迁入迁出情况来考察其婚姻迁移动态平衡情况。“跨省婚姻净迁移率”定义为某地跨省婚姻迁入和迁出人口之差与当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净迁移率为正表明该地是净迁入地,大量外省女性婚姻迁入有利于降低该地婚姻挤压程度。而净迁移率为负则该地是净迁出地,大量女性婚姻迁到外省会推高该省婚姻挤压程度。图3是从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推算的女性跨省婚姻净迁移率对比图。从图3可以发现女性跨省婚姻净迁移率绝对值较大且为正的地区仍然是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和天津、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和福建等婚姻迁入率较高的热点区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北京和上海2005-2010年的女性跨省婚姻净迁移率相对1995-2000年呈现数倍增长且远大于其他省份。这说明当前北京和上海不仅对外省婚姻迁移女性具有巨大吸引力,而且本地婚姻迁出女性规模也非常小。从图3来看,中国传统女性跨省净迁出省份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云贵川陕甘宁等西部地区和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中部地区湘鄂豫三省女性跨省婚姻净迁出人口近10年有不断扩大趋势,河南甚至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净迁入地变成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净迁出地。中部地区外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基数特别大,又临近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婚姻迁移聚集地,2000年以来逐渐成为继云贵高原之后又一新的年轻未婚女性净输出地。长期来看会对中部地区婚姻市场产生较大压力,婚姻挤压也逐渐从西部蔓延扩散到中部地区。
3.个人特征变迁
年龄直接影响女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年龄分布是婚姻迁移模式中最受关注的个人特征之一。2000年以前中国婚姻迁移女性年龄分布高度集中于低龄化区间,具有明显的低龄尖峰。[21]图4是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按年龄段分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1995-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05-2010年)数据对比。1995-2000年29岁以下跨省婚姻迁移女性高达73.0%,30-39岁大龄女性仅占18.6%。而2005-2010年29岁以下年轻女性急剧下降到43.0%,30-39岁大龄女性则迅速攀升到33.6%。这种变化使得近10年来中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年龄尖峰明显削弱,分布也开始扁平化,35-44岁年龄段迁移女性仍高达25%以上。当前中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低龄峰值钝化和年龄分布扁平化趋势与近10年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密不可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婚姻家庭文化更加自由和开放,女性初婚年龄不断增加和再婚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平均年龄也会随之不断攀升。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省婚姻迁移人口主要集中于年轻女性不同,年龄已不再是制约当前中国女性实现跨省婚姻迁移的主要瓶颈。

图3 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净迁移率

图4 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年龄分布变化
从户籍性质来看,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长期以来以农村女性为主体,主要表现为从农村迁移到农村的平行或向下迁移模式。[20][21]而近10年来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首先农村到农村迁移模式比例不断下降。尽管2005-2010年农业户籍迁出女性仍高达77.5%,但比1995-2000年下降了8.5%。同时传统农村到农村迁移模式内部也在逐渐分化,从落后农村迁移到更落后地区农村的向下模式比例急剧减小;而从落后地区农村迁往发达地区农村的向上模式在近10年有了很大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5-2010年迁往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农村地区的跨省婚姻迁入女性就占到全国30%以上。这说明跨省迁入到发达地区农村平行略微向上的迁移模式逐渐成为落后地区农村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主要选择之一了。其次,从农村到城市的向上迁移模式和城市到城市平行迁移模式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近10年从城市迁移到城市的婚姻迁移女性占全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比例增长了5.51%。这表明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和婚姻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跨省婚姻迁移不再仅限于自身资源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农村女性,自身条件较好的城市女性也越来越容易接受跨省婚姻迁移。总的来看,各种向上迁移模式比例增长的背后蕴涵的是经济因素在跨省婚姻迁移选择中贡献度的不断强化。
从职业来看,工作流动性较大的女性婚姻迁移所面临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选择远距离跨省迁移。1995-2000年从事流动性较强的商业服务业工作女性比例最高,接近一半。到2005-2010年从事服务业的婚姻迁移女性退居第二,其他不便于归类的各种流动性或临时性工作的婚姻迁移女性上升到第一位。工作流动性较差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比例均相对较低。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当前跨省婚姻迁移女性受教育程度总体水平与以往一样仍然比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女性仍然占据了70%以上。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出一些新的变化,跨省婚姻迁入城市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在快速提升。2005-2010年跨省婚姻迁移女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相对1995-2000年急剧增长了近5倍,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3.78%。这主要是一线城市通常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准入积分制度,迁入这些城市需要有较好的自身条件。例如,通过婚姻迁入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均超过了30%,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三、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的宏观环境分析
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迁入地的吸力是婚姻迁移的主要因素:一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未婚女性通过婚姻迁移期望获得更高质量生活;二是迁入地未婚人口性别比偏高,婚姻挤压严重,客观上形成了对婚姻迁移的巨大需求,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11](PP97-116)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实行完全不同的户籍制度,人口长期以来并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迁徙,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不仅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变迁密切相关,而且与中国近20年来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婚姻挤压的逐渐显现也有很大关联。
1.社会经济制度
从西方人口迁移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是推动人口迁移包括女性远距离婚姻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空间模式变迁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转型的同时带来了择偶观念的转变,人们对经济物质基础在婚姻质量中的重要性开始重新认识,女性在择偶中开始对男性经济地位有所追求。经济落后地区的年轻女性通过婚姻交换而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来改善自身生存福祉,是在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最现实的选择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时期,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并不是很大。这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目的地在江苏、山东、广东、安徽等联产承包改革实行较早或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多点开花。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已经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于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走在了中西部地区前列。因此,跨省婚姻迁移女性开始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向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实力飞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从而形成了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东部沿海“S”型曲线。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北京、上海和广深为中心三大都市圈的快速崛起,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从而撕裂了东部沿海“S”型曲线,成为当前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首选目的地和聚集区。2005-2010年仅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就占到全国跨省婚姻迁入城市女性人数的48.7%。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使得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成为未婚女性跨省迁出大省。
2.户籍制度
对于跨省婚姻迁移来说,除了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所产生的巨大拉力之外,户籍制度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而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非常严格的选择性政策,迁移优先权赋予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普通人要进行跨省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而通过婚姻落户是改变户籍性质和实现户口迁移门槛相对较低的途径,因此跨省婚姻迁移是实现较为严格的户籍迁移制度下中国农村女性实现远距离迁移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门槛也非常高,落户农村则远比城市容易,因此85%以上的中国女性的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均是从农村迁移到农村。这种平行略微向下的模式也使得中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群体表现出比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成为婚姻迁入最热门地区的北京和上海,由于其农村也实行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迁入规模在上世纪并不大。但随着其居住证制度和户籍积分制度的推行,北京和上海迅速成跨省婚姻迁入规模最大的目的地。随着中小城市落户制度逐步放松,户口迁移到中小城市变得相对容易。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跨省迁移到城镇的女性也已经超过了20%。[10](PP85-98)国务院于2014年7月30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推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随着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全面放开,中国人口自由迁徙越来越容易,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和从城市迁移到城市两种跨省婚姻迁移模式比例会越来越大。户籍制度的改变将对今后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户籍制度的放开自身并不能使跨省婚姻迁移流向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相反还有可能伴随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动而强化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女性跨省婚姻迁入,并促使中西部地区年轻未婚女性净流出现象近一步加剧。
3.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
如果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吸引了大量未婚年轻女性涌入经济发达地区以期望获得较好的生活福祉,户籍制度的逐渐放松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得远距离婚姻缔结机会增加,那么跨省迁移未婚女性在新的婚姻市场能否最终完成婚配,还要取决于迁入地是否有足够多的合适成婚对象。当迁入地婚姻市场挤压较大或者说迁入地未婚男女比较高,外省迁入女性才有较大机会在迁入地婚姻市场上完成婚姻缔结。中国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主体是农村女性,大部分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多从事流动性比较强、收入也不高的职业。相对于流入地当地未婚女性,外来未婚女性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在当地婚姻挤压程度相对比较严重,有相当比例当地男性无法与当地女性完成婚配的情况下,外来女性才有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实现和模式变迁,与中国各地婚姻市场特征特别是挤压程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全国范围内较为权威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跨省婚姻迁移与性别结构的关联性难以得到全国层面数据的验证。本文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2005-2010年间各省跨省女性婚姻净迁移率与该省婚姻挤压比和0-4岁婴儿性别比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到新生婴儿成年后才会进入婚姻市场,本文采用1990年0-4岁的婴儿性别比来度量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当前婚姻迁移的影响。从婚姻市场挤压的吸引到完成婚配的时间滞后性,选取2005年各省28岁以上未婚男女数量比例来度量“六普”统计时间段婚姻挤压程度。研究发现,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0-4岁婴儿出生性别比较高的省份,也正是婚姻挤压程度比较大的省份。这些省份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跨省婚姻迁入女性人口数量和净迁移率也相对较大。例如,2005-2010年跨省迁往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婚姻迁移女性就占到了全国40%以上。而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恰好也是男女未婚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同时,伴随着大量省外女性的婚姻迁入,这些省份户籍人口男女未婚比例也是逐年下降的。例如,北京户籍人口男女未婚比例从1990年的1.61降到2010年的1.19;上海则从1.91降到了1.28;江苏则从1.58降到1.27。这说明,大量来自外省的婚姻迁移女性的确有助于缓解迁入地户籍人口婚姻挤压的作用。而同一时期云南、贵州和内蒙古等婚姻净迁出地,其户籍人口男女未婚比却在持续升高。1990年到2010年,云南男女未婚比从1.55上升到了1.65;贵州从1.50上升到了1.53;内蒙古从1.33上升到了1.44,这说明大规模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输出地的婚姻挤压程度。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当代女性的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当前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体现为以下几个新特点:第一,从态势来看,表现为“两个下降”和“两个增长”。具体来说就是跨省婚姻迁移在女性跨省流动中比例在急剧下降,且跨省婚姻迁移人口中女性比例也在逐渐下降;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绝对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且在全部婚姻迁移女性中比例也在快速增长。第二,从空间迁移模式来看,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目的地从东部沿海的“S”型加速向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都市圈集中,形成了上述三个地理空间不连续的独立区域。同时,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城市的向上或平行迁移模式比例也在快速增长。第三,西部地区持续成为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净输出地区,并且有加速向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新的跨省婚姻迁移净输出地。第四,从个体特征来看,大龄女性婚姻迁移人口比例在快速增长,跨省婚姻迁移女性的低龄峰值明显削弱,年龄分布开始扁平化。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可能带来的更多大规模远距离婚姻迁移,婚姻迁移女性在当地社会融合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综合考虑的现实课题。需要进一步加快婚姻迁移人口家庭在经济、生育、就业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人口流动和迁移带来的红利尽可能体现出来。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制度以来,中国较为严重的男孩偏好使得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导致中国女孩严重缺失,预计到2020年可能会产生大约3000万男性无法实现婚配。[14]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这些婴儿潮成年进入婚姻市场后,未婚男性会发现适合婚配的当地未婚女性出现稀缺。只有具有足够竞争力的男性才能优先娶到当地媳妇。被挤出由当地未婚女性构成的婚姻市场的“输家”则只能转而寻求外地媳妇,这就使得跨省迁入女性的婚配成为可能。如果只是局部婚姻挤压,外来媳妇的加入可能会降低当地的婚姻市场挤压。婚姻市场是具有排他性的零和游戏。在中国当前整体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存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一地婚姻挤压程度的降低,往往就意味着另一地婚姻挤压程度的上升。局部婚姻挤压可能伴随着远距离跨省婚姻迁移而在全国范围内传导。也正是婚姻挤压的存在,使得中国当前女性的跨省婚姻迁移目的地不仅仅限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大量外省女性婚姻迁入,只不过迁出的女性更多罢了。可见中国女性的跨省婚姻迁移现象,其迁移机制呈现多元化,不仅仅只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户籍制度变迁的驱动,也直接受到当地婚姻挤压程度的影响。
尽管当前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开始下降,但中国性别结构仍然呈现失衡状态,需要持续关注性别失衡的治理。如果不关注弱势群体的婚姻挤压现象,大量未婚女性会加速从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或沿海地区,从而加剧西部特别是西部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当前东部发达地区存在的较大婚姻挤压和巨大的经济优势仍会吸引大量外省年轻未婚女性迁入,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在逐渐上升的婚姻挤压反过来会迫使该地区大龄未婚男性被动迁移。大量大龄未婚男性被动迁移则有可能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较大压力。在跨省婚姻迁移受到经济和婚姻挤压双重驱动的同时,规模更大的省内婚姻迁移也遵循相似规律,使得婚姻挤压也会在省内局部传导。最后被挤出婚姻市场而终身娶不到媳妇概率最大的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自身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如何妥善解决大量女性婚姻迁移所造成的落后农村地区婚姻挤压,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将是今后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战略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出生性别比失衡产生的婚姻挤压和大规模婚姻迁移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的综合治理亦非常复杂。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治理,继续坚持对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进行综合治理,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尽快恢复到正常范围。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未婚年轻女性教育程度和积极拓展当地就业水平,尽可能降低经济欠发达地区未婚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快速增长的势头。在关注女性婚姻迁移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迁出地大龄未婚男青年和被迫失婚的男性群体。有针对性地出台帮扶政策,努力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素质,增加其收入。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帮扶政策,努力提高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
[1]BonneyN.,Love J..Gender and Migration:Geographical Mobilityand the Wife's Sacrifice[J].Sociological Review,1991,(39).
[2]Fan,C.&Huang,Y..Waves ofRural Brides: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8,88(2).
[3]C.Fan,L.Lin.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AField StudyofGaozhou,Western Guangdong[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2,(34).
[4]赵丽丽.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Davin D..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The Enlargement ofMarriage Markets in the Era ofMarket Reforms[J].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2005,(12).
[6]Davin D..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 and East Asi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7,50.
[7]谭琳,柯临清.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J].南方人口,1998,(2).
[8]丛臻.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女性人口迁移水平与模式研究[D].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9]乔晓春,黄衍华.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3,19(1).
[10]李树茁.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研究[R].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委托课题报告,2012.
[11]Laurel Bossen.Village toDistant Village: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LongDistance Marriage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7,50.
[12]Locke,C.and HXZhang.ABetter Life?Migration,Reproduction,and Wellbeingin Transition[J].SBHA,2010,75(2).
[13]ZengYi,Zhenglian Wang,Leiwen Jang,Danan Gu.Future Trend ofFamilyHouseholds and ElderlyLivingArrangement in China[J]. Genus,2008,64(1-2).
[14]姜全保,李晓敏,M.W.Feldman.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5).
[15]李树茁,胡莹.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评述与展望[J].人口与经济,2012,(2).
[16]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J].地理研究,2001,20(4).
[17]LiangZai.Patterns of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ContemporaryChina:1985-1990[J].Development and Society,2004,33(2).
[18]丁金宏,刘振宇,程丹明等.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J].地理学报,2005,60(1).
[19]王桂新.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0]谭琳.八十年代中国女性省际婚姻迁入的逐步回归分析[J].人口学刊,1999,(4).
[21]Monica D.G.,Ebenstein A.Sharygin E.J..China's Marriage Market and UpcomingChallenges for ElderlyMen[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Paper 5351,2010.
[22]程广帅,万能.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人口的成因及影响[J].西北人口,2003,(4).
[23]倪晓锋.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28(4).
[24]陆淑珍.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J].南方人口,2010,25(5).
[25]艾大宾,李宏芸,谢贤健.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以四川盆地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8).
[26]胡莹,李树茁.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7]王桂新,潘泽翰,陆燕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12,(5).
责任编辑:玉静
Changes in Women's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HU Ying1LI Shu-zhuo2
(1.2.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Shaanxi Province,China)
the 6thNational Census;marriage migration;migration pattern;imbalance in sex ratio
Large-scale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is one of Chinese women's important conditions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Chinese women's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based on the 6thNational Census and the previous censuses.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female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and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population structure.It is becoming apparent that the female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affects and is affected by the imbalance in sex ratio and the imbalances i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Large-scale female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migration may be easing,at some level,the marriage"squeeze"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but aggravating the marriage "squeeze"in the less developed midwest areas.
C913.13
A
1004-2563(2015)01-0020-08
1.胡莹(1986-),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动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2.李树茁(1963-),男,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流动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