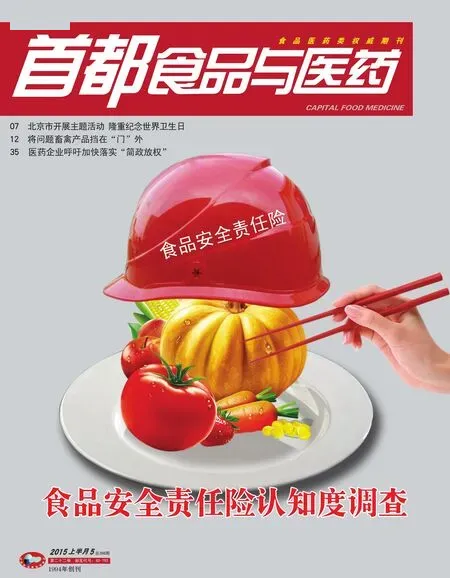坚守西藏三十余载的妙手大师
——访解放军第八医院疼痛科主任张德鹏
◆本刊记者 许方霄


正是由于高寒、缺氧的高原环境,才使西藏成为肩周炎、颈椎炎、坐骨神经痛等病症的高发区,这些病症令当地军民痛苦不已。除了疾病带来的痛苦外,他们甚至感到绝望——靠先进的药物目前尚无法根治。就在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默默忍受折磨之时,高原上来了一位妙手仁医,带着他精湛的医术,穿梭于这片圣洁的雪域高原,用银针和娴熟的手法点亮患者心中那盏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灯。他,就是张德鹏,一位几乎走遍高原每一个角落,坚持在西藏驻守31年的倔强军医。
减轻患者痛苦是行医初衷
张德鹏出生在甘肃酒泉临水乡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气候原因,冬季长时间的寒冷令张德鹏所在的村子里很多人都遭受关节疼痛的困扰,看着熟悉的脸庞上泛着痛苦的表情,张德鹏的心像被人狠狠地扎了一下,心里产生莫名的难过,一个“我要学习医术,为患者减轻痛苦”的念头跳进他的脑海。那一年,张德鹏还是个初中生,刚刚15岁。
在治病救人的责任和对医学的无限憧憬下,张德鹏四处搜集医书,并就此走上了漫漫自学之路。张德鹏说,自己有个“启蒙老师”——当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祖上四代行医,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医世家,为了能学到更多的医术,张德鹏每天放学后都会到老中医家里去,看他如何为病人把脉、扎针,跟他学习怎么开药。
谈起自己诊治的第一位病人,张德鹏至今印象深刻:那还是1974年的一个冬天,村里有一个13岁的女孩儿犯了风湿性关节炎,但由于女孩儿的父母都是“走资派”,即使四处苦苦哀求,也无人敢替“走资派”的女儿诊治。无法言喻的病痛使女孩儿疼得哇哇直哭,女孩儿的父母看着是既着急又心疼,但现实很无奈,他们当前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流泪。也许实在是别无选择了,女孩儿的父母最后找到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张德鹏。女孩儿痛苦的哀号声使张德鹏的悲悯之心瞬间涌上心头,虽然紧张,但他还是从容地拿起银针。银针刺进女孩儿皮肤的那一刻,意味着张德鹏真正走出了行医生涯的第一步。张德鹏连续一个星期帮女孩儿针灸治疗,女孩儿的疼痛感逐渐消失。看到女孩儿一家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张德鹏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随着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张德鹏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乡间邻里只要有点不舒服,都会来找张德鹏给瞧瞧。由于拥有医术上的特长,张德鹏在高中时就被当地医疗合作站招去,当起了赤脚医生。在张德鹏眼中,自己是个幸运的人。“那个时候,大城市的医生们都会组织医疗队到农村来,对农村的合作医疗站的医疗骨干进行培训。”张德鹏说,在这为期3个月的医疗培训中,他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也更加勤奋地学习传统医学。

▲年轻时期的张德鹏夫妇
不能放弃“老本行”
凭着医术上的好口碑,1976年2月,张德鹏被特招入伍,并被分配到重庆某工程团卫生队,专门从事针灸推拿工作。1977年,张德鹏来到重庆的解放军163医院进修放射专业知识,但对于自己的“老本行”,张德鹏舍不得就此丢下。他将点点滴滴的休息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刻苦钻研针灸、按摩、正骨等知识。
张德鹏所在的工程团长年挖深井、打隧道,长期要弯腰低头,加之受风寒影响,很多战士们患上颈椎病、肩周炎、腰背病等病症。虽然张德鹏在家乡名声在外,但他深知医学就像一片广阔天地,自己目前所掌握的犹如沧海一粟,等待他去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为了能使战士们尽快摆脱腰背病折磨,张德鹏可谓是使尽全力,为了更精准地找到人体相关穴位,准确地把握力道,张德鹏不惜以自己为“靶子”,用银针在自己身上进行反复试验。
此外,张德鹏还多次利用休假机会,向行业内诸多知名专家教授和民间医生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艰辛摸索,急性腰扭伤、小关节紊乱、椎体错位等不同类型的腰背病,都被张德鹏一一攻克。当年的赤脚医生,此时已成为部队人人皆知的“妙手神医”。因工作成绩突出,1982年12月,张德鹏被破格提升为干部,不久又被调到解放军163医院放射理疗科专门从事针灸推拿按摩工作。
1984年,张德鹏在重庆的部队已经生活了8年,这8年的部队生活虽然艰苦,但在张德鹏看来,为无数战士们解除痛苦给他带来了别人无法体会的快乐,而且在这期间,张德鹏也与一位善良而美丽的湖南姑娘结成连理。就在张德鹏以为一切就这么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的时候,部队传来援藏的号召。由于西藏缺医少药,成都军区打算派出100名医务干部前往西藏进行援助,张德鹏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申请进藏,但很“不幸运”地被分在全军海拔最高的解放军第八医院工作。
再难也要坚守下去
离开重庆,前赴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西藏,留下新婚妻子独自一人,张德鹏心里也不好受,觉得对不住她,但为了边远地区更多病患的福祉,他强忍心中的留恋与不舍,毅然远行。张德鹏说,西藏是坐骨神经痛、肩周炎、肱二头肌腱炎等世界性疑难杂症的高发区,来到这种特殊环境也是对他提出了新的挑战。
张德鹏坦言,刚去西藏的时候确实存在不适。气候不好,海拔3900米,缺氧,高原反应产生的生理反应让张德鹏极度难受。“当时的西藏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天天就是自己煮些面条,偶尔蒸些米饭。那时候没有新鲜猪肉卖,更别说新鲜蔬菜了。馋肉了,就托人买上点冻猪肉。”张德鹏笑着回忆道。海拔5300多米的查果拉山,四季都覆盖着厚重的白雪。长年驻守在查果拉哨所的官兵们在此严重缺氧的高原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脏肿大、造血功能异常、风湿性关节炎等高原疾病。张德鹏不知道已经多少次避过雪崩、塌方来到这里,为驻守的战士们诊治。提及此事,张德鹏不禁红了眼眶,他说,为守边防,战士们几乎是用生命在战斗,只要能让他们拥有健康体魄,即使路途险阻又有何妨?“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他们服务好”。纵然经历万种艰险,张德鹏都没有萌生逃离西藏的心思,他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名军人,同时也是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当地军民需要我!我必须坚守在这个需要我的地方!”这个信念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始终屹立在张德鹏的心中。多年来,张德鹏多次深入边防一线,为边防战士和地方群众巡诊达上万人次。
按规定,援藏工作3~5年的援藏军医就可以申请回内地工作。为了能一家团圆,张德鹏的妻子及家人多次提议让张德鹏转业。一边是无时无刻不挂念的家人,一边是饱受病痛折磨的西藏军民,张德鹏该做如何抉择?“既然已经来了,就要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倔强的张德鹏最终说服家人,坚持要留在这个让他放心不下的高原,用他手中的银针和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手法为患坐骨神经痛、面瘫等疾病的西藏军民送去希望。今年是张德鹏坚守西藏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当年百名援藏军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依然留在西藏。
大师是从“创造”中出来的
除了父母起的名字以外,张德鹏还有一个代号——大师。张德鹏笑着说,这个称呼是部队的战友们给起的,从年轻时就一直被这么叫着。对于这个称号的由来,张德鹏解释道:“大师的意思不单是专家,还有创造者的意思。”张德鹏认为,一名真正的医者,不能一味地照搬书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思想与手法。如今,大师张德鹏的很多治疗手法和方法在书上是找不着的,因为那是他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张德鹏说,与中医的辨证论治说法相似,针灸、正骨也得根据掌握的病情情况来具体对待。“同一个病在同一个患者身上,治疗方法可能都不一样,而且扎针的手法、角度也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扎,这不是找书就能够学会的。”
治疗面瘫是张德鹏的擅长领域之一。凭借自己的独特手法和创造性想法,在某些病例治疗中,张德鹏会将两个穴位串起来,他说,虽然病人当时会感觉特别疼,但经过多次治疗验证,效果都特别好。其实,张德鹏的“自学成才”与其多年从事放射科工作有很大关系,因为放射科对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所以患者在得了腰背病以后,只要把拍的片子放到张德鹏的面前,张德鹏立刻就能知道此病的原因所在。“在哪个位置有问题,扎针和正骨的时候我就能想到,因此,只要按照相应的手法或针灸的配置去治疗就没什么问题了。”但严格来说,张德鹏不能被称之为“纯针灸人”,因为纯粹学针灸的人,只是按照中医理论,如奇经八脉、十二经络等来下针,而张德鹏所运用的针灸、正骨等手法却是从解剖的角度出发,是西医基础上的中医。为了更直观地表达,张德鹏举例说:“比如关节脱臼,或者在腰椎检查之后,虽然感觉很疼,却没发现有骨折迹象,但用解剖的知识,我则认为,这种疼痛是由小关节的错位引起的,而这种错位,仪器是检查不出来的。”此时,张德鹏则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将中西医结合,为患者正骨、按摩、针灸,无需打针吃药,患者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基于张德鹏不断创造新技术的精神和取得的优异成绩,西藏军区还授予他“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的称号。但张德鹏却没有将他的独创手法编写成书,对此,他虽然感到很遗憾,但却表示“没办法编”。“同一个面瘫,针灸的方法都不一样。根据面瘫的具体情况,哪一根经络上来以后,再根据面部的几种表情来配穴,包括面部本身和背、腿、手的穴位。在治疗坐骨神经痛、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张德鹏说,“即使编成书也是不行的,因为很多都是我自己经验的总结,如果编成书了,别人在看过之后很可能会按照同样方法去实施,但因为情况不一样,比如患者的舌苔、脉象等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治疗方法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像开中药一样,特别是针灸,配穴特别重要,书是死的,但是扎针、按摩是活的,必须得根据具体情况来操作。”

▲张德鹏在厄瓜多尔为病人诊治

▲在中厄两国建交纪念会上,张德鹏(右二)与厄方领导合影
神医美名传播国际
2004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休假的张德鹏突然接到成都军区外事办的电话。“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吧?”张德鹏接听电话后,才知道有一个援外医疗任务,成都军区外事办打电话的目的就是问其是否参加。“这个任务很光荣,得去!”张德鹏再一次“先斩后奏”,没有和家人商量就立马答应下来了。
援外医疗,顾名思义,就是前往国外进行援助医疗工作。与驻扎西藏不同,张德鹏这次必须得远渡重洋,在一个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家——厄瓜多尔待上一年半时间。得知消息后,张德鹏的妻子是又气又担心,但张德鹏的性格她又怎会不了解?她知道,当前她能做的,就是偷偷擦掉眼角的泪水,好好珍惜宝贵的相聚时间,不断嘱咐丈夫多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去厄瓜多尔的前几天,孝顺的张德鹏夫妇来到甘肃酒泉,看望年迈的父母。张德鹏说,当时也和父母“聊了聊”。得知儿子即将前去国外,张德鹏的父母并没有阻拦,而是让儿子到国外放心工作,不用担心他们。父母的深明大义让张德鹏无比感动。
“当地医疗设备十分欠缺,走的时候我们从国内买了一些医疗器械带过去。”张德鹏回忆道。2014年8月,张德鹏作为医疗队队长带领医疗队到达厄瓜多尔的三军总医院。虽说中国医疗队员的医疗水平远远高于当地医生,但若想很快在异国打开局面亦是不易之事,但张德鹏及中国医疗队却很快获得厄瓜多尔及国际上的赞誉。到厄瓜多尔没多久,张德鹏就接手一个病人——一个患了面瘫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在当地医院做了四个月的治疗,结果却越来越糟糕。“嘴角得挂钩子,不然受不了,当地已经治不好了。”张德鹏说。最后,这个大学生怀揣最后的希望来到三军总医院,并被安排给张德鹏。从接诊的第一天起,张德鹏每天都会耐心地为其针灸,半个月后的一天,该患者突然气急败坏地质问张德鹏:“整张脸绷得太紧了,还使劲跳,感觉特别难受”。“这说明神经马上就要恢复了。”张德鹏兴奋地说,并让翻译及时告诉患者,让他放心。就在患者将信将疑,并焦急等待之中,“整张脸一下子就全都恢复过来”。这个消息像插上翅膀,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瞬间传开了,张德鹏更被当地人视为神医,每天来找他看病的患者都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他根本就没有坐下的时间。虽然援外任务重,工作强度大,但张德鹏诚恳地说,看到亲手治好的病人脸上洋溢着笑容,自己心里也会很开心,这种幸福感超越了其他,也就忘却了疲惫。
由于张德鹏盛名在外,厄瓜多尔唯一一所培养研究生的重点大学——玻利瓦尔大学研究生院随即邀请张德鹏为医学系学针灸和按摩专业的20多名研究生上课。只要有张德鹏的课,不必打听他在哪间教室,顺着掌声最热烈的地方走去,准能找到。教室里的张德鹏认真讲解,仔细示范,还不时过来纠正学生的错误手法,一幕幕专注而温馨的场景,让所有人感动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强大力量,它让国籍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不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正气源于原则
见到张德鹏的第一眼,就会感受到他由内而外散发的正气。张德鹏说,自己的性格随父亲。张德鹏的父亲自小就在农村生活,是苦孩子出身,解放以后,18岁就当了村支部书记。张德鹏说,身为老共产党员的父亲原则性非常强,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80多岁的人了,还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个正直的人。”也正是在这股正气的作用下,虽然张德鹏诊治了难以计数的病例,却从未出现过一例收受钱物的事。
张德鹏说:“虽然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清贫,家里还有老人,但是我从来不接受别人的一分钱,这是我的原则。”张德鹏也毫不避讳地说,也许是为了感谢自己的帮助,也或许是受当前“送红包”的风气影响,他确实也遇到很多病人给自己“塞钱”的情况。每当这时候,张德鹏都会收起平日和蔼的笑容,严肃地说:“你要给我钱,可以啊,那你明天不要来了。”看到张德鹏“变脸”了,患者们都会略感尴尬地拿走钱。说起自己的“不近人情”,张德鹏哈哈地笑着说:“这是我的原则,不能坏。”
即使尚在休假期,在医院的病房里也会经常看到张德鹏的身影。只要病人找到他,张德鹏都会给他们治疗。在来北京参加“最美援外医生”颁奖典礼的前一天,张德鹏还在为一位得类风湿关节炎的病患做治疗。该病患已经去过广东省好多大医院,在某大医院打一针就要开销8000元钱,十多万元花出去了,但病痛却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面对顽疾,该病患的目光中浮现出丝丝绝望。也许是上天眷顾,该患者无意中得知张德鹏在这方面具有极高造诣,几经周转之后终于找到张德鹏。“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手都蜷不起来,但毕竟才一年,骨头还没变形,还没发展到骨节增生。”对于这位绝望的病人,张德鹏耐心地劝他放宽心,并表示很有信心治好他的病。果然,在接受张德鹏7天的治疗后,该病患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问及这种情况要花费多少钱后,张德鹏乐呵呵地说:“看到别人痛苦,我就给他治一下嘛,不要钱。”
“年轻的时候,要好好地把手艺学好,饭后休息半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看书,医学方面的书都要看。有了知识的积淀,工作以后再积累经验,技术才能提高,才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张德鹏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这是他对学生们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一路走来的写照。“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一行,要做就要做好,如果半途而废,划不来。”
人物小传

张德鹏,1957年12月出生于甘肃酒泉,解放军第八医院疼痛科主任,技术五级。1976年入伍,在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0282部队卫生队任班长,曾多次被评为学习雷峰先进个人;1982年调入成都军区163野战医院放射理疗科;1984年调西藏军区解放军第八医院放射理疗科;1995年任放射理疗科主任。2004年8月至2006年2月在厄瓜多尔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被厄瓜多尔国防部授予“部队之星”荣誉勋章。2006年被西藏军区树为先进典型,评为“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并荣立三等功。2015年3月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最美援外医生”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