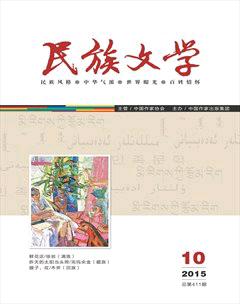新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歌剪影
赛娜·伊尔斯拜克
新疆塑造了悠久的多元文化传统,新疆少数民族诗歌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审美成为了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新疆少数民族诗歌迎来了新的繁荣期。
通观新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绝大多数以母语写作,一个普遍特征是他们都无法摆脱自身民族文化和身份的浸染与制约。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让诗人在文化心理和个性气质上都显得与众不同,这也会突显在诗人的创作上。执著于对故乡的书写是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一个创作特点。在诗人那里,故乡不只是原始的苍茫,更是自己的精神根基和身份源泉。柯尔克孜族青年女诗人祖拉·别先纳勒把故土比作金色秋苑:“花朵失去了娇艳/落叶铺满金色秋苑/迷失的方向/不知是否能通向幸福的终点/人群在涌动/车如流水,鸟雀高飞/点点残秋撒落在伤痕陈旧的路面/金色裙摆在冷风中摇曳/残阳如火/却留不住逝去的时光/秋天肆无忌惮地袭来/谁能阻止她的脚步/捡起秋季遗落的果实/储藏起来,就像收藏一丝希望/一片未来/树林沙沙作响/高压线随风应和/金色河流低吟一曲民歌/无始无终/孤独的背影/人群渐渐远去/随风摇摆的秋叶渐渐消瘦/太阳依旧灿烂/秋去春来/纯真依旧/没有依靠的港湾/我的根深深扎进金色秋苑。”蒙古族诗人铒达这样抒发故乡情:“我是乌尔禾的月亮/ 洒在艾里克湖上的涟漪/我是乌尔禾的风/画在胡杨林里的水墨/我是围在沙包生活的一粒沙子/从来没有想过和风一起比翼双飞/我是阿拉德山上的一颗石子/从来不怕雨水的侵蚀/我是土尔扈特父亲的一句教导/也是土尔扈特母亲的一首长调。”这种疼痛的乡音乡情,是我们今天面对故乡时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故乡”和“家”都是我们曾经拥有却又回不去了的地方。祖拉·别先纳勒就书写了自己的这种疼痛感:“天地混沌/风卷着雪/旋转起舞/舞动着冰冷的长剑/即将摧毁一切/大雪纷纷飘落/小草瑟瑟发抖/被季节娇宠的园林/凝望冰冻的湖泊/风雪戏弄着马耳朵般硕大的叶片/无奈的树干/默默哭泣/谁能改变四季轮回/谁又能让时光回流/把身体藏进混凝土建成的温室里/怀揣的梦想/又该去往何方。”
康德说,两件事让我凝神静气地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对自然的言说,与自然的融合,是一个诗人挚爱情怀与普世精神的体现。对大自然的解读,使诗歌文本更为纯粹,语言更具弹性。哈萨克族诗人阿依达娜·夏依苏力坦亲近自然,感知万物,在诗中融入爱与虔诚:“北极熊们/穿着短袖 /喝着啤酒跳着舞/孔雀们裹着军大衣/围着篝火搓着手/骆驼们/在沙漠中央/穿着高跟鞋走着猫步/人类在大洲中举家迁徙 /斑马们却热衷于奢侈购物/如果可以角色互换/她也想变成一只小鹿/在森林里偶遇一只老虎。”对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诗歌的言说仅停留在对大自然的吟唱上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一个有着文化情怀的少数民族诗人来说,如何汲取本民族的文化营养、表达本民族的历史与梦想则是她的使命。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民族传统、寓言和梦想表达的欲望,也是属于这个民族独特的言说方式。
八十年代以来,诸多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族群文化传统与汉文书写传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和相互丰富的文化互动中找到了自身日臻演进的发展道路。各民族口头传统丰富多彩,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强烈的美学魅力。新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歌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大多来自于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生活、史路历程与文化传统的抒叹,来自于对民众独特的审美心理和思想感情的表达。他们大都善于广泛地汲取民间口头传统中的题材和形象,融汇了各支系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等口头文学的语言艺术成果,有的也借鉴了本民族古典诗歌的神韵与口诵传统的风采,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哈萨克族青年女诗人古来夏·也拉合买提的《谎骗》采取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诗歌话语,更多地借鉴了本民族民间歌谣新颖独特的构思、洗炼明快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比喻、清新柔美的风格。“你又在敲我家星光下的家门/我心里自然又乱了方寸/母亲又停下手中的活计/责怪是谁总这样不让我们安生/月亮在夜空偷笑黑狗也叫个不停/母亲上了门栓/好像怕人偷去了女儿/心越过窗去却不知/给母亲一个什么样的谎言/你说得轻巧:谎骗母亲/本该是女人天生的本领/谎骗母亲?对,一定还要谎骗家人/谎骗邻居,谎骗草原和自己的心情/但是啊,怎么就那么一线鸿沟/最终让我放弃与你的相约?你失望了/怪我无能要听失约的理由吗?一个谎骗了母亲的女孩儿/一定也会谎骗心爱的人。”各民族新诗创作的队伍中,这一批诗人中不乏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者,热爱民间歌诗的审美传统,在世代相承口耳相传、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传统中探究其深蕴的诗歌精神,并对文化传统进行全新开掘。
新世纪以来,新疆少数民族诗人在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地域写作风格和特点的同时,也兼具了新世纪诗歌的一些特征,在现代性诗学书写上甚至更胜一筹。随着现代文化浪潮的冲击,他们的诗歌创作在保持丰富性和纯洁性的基础上又注入了现代性的因素。他们固执地用诗歌经验来维护仅存的身份特征和母语的纯洁。
新疆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仍是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地方性”让他们的诗歌更具民族特色。“诗歌的地理学一方面是关于情感(经验)的认知,经验的场所,经验自身所包含的地理因素为情感表达提供了修辞,另一方面,诗歌的地理学涉及到空间、场所与事物的意义,它是关于地理对人的经验的构成作用,以及地理空间对主体意识的建构作用的认识。”(耿占春《诗人的地理学》)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显然处于文学场域的边缘,在文化资本的占位上处于劣势。然而,这些少数民族的青年诗人继承了前辈诗人和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用诗歌书写诠释着个体与民族的文化渊源,向中国诗歌彰显着其独特的文化个性与尊严。边缘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在诗歌的领域,边缘的光芒已从一部分优秀的群体中照射出来,滋润着我们渴望被照亮的心灵。地方性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生活理念的文化冲撞在诗人那里则显得更为激烈、奔突。维吾尔族诗人博子蓝的诗歌里面,一方面表达了对草原大地的向往与热爱,一方面又诉说着民族文化基因退化的焦虑和悲哀。“你的面孔是焦虑吗/或者/是玫瑰之向晚的肉体?你的祖国是岩石吗?或者/是新月的沉淀物?飞在黎明的面庞上的鸟啊/你鸟上的是伤痕吗/或者/是传统所遗留的毁灭?”在诗人看来,这片神奇的土地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民族如今已经生病,在继承本民族的地方性文化传统和抵抗现代文明侵蚀的双重纠缠下,我们似乎了解到诗人的诗学追求和文化价值取向。面对这些文化冲突的时候,青年诗人由于曾亲身经历和体验城市的纷繁多变和世故功利,仿佛游弋于城市边缘的鱼,在细碎的痛苦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文化的源流。诗人置身于所谓的现代城市文明中的身份焦虑可见一斑。对全球化生存体验的书写,尤其是其中关于民族文化受到侵蚀,从而引起诗人身份迷失的疼痛体验的书写,是今天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歌最扣人心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