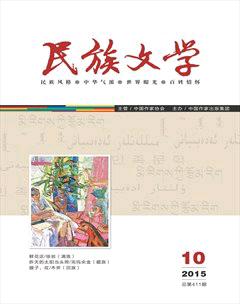致撒拉尔的孩子
马明全
一
孩子,你的第一声啼哭划破了黎明前的东方。今天的朝霞像猎猎旌旗从山的那头列队而出,天象奇特而又壮烈——火红的霞、绯红的云、蓬勃的光把早晨的天空割裂得支离破碎,像十八万个天使甩动十万八千里的翅膀搏击黎明前的黑暗,给你提前带来曙光。这真的是个吉祥的时刻。其实每个孩子的出生时刻都是吉祥的,因为孩子是天使的化身,父母只是体会到了自己的孩子降生那一刻的快乐而已。
孩子,我听到了你的哭声,同时也听到了泊在胶州湾的军舰、轮船、渔船鸣笛起航的呜呜声,伴着晨起海鸥的鸣叫,天空的色彩更加明朗。在湿润的海风中,我发现自己哭了,其实眼泪早在你的哭声之后哗哗流过,只是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脆弱,并且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这叫喜极而泣!
此刻,在异乡土地上奔命的我却想起了故乡。思绪早已飞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庄:三三两两的人,窄窄的巷子,不大不小的土木房子,袅袅升起的炊烟。清晨的乡村正从睡梦中醒来,薄雾弥漫的音容不乏浓浓的幸福意味。我能想象到,隔壁的阿依莎大婶礼完晨礼急匆匆地钻进草房抱来一把麦草,在有些年岁的斑驳的土灶炉膛内点燃全村的第一把火。麦草的特殊气味是阿布都大叔五十多年来最喜欢闻的味道,他说灶炉里的麦草有大婶的味道——大叔自从和大婶结婚以来,吃惯了大婶烙的薄面饼子。当然,阿依莎大婶烙的面饼在撒拉八工那是出了名的,她烙的饼酥、绵、韧、香。从姑娘时候起,凡是到她家吃过面饼的人无不啧啧称赞,阿布都大叔就凭这一点当时死活缠着父亲到阿依莎大婶家去说媒。阿依莎大婶的第一张饼子烙熟了,菜籽油金黄的絮沫在面饼上撒欢,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阿布都大叔端坐炕上,面前是实木的小方炕桌,三炮台的碗子已喝过三道早茶。大婶又用锃亮金黄的铜茶壶往大龙碗里倒上滚烫的奶茶递到大叔面前,奶香和饼香使阿布都大叔的心里幸福满满。
孩子,你再一次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声。老人说,孩子在娘胎里的世界是非常宽广的,生下来的那一刻发现世界如此的狭小,所以用哭声来表达他们的恐惧和无奈。你也是这样吗?
世界大不大我不知道。尽管我走过大江南北,但是我脑海里的世界就是那么一点点,那就是中国西北部偏东一隅的撒拉山川。
隔壁的奥斯曼大伯用他惯有的嗓门在吆喝:“阿力!阿力!还不起床吗,太阳照到屁股上了,圈里的黑牛在骂你呢,你还不动弹!”其实,太阳刚刚露出半个头。巷子里左邻右舍的牛羊“咩咩咩”“哞哞哞”地叫唤着。这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炊烟,年轻的撒拉艳姑们从泉边淘来清凌凌的水,水缸满灶前清,庭院内外清清爽爽。艾布叔叔赶着他二十年前包产到户以来不多不少的十二只羊从家里面走出,干净的巷子里立马撒落一地的黑珍珠,门口阿娜们的嘟囔也是短暂的那么一两句,艾布叔叔像没事人似的只顾低头赶自己的羊儿。二十年,习惯了,他的眼里只有他的羊群。巷子在阿娜们的扫帚下又变得干净了。
巷子口上索菲亚一手拎着个花布做的小书包,一手使劲拽住小儿子的胳膊往前走,小顽童亚海雅对上学不知哪来的惊恐,那种歇斯底里的哭和“我不去!我不去!”的喊叫是自他进入六岁以来每天早晨不变的音律。邻居听不到他的哭声时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天。索菲亚不停地哄着亚海雅:“阿妈的宝贝!阿妈的棉花骨朵!你一定要去上学,要不然将来你就得像阿妈和阿爸一样去放羊,做苦活。长大了你去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都不认识厕所,坐不了飞机回不了家呀!”“我不坐飞机,我不去北京,我不离开阿爸阿妈!”亚海雅的回答仍然是倔强和不屈不挠。
这就是我们那时的生活场景,孩子,你们将来会相信吗?
二
孩子,此刻的你正在吃人生的第一口奶,妈妈的奶水安抚了你的恐惧和不安。你咂巴着小嘴一下一下地吮吸着妈妈那带血的初乳,一脸的幸福展现在脸上。你也会长大,孩子!人的喜怒哀乐与生俱来,谁能拒绝?
胶州湾海面近处的景物愈加清晰,千帆竞发充满勃勃生机,潮汐涌动,海浪前赴后继。极目远眺海天一色,山一程水一程,脉脉相通。老人们常说,回家的路隔山不远隔河远。可是,千山万水阻挡不了我回家的心啊!
送葬的人们像列队的天使,在德高望重的阿訇带领下从清真寺直接去了穆斯林公墓。不论贫穷富贵,不论年老年少,齐刷刷跪坐在墓园地上,膝下黄土翻滚。阿訇的嘴里发出字正腔圆的《古兰经》诵读声,在静谧的清晨格外响亮。众人举双掌于胸前,祈求真主赐予人类一切美好与安宁。
也许在送行者从墓地归来的时刻,清真寺米纳楼高塔上的呼喊声传来:“村里的老少爷们,赶紧拿起?头,扛上铁锹去麻扎挖坟坑,上村有位老人去世了。”孩子,你的啼哭无法掩盖那熟悉而又让人伤感的呼喊声,八百年来用一贯的腔调告知一位亡灵的归真。每一位长者是部落里的珍宝,是民族的活化石,尤其对这样一个有历史,有语言却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任何一位长者的去世就是一段历史的断代。
曾经,我跟着年迈的叔叔去送别一位更年迈的长者。那天早晨,亡者的家中人很多,当然他并不是一位大户人家的主人,甚至因为老来得子,挣下的家财勉强能维持日常生计。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人们照样去赴丧吊唁,作最后的告别。众人在院中,立者肃穆端庄垂手含胸,行者步履稳健小心翼翼。那是对亡者的尊敬,是对一位并不知名的民族先辈的尊敬。生前高高大大气宇轩昂的八尺男子,此刻静静地躺在木质的水床上,印有阿拉伯经文的苫单覆盖在亡者身上,使他显得更加修长,头部枕得高高的,整个面部朝向神圣的天方“克尔白”。那块布下面的人和我们近在咫尺,揭开那块布我们就可以四目相对,死亡就是这样吗?我突然间感到害怕,一呼一吸之间的生与死那么短暂,此刻我强烈感受到的生命不是我的心跳,也不是我的手足,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那略略感到压抑的呼与吸——现实中的出一口气和争一口气,现在看来是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呼一口气吸一口气我们的生命还会鲜活地存在着。不是吗?前几天还曾拜访过的这位睿智的长者,现在永远地屏住了呼吸,世界就此划开了一道谁也难以逾越的鸿沟。
是的孩子,我的思绪有点乱了。
当叔叔掀起护单的一角瞻仰亡者遗容的那一刻,叔叔嘴角抽搐,没有牙齿的口腔显得干瘪而无力,嘴上微弱的声音我却听得真真切切:“哥哥!”那是一位和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长者,一声哥哥送同辈,令我动容。那个安详的面容在我看来只是那样睡着了而已。我不相信,那个曾经给我讲过许许多多奇闻异事的老者走了:炮火连天的日子被抓去手里塞给一杆枪,但枪口不知道对准谁的雇佣兵经历;莫名其妙地连续几天几夜赶到那个叫河南的地方,懵懵懂懂挥起大刀劈头盖脸砍向小日本的豪情。哦,对了,你说过:那些小日本,见到我们缠头撒拉尔,撒丫子跑的,呵呵呵呵!你捋着胡须笑了。晚年的你很孤独,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你们面对着杀人恶魔般的日本鬼子,决不投降决不后退,撒拉尔头割下来也要喝黄河的水!你们就那么硬气。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看见了那些走亲戚借用一件皮袄共穿的伙伴们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了;喜欢在每一家的婚礼上狂欢似的演绎传统《骆驼舞》的伙伴们不在了。你们其实是在抗日,知道吗?可惜你听不到了。
这是他们的历史,孩子,你们将来会相信吗?
三
孩子,是你戳中了我的泪点。这个节骨眼儿,想起吉狄马加的那首《致他们》,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曾经为一个印第安酋长而哭泣
那是因为他的死亡
让一部未完成的口述史诗
永远地凝固成了黑暗
是的,撒拉尔是一部永远叙述不完的口述史,那些“酋长”们却一个个亡去。
孩子,你哭吧!其实,我的泪点并不低,我们撒拉尔的泪点也不低。我们不善于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撒拉尔的子孙是从小在家人的吆喝和村里长者的训斥声中长大的,这个民族禁不起溺爱和放纵。那时候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一家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成年后的我曾经在村道小巷逛游,内心极度渴望能有一位老者像我儿时那样用他的藤木拐杖勾住我的脖子——我躲,我闪。但他上下翻手,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用农具改装的挠钩勾手勾脚。那时候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到不论谁的孩子都可以逗弄一番,不听话还可以拐杖伺候呢!可如今巷子空空没有一个人影儿。左右四邻都说孩子们在北上广深打工开面馆。我路过那个从小不喜欢上学的亚海雅的家门,听说他在北京开了八年面馆,腰缠万贯算不上,但在城里有了不小的房子,老家的低矮草房也已经一扫而光,面前矗立的是一面高高大大的青砖雕花门楼,檐子和门楣用黑色的遮阳网绷住了,上面落满了鸽子屎。亚海雅母亲索菲亚不到五十岁,她老公早已在十年前去西藏墨脱县搞运输时连人带车冲进雅鲁藏布江,埋体也没能找回。索菲亚从大门旁临时开的小门里探出头来,见到我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满以为她是跟着独子亚海雅在大城市生活,而且很滋润。她却幽幽地对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这时候,我想哭的欲望比你强一万倍。孩子,你的哭也许是本能,而我的哭是发自内心的孤独与凄惶:我们有了房子、车子、妻子、儿子、票子,而想要内心富足却没有法子。
四
你说,你的降生我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我们的祖先捧一部珍藏千年的《古兰经》从历史走向了现实,轨迹清晰可辨。可是,这部《古兰经》的来历,撒拉尔民族的族源是否也会渐渐淡忘。八百年前,咱们的祖先从中亚带着信念和力量向东寻找乐土,像沙漠中的芨芨草坚韧地扎根在这方净土。而如今,孩子,咱们像风儿吹起的沙子飘向五湖四海,我们是无根的种子飘到哪里算哪里,八百年后的咱们还会这样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忠诚吗?毕竟我们没有带来内心的赤诚和理想,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迷失方向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在胶州湾这座向世人展示年轻活力的城市里我莫名地感到伤感和不安。
孩子,胶州湾的船笛声搅得我心慌意乱,你已经安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睡了。你的母亲也因为产后的虚弱,此刻歪歪斜斜地躺下睡了,她怕惊动你不敢把自己孱弱的身体放正,你们俩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满足的喜悦和幸福。一夜的守护使我的眼睛布满红血丝,是眼睛刺痒还是我感情的堤坝彻底崩溃,眼泪不争气地一次又一次流下来。咱们撒拉尔千万个母亲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子子孙孙,可是有多少个母亲是在这么好的医院里,从怀孕第一周期就开始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测试、胎教和营养搭配呢?看你的周围摆满了多少先进的设备,就在你还没有出生的前一刻我还在想,如果女人生不出来,那些钳子钩子会把我的孩子生生拽出来吗?也许,那样可能对你更好一些孩子,让你在降临人世的过程中受一些苦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对婴儿管不管用我不太知道,但是,咱们曾经的祖宗几乎都是在马厩里出生,马鞍下玩耍,马背上长大。母亲们在布满荆棘的田间地头生下多少个孩子,自己咬断脐带揣着孩子回家。其中出了多少烈性汉子不得而知,最起码我们的骨子里都有一股原始的浩然正气,这就是咱们民族的气概。如今的你们在温暖的床上显得那么柔弱,今后能否扛起大梁。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男人和父亲,混在人群中就是一个路人甲而已。但是,咱们的社会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们都在观望何去何从,是刚毅地坚守还是无奈地随从。而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一股撒拉尔的热血,那叫血性。我也许不需要悲天悯人,但我无法管住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眷恋,对这片土地上草根文化口口相传的人们的敬仰。我的眼泪只为那些生于斯长于斯安息于斯的人们而流。
孩子,是你戳中了我的泪点,让我从幸福中窥探到忧患。我因敬仰和怀念而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