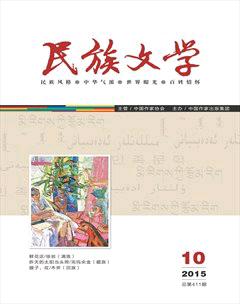背出来的家园
陶玉明
我的老家地处滇西高原澜沧江西岸的一个中山河谷地带。小山村所坐落的这个山坡比骆驼脊背还陡峭,进出村的道路比羊肠子还弯曲。有人用歌谣形容这个地方:“江边大地日头黄,出门就爬大石坎,猴子过山淌眼泪,山羊下地滚撇坡。”
老家人管盖房子叫“背房子”,一个“背”字道出建盖一间房子的辛苦与艰难。
自我记事起,40多年的时间,我们家的房子先后更替了四次:第一次盖的是“罩笼房”;第二次盖的是土坯房;第三次盖的是砖瓦房。直到去年,“10.7”普洱大地震,政府号召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我们家才盖起楼房。
这四间房子与其说是盖起来的还不如说是“背”出来的。
1983年,我家拆除原来像鸡窝一样的“罩笼房”,开始盖土坯房。那时我在读初中,几个弟妹都还小,为盖这间房子,父亲和母亲开始了一生以来最艰苦的劳作。1983年,在我的家史中将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土坯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是:下基础的方块石,支撑屋架的柱子、函条和椽子,砌墙用的土坯、沙子和石灰,铺屋顶用的稻草。
筹备这些材料,父亲和母亲作了相对明晰的分工:父亲负责砍木料、打石头、脱土坯,母亲负责搬运除木料以外的其他建筑材料。
父亲的石场在离村子5公里外的玉米地头上,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天还没亮,母亲就出门去背石头去了。一块方块石长两尺、宽一尺左右,小的有30多公斤重,大的有40多公斤甚至50公斤。母亲一次只能背一块石头,一天到晚顶多也只能背三四趟。下基础用的400多块石头,母亲一共背了四个月。待所有的石头都背到家门口的时候,麻栎树做的背架都已经散架了。
脱土坯的场地没有那么远,就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园圃地头,但盖房子需要的1万多块土坯,母亲还是背了三个多月。
稻草得从收割后的稻田里背来,母亲一次能背20多把稻草。我至今记得母亲背稻草时的情形,远远望去像背着一团硕大的云朵。
背东西的时候,母亲喜欢拄着一根拐棍。拐棍有两个作用:一是助力,二是平衡。拄着拐棍,再陡的坡也不会跌倒。村里人戏称拐棍是江边女人的第三只脚。
母亲背石头、背土坯、背稻草行走在江边坡路上的情形有点像沙漠上负重前行的骆驼。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见过真正的骆驼,但在所有的动物中,骆驼给我的印象最深。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作文,提到过母亲的精神就是骆驼精神。老师对这篇作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可我这位蹩脚的作家一辈子也没能写好关于母亲的文章。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这一辈子吃过的最高级的营养品就是红糖。一天的劳累后回到家,母亲常常啃一点红糖。母亲说红糖可以消解疲劳,安神定心。我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回家都会买几块红糖给母亲,我希望母亲多吃红糖,健康长寿。
那时,我也想到运送这些建筑材料能不能用自制的独轮车。但母亲说,用独轮车要挖路。在岩石丛生的江边地上挖这样的路别说一家人,就是一个村子的人合力也办不到。
通公路是江边山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后来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可母亲却没能坐过一次车。母亲说,车这个比水牛还大几倍的东西,跑得比兔子还快,坐上去还不把人弄散架了。
背这些盖房子用的材料,母亲的背上尽管垫了一块编织袋,衣服还是磨出了方块石一样长宽的破洞来。后来,母亲把衣服上的这个破洞补了,继续穿着这件多了一块长方形“图标”的衣服走在江边山地的路上。看到母亲的背影,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一样疼。
一年后,我家的土坯房终于巍然耸立在我们村中。盖起了土坯房,母亲的脸上增添了一些笑容,父亲的腰杆也挺得更直了。母亲走在村路上逢人便讲:“盖这间房子真是累坏了孩子他爹。”父亲则说:“这间房子是孩子他娘背出来的。”我从父母相互赞许的话语中看到了人间恩爱。我相信,没有领过结婚证的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几十年,一定有着坚如磐石的感情。否则,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就不会像现在这般智慧和善良。
10年后的1993年,我家开始盖砖瓦房。父母和我在家的几个弟妹又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房运动。1993年的乡村已经普遍通公路,但乡村稀缺的车辆只适用于进城运水泥、钢筋和化肥等农用物资,当地建房用的砖瓦仍然得靠背。母亲说背砖瓦不像背石头、背土坯那样劳累,砖瓦场就在离村子不到一公里路的村旁,一天可以背十多个来回。但那年,我感觉到母亲的腰更弯了,背着砖瓦上坡的时候几乎是手脚并用,不是在走,而是在爬。我对母亲说:“背不动就别背了。”而母亲却说:“还背得动,别说盖这间房子,就是以后盖一间楼房也可能还背得动水泥。”
盖这间房子的时候,我的几个弟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间房子用的砖瓦,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为此,母亲常常自豪地说:“儿多便是福。”
我家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除了我,其他几个弟妹都在家务农。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气,除了春节过年的那几天,母亲几乎一年四季都“爬”在江边的坡地上。对不起,我形容母亲在地里劳作的情形不用“站”这个词而是用“爬”,是因为“爬”字更准确。在澜沧江边的陡坡地上劳作,“站”是站不稳的,只能弓着腰以“爬”的姿势,劳动的时候才稳当。我们那个村子常常会笑站着挖地的年轻人。老人们说:“站着挖地不是在用锄头挖地,而是在给锄头喂奶。”我们出来工作的人偶尔回家帮父母干农活,最怕村人说我们在“给锄头喂奶”。劳动虽然很光荣,但我出来读书的时间长了,干农活很不得劲。挖地的时候,我不会弯腰,挖地的姿势真的像给锄头喂奶。
儿多便是福。这句话我一辈子也无法理解,因为在母亲的身上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母亲这一生一共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而她一辈子不是在江边地上劳动就是在“背房子”。她非但没有看到后来我们家盖起来的楼房,就是城里的楼房都没有看到过,因为她这一辈子压根就没有进过城。
关于进城,母亲说:“进城路太远。”其实,我们村离县城也只有85公里,走山路顶多也只要8个多小时。母亲背出的3间房子所走的路也许要比进城的路长得多。
年轻时候的母亲和老了的母亲在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背房子”的时候,走路的次序是不同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走在我几个兄弟姐妹的前面。母亲老了,走在我几个兄弟姐妹的后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娘年轻的时候是娘领儿,娘老了的时候是儿领娘。”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母亲的这句话比哲学问题还深奥。
2014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家盖起了100平方米的楼房。进新房的那天,市文联派出几个摄影家为我们村盖起楼房的80户人家照全家福。最遗憾的是我家的全家福中没有母亲的照片。按理说,全家福这样的照片,如果家中的某个人不在场是可以用旧照片“克隆”出来的。但我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照过相,就是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直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母亲的汉族名字。母亲的布朗族名字叫“叶亮”。“叶亮”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的意思。母亲的形象像一枚月亮一样永远别在我故乡夜晚的天边。
看到城市的楼房我常常想家。思念故乡的月亮,思念那位名字叫月亮的女人。天底下最伟大的人是母亲,因为母亲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背出了那么重的房屋。有了房子才算有家,有了家才有人间的温暖。
40多年的时间,我们村80多户人家的住房一共新旧更替了4次,也就是说这个村40多年来一共盖了300多间房子。参与建盖这300多间房子的许多母亲都已经很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世。但是,背方块石用的架子和背砖瓦用的旧背篓还在。因此,我建议文化部门把这两件东西作为文物收藏起来,便于将来向后人解读澜沧江畔这一片背出来的家园。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在我所见过的人类创造的景观中,最美的风景就是澜沧江畔的梯田。
梯田灌水的季节,这些像月牙形镜面一样的田块,阡陌纵横、拾级而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在山岳河谷中的梯田与波光粼粼的澜沧江水遥相呼应,让人联想到台湾的日月潭。稻苗泛青的季节,这些梯田又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在毒辣辣的阳光下,让人做梦都想在它上面睡。秋天到了,稻田一片金黄。这个时候,那金黄的不仅是稻田,还有夕阳映照下的澜沧江。此时此刻,有一种想画一幅画的冲动。
从普通人审美的角度上看,干旱和冬闲的季节,梯田并不美。在阳光的暴晒下,澜沧江边的土质是灰黑灰黑的,那些陡峭的山包也像灰黑灰黑的水牛,而山包上的梯田就像一排排牛肋骨。此时的梯田景观像褪了色的黑白照片。不过,正是这并不美的景观,才真实地反映出梯田特有的风骨。梯田本来就不是用来取悦眼目的,其真正意义是农耕社会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这一时代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所谓的家园应当是有家有园才算家园。只有房子,没有田地的乡村只能算空村。现在有的乡村已经开始不种田了,多少梯田已经荒芜。这样的乡村还算得上是乡村吗?人类建设美丽家园,应当呵护梯田,对梯田怀着崇高的敬仰。
中国是农业大国,梯田比比皆是。但滇西高原澜沧江西岸的梯田与别处的梯田不同。这里的梯田因地势原因,田块小,田坎高,造型千姿百态。梯田的轮廓有的像月亮,有的像树叶,有的像鸟,有的像鱼,有的像牛马,有的像骆驼。像一面圆镜一样的梯田往往在山包包的顶上,一个山顶就只有这么一块梯田。这种镶嵌在山顶上的圆形梯田我曾在一篇文章上将其称为“蓝天的镜子,大地的眼睛”。
澜沧江边的梯田准确地讲不是挖出来的,而是“背”出来的。澜沧江的水再怎么波澜壮阔,对于梯田来讲根本用不上。因为不可能安上几千米的水管,用抽水机把处于峡谷深处的江水抽到坡头的山包上。这样,梯田就只能是沿着一些河谷开凿并且要位于河的中下游,水往低处流,才能够流进田里。而澜沧江边的这些地带往往只有石头没有土,即便有土也是砂石土。这一来,就逼得江边人一代接一代地背土造田了。
造梯田的时候自然先得在坚硬的砂石土上挖出田坵来。这样的砂土庄稼无法生根,即便生根了也不会长出粮食来。因此,所有的梯田都得填上一层厚厚的熟土。这些熟土要在远离梯田的密林深处去背,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适合种庄稼的熟土。当然,除了填土还要施农家肥,否则这块田长出的稻苗就只和铁丝一样细,长出的稻穗也只和狗尾草一样轻。施肥还要讲究,肥料要经过堆渥发酵,不然,田里长出的草就会比稻苗还多。
挖好田坵以后,还得背来石头在田块的四周围起来,形成一道类似屏障的田埂。这样围出来的田才能既保水土,又保肥力。否则,夏季的一场暴雨会毫无悬念地把田冲毁。“大水冲田,饥饿三年”,这是江边山人早就有过的无数次教训。
包产到户那年,我家6口人只分得3亩水田,种出的粮食是不够吃的。为解决吃饭问题,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开田。
开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也相对作分工:父亲负责挖田坵,母亲负责去背土来回填。
因为土质坚硬,挖田的工具也要锋利而刚硬。除了用锄头,还要用铁锤、錾子和羊角凿。父亲抡着铁锤砸石头,大汗淋漓。一锤下去,地里的石头冒出火花,父亲也两眼冒金星。
天刚亮,母亲就挎上背篓上山去背土了。从有熟土的地方到父亲开田处至少有五六公里,除去空身返回的时间,母亲一天最多也只能背两趟。一坵田究竟需要回填多少土,我无法计算,但把一坵田填满,母亲至少要背3天的土。这样造出来的梯田与其说是挖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背出来的。
也许是民族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吧,我们老家的人都把给田背土、给田背肥这样的农活说成是“背田”。老家人有一句俗话:“背出来的田,长出来的稻,舂出来的米,磨出来的面。”这句话连贯起来的意思是形容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去做。对待造田这样的活计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还有一句俗语是:“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意思是种庄稼要用心,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会挨饿。
在江边山地毒辣辣的太阳下,父亲挥汗如雨地挖田,母亲步履蹒跚地背土。三年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将近开垦出了5亩梯田。这5亩梯田因为是在包产到户后开挖的,所以没有进入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本。父亲经常开玩笑说:“这些田进不进合同本没关系,种出来的粮食进全家人的肚子就行了。”事实上,父亲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后来政府落实的粮食补贴及其他一些与土地有关的惠农政策中,这没有“身份”的5亩水田都无法落实。
其实,背土造田在我们村历史已经很悠久。据父亲讲,爷爷那一代,甚至更早的年代,许多水田都是这样造出来的。我们村合同本上许多田块的名字不是以田块所坐落的那座山来命名,而是以人来命名。不用讲都知道,以人命名的田块,那个名字就是那块田的最初开垦者。
大集体的时候,我们村出了一位造田模范。这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从50岁的时候开始,用10年的时间为集体造出50多亩水田。有一次,公社开劳模表彰大会,奖给他一把闪闪发光的新锄头。这位老人回家后把拴着红绸的锄头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激励人们艰苦奋斗,大造梯田。这家人在包产到户后,率先成为我们村走上富裕之路的人家。
为解决梯田的灌溉用水,七十年代初期,政府组织澜沧江沿岸的群众大干水利建设。在全公社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村利用近8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小型水库。建水库的那几年是我们村历史上劳动场面最壮观的时期。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运土时,用推车运送土方的人如鱼穿梭;压坝时,几十个男人一组拉着上吨重的石磙步履矫健如燕;每到上工高峰期,敲石声、吆喝声、驴叫声和高音喇叭声响彻山谷。
水库建成后,我们村的那些梯田像一面面镜子在澜沧江西岸的河谷中熠熠生辉。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片怪石林立,连茅草都无法生根的江边砂石土竟会像铺上了地毯似的茵绿起来。
在江边山建水库、造梯田是辛苦的。人们一天到晚汗水淋漓地劳动,每顿却只能吃到2两米饭,3两苞谷,菜汤上没有一滴油腥。可就是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们的精神却出奇的高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标语写在墙上,挂在嘴上,也确实落实到行动中。
特殊年代有特殊的情感,特殊的环境有特殊的歌声。上工和收工的路上总会听到《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曲。回想当年,“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这几句歌词还在我耳边萦绕。
现在想来,青山、白云、梯田、歌声,这多美的形容词呀,这些词语用来形容昔日山坡陡峭、怪石丛生、烈日炎炎、大地昏黄的澜沧江西岸的故乡是多么的不合适宜。也许,正是这些不合适宜的词语流过不适宜的乡土,澜沧江西岸才造就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包产到户近40年,我们村一共开垦出这样的梯田上千亩。村里的水田由原来的3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亩。还在20年前,这个靠山茅野菜填饱肚皮的村子就已经不再吃杂粮。全村的人家家户户吃的都是稻米饭,种出的苞谷只是用来喂猪和酿酒。这得归功于这些背出来的梯田。
插秧的季节,澜沧江畔的梯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插秧的女人们以“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队形在梯田上排开。这个季节,层层梯田是书写在江边大地上最美的诗行。
站在城市的高处,眺望远方的故乡,我要向澜沧江畔千回百转的梯田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