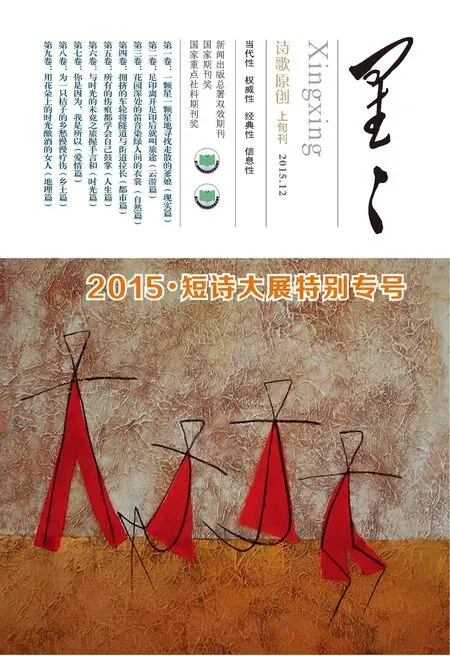每一次行走都可能踩到灵魂的痛
蒋登科
每一次行走都可能踩到灵魂的痛
蒋登科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山水诗一直比较发达,不少诗人寄情山水,抒性灵,写情怀,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佳作。这种传统的形成除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深度体验之外,更主要的恐怕和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以道家哲学思想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诗人们往往借助山水、自然抒写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感悟与体认,开阔、达观、超然,似乎在说事,其实是在写人,特点非常鲜明。
随着物质条件和交通方式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行路”的意义,很多诗人也在“行路”中发现了独到的诗意。诗人因为行旅而产生的诗篇,由于是在新的环境、氛围中获得的体验,往往会因为新的发现而对过去的人生产生反思,或者对人生产生新的向往与思考。欣梓在《在塔尔寺》中说:“我心虔诚/我心虔诚不为别的/只为尊重和崇敬/只为佛能够赐我一颗装得下/蓝天、草地和万物的悲悯之心”,诗人祈望的“悲悯之心”其实就是对一种人生境界的思考。陆子在《沙漠里的孤树》中写道:“命运只给一种选择/必须把根扎得更深/当荒漠变成桑田绿洲/你就是树中的神”,语言并不深奥,但诗人从中获得了关于坚守、境界甚至生命重量的感悟。毕福堂是一位资深诗人,他的作品常常从普通的对象中发现不普通的情思,《速度》是对快节奏甚至浮躁人生的一种反思,当人们借助现代交通工具“狂奔而去”的时候,“她们,一步三叩首/把道路折叠起来/把速度折叠起来/把迢迢几千公里的/餐风露宿折叠起来//把匍匐当行进的她们,相信/身子低下去再低下去/就低进了缓缓上升的祥云”,“低”是一种虔诚,一种姿态,在诗人看来,只有这种对“低”的践行,才能摆脱过分的功利,才能有灵魂的净化与飞翔。诗人使用的“折叠”一词很有意味,既是动作,也是情怀,更包含着梦想,还可以理解为内在的精神力量的积蓄。小语在《国台,暖烫我的文字》中发现:“转山转水之间/男人通红的脸趴在重阳节的高粱上/像魂从远方归来”;离离《在郎木寺》获得了一种净化:“离开之前,我多看了几眼/酥油灯 和藏区的孩子/内心里果然清净极了,甚至有点怀疑/之前进去的我们/都出来了吗”,有这种“怀疑”就对了,因为诗人获得了新的体验和发现,生命的境界也因此提升;文芳聪的《马锅头》说“走出去就是归宿”,这看似矛盾的表述中,蕴含着诗人对于行走的理解,对于执着的思考,为此才发现了“摇摇晃晃的一生”的意味;谷雨的《微雨洗过高原》中,“边地景象”也是诗人提升和净化自己的一种选择:“冰雪堆垒成的世界,呼喊埋于雪下。/一年一年,左手故乡,右手异乡。/开满向日葵的田埂吊挂在钥匙扣上,/一把异乡的锁,打开被撕裂的人生。”对于作者,这些诗句都是新鲜的,他们在行走中获得了在书本上难以获得的体验,或者调整了过去的某些感受,或者在过去的人生体验中增加了新的元素,甚至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一种豁然洞开的明亮,从而在他们的人生与诗歌中增加了新的意味。对于读者,他们即使没有去过诗人抒写的这些地方,但他们同样可以从中体悟到物质文化之外的心灵文化,以精神的方式伴随着诗人的诗意发现而行走甚至飞翔、升华。
诗歌不用心、不入心,肯定不是好的诗。诗歌可以及物,那样可以避免作品的空洞化与理念化,但诗歌创作最忌讳的是见物写物,见景写景,见人写人,否则就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行走应该是一种用心的旅途,应该拒绝表面的新奇,努力去发现诗意甚至生命的新,这样才能做到“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诗人的行走不是追随热闹,有时甚至没有目的,还可能是一种孤独的逃离,但他们却在行走中突然获得了新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灵魂得到一种纯净的洗礼,生命的境界为之而提升。吴春山对《旅途》的体验,应该说是属于诗人的那种行走:“车站空旷。你走向另一个出口/没有人留意长夜的长/没有人告诉你,足印离开足印后,叫旅途/黑暗中,花朵偷偷练习呼吸/而时间仓促,时间无意种下/一枚金属的种子”,对于诗人来说,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行走,就有较高的几率获得诗的发现。当然,我们不祈求每次行走都能够带给我们巨大的收获,恰如诗人所说的:“……蝉鸣/就那么挂在枝头/人们一次次试图靠近它/却一次次/离它越来越远”。写诗也是如此,带着目的的创作往往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我们“必须学会等待”,等待积累的爆发,等待全心的投入,等待诗情突然被激发的瞬间。
诗的写法多种多样,诗的境界有高有低,诗的情怀有大有小,这和诗人的积累、视野、修养有关。但无论怎样,对于新的发现、新的表现的追求,始终应该是诗人在艺术探索上的取向和目标。诗不拒绝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但诗最终是向内的,诗人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行走,都应该触碰到灵魂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