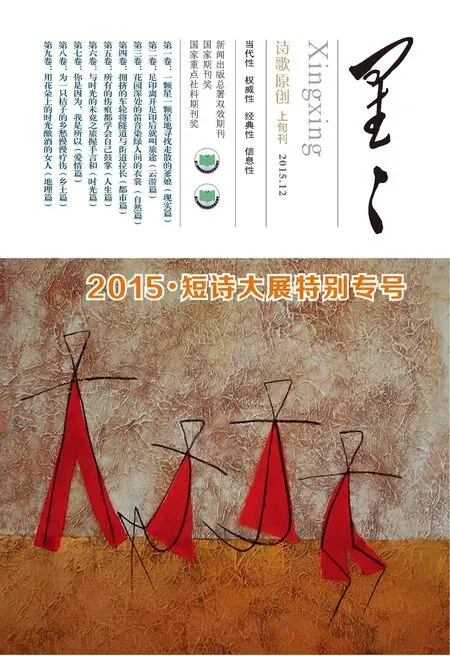走不出故土的灵魂——评《为一只桔子的乡愁慢慢疗伤》
胡 畔
走不出故土的灵魂——评《为一只桔子的乡愁慢慢疗伤》
胡畔
当乡愁没有寄托的时候,人的灵魂是漂泊不定的。古往今来,人类最普遍意义上的乡愁情感一直都是文学艺术领域亘古不变的话题,而诗歌这种以抒情见长的文体便成为了人们倾诉思乡之情的重要表达形式。诗为美的化身,诗人将浓浓的乡愁融入诗语形成艺术化的乡思,即使随时空变幻,也如陈年老酿,余味悠长,无时不刻萦绕在诗人与读者的心间,即便历经时间的沉淀,那些思乡的心,漂泊的灵魂总能在精神家园里得以皈依。
乡土篇《为一只桔子的乡愁慢慢疗伤》这卷诗歌充满了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亲人的真切眷念,不同的诗作或直接,或委婉,或悲绝沉郁,或细腻悠长,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无限深沉的爱与切入肺腑的思乡之苦。在诗人程良胜的心中“故乡是一张网/年少时我拼命挣脱/中年时我编织梦想/年老了我渴望还乡//尽管我走遍四方/走得出叮咛,走不出张望/走入的是江湖/ 走不出的是故土//当生命之火燃尽/当心已疲惫忧伤/我终要回到故乡/或是长眠/或为疗伤”(程良胜《故乡》)。纵使离开故乡到了城市,但对于孕育生命的泥土和浓浓的亲情都成了诗人心中难解的情结。
诗人一寒的《方言》通过讲述多年来故乡方言对自己的深厚影响,实则表达的是对故土那份不可割舍的情感,他感叹“方言,已经成了我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一个象征//在方言里活了几十年/我想,某一天即使我倒下了/倒下,不能再起来时/我最后发出的,依旧是一声/地地道道的,方言/这纯正的母语”。(《方言》)。母语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谓一生之久,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牙牙学语都沾满了方言的味道,即便长大后背井离乡,接受了种种语言的洗涤,却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方言里。
童年乡村的贫穷苦涩常常让诗人难忘,“土碗盛着我沉重的童年/那缺口的粗瓷容器/是我残落乳牙的嘴//记忆的那岸/和土碗相依为命的一双筷子/一根是娘/一根是爹/再见到土碗/在都市豪华的餐厅里/盛满故乡的风雨”(张春生《土碗》)。但在诗人的眼中,故乡永远都是那个最初最美的地方,诗人试图用笔勾勒描摹乡村过去现在的面貌,寻找那些不曾遗失的情感和阐释着真正意义上的乡愁。正如赵长在的《和女儿说起秋天》写道: “说起我童年的秋天/说起雁阵、麦苗、竹筐、柴火/说起镰刀、锄头,以及挖到的红薯和胡萝卜/说到烤玉米、烧花生,一直说到现在/生活的香甜/女儿诧异的表情,像一簇底边的野菊花/仿佛在说,除了美/原来乡村的秋天,可以这样度过”。
难忘的是那些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时光,割舍不去的亲情给了诗人无限的温暖、慰藉与希望。张家龙在《梦里老家》里写到:“怎么努力也走不出你粗犷的视野/再任性也没逃出你沾满泥土的呵护/踩着父亲用脚丫铺成的小路/孤独地捡拾记忆遗落的那些碎片”。
由时间沉淀下的浓浓乡思,绝非用一物可比,一语能言。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世界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乡愁总是人类对于已经失去的时代的怀恋和向往;是对于那些“逝去年代”的一种记忆和情感的维系;是人们精神世界里不可丢失的梦想。乡愁还可让我们从潜意识里从容应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烦恼,纵然变迁了时空,乡愁依存,故土依旧难离。如赵长在《受伤的桔子》中那株离开南方来到北方生长的桔子,怀念向阳山坡和江南烟雨,但终将沐浴北方的春光,为小小的乡愁慢慢疗伤。
整体来看,该卷诗歌从普遍意义上表达了现代人对故土强烈的眷恋之情,诗人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以简洁的语言和单纯的意象结合,自然流露,纯净真实,撼人心魄。诗人纵使早已背井离乡,漂泊在外,却始终走不出心中那片供精神皈依灵魂安放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