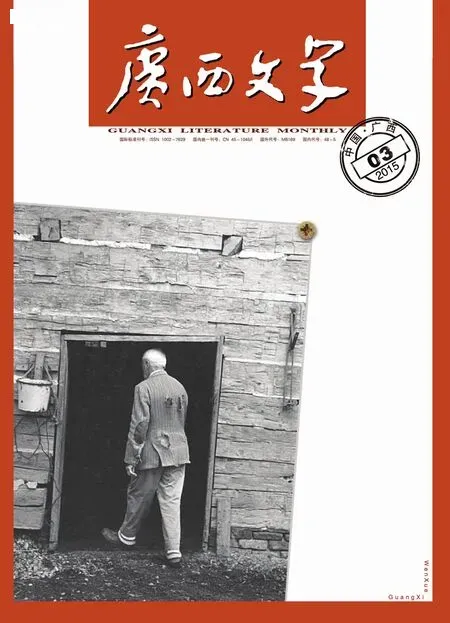廊前有棵苦楝树

本文选自《环江文艺》2014年第2期
我家北边走廊外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
当时选择购买这处房子,不仅仅是因为有棵苦楝树,还因为这里有一片宽阔的草坪,有一座原始的小山。
时隔两年之后,草坪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幢高楼,留下的只有我对草坪的无尽怀念。
一年四季,草坪都长草,春夏季青翠欲滴,像个青春年少的脸庞,随时可以掐出汁液琼浆;秋冬时节虽然有点枯黄,但并没有枯死,黄色的根部绿意深藏,依然潜藏着无限生机,这个时候的午后常常有三三两两的人过来坐坐,晒太阳,各种色彩的衣服点缀着草坪,颇似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他们在窃窃私语,我坐在走廊里是听不到的,但我能感觉得到此时的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沉浸在深深的感情蜜糖里,不能自拔。等到人走之后,几张被坐皱的报纸在冷风中微微飘动,像在祝福,也似是诉苦。
最热闹的是春夏时节,并不十分平坦的草坪,有些小坑洼,雨后往往积水,这些小坑洼就是青蛙们的天堂了。早上,咿咿呀呀的,叫得欢,很像是一群小学生在进行热烈的早读。听听,它们几乎是同时开始叫一阵,又几乎同时停下来,然后还有几个零零星星的在不紧不慢地叫一两声,像几个捣蛋的学生。几只大青蛙的叫声从容不迫,浑厚温和之中有一股威严,倒有点像是指导早读的教师,这真真是一节有序的早读课。下午,却静悄悄,不知道它们干什么去了,估计是休息或是觅食去了吧。而夜里,蛙声喧嚣得有点夸张:几乎是人声鼎沸的自由市场,讨价还价,争吵声、呵斥声、埋怨声、叹息声、摩托车喇叭声夹杂其间,处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蟋蟀也不示弱,叽叽叫唤,似在唱歌,又似在呼朋引类,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虫子也在清唱,有似扯破嗓子的架势。这样的蛙声、蟋蟀声嘈嘈杂杂,喧闹沸腾,但并不令人心烦。夜晚枕着这样的声音睡觉,很是安稳。
还有一个怪叫声久不久在秋冬的深夜响起,凄厉、怪诞、撕心裂肺,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滚动的声音,是从草坪的东边滑向西边,然后在深阔的夜幕中渐渐消失。这怪叫声小时候在乡间的夜晚听到过,村上的老人说是冤死鬼的号叫,也没有依据能肯定或否定。
草坪南边有一条鹅卵石小道,东西向,每天都有各色的人来来往往:有人行色匆匆,像在赶赴一个紧急的约会;也有人慢条斯理地走着,不慌不忙的,悠游自在;傍晚散步的人,更加悠闲,走走停停,看花花草草,或一两人相互依偎地边走边私语。抄近路要往西北角方向走的人,踏过草坪,自然形成一条泥路,泥路和鹅卵石路,这样的两条路刚好将草坪斜切成一个“人”字,头在东南边,两只脚一西南一西北。去年开始,这里就变成了轰隆隆的工地,昼夜不停,今年,三幢楼就拔地而起,草坪从此消失了,“人”字荡然无存。
靠近我家的北边,有一座小山,是这一带仅有的两座小山之一,另一座在距此两百米的东边。山上杂草丛生,有几株自然生长的小叶榕,因为泥土贫瘠,长得十分艰难,数年以来,一直就这么大,如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侏儒,但其枝叶还是很葱茏的。勤奋的楼下退休人员,上山去割开杂草,捧上泥土种了夜来香、三角梅等花草,有时也开了些稀稀拉拉的花,也算是对老人劳动的回报和感恩。山体的南麓,长了不少的蕨类植物,不张扬、不吵闹,静悄悄地生长着,文静若处子,四季绿意可人。
苦楝树就站在小山的西头。
冥冥之中,苦楝树总是跟我有缘。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住在洛阳镇,门前就是铁路,铁路两旁种的都是苦楝树,一排排的,一眼望过去,宛如列队的士兵,整齐、昂首挺胸。又像夹道欢迎军队凯旋的人群,手中舞动着彩旗,洋溢着欢乐的气息。那时候,每天放学了,沿着铁路去菜地给菜浇水。路上捡起苦楝树黄亮亮的籽,塞在裤子衣服的口袋里,鼓囊囊的,作为弹弓的子弹,常常把邻家的鸡打得一度昏迷在地,或是把路灯打得咣啷粉碎,然后撒腿就跑得无影无踪。有时候,也把苦楝树的籽摆满铁轨,让路过的火车碾压成饼或粉碎,不免被路过的巡道员追得鞋子横飞、两腿是泥、脸色铁青、满头大汗,最终还是逃脱了严厉的惩罚。这是苦楝树伴我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驯乐中学,当时住在瓦房里,门前就有一棵硕大的苦楝树。课余时间,我拿着一张大椅子当桌子用,再以一张小椅子坐着,在苦楝树的浓荫下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候也抄写文学作品。苦楝树的叶子,随风轻轻落下,落在我批改的作业上,落在一片诗意盎然的文字间,鲜黄的叶子,叶脉纵横交错,像天地间的山河流水,叶子边有锯子般的齿,柔软,不锋利。也有叶子擦落在我的耳朵边,有点微微的辣痛。这个时候,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这棵高高的树,摆动酸痛的颈脖,耸耸肩膀,略作休息,调整紧张的工作。从内心里感激苦楝树,感谢生活。月夜,苦楝树枝的影子印在墙上、印在窗玻璃上,风一吹影子也摇曳生姿,像有人在窗外监督我是否在用功。我的一个蒙姓同事,在这棵苦楝树边收获了他幸福的爱情。那时,他在追求学校里的美女同事,每天都过来女同事门口聊天,有时是酒后壮胆过来滔滔不绝地演讲、表白,女同事只是咯咯地笑,不置可否。历经数月艰苦卓绝的演讲,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咯咯乱颤的女同事终于将爱情橄榄枝抛将过来,成为女朋友,后来自然就成为他的妻子,爱情开花结果,终将圆满。苦楝树见证了这场爱情。
当时,全国正刮“下海”风,我和几个同事经常在苦楝树下讨论关于“下海”的梦想,设想绘就许许多多美好的蓝图,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棵苦楝树,在世纪末的学校建设中被砍伐了,听说轰然倒地的时候溅起的尘灰久久不散。那是我已经离开驯乐中学许多年之后的事了,详情不知道,听说后内心的某个地方隐隐作痛。
廊前的苦楝树,树干直径有三十公分许,高至五层楼。经过几年的细心观察,发现这棵树对季节的感应很迟钝:春季和冬季一样,光秃秃的,有几棵稀稀拉拉黄颜色的籽在空中晃荡,毫无生机,致使我老担心它已经死去,可到了五月份开始慢慢抽芽了,继而绿叶葱葱,六七月份开了粉白粉白的花,簇簇丛丛,在风中摇曳,还有些许的香气。而到了秋季树叶却依然绿幽幽的,没有其他树的那种枯黄的迹象。深冬时节树叶变黄,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全部落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不管别的花草树木在春天如何争奇斗艳,如何吵吵闹闹,然后又在秋季如何地相继凋零,它一直保持着它自己慢悠悠的速度,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保持着与世无争的态度稳步前进。年年如此。
廊前有了这棵苦楝树,就招来很多的客人。偶尔到树下乘凉的老人或在树下玩耍的小孩是不算在内的。这些客人就是欢欣雀跃的鸟类,也因此,我有幸每天在鸟声中醒来,在走廊前发一阵呆,听鸟声,观察鸟的活动,看树枝在晨风中长袖善舞。临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我却不识鸟。来这树上的鸟大致有以下几种:麻雀较多,一般飞来的都有三五只,叽叽喳喳的,在枝叶间上上下下地穿越,相互追逐,一直没有消停,有点像多动症的小孩。我家乡俗称的一种鸟叫墙脚鸟,身上羽毛黑白相间,离开树向空中飞的动作一腾一落,又一腾一落,飞行曲线颇似股票涨落图,在树上,喜欢沿着横斜的树枝步行,有时是低头走路,有时昂首走。台湾隐者陈冠学在一篇题为《树兰》的文章里说:“可以断定是台湾鸟书未曾记录的新鸟,我叫它地行鸟。它在树兰下啄食一圈之后,跳上树枝,居然在树枝上步行,原担心它是只病鸟,飞不起来,没想到它本性动作慢。”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类鸟?有一只鸟,每次都是单独行动,上身咖啡色,下身米黄色,两色之间交会处接合得天衣无缝,肉眼无法确定它们的界限,这只鸟叫声很小,叽哩几声,在树枝上停留时间较长(我用长焦镜头拍下它的几张照片),兀自梳理羽毛,左顾右盼一阵之后飞走了。夏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有只鸟,在树叶间发出浑厚的叫声,像民族唱法,但是从来看不到它的身影,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这是一个害羞的歌者,只在录音棚唱歌,从不登台亮相。还有一种鸟我们叫它臭嘴婆,这只鸟也偶尔在苦楝树上出现,但不多。农村人早上出门做事,喜欢图个吉利,偏偏这个臭嘴婆在前面叫开了,声音急促、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讽,令人心烦,往往今天的事八成是办不顺利了,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碰着臭嘴婆叫,就立即朝它吐口水,呸呸的,把晦气还给它,是不是奏效,没有实践过,不得而知。如今在走廊听到臭嘴婆的叫声,我倒是觉得很亲切,令我一下子回想起乡下老家的许多旧事和故友,所以从不朝它呸呸。
到了冬季,其他鸟都遁迹了,只有麻雀还是零零星星地来,在午后的暖阳里,飞飞落落,嘴里家长里短地议论,遇着有小汽车经过、鸣笛,扑棱棱地飞远。
冗长蝉鸣声也是来自苦楝树上,但我从来没见过蝉。刚刚搬到这里住的那年夏天,我记录了关于蝉鸣的文字:蝉到底有多少种类,我没有研究,自然不知道。在我窗外的这蝉,估计不是书上说的知了,它的叫声不是“知了知了”,而是“西——下——,西——下——”,像是提醒人们:已经是午后,太阳就要西下了;或是在咏唱“西夏西夏”那个遥远的朝代?这声音有点单调,但并不乏味,动听悦耳,百听不厌。正如一些凄婉的爱情歌曲,尽管凄凄惨惨戚戚,但很美,美得令人心痛。傍晚的时候是另一种蝉鸣声:来来来——来来来——,声音由强变弱,然后渐渐消失,像一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茫茫天空下。十多年前,我住在城东教科所办公楼三楼上。那时候穷困潦倒,双休日基本不出门,整天吃着双狮面拌辣椒西红柿。光着上身躲在房间里听收音机、看书、临帖,实在热得难耐,就到楼道尽头,用满满几桶水从头上泼洒下来,体验在瀑布下被水灌顶的感觉——凉爽、痛快淋漓。写章草,是从那时候开始,章草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着痛快。教科所有个小院,院里有棵龙眼树,正对着办公楼前,枝叶繁茂,树冠高过三层楼。在浓密的枝叶间,藏着数只蝉,夏日的时候,我就是在蝉们疲惫的歌声里体验瀑布的痛快淋漓,体验章草书法的沉着痛快,穿越书香阵阵。我曾在一篇小文《寂寞写章草》中做了较为详尽的记录。每次听到蝉鸣声,总不由得想起那个艰苦而快乐的青春岁月。
廊前的苦楝树,就像个老友,伴我几个春秋。除了听鸟音,休息时间,我常常到走廊朗读,树就是我的听众,读得更认真。午夜醒来,有时候站在走廊,看月光把树影印在白色的墙上,像一幅动感的水墨画,让人没有来由地欢喜。有时坐在廊前听雨,雨点与树叶摩擦的簌簌声,树叶在雨中的湿绿诱人,雨点溅起的细蒙蒙的雾气十分养眼,植物的气息直窜鼻尖。
这是这座小山和苦楝树给我带来略带点诗意的生活细节。